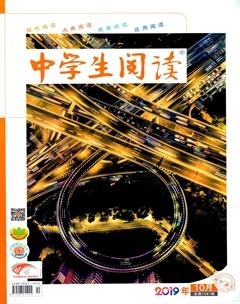我的汉语老师
丹增

我的家乡在西藏。一九五三年藏历新年初一,天还没有亮,从我家大门外传来“折嘎”(意为白发老人)的说唱声。藏历新年初一,“折嘎”会到大户人家门前,用洪亮的声音说着唱着一番动听的赞美话,带来吉祥的兆头。那年“折嘎”的唱词有许多新意:共和国诞生,解放西藏,汉藏团结……。西藏刚获得和平解放,希望的曙光闪现在“折嘎”的唱词里。
一九六〇年,家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个人碰上了千载难逢的机遇。那一年我十三岁。脱掉绛色的僧服,走出古老的寺门;穿上整洁的校服,走进现代的校门。我从县城出发,骑马、坐车、乘火车,历时三个半月才到达目的地——陕西咸阳的西藏公学。
千亩校园,青砖筑成的围墙,高大的校门上方,白底红字用藏汉两种文字书写着校名“西藏公学”。我们在敲锣打鼓、欢声笑语中走进校门,沿着一条宽敞的水泥路寻找宿舍。繁密的树林中掩映着一排排整齐的平房,青砖墙,灰瓦顶,门前是黄泥铺的走道。每一间宿舍十来平方米,摆着四张上下双层床,可以住八名学生。五层高的教学楼,显得威武高大,屋顶是灰色大瓦。房脊上有透窟窿的瓦做装饰,还涂上彩绘,迎着太阳看去,充满着希望。房脊的两端各塑有一只鸽子,既是和平的象征,也有我们这些学生就像小鸽子一样,从遥远的西藏飞到咸阳美丽的校园的寓意。上课第一天,在明亮的教室里,懂汉语的藏族班主任介绍汉语老师和数学老师。我数学很好,但是一句汉语都不会说,一个汉字都不认识。我全神贯注地看着那位汉语老师。
他叫陈钦甫。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仪表堂堂,体格匀称,面孔俊秀,散发着青春的活力。他穿的黄色衣裤明显旧了,但非常干净整洁。每一个纽扣都扣得认认真真。更让我惊讶的是第一次开口,他用流利的藏语说:“你们一路辛苦了,这学校你们喜欢吗?”这下不仅拉近了师生距离,贴近了民族情感,而且让我产生了对老师的敬畏之心:人家是藏汉双语兼通的老师。正式开课后,陈老师教的第一句汉语是“老师,你好”。后来我才深刻体会到:一位好老师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一句“老师,你好”值得终生铭记。
咸阳这座安静的城市中,猛然来了一大群藏族学生。三千多名学生,不论出身,学校一视同仁,都是学生。有人说,我们这个学校“四不像”:不像小学,不像中学,学生大的四十多岁,最小的只有十来岁,我当年十三岁,是极小的;也不像干校,尽管学生中有县长、乡长,但学的还是文化知识;更不像大学,尽管教师中有教授、讲师。但课程是汉语拼音这一类的小学内容。
我人校之后立下的第一个人生目标是:学好汉语,走遍全国。这个目标也是去年才实现的。我学习汉语特别用心。汉语老师用藏语讲解汉语拼音和字词,声调高扬、语音铿锵,区分着两种语言的发音方式。教汉语,没有课本,只有提纲,老师一边查看学生做的记录,一邊整理自己的教学笔记,然后整理成文,油印发给学生。我们在五年多的时间里读完了初中以下的汉语课程。学生不仅可以流利地用汉语对话。而且能认识三千多个汉字,能读报看书。老师特别关注我的作文,让我担任写作的课代表。老师把学生的作文簿批改完后,总在课堂上亲手发给每一名学生,先发的是写得不好的,最后发的是最好的,还占用一些时间宣读和讲评好的、差的作文。
课堂前面墙上是黑板,只有老师拿粉笔书写。后面墙上是报栏,我的作文常常贴在报栏最前面。我为了写好作文,课余大量阅读文学作品。还想读四大名著。图书馆的老师说:“你才学了五年汉语,有点……”这些书当时被视为“闲书”。我于是跑到咸阳街头一个旧书出租屋花钱去租书。有空就读,还常常在宿舍熄灯后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读。有一天学校出了一个作文题目“美丽的校园”,我心血来潮,写了一首赞美学校的长诗。我交完作业后心里忐忑不安,总觉得作文既离题又离谱,不知老师怎么想。没想到发作文的时候。还是“压轴”,我才吃了定心丸。但这次老师没有念给我的批语,我翻开作文簿一看,红笔写的“诗写得很好,但注意不能好高骛远”映人眼帘。对前一句话我有点沾沾自喜。后一句不就是批评我还不会走就想跑吗?
有一年学校组织全校汉语普通话比赛,在三千名学生中我得了第三名,原因是朗诵中卷舌音发音不标准,老师有些失望。不久又进行全校汉语作文大赛,我获得第二名。老师拉着我的手走进学校门市部,掏出一斤粮票,买了一斤糕点,把一半分给我吃。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那算是最大的奖励。老师的一举一动鼓起了我的写作激情。使之就像鼓满船帆的风,激励着我不断远航。
十多年前,我专程前去咸阳看望我的老师们。将我出版的散文集和专著送给他们。老师们的恩惠我藏在心底,师恩是报答不尽的,只能作为内心的纪念。我最高兴的是老师们虽年事已高,但风度如故,威严如故。
去年,我去咸阳看望我的汉语老师陈钦甫。他已经八十多岁了。他见证西藏和平解放,用心培养藏族学生。他对我的无私付出改变了我的命运,就像新中国无数的教育工作者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那样。
(选自《人民日报》2019年5月27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