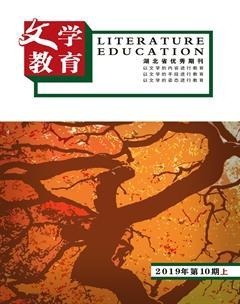“夷夏之辨”还是“卫道护统”:以两篇檄文的争夺为例
内容摘要:作为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两篇历史文献,《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与《讨粤匪檄》分别抒发了太平军文人与指挥湘军与之对抗的曾国藩的各自立场,具有深厚的文化价值。通过战争动员文本的分析,体察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与以曾国藩为中心的晚清士绅支持的地方团练冲突双方的话语权的争斗,体会其中对传统合法性资源的筛选、运用、扬弃、发展、传承,归纳其相同以及不同特点,总结其成败得失,发掘其中的儒学传统内涵,从而窥测晚清统治的合法性特点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关键抉择。
关键词:夷夏之辨 卫道护统 檄文 奉天讨胡檄 讨粤匪檄
冲突乃至战争是考察政治权力的重要场所。从文化主义的维度看,政治立场取决于个体记忆、民间记忆和政治记忆,因此要界定争夺合法性的各种主体有怎样的立场存在,可以将他们放在不同的合法性阵营之中,双方用质疑、辩护、灌输、对抗以及颠覆等方式将其主张刻写在政治记忆之中,并加以扩展传播。[1]87“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檄文正是一种能反映立场、动员社会、汇聚义愤从而达到师出有名的宣战目的的文书。《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①是1852年夏太平天国军队北进途中以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联名发布的旨在反清斗争的最经典的文告之一。而1854年春曾国藩在练成湘军开拔衡阳战场之际以示维护满清、保卫名教、镇压“叛乱”的文告《讨粤匪檄》则体现了曾国藩其人的学识与品格与士大夫阶层的整体政治态度与思想风貌。双方在特定的历史时空形成了呼应,不仅在内容上具有极高的文学、艺术价值与感召力,而且双方势均力敌,都具有很强的动员力、战斗力,因此堪称中国历史上成对檄文的巅峰之作。交锋双方都不是皇家军队或国家正规军,背后还立着一个象征当时国家正统的开始逐渐衰落的满清朝廷,显得十分微妙。此外作文的时间处于鸦片战争之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是我国走向现代化的初始抉择期,更是现代史意识形态建构的各派争夺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当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史观给予了太平天国极高的革命正当性价值,比如人民英雄纪念碑刻写了的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浮雕,从官方肯定了太平天国英雄人物对现代历史的积极作用。而新儒家则无比推崇曾国藩,陆魁宏(2015)、曾琦云(2011)称其为“新儒家起点”“新儒学的开创者,也就是‘一代儒宗”。[2][3]姚中秋(2013)也认为“曾国藩唤醒了儒家士君子的道德自觉,打开了晚清制度转型之文化与政治通道,实为中国现代史之开端”[4]425。特别是近十多年来在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的大背景下形成的“曾国藩热”,一批通俗历史作家捧红了曾国藩,认为他是中国最后一个传统文化集大成者。因此综上所述,这一对檄文与这场战争成为中国现代史的转折点,对于国家走向、社会风貌、文化形态具有极高的战略意义。时下一些思想界的争议恰恰反映了当时双方的立场争斗、文化辩论、道路选择之分歧的重要价值张力与对当代中国政治与文化的持久影响。
目前学界专门对两份檄文的单篇研究、比较研究都不多,之前的学者侧重于对文本的直接考察,得出作者的不同思想立场和斗争策略。如成晓军、彭小舟(2001)把《讨粤匪檄》视作理学经世派的文化宣言,认为曾国藩一派的宣战与胜利揭开中国近代化序幕,檄文充当了思想武器,其精神内涵与中体西用相接续,促进了同治中兴。[5]董丛林(2016)對比了“杨萧三谕”与《讨粤匪檄》,认为太平天国的失败实则是在檄文立场上略低一筹,过于立洋教,激发了社会仇恨而给曾国藩的斥责洋教护卫道统争取民心留下机会。[6]李志茗(2012)同样认为太平天国侧重于宣传西教色彩的天父天兄来建构神圣性与合法性,然而这既不能争取到民众也不能让自身贯彻这种平等主义,而曾国藩的夷夏之辨策略比太平天国的主张更有说服力。[7]笔者认为若能结合前后的时代背景与思想渊源流变,把这两篇檄文的立场融合起来而不仅是分离开来,或许能得到更多新的阐释。
一.两份檄文的内涵差异与叙事策略
南朝刘勰认为,檄文起源于西周,但以春秋为根。在《文心雕龙·檄移第二十》则记载,“昔有虞始戒于国,夏后初誓于军,殷誓军门之外,周将交刃而誓之。故知帝世戒兵,三王誓师,宣训我众,未及敌人也。至周牧西征,祭公谋父称古有威让之令,令有文告之辞,即檄之本源也”。而《文心雕龙·宗经第三》中记载着“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8]而《春秋》首句“元年春王正月”,本质上交代了政治权威(君权)的合法性之源头——天道。可见,檄文的诞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重要时刻,它不仅是军队内部动员的文书,更是为合法性的建构与争夺而作,是权力的再生产。《孙子兵法》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争是国家建立的途径,檄文又是战争的宣言,因此檄文必须不仅要阐明战争的起因和发兵的正义性,更要与国家政权的道统相联系,从而论证军事行动的合法性、合天道性,以便师出有名,赢得战役,为日后的斗争或抵抗争取更多支持。檄文联同其自身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发布檄文的政治仪式一道维护合法性中的神圣性、权威性与有效性,具有很强的政治记忆刻写功能,从而影响当时的社会动员、公共舆论与军民生活。
太平天国笼络的文化精英试图以华夷之辨为题,定下基调。开篇“嗟尔有众,明听予言。中国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9]108-110,矛头直指满洲贵族统治者,揭露其所谓破坏中华衣冠、礼教、人伦、制度、语音,欺压汉人,淫虐子民,为所欲为,贪腐盛行。将满洲贵族描述为“流毒”“妖气”,反观“中国之人,反低首下心,甘为臣仆”[10] 108-110。把中国在满清统治下的种种惨状进行虚构,在经济上压榨盘剥,在政治上打压,在文化上欺压,在人格上凌辱,以主人翁的姿态指责满清“霸占中国”、“盗窃华夏”、“愚弄国人”、“使中国之人为禽兽”“绝我中国英雄之谋”。此外还举出了姚弋仲与符融身为“胡种”,对华夏尚且有义,而满洲贵族“忘其根源”,还举出“昔文天祥、谢枋得誓死不事元,史可法、瞿式耜誓死不事清”[11]108-110的感人的事例来唤起支持。总的来说是一种常规的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天下观,意在对清廷的合法性提出严厉质问与激烈贬损,从而鼓动受政府政治压迫、民族压迫、经济压迫的失意者或是受灾害或地主压迫等的底层农民的民族情感,唤醒反抗意识。接着从神话建构的角度杜撰了满洲贵族统治者的祖宗的“白狐与赤狗交配”起源,但并未写明他们眼中的中华图腾而是指出中国复兴之路在于“蒙受皇上帝开大恩,洪秀全作为天王,有着天赋的正当性”,并赋予了“神州”这个词中“神”的意义——也就是上帝,指出世居于中国的人都是上帝子女,而这个上帝毫无疑问是带有基督教教义色彩的。通篇1500余字,上帝出现了10次,还提出“上帝纲常”等概念,用“顺逆有大体,华夷有定名。各宜顺天,脱鬼成人”[12]108-110来攻击“妖人反盗神州”的局面,用太平之乐反衬胡氛之苦,用“上帝子女”之荣光来反衬“蛮夷臣仆”之屈辱。
另一方面曾国藩的始终站在“卫道”的制高点指斥太平天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叛逆,并且归咎于西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将内乱上升到外患的层面,唤起天下读书人的义愤之情;并将矛头指向西方一神崇拜的宗教的危害性,以及太平天国激烈的文化“革命”(毁孔庙、毁佛道等民间信仰,堪称无所不毁的文化灭绝行动)带来的巨大灾难。他首先描绘了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来的种种残忍惨酷行径,是对无辜生命的践踏荼毒以换取同情,接着利用传统文化的感染力来痛斥“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13]232-233,这种教义本身让人不可理喻。指出“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还列举“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 [14]232-233的事例以说明太平天国历代与历代王朝末期的农民运动都不同,思想上的“夷”比血统上的“夷”更可怕,暗示大清尊崇中华礼教,是接续了中国道统,而天主教旗号的洪秀全完全无法接纳孔孟之道,是数典忘祖的类型,在现实层面与文化层面都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因此这是非常巧妙的,结合曾国藩晚年处理天津教案的事例,可见晚清士绅、民众对洋教的疑虑、误解的态度是十分明显的,曾国藩恰恰抓住了“卫道护统”的辩论空间加以还击。正如学者简又文所言,“国藩之兴师,并非为区区一朝一家而效忠,实为拥护中国数千年固有之名教,其影响之大,可想见也”。[15]综上,双方的分歧主要是在具体的文化主张与对清廷的态度上。
二.双方论点的潜在共性:儒学价值
吊诡的是,如果双方意识形态截然对立,那靠什么争取社会资源与支持呢?实际上,若抛开双方华夷之辨的不同指向与对清王朝的攻守态势,可以发现双方写作的初衷是非常相似的,从《讨粤匪檄》那里借用一个词——“以卫吾道”来审视,两者都是在护卫自己的“道”。道不是一个人伦、礼教层面的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它的条件与表现形式因时代和利益主体的差别,可以有不同,但是其内核却是相当稳定一致的。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将统治的合法性“道”与“天”相连,形成“天道”,正是基于这种对中国民间合法性信仰所做出的精准把握,并形成了中国传统政治中君权“天授”的政治传统。[16]天道赋予了传统社会对正义的崇高信仰,因其本身就具有神圣性。太平天国意识形态中的天道,看似有基督教成分,本质上是传统文化中的道,太平天国笔下“天父皇上帝”与儒家传统典籍中的“天”、“天帝”、“上帝”如出一辙。除了太平天国典籍里借用基督教义理对上帝人格化的描绘与儒家不承认充分具有人格性的上帝存在有所矛盾,笔者实在是看不到根本性的不同。先秦典籍《尚书·皋陶谟》中有“天叙有典”、“天秩有礼”、“天命有德”、“天讨有罪”的说法,把天的永恒秩序推延到人间的政治活动中;孔、孟、荀建立的道统尽管更注重人与阐发人性,但也没有离开天人关系;而汉儒董仲舒更是发扬了西周对天的信仰,构建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天人体系,甚至是根据五行学说而来的系统天人感应理论;到了宋明理学时,宋儒更是高扬“天理”,认为世间万物不过是“天理循环”,“无人欲即皆天理”;直到明儒王陽明的心学之前,天道在绝大多数儒学流派是彰显的,尽管在天人关系部分存在反思与争议,但这是局部性的。尽管在人与 “上帝”、“天”的关系中,儒家都凸显了人的地位,但这与历代王朝统治者与广大民众对天道的信仰与天命观的认知把握是完全不矛盾的。《奉天讨胡檄》叙事里的上帝也是有纲常的,上帝认可并具有一种有等差的爱而不是真正基督教的博爱,它表现为爱国、崇尚正义,具有英雄气概,有夷夏大防的心态,自认为天道在己方,而正统儒学影响下的曾国藩同样具有这些情怀,此为共性的第一点。
就天下观而言,《奉天讨胡檄》通篇 “中国”一词有五十多个。认为“盗中国之天下”“中国以六合之大,九州之众”“中国首也,胡虏足也。中国神州也,胡虏妖人也”“腥风播于四海”“盗据华夏”“廓清华夏”“四方英俊”“檄布四方”“布告天下”[17]108-110,而曾国藩则言“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粤匪”“两湖三江”“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所过郡县”“横行中原”[18]232-233……这无疑是相当值得玩味的,双方基于共享的历史观,似乎是在相互唱和。它们对传统中国的天下观不仅有着深刻体会与认同,而且在文学创作时共同彰显了这种天下观——其中“中国”“神州”“华夏”“四海”“六合”“九原”“九州”是几乎同义的概念,很好地对应在一起。曾国藩还细化了地理范围,列举了“粤”“两湖三江”“长江”与“中原”,让那些沦陷之地与未沦陷地的人民都有了直观体会,利用版图空间的延展来强化了“家仇国难”的政治记忆。“九州”原本是一个《禹贡》记载的概念,它一直被当作全国、“天下”的代名词。抛开政治、文化主张不说,两篇檄文同样如此传递出的传统中国的共同体意识是完全一致。而“天下”意为上天之覆。“天”指“天道”,“天下”乃是“天道”所覆载的,是“天道”在现实中所体现的人伦生活。“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儒家的天下观与大道合为一体。在大道运行的情况下,天下呈现出公平正义的良好状态[19],是儒家对国家、社会的最高理想。赵汀阳把传统中国的儒家天下观解释为“地理、心理和社会制度三者合一的‘世界”:一为“地理学意义上的‘天底下所有的土地”;二为“所有土地上生活的所有人的心思,即‘民心”;三为“伦理学/政治学意义,指向一种世界一家的理想或乌托邦(所谓四海一家)”[20]41,从檄文通篇来看,双方的天下观暗合了中国大地应该追求地理一统、心理攸同、社会制度正义公道的政治主张,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情怀是其堪称经典檄文的重要原因。
《奉天讨胡檄》表面上将诉求诉诸“排满”的激进革命带来的平等主义和对民族的独立、复兴之向往,并掺杂着拜上帝教思想加以调和,作为一场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帝制时代国内自发的大规模的末世抗争,实际上是一次大尺度的、富于想象力的披着反儒旗号的传统文化自我救赎,是一次不成熟的混合了基督教色彩的排他性文化反思运动。特别是从杨秀清来看,他在武昌期间曾亲自谒孔,也在定都天京后一度对洪秀全“防妖太甚,毁尽古书”的激进行为做出纠正,因此他的的“儒家化”思路不仅在宣传动员中,而是一系列活动中都带有儒家式的政治轨迹。[21]因此太平天国内部具有差异性、妥协性和复杂性。而曾国藩的《讨粤匪檄》发轫于人文荟萃的三江两湖地区,试图接续了程朱理学,发扬了湖湘学派,在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试图唤起清儒的道德觉醒,将道德理想主义诉诸儒家士绅,并建构伦理与政治主体意识,可谓宣扬了儒士丧失的文化权力的回归。
双方作为意识形态策略的道统,表面很不一样,实际上都以类似的天道观和天下观展开,奉行相似的儒家传统道德与观念以及实现社会思想的统一,只是隐藏在文字背后罢了。
三.清的合法性与文化现代化问题
既然双方都具有如此的才识与魄力,那么时代为什么会把他们推向战争边缘呢?接下来要探讨两份檄文背后的成败得失——它们自身都有着革故鼎新、新旧交织的双重因素。
首先这两份檄文是对清代正统性的一次大探讨、大辩论,是代表的两派观点矛盾的总爆发。中国传统历史叙事强调得位之正统性,而清朝的建立是在学术上一个很有争议的事件。欧阳修在《正统论》中指出“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正统性在传统“正闰”“王霸”之辨的记史规则下包括三个核心要义,一是“大一统”,即王朝需要占据足够的疆域,统合广大地域里的人民,同时具备德行,尚德不尚力;二是制作礼乐,有一套区别于前朝的服色等制礼风格;三是以中国之地为本位,“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天下观来处理各族群之间的关系。[22]434不难看出,太平天国檄文指出清代统治者不具有正统性是主要因为“夷狄”的身份,辅之以实行霸道加剧了不正义,这一点几乎是明末清初江南士人的共识——顾炎武在《日知录》指出“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夫以君臣之分尤不敌华夷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23]245黄宗羲认为“中国之与夷狄,内外之辨也。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由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不可杂之于人也。是故以中国之盗贼治中国,尚不失中国之人也。”[24]12。而曾国藩则深谙其中的原因,他那里的“夷狄”身份是文化上的概念,是处于变化中的、以一种实事求是的眼光来衡量的。实际上,纵观历史,中国的版图从先秦起不断地变化,历经多次民族融合,血统上的“夷狄”早已不复存在,而文化上的“夷狄”也被包含在“大一统”的论述中,夷夏并非处于对立。在曾国藩那里,今日的“天主教”或者明日的什么学说教义否定儒家,破坏礼教,在文化身份上就已经不是正统而是“夷狄”,而清代统治者在治统上体恤百姓,施行仁政,还接受了“道统”教化进入正统谱系,比如在历史书写上与宋元明对接而不是与辽金接续,就已经解决了合法性问题。不论孰是孰非,我们都能看出清代“道”的秩序重塑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晚清以前历史中,将“道”与“治”合一的尝试与相关施政策略并未完全落实,统治者一方面拉拢一方面压制儒生,矛盾处于积蓄状态,给这次檄文中的辩论留下了丰富思想渊源。
其次这两份檄文彰显了文化现代化的阶级因素,即对乡绅阶层的争取主张不同。明代中叶至民国中期,乡绅阶层在历史舞台涌现,费孝通、吴晗认为乡绅是传统社会的乡村知识分子,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卫道者。[25]45在一个识字率很低的社会,乡绅在文化上控制了农村意识形态,由此承担起教化乡民,追求一种“礼”的道德生活,在经济上占有一定的财富并愿意做出奉献,提高管理效率,促进公共利益(包括安全与福利),在身份上有机会经过科举而获得功名,但归根结底乡绅的授予在下而不是在上。[26]18清代设置了保甲制度意图延伸国家正式权力来控制乡绅的非正式权力,但实际上是被乡绅阶层的权力反控制了。绅权具有民间属性、对国家权力的不合作性质[27]101,当国家权力面临衰退——经济困顿、对内军事失利、财政汲取吃紧、外国列强入侵等挑战时,就会给绅权的兴起、扩张留下机会。19世纪中期的乡绅权力,正处于崛起、扩张状态,表现在对人事、财政、军事、政策动员等领域对国家能力的弥补,开始走向合法化、正式化,甚至是越界。特别是在19世纪初期(嘉庆初年)四川湖南等地的团练为了镇压白莲教就已经兴起。因此在斗争中,谁能争取一个正在崛起扩张阶层的支持,谁就能获得成功,相反若无视则可能失去机会。而从文本上看,不注重对士绅阶层的笼络为太平天国的失败埋下伏笔,表现在其文风过于泼辣粗鄙,特别是对现实的夸张成分太多,稍有理性的人都会感觉到清代并非一个“无人伦风化”、施行“妖魔条律”、率兽食人的局面。在意识形态与利益分配政策方面也无法迎合一个成长中的士绅阶层特别是中上层士绅的既得利益,追求一味的文化排他主义,导致了在满洲贵族与民间汉族士人的两重被动。而团练的创办则正好彰显了绅权作为国家权力的延伸,曾国藩的团练及其檄文既发扬了讲求“内圣”的理学特点,又带有注重“外王”的经世学气质,并笼络了一大批具有影响力的汉族儒家士人,一方面吸纳了朝廷重臣(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的力量,壮大了团结对象——湘军笼络了当时儒家文化的大批精英,幕僚多大三四百人,正如冯友兰所说,“湘军不是武人建立起来的,而是由文人特别是道学家建立起来的”。[28]78另一方面也让广大乡绅有了精神支柱,特别是一些退守乡间“自修”的隐士,激发了“以挽救道统为先,暂放政统的纠葛争议”的认识,集中力量以抵御内忧外患。此外在文风上比较文雅,在节奏上抑扬顿挫,笔墨凝练,重点突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特别是强调士人的主体地位与责任担当,如“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29]232-233。另外善于广泛动员不同阶层的对象,比如对“血性男子”,采取“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对“仗义仁人捐千金以上者”采取“专折奏请优叙”;对“抱道君子”,采取“礼之幕府,待以宾师” [30]232-233;对敌方投诚者,采取优待安撫,去留随意。实可谓“统一战线”的思想渊源。曾国藩作战胜利之后,同治中兴逐渐形成,但政治社会危机依然深重。太平天国虽败于相对落后的军事和文化底蕴,但“拜上帝教”之后的西化运动仍不断席卷神州,半个世纪多以后,体制内外的儒家士人、绅商、新军、新学学生等共同力量交织在一起,推动了现代国家的探索建立。
两份檄文站在“华夷之辨”“卫道护统”的角度共同阐发了现代中国在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的基本主张,既对立又统一,共同阐发了晚清的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合法性诉求。作为激进的反叛路径与理性重塑的修补路径的典型代表,推动了晚清时期儒学的近代化,促进了清代的历史转折,为日后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化现代化道路探索铺路。双方的争斗,是当时传统儒学与基督化儒学的输死较量,也是传统儒家文化与民间信仰体中的异质元素的的对抗。其过程和结果再一次宣告了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体系内的生命力。尽管当时的双方都没能开出一个文化史意识形态中的现代国家,但一个波诡云谲、风云变幻的时代已经拉开了帷幕。
注 释
①这是一个惯常的篇名。本文根据的《太平天国印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中并无单独的此篇,而是与《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就一切上帝子女中国人民谕》一并置于《颁行诏书》的题下,史称“杨萧三谕”。
参考文献
[1]王海洲.合法性的争夺——政治记忆的多重刻写[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2]枕戈、陆魁宏.枕戈访陆魁宏:曾国藩是新儒家起点[EB/OL].(2015-08-06)[2018-12-15].http://www.aisixiang.com/da
ta/91096.html.
[3]曾琦云.再论曾国藩——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开创者[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1(4):36-48.
[4]姚中秋.国史纲目[M].海口:海南出版社,2013.
[5]成晓军,彭小舟.清代理学经世派的文化宣言——《讨粤匪檄》文化内涵新论[J].社会科学辑刊,2001(1):117-123.
[6]董丛林.“杨萧三谕”与《讨粤匪檄》比较论[J].河北学刊,2016(3):44-48.
[7]李志茗.天父天兄之教与名教之争——《奉天讨胡檄》与《讨粤匪檄》比较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4):61-66.
[8]刘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9][10][11][12]太平天国印书:上册[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
[13][14][18][29][30]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M].长沙:岳麓书社,1995.
[15]简又文.太平天国与中国文化[J].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论集·第3编[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7-18.
[16]徐燕斌.天道观念下中国君权的合法性建构——基于礼的视角[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4):21-26.
[17]太平天国印书:上册[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
[19]李兰芬,朱光磊.社会管理创新的儒学解读——儒家天下观与当今社会的会通及其现代转型[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4):83-88.
[20]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21]王明前.太平天国政治的“儒家化”轨迹[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45.
[22]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23]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七,管仲不死子纠[M].长沙:岳麓书社,1994.
[24]黄宗羲.留书·史,《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25]費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26]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27]徐祖澜.绅权与国家权力关系研究——从明清到民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2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M].台北:蓝灯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
(作者介绍:周嘉豪,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