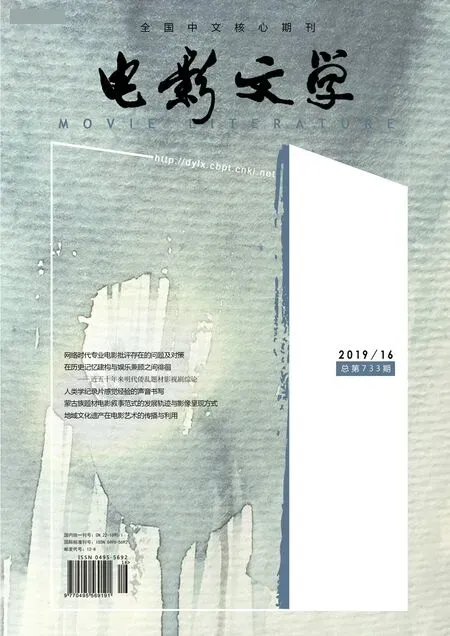融媒体时代下互动电影的叙事研究
——以《黑镜:潘达斯奈基》为例
张 晗(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
融媒体时代下,原有的媒介与媒介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弭,融合后的新媒介又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电影这种传统艺术与新兴的游戏媒介也实现了融合,并且近年随着移动设备的普及、游戏引擎技术的进一步提升,电影与游戏之间的跨媒介交流变得越加频繁,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即是互动电影。
互动电影(Interactive Cinema)也被称为电影游戏,通常是使用动画或真人录制的视频,内设在游戏程序之中,通过游戏玩家的一系列游戏动作激活。但互动电影比游戏更强调故事的呈现,而非其游戏性。学者达文波特(Glorianna Davenport)曾如此描述:“互动电影是这样一种类型,它将电影语言及美学与一个能够实现观众反馈及控制的传送系统整合起来。互动电影鼓励其观众主动参与到电影体验的构建、个性化、消费和分享活动中。无论它所上映的‘电影院’是公共场所还是私人空间,其功能和设备都能让观众着手讲故事,并主动地推动情节发展。从这一点上说,互动电影向传统电影发起了挑战,后者的故事往往以固定不变的线性叙事。”[1]
2018年,流媒体平台Netflix推出迷你剧《黑镜:潘达斯奈基》(以下简称《潘》),这部作品是一部具有庞大叙事线索和多向结局的互动电影,共拥有16个主要结局,在每一条叙事线索上都设计了情节点分支,观众需要在屏幕前进行点选,替故事中的主人公做出选择,才能达到最后的结局。虽然《潘》这部电影并不是互动电影的第一部作品,但是它故事内在逻辑线的编排,情节叙事的流畅度,外部游戏程式以及情节点的跳转技术设置都做得相对成熟,在叙事上也呈现出鲜明的新媒体叙事特征。
一、“游戏+电影”的超文本叙事媒介
互动电影的尝试由来已久,1967年蒙特利尔世博会上捷克馆中播出了史上第一部交互式电影《自动电影》(Clovekajehodum),观众可以通过按手中的红绿按钮来投票选择剧情发展。不过碍于当时的技术限制,每当电影到了需要选择的关键节点,都需要暂停放映,然后由主持人上台引导观众做出选择,再按照观众的投票结果播放相应的片段。种种技术上的阻碍限制了互动电影的发展,但是这种形式却在游戏产业之中开始了进一步的创作尝试,如1992年的《午夜陷阱》、1996年的《红色警戒》都采用的是真人拍摄影像片段的方式,替代游戏中的动画或即时演算,当玩家进入游戏“节点”时,可触发影像播放条件。但这些影像在游戏中所占比例较少,只能交代部分信息,承担了玩家引入游戏世界的“导引者”功能,却难以形成完整的叙事,玩家仍然专注于游戏交互体验,而非影像内容。

图1 《自动电影》影像资料
近两年随着移动设备的普及和流媒体网站的发展,全视频影像(Full Motion Video)开始大批量涌现,如《夜班》《马赛克》等。它是早期游戏中嵌入真人影像形式的延伸,然而不同的是,全视频影像中的游戏过程被大量压缩,观众不需要操纵主角在游戏世界里游荡,而只是根据屏幕上的剧情跳转选择,完成几段影像文本的拼接,组装成一个完整的电影。全视频影像是目前互动电影的主流呈现方式,它与传统电影拥有几乎相同的镜头语法,当主角出现选择行为时,流畅的画面叙事会暂时性地中断,而该画面的结尾也是剪辑点,在观众代替主角进行抉择之后,画面会跳转到新镜头序列中。但是大多数的全视频影像制作较为粗糙,故事逻辑简单,跳转选择也很随意,往往只有三到四个结局。2018年底《潘达斯奈基》上线,它采用的也是全视频影像的形式,但是明显地制作更加精良,人物塑造更加具有层次感、情节组织方式更严密,是一部成熟的互动电影。
互动电影和传统电影的区别首先来自媒介的改变。互动电影跨越了电影和游戏两重媒介,将两者聚合成了一个新的超文本。“超文本”由“文本”和“超”两部分构成,指文本分散而靠联结点串起,读者可以随意选取阅读。超文本将各种不同空间的文字信息汇集,使互有关联的文本以网状式、交叉式相互连接,形成一个庞大复杂的网状文本结构。学者乔治·兰道认为超文本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小到一个多向文本,大到整个互联网都是超文本,它意味着超文本的内容无限增加和动态扩展,超文本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它的本质和基本特征就是在文档内部和文档之间建立联系。[2]
《潘》的叙事文本组织形式呈现为双层结构,即内层的电影文本与外层的电子游戏程式文本的融合,两者通过链接技术形成了一个新的超文本,电影叙事文本是它的主体构成部分,这决定了互动电影的本质仍然是电影而非游戏。相较于传统电影,《潘》的呈现方式具有明显的超文本媒介特征,首先它的呈现方式为窗口呈现,这与传统电影的屏幕呈现有着很大的区别。屏幕是单一的,而窗口是多线的,窗口具有通向无限空间和双向交互的潜力,屏幕相较于窗口,是一种单向窥视,而窗口是双向甚至是多向窥视。在剧情进行过程中,当主人公面临选择,画面上都会浮现出两个新“窗口”进行选择提示(如图1),如主角斯蒂芬在编写游戏时,遇到了阻碍心情烦躁,父亲劝说斯蒂芬停下,斯蒂芬则拥有两个选项“把茶水泼到电脑上”和“朝父亲发火”。如果选择了“把茶水泼到电脑上”,则会直接进入“游戏编写失败”结局。选择“朝父亲发火”,剧情将会接入新窗口,斯蒂芬在父亲的带领下去看心理医生,开启一段新的人生。观众也可以随时中断、返回、续播,在不同窗口之间来回穿梭,被赋予了比遥控器选择更多的主动参与权。

图2 《黑镜:潘达斯奈基》剧情截图
其次,《潘》也具有超文本的链接特性。超文本并非是一次性全面呈现的文本,而是由无数个窗口和链接层层叠叠,最终以一个混合文本的形态呈现在人们面前,它的链接是无形的,链接与链接之间有着潜在的文本排列逻辑规律,《潘》在每一个情节点都设置了跳转选项,每一次观众只能组接一条叙事线索,当观众点选组接链接时,一条叙事线索渐渐浮现出来成为显性叙事线索,而其他链接则呈隐性、未组接状态。最后,《潘》具有超文本动态性。文本的动态性具体指两个方面:一是指在文本上不断地添加、删除、中断、返回、改写,使文本有了新含义;二是指文本本身的排列顺序并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动的,以不同的顺序阅读,有可能使文本意义发生偏差。观众在《潘》的叙事线索组接过程中,是可以不断地改写文本,某一条路走向了悲剧结局时,观众完全可以重新跳转回上一选项尝试建立另一条叙事线索,整个故事的叙事顺序可以被打乱,叙事文本的意义也不再具有固定性。
二、交替叙事的多重叙事主体
互动电影将电影文本与游戏文本通过技术手段聚合在一起,其聚合过程是技术和符码的拼贴,从叙事的角度而言,这个聚合的过程也是消弭文本材质和体裁界限的过程,是艺术语言、艺术材料和艺术工具从分离到再融合的过程,这一过程势必会对其叙事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
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出现在叙事主体的多重性上。这具体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叙事的创作主体具有多重性。游戏媒介赋予了互动电影交互性,交互性艺术最大特点在于建构作品与参与者的对话,让参与者有能力对作品施加影响。交互性在作者—文本—受众的关系上影响是最深远的,受众永远在和作者争夺着对文本的控制权,使作者和受众之间产生协同/斗争的紧张关系。作品是否具有交互性决定于受众是否能够控制文本。
互动电影的创作主体分别是电影编剧和观众,电影编剧先对故事进行了构架,创作了故事的内层叙事(游戏故事),留下了多个选项和路径构建了游戏的外层叙事(游戏选择)。《潘》在Netflix上线之前,就已经拍摄了500分钟的素材,将所有的分支线和结局都编写完成。显然在这一期间,观众是无法干涉剧情的,互动电影的电影编剧对叙事具有绝对的控制权。但是当观众开始观看互动电影,并且通过选择和发现展开部分故事情节时,电影编剧原有的控制权则慢慢丧失,并转移到了观众的手中。在这个过程中,观众与电影编剧进行了身份的“客串”甚至是身份互换,最后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故事,形成独一无二的玩家个人叙事(玩家体验)。这一点在《潘》中也有所暗喻,主角斯蒂芬突然感觉自己的行为被第三者操控了,他向天空发出疑问的时候,这时他看到电脑屏幕上出现了一行字:“我在Netflix上看着你。”在这时,观众的创作主体身份在影片之中得到了确认。但值得注意的是,观众虽然拥有了一部分作品控制权,但主要的叙事线索和情节结构仍然被牢牢地掌控在电影编剧手中,正如《潘》中斯蒂芬所说:“他们(游戏玩家)只有自由意志的幻象,但其实结局是我定的。”暗指交互艺术仍然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创作自由。
其次,电影文本中的叙事主体是多重的,在传统电影文学作品之中,叙事主体往往是剧中主人公或其他角色。但是在互动电影中,电影编剧将故事切割成时长不一的文本块,散落在不同的情节点上,观众在进行选择、拼接节点的过程中,叙事主体从故事内层中的主人公变成了故事外层的观众,节点链接后触发主要剧情,进入正常的影像叙事时,叙事主体又从观众变成了故事主人公。《潘》在选择点上做了如下设计,每一个选择点给观众十秒钟的反应时间,如果观众不反应,则系统自动替观众进行选择。主人公斯蒂芬在跨越两段叙事段的十秒钟之内,原叙事主体即主角斯蒂芬离场,并且被抽象成了一个人物符号,成为观众手中的工具,其主体身份被观众所取代。对于电影本身来说,叙事已经出现了中断,但对于观众来说,影像时空仍然是连续的,但他们并没有发觉叙事主体已经被暗中偷换。
三、非线性分叉结构的链接叙事
麦克卢汉在《人的延伸》一文中就提出“媒介即信息”的理论。媒介的特质决定了叙事艺术发生的地点和时间,也决定了生产和传播的方式,进而影响到了其文本形式和话语模式。
互动电影依托于超文本媒介,相较于传统电影,它在文本组织形式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潘》是一部典型的非线性分叉结构链接叙事作品。虽然观众在观看过程中,故事情节是流畅的,每一种选择都会通向一个闭合的结尾,呈现出线性叙事模式。但是确认一部影视作品到底是线性叙事还是非线性叙事,首先要考察在整部作品里它的情节是否有延续性,情节的延续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必定是在时间的推延之下展开的。其二,它永远不会停滞在一种物质关系状态下,而是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其次,线性或非线性叙事的区分点在于情节的组织形式。在一部传统的线性叙事作品中,主人公与外界的冲突构成事件,事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组织和取舍,其安排的结果就构成了情节,情节堆积之后就形成了故事。情节与故事的意义还不尽相同,大卫·波德维尔在《电影诗学》中引用了俄国的叙事理论对情节和故事加以区分:“我已经发现采用俄国形式主义者们使用的概念能达到最佳效果,他们用‘fabula’,即故事中事物与事件的状态,以及‘syuzhet’,在叙事中对他们的组织。”[3]这也即是说,故事是事件的总和,情节是事件的组织方式。是否拥有线性特征,最重要的就在于“情节”——即如何进行事件的组合,只有拥有因果的逻辑性,时间的连贯性和叙事的戏剧性组织方式的故事,才能够构成线性叙事。《罗拉快跑》《低俗小说》等作品都是典型的非线性叙事作品,它们的情节排序自由,叙事主体多变,人物在每一段情节线之中都呈现出不同的状态,整体情节呈现出去中心化、反戏剧化的特质,最终形成了结构复杂的“多向文本”。但是传统电影在非线性叙事上的探索不可避免地遇到技术上的壁垒,观众无法控制叙事时序的单向流动,情节组织、叙事顺序是由电影编剧创造,观众也只能被迫接受一种故事讲述方法,传统电影无法展现出一个多向文本的真正面貌。
而由于互联网链接技术的介入,这种多向文本叙事的局限性在互动电影中得到了缓解。所谓“链接”指的是将一个超文本呈现为有意义的、联系的、网络的基本结构。它不仅表示的是语义联系,而且还代表网络空间内建立可能的运动的路径,并且控制对于信息的访问。[4]互动电影往往呈错综复杂的根茎状或网状结构,叙事线索被连接在无数的节点上,拥有数十甚至上百种排列组合的可能,观众获得了极大的自由性,故事的开端、中间情节和结局都可以被观众提取出来,重新组合或者主动延续,最后形成一条完整的线性叙事。《潘》可以通过数十种的选择达到同一个结局,也可以通过不同选择达到不同的结局。当观众不满足一个结局时,就通过“返回”链接回到上一个情节点,使时空再一次重复,主人公斯蒂芬实际上也已经不再是上一个故事中的斯蒂芬。观众可以在情节之中来回穿梭、回溯,获得不同叙事线索拓展的可能。观众的游戏行为时间与银幕时间完全重叠,游戏选择也变成了叙事的一部分。影片的结尾由于其多重结局的设置,也具有了不确定性。《潘》的几种结尾有:斯蒂芬游戏设计失败,斯蒂芬游戏设计成功但杀死了父亲而坐牢,斯蒂芬被逼疯,但发现自己是被观众操控的,斯蒂芬发现自己是一名正在拍摄《潘》的演员,斯蒂芬发现自己生活在“楚门的世界”,斯蒂芬游戏设计被雪藏,但是一名21世纪的年轻人打算将该游戏重启……多达十余种。多向度文本的随意性在互动电影之中得到了更全面的展示,多向文本的面貌是经由读者的路径挑选动作而产生,每次所得的面貌仅是众多可能之一。读者的参与决定作品发展过程的次序编排,大大增加了作品结构和内容的任意性。[5]可以说,链接叙事是互动电影最主流的叙事模式,也是它最大的叙事优势。
四、结 语
电子游戏与电影的融合下诞生的互动电影,不仅在叙事上突破了传统电影的局限,也极大丰富了电影的形式,增强了电影的可看性和可玩性。但是目前由于创作和技术的限制,互动电影还处在探索阶段,链接叙事模式还略显生涩。比如《潘》中其中一个情节是主人公斯蒂芬吃抗抑郁的药,认为自己吃药会影响创作,这时的两个选项一个为“把药冲掉”,另一个是“把药扔掉”。这其实是一个伪选项,因为无论选择哪一个都只能通向一个结局。
并且,传统电影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建立的镜头语法与叙事节奏的魅力在互动电影之中被大大削弱了,互动电影中无时无刻情节会被中断,观众无法感知叙事节奏,传统创作法之中的“起承转合”形同虚设,所以观众对《潘》最大的诟病也在于它没有故事感。
目前互动电影暴露出的诸多叙事问题,都源于创作者并没有真正找到一条令观众舒适,也同时能够充分利用新媒体优势的叙事方法。在不久的将来,电影与电子游戏的融合会进一步加深,如何让二者在保留自己叙事的独特性的同时,寻找到适用于互动电影的新叙事体系,还亟待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