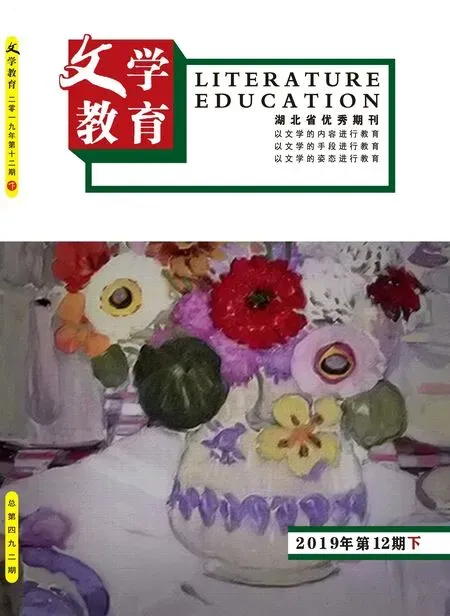《使女的故事》中的羊皮纸意象
魏 巍
纸张未发明前,羊皮纸是欧洲人用来书写的主要工具。因其价格昂贵,人们常反复使用它,只需将其表面的文字擦除后,覆盖上新文字即可。但是原有的文字很难完全消除,它们的痕迹就隐藏在字里行间。引申开来,羊皮纸可用来指任何保留历史痕迹的事物。《使女的故事》中,羊皮纸的意象最早出现在主人公奥芙弗雷德(Offred)描述培训基地的时候,“这里曾经举办过舞会;乐声萦绕在房间内,无人倾听的声音如同羊皮纸,一种风格叠加着另一种风格”(Atwood,1998:3)。实际上,这一意象在全书都有体现。
一.消失的历史
阿特伍德在《使女的故事》中虚构了一个存在于二十一世纪初的基列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Gilead),这是一个神权统治的国家,由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推翻了现有美国政府而成立。他们奉《圣经》为最高权威,逐字理解圣经并照搬其中的做法,相信只要笃信上帝,让一切“回归自然”,就能解决社会面临的一切问题,包括低生育率、环境污染、道德堕落和社会动乱,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他们将人分成各个等级,女人被分为夫人、嬷嬷、使女、马大、经济太太、荡妇;男人分为大主教、眼目、天使军、卫士等。女人被剥夺了财产和工作,只能从事家务活动,或提供性服务,或与基列国统治者共谋压迫女性。“基列政权有效地剥夺了女性的个体身份,将她们转化为男权中心经济中可替代的物品”(Bouson 1993:137)。
当权者认为过去的时代“均属于畸形年代”,是“历史的偶然罢了”,他们所做的是“使一切回归自然”(阿特伍德 2008:230)。于是他们抹除历史,禁止女性阅读,从而禁止她们获得知识和历史。剥夺女性的财产和工作,宣布再婚女性的婚姻不合法,逼迫她们进“红色感化中心”再教育成使女,为统治者提供性服务。“红色感化中心”建立在原本获取知识的学校中,但即使极力抹除,过去的痕迹依旧存在。“这里曾经有过性、寂寞及对某种无以名状之物的企盼”(阿特伍德 2008:4)。店招牌上的文字被删除,只保留用来标示的图片,“田野中的百合”(Lilies of the Field) 是定做裙子的地方,“奶与蜜”(Milk and Honey)是食品店,“众生”(All Flesh)则是肉店。这些招牌虽然没有文字,但图片也有诱惑作用,暗示着性等基列国所严禁的东西。书写被禁止,因此写于过去的文字便如同穿越时空的使者,言说着过去的痕迹,如那些嵌进木头里的姓名缩写,是过去的记忆。
二.现实的影子
基列国尽管可怖,但有许多现实的影子。阿特伍德说“使女的故事中描述的事情没有一桩是完全新的,全都在历史上发生过不止一次”(Atwood 1998:316)。我们可以逐一找到证据。基列国的神权统治和伊斯兰极端国家类似,伊朗在1979年建立的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曾一度禁止妇女上学,要求穿只露出眼睛的长袍面罩。使女穿的红色服装,将皮肤全部遮盖,“裙子长至脚踝,宽宽大大的,在乳房上方抵肩处打着褶皱,袖子也很宽”,还要戴“包裹着脸的带翅膀的双翼头巾”,“它使我们与外界隔离,谁也看不见谁”(阿特伍德 2008:8)。在极权国家,对女性的压迫严重,强制女性穿保守的衣服就是一种体现。
除此之外,基列国的情况与美国早期清教社会很类似。《使女的故事》发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这里是美国清教徒兴盛的地方,阿特伍德借此来隐射清教社会与基列国的联系。在小说中,奥芙弗雷德和奥芙格兰(Ofglen)走过的一座博物馆,是年代久远的教堂,“人们可以在里面看到许多画像,有一身素裹、长裙曳地、头戴白色帽子的女人;也有身板笔直、穿着深色衣服、表情肃穆的男人。全都是我们的祖先”(阿特伍德 2008:33)。“祖先”指的是那些建立美国的早期清教徒,阿特伍德在这里描述的这些人物是清教徒的代表,体现出其在基列国的影响力。
此外,我们可以从基列国的环境恶化中看到现实中的影子。当今环境破坏严重,极端天气、核污染、低生育率、雾霾威胁、臭氧层空洞等威胁着人类生命安全。而在小说中,基列国的环境污染已经极其严重。此外小说还隐射了当今美国的一些社会问题,如社会暴力犯罪、随意的两性关系等,处处可以看到现实的影子,阿特伍德把现实融入虚拟中,是对现实情况的复写。
三.一部反乌托邦小说
反乌托邦小说通常设置在不远的未来,作家在小说中构想出一个世界,当代最危险的因素被放大和夸张。“反乌托邦是讽刺,更是恐怖的预警,现实中的暗影延伸到未来”(Atwood,2005:94)。《使女的故事》中环境污染被夸大为严重威胁人类生育,由此产生了控制生育,争夺生育权的极权国家基列国。《使女的故事》与之前的《一九八四》《发条橙》《美丽新世界》一样,是一部反乌托邦小说,我们可以看到它和之前小说的许多互文性。这里主要讨论《一九八四》,实际上使女的故事被称为女性主义的《一九八四》。《使女的故事》中有基列共和国,在《一九八四》中则是虚构了大洋国(Oceania)。在《使女的故事》中是把人按照地位和功能分成各种等级,而《一九八四》中,大洋国政府则分为四大部门,真理部、和平部、仁爱部和富足部。奥威尔在小说中把历史也比作了一张羊皮纸,“历史都象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奥威尔 2006:74)。
“在反乌托邦小说历史中,文本的复杂性往往体现在对语言的控制上”(Moylan 2000:148)。在《使女的故事》中,书籍被销毁,禁止女性阅读写字,大众传媒被操控,语言作为思想载体被控制在最小使用范围内。在大洋国,统治者也控制思想和语言,他们用新话、双重思想这样的人造词汇和分类来覆盖原有的思想。主人公温斯顿在真理部工作,将已经出版的《泰晤士报》上的各种信息进行篡改,原版被销毁,校正的版本取代原来的存入档案。
此外反乌托邦小说中的极权统治都有严密的监督者,如《一九八四》里的老大哥和思想警察,而《使女的故事》中则是卫士和眼目。但尽管严格控制,两个故事中都存在黑市,出售严令禁止的东西。其中对性的压制有最大的体现,在基列国的“红色感化中心”,丽迪亚嬷嬷教育使女,“成功的人生要避免那种事,杜绝那种事”(阿特伍德 2008:57)。使女被分配给大主教后,每个月要进行授精仪式,但这也没有丝毫刺激之处,必须“小心排除任何有可能制造浪漫气氛或激发情欲的东西”(阿特伍德 2008:168),变成冷冰冰的行为,一切以生育为目的。在《一九八四》也要消除性快感,“生殖的事要弄得象发配给证一样成为一年一度的手续形式”(奥威尔 2006:385)。
结语: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使女的故事》中体现的羊皮纸的意象,包括基列国社会方方面面所体现的前基列时期的痕迹,蕴含的现实世界的影子,以及同其他反乌托邦小说的互文关系。这表明,基列国不仅仅是小说中一个架空虚构的世界,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代表。这是一部意蕴丰富的反乌托邦小说,涉及现实问题,体现了丰富的历史痕迹,对于极权主义统治的危害具有现实的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