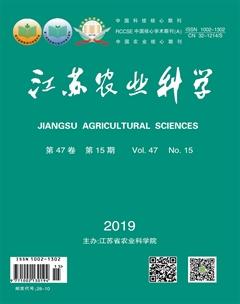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感知的分析框架
陈万明 刘畅 蔡瑞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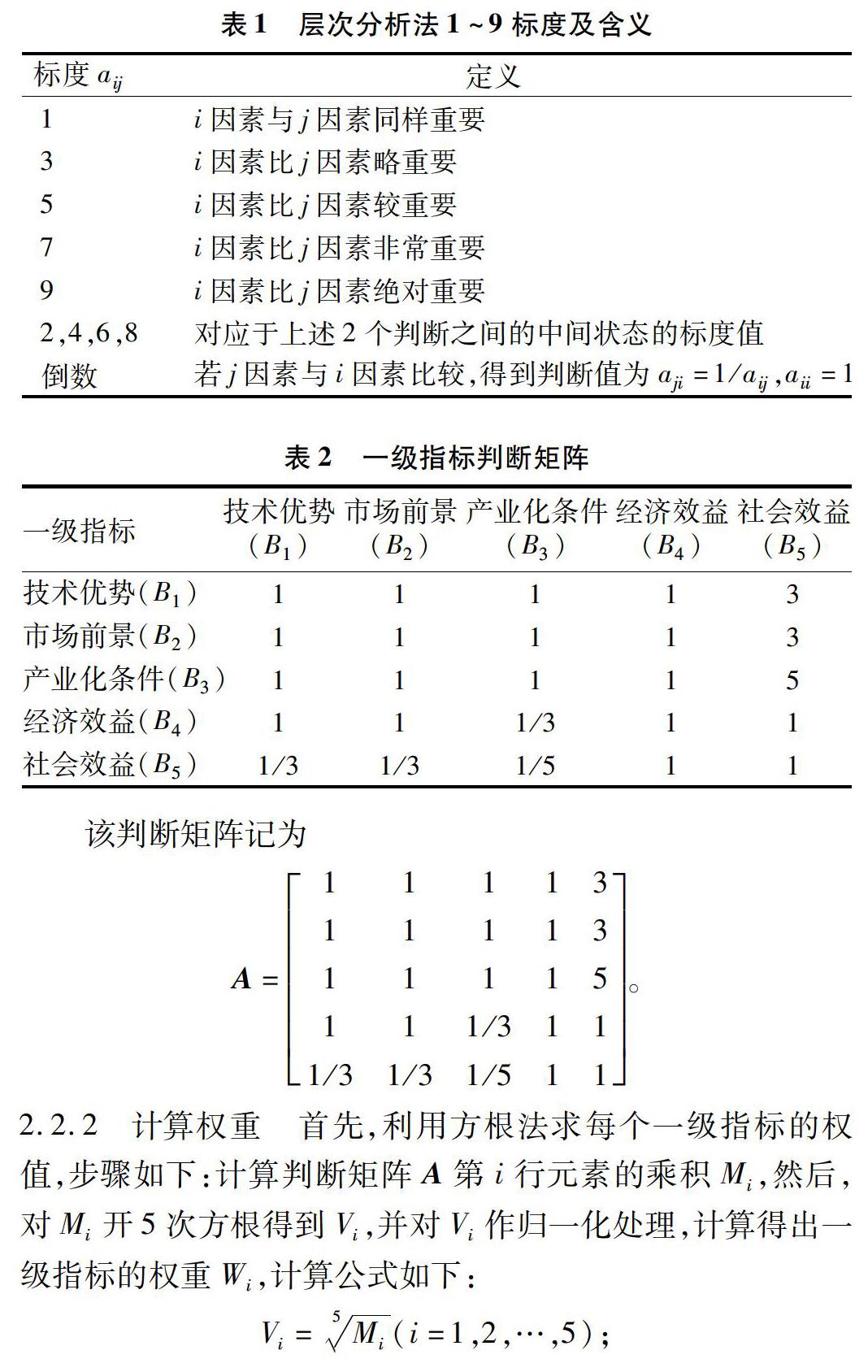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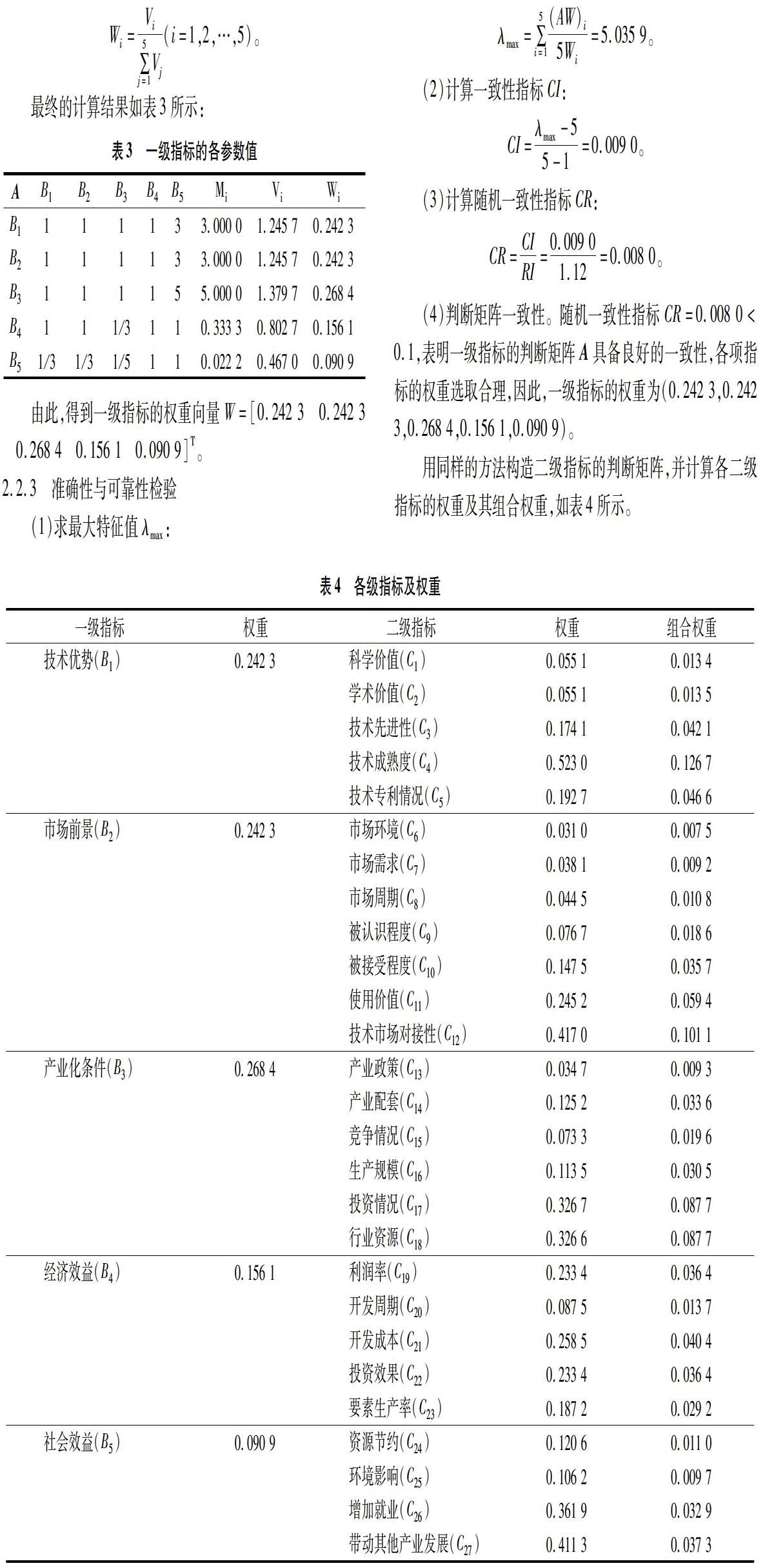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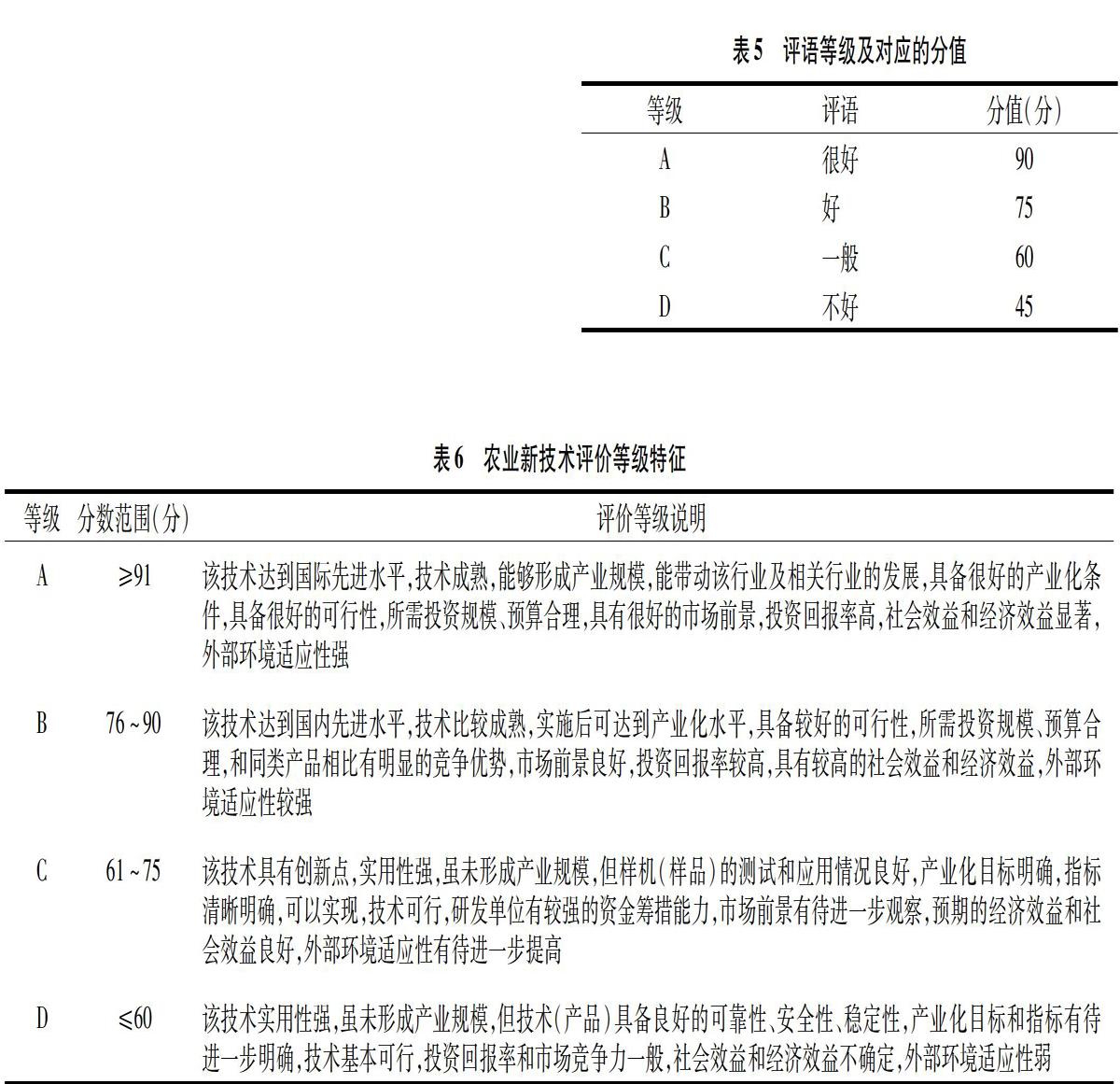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更多人口融入城市的”目标。农民是否“进得来、留得住、过得好”,自我感知往往是市民化程度的真实写照。现有文献多从城市融合和经济计量模型评判市民化程度,这是市民化程度的“他评”方法;从“自我感知”视角,可以作为“以人为核心”城镇化的补充诠释。本研究从市民化“自评”视角,采用建构扎根理论方法研究市民化感知的分析框架,经过初始编码、聚焦编码、轴心编码、理论编码和理论饱和度检验,揭示了自我感知的市民化可以从经济条件、社会保障、社会融合、文化融合、户籍限制和政治权利6个维度判定分析,并对“客观指标”和“自我感知”2种市民化分析框架进行了比较,据此提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5点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新型城镇化;扎根理论;自我感知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9)15-0316-04
坚持以“人为核心”,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是国家新型城镇化的阶段性目标。目前,对于市民化程度的判定,学者们采用经济计量模型和统计数据进行计量。但是,由于许多经济指标采用均值计量,这些均值与农业转移人口的实际情况可能存在较大偏差,因此,使用统计指标可能较难客观地刻画处于弱势社会地位的农业转移人口,直接影响到市民化程度的客观判断。自我感知强调情境中不存在强烈且明确的外在诱导或刺激而作出的行为选择,由此人们可以根据当事人行为情境中是否存在外在或内在的诱导或刺激物归因他人的行为动机[1]。根据自我感知理论,农业转移人口在没有明显诱导或刺激情境下对其市民化的自我判断才是最真实的感知;事实上,市民化进程涉及方方面面的共性问题和进城农民个性的差异,难以用数学模型或数学推理定量刻画这一高度中国情景化问题。据此,开展市民化感知的分析,可以弥补单纯通过统计指标测算的不足,也更能体现“倾听民声、反映民意”。本研究运用建构扎根理论方法开展质性研究,尝试构建基于自我感知视角的市民化分析框架,研究目的主要有2个方面:一是通过质性研究,构建基于自我感知视角的市民化分析框架;二是比较“客观指标”和“自我感知”2种市民化分析框架,提出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真正市民化的政策建议。
1 文献回顾和研究问题
1.1 市民化程度的判定分析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既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过程,又涉及经济、社会、人文等众多方面复杂的社会问题。由于“三农”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中国农村人多地少和城乡经济水平差距的国情决定了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必须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目前,关于市民化程度的判定分析主要分为以下2类:
一是从城市融合程度间接测量评判市民化程度。例如何雪松等以香港移民作為研究对象,从社会网络、社会认同和社会参与3个维度构建农民工城市融合的测量指标体系[2];卢国显从行为和心理情感2个维度,构建了13个二级指标的测评体系,通过进城农民与市民的社会距离间接反映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3]。类似地,吕佳等提出了基于微观个体的内生性指标和基于中观城市环境和宏观国家政策的外生性指标共同构成的测量指标体系,据此测量市民化程度[4]。
二是采用经济计量模型、运用统计数据或微观调查数据,直接判定市民化程度。例如刘传江等依据市民化意愿与市民化能力构建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指数,分别测算了第二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5];徐建玲在此基础上引入外部制度因素,认为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指数为外部制度因素×(市民化意愿×市民化能力)1/2,并对武汉市市民化程度进行测算[6]。此外,沈映春等也构建经济计量模型,以统计数据为主测算了市民化程度[7]。但是,无论是城市融合的间接测量还是计量模型的直接测量,由于测量内容、测量形式和技术方法上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市民化程度的评判成为关注重点。
1.2 研究问题的产生
综合现有关于市民化程度判定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上述两类分析方法为准确描述市民化提供了很好借鉴。但是不难发现,现有的分析方法还存在可能的完善空间,原因有3个方面:一是我国现有的很多统计指标多采用均值计算,与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农业转移人口群体存在较大的偏差;二是现有市民化程度测算的经济计量模型各不相同,测量指标体系存在较大分歧;三是现有分析方法忽视了农业转移人口对其市民化的自我感知,而“自我感知”的市民化往往比统计指标“冰冷地”测算出来的市民化更加贴近进城农民的真实情况。据此,自我感知的市民化分析框架,是对运用统计数据测量市民化程度的有益补充,也更能反映千差万别的农民进城后是否“进得来、留得住、过得好”的真实情景。
2 市民化自我感知的质性研究
2.1 理论选择
自Glaser & Stauss的经典著作《扎根理论的发现》于1967年正式出版以来,扎根理论被认为经由质化数据构建理论的方法论。目前,扎根理论主要演化为以Glaser & Stauss为代表的古典扎根理论、以Stauss & Stauss & Corbin为代表的程序化扎根理论和以Charmaz为代表的建构型扎根理论,扎根理论方法的学派之争使得被誉为“定性革命”的扎根理论在广泛运用的同时也充满了争论[8]。Mill等在综述建构扎根理论时强调“建构扎根理论适用于通过个体主义辨析事物本质和探索性逻辑关系,即通过小样本的经验和事件尝试构建理论”[9],建构扎根理论坚持社会建构主义,秉承了解释学的传统,强调通过研究者对被研究者认知的深度挖掘,比较适合特定的时间、空间、文化与环境中挖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的自我感知研究,故选择建构扎根理论进行感知市民化的质性研究。
2.2 研究过程
2.2.1 数据收集 通过目的性抽样获得调查样本,并运用深度访谈方法获取农业转移人口感知市民化的数据。具体实施时,借助常州巾帼咨询服务发展中心平台,主要开展半结构化的深度访谈。之所以借助这一平台,一是因为巾帼咨询服务发展中心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属的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的公益性组织,免费为弱势群体提供就业服务培训,受访者在融洽、祥和的情景下没有心理压力;二是方便开展目的性抽样,每天都有进城农民前来咨询或寻求帮助,很容易获得有效样本,共计访谈104位农业转移人口,其中华北15人、东北16人、西北19人、华东19人、中南18人、西南17人。为了消除被访谈者的担忧,在访谈时并没有采用录音的方式,而且采用了现场笔记的方式,尽可能“原汁原味”地记录信息。访谈结束后,于当日撰写备忘录。
2.2.2 初始编码 按照Charmaz强调的“初始编码应该紧贴数据,而不是让强制数据去契合编码”的要求[10],对访谈备忘录进行逐行、逐段编码。为了减少编码中研究者“先入为主”的主观偏见,特别是为了“保持一颗无知的心”,研究者没有选择有“学术功底”的研究人员一起组成编码小组,而是与巾帼咨询服务发展中心的2位普通工作人员共同译码,并强调尽可能保持“开放和无知”的心态完成了初始编码(表1)。对于同一内容不同初始编码的情况,采用返回重新编码、不断比较基础上的共同研讨,达成对初始编码的统一意见,共产生了186个初始概念。
黄:从来没有参加过社区的活动,社区也没有人来叫我们参加过会议。但如果有机会还是想参与的,毕竟我来常州也7年了,也算是半个“常州人”,而且也可以多了解自己的社区,还可以多交几个常州朋友。 d23:参加社区活动
2.2.3 聚焦编码 聚焦编码是建构扎根方法的第二阶段,即根据访谈筛选出最重要的和/或出现最频繁的初始概念,并用提炼出的范畴来反映研究问题。按照Getz的建议,开始时编码较宽,随后逐渐缩小,直到码号饱和[11]。围绕“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一核心议题对186个初始概念进行聚焦编码,通过逻辑关系将概念“类属化”(表2),聚焦编码后共得到25个范畴(表4)。
2.2.4 轴心编码 聚焦编码后的范畴之间几乎是相互独立的,而轴心编码使得范畴间联系起来,使范畴的属性和维度具体化了。按照Glaser et al(2007)的建议,通过分析现象的“因果条件→现象→脉络→中介条件→事件中采取的行动/互动策略→结果”这一典范模型,得出主范畴与副范畴之间的归属关系[12]。轴心编码的过程如表4范例所示:市民化必须有一定的经济条件,这些条件蕴含于工资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收入等10个初始概念,但因果条件与现象又受到中介条件消费水平的影响,通过获得稳定的较高水平的经济收入,农业转移人口才有可能购买住房和提高消费水平,最终具备市民化的经济基础。经过轴心编码后,25个范畴经过类属化形成了6个主范畴(表3)。
2.2.5 理论编码 理论编码即综合初始编码、聚焦编码、轴心编码结果,尝试进行理论建构。这主要包括2个阶段:一是实质理论建构阶段,即通过初始编码与概念、概念与范畴、范畴与主范畴之间的关系,分析其间的逻辑关系及相互作用机制。二是形式理论构建阶段,即基于自我感知视角,实现市民化究竟应该具備哪些条件,构画出自我感知市民化的分析框架。Glaser将理论编码比拟为“把支离破碎的故事通过主范畴串连成一个整体,使分析的故事具有连续性,最终形成清晰的理论脉络”,至此,可以从资料中提拎出以下故事线: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主动或被动地向城市转移,但农民进城后并不意味着市民化的真正实现。这一方面受到农村农业部门、城市工业部门、乡镇企业部门、城镇非正规经济部门四元经济社会结构划分的客观限制[13],使得许多农业转移人口虽然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城里,但事实上没有融入到城市,只是在城镇和农村之间不断地“迁徙”;另一方面,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和进程的影响因素众多,而且这些因素的相对影响程度可能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许多进城农民无法承担过高的市民化个人成本而成为城市的边缘阶层,造成了“伪市民化现象”。只有当进城农民在经济、社会保障、社会文化、政治权利等众多方面具备基础,特别是逐渐取消附加在户籍上面的机会、权利等方面的不公平,才可能真正实现市民化。表3是市民化自感知的分析框架。
行动/互动策略:通过稳定的工作获得较高的经济收入,或通过异地成功创业,外来农业转移人口才能解决工作所在城市的住房问题,并能拥有和当地城镇居民相近的消费水平。
结果:农业转移人口具备了市民化的基本经济条件自我感知的市民化往往比“经济指标测算”出来的市民化更加贴近他们的生活。运用建构扎根理论方法,形成了经济条件、社会保障、社会融合、文化融合、户籍限制、政治权利6个主范畴,理清这些主范畴与25个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构建市民化感知的分析框架。
2.2.6 理论饱和度检验 Charmaz认为“当收集新鲜数据不再能产生新的理论见解时,也不再能揭示核心理论类属新的属性时,理论便趋于饱和”[10]。为了保证研究的信度,本研究采用了以下4个途径检验理论的饱和度:一是利用就业培训中心会议室,召开了2次市民化主题的小型座谈会,每次6人,采用主题讨论方式交流市民化的自我感受;二是与课题组成员研讨,探讨可能遗漏的市民化评价的可能指标;三是进一步深度访谈,再次选择了来自安徽、河南、江西10位农业转移人口新样本,重复撰写备忘录和逐级编码工作,试图找到新的概念或重新划分范畴的依据;四是开展文献研究,主要是利用CNKI中文数据库、EBSCO等外文数据库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或城市融合的相关论文,通过文献研究检验建构的分析框架。最终无法获得新的范畴。至此,认为上述感知市民化的分析框架构建是合理的。
3 结论、讨论和政策建议
3.1 结论
运用建构扎根理论方法,构建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感知的分析框架,包括经济条件、社会保障、社会融合、文化融合、户籍限制、政治权利6个维度的25个条目,具体分别是:(1)经济条件主要包括经济收入、消费水平和住房条件3个条目;(2)社会保障包括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社会扶贫救助、就业培训等6个方面;(3)社会融合主要包括志愿者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活动、建立和谐邻里关系、拥有与城市人相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5个方面;(4)文化融合主要包括方言、风俗习惯、交当地朋友和休闲娱乐方式等4个方面;(5)户籍限制主要包括子女教育、购房消费、平等享受公共服务设施3个方面;(6)政治权利主要包括选举权、被选举权、信访或申诉、表达社情民意4个方面。
本研究的可能贡献在于从自我感知角度探讨了市民化判定问题,有效地弥补了单纯通过计量经济模型和统计数据评价市民化程度存在的不足,即主张在“他评”的同时还应该由农业转移人口“自评”市民化程度,这也是对“以人为核心”新型城镇化的补充诠释。本研究构建的分析框架,提供了新的市民化判定分析框架。
3.2 讨论
对比近5年同类主题典型文献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市民化“自评”在维度、条目和权重等方面与现有市民化“他评”的研究结论存在较大的差异,具体如表5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在经济指标维度,进城农民除了关注收入和住房2个方面外,对“是否拥有城镇居民相当的消费水平”同样有诉求,这意味着进城农民不再满足于基本的生存,而是追求消费能力基础上的生活质量。社会保障共6个条目,反映了进城农民多方面的社会保障诉求,这也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追求目标;社会融合和文化融合2个维度中有许多“软性指标”,一方面很难用现有计量模型和统计数据衡量,另一方面这些指标在地区和个体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但却是“留得住、过得好”的重要“自评”维度;政治权利成为是否真正市民化感知的独立维度,说明新型城镇化推进中需要逐步关注进城农民的社会治理与社区管理的参与程度。可以看出,自我感知的市民化分析框架在衡量维度、测量条目方面与现有“客观指标”评价方法既有相同的方面、也有不同的地方,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对市民化评价的有益补充,也为下一步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
3.3 政策建议
由于地区社会经济的不平衡,市民化进程的速度和程度也会存在差异。根据市民化自我感知的分析框架, 需要优先典型文献 研究方法 主要观点与结论张建丽等[14] 修正了C-D函数的市民化进程模型,添加了外部环境因素,通过问卷调查获得一手数据进行测量 外部环境包括制度环境和市民的社会认同接纳2个条目,此外用7个条目测量市民化意愿,用5个条目测量市民化能力张斐[15] 在文献研究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分析体系,采用等权重设计,通过问卷调查获得一手数据进行测量 从经济因素(包括收入、居住条件、社会保障、职业状况);社会因素(普通话);心理因素(身份认同、未来定居意向)3个维度评价周密等[16] 采用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测算沈阳、余姚两地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并分析了差异的影响因素 以需求为因变量,以外出务工目的、社会网络高度、人力资本、社会网络结构、收入满意度等为主变量,通过回归分析测算出两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市民化程度为73%王晓丽[17] 利用2011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熵值法对市民化程度的相关维度进行赋权,测度城乡流动人口的市民化程度 构建由市民化意愿、市民化能力、市民化行为、居住市民化、基本社会公共服务市民化5个维度的市民化指标体系,测度城镇化率与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差距,以此修正城镇化水平魏后凯等[18] 利用统计年鉴和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数据,测算中国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 从政治权利、公共服务、经济生活条件、综合文化素质4个方面构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综合指数,测算出2011年中国市民化综合指数为39.56%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解决进城农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从表3可以看出,进城农民在经济方面除了首要关注收入和住房2个方面外,对“是否拥有城镇居民相当的消费水平”同样存在诉求。这一方面要求通过政策性住房、租房措施逐步解决进城农民的住房问题;另一方面除了生存型安置外,还要解决进城农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当前,留地安置政策让农民实现了“带着财产权进城上楼”,能够延续农地的资产性收入;不过,由于农地数量较少,农地的资产性不足以解决进城后的发展,还需要特别重视拆迁安置后农民的就业创业问题,从根本上解决进城农民可持续的预期经济收入。
(2)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由表3可以看出,市民化的社会保障呈现多元并重的特点,虽然绝大部分地区已经构建了进城农民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甚至将部分农地非农化增值收益作为专项社会保障资金,但不可否认给进城农民的社会保障仍维持在基本生存水平,与当地城镇居民之间还存在身份差异,特大城市对进城农民的“就业吸纳、保障排斥”的格局还没有完全打破。此外,嵌入户籍制度的社会福利并没有完全剥离,一些中小城市对进城农民子女教育还存在户籍上的歧视,把进城农民平等地纳入当地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城镇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挑战。
(3)促进城镇农村文化交融,增强进城农民的城市归属感。表3显示文化融合是影响自我感知市民化的重要影响因素,需要满足城镇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不同的文化诉求,规避一些地区“赶超式”城镇化导致城市文化、农村文化和城乡文化的断裂[19]。中国快速的城镇化决定了城市是包容性文化的容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伴随着市民化的进程需要相容相通,这需要柔性的、非正式制度式的文化自由式演进;同时,政府还需要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公共文化产品,通过刚性的、正式制度式的政府主导式文化演进,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4)增进农业转移人口与当地城镇人口的社区生活交流。表3说明社会融合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测度的“软指标”,尽管这很难用现有的计量模型和统计指标进行测量。由于语言、文化、生活方式的隔阂,使得他们在社区与当地城镇居民无形中保持着心理距离,形成隔离于当地城鎮主流群体的边缘群体。就业是进城农民工作的主要载体,而社区是进城农民生活的主要载体,需要将进城农民纳入社区的党建、卫生、物业、各项普查、计划生育、治安综合治理、群众文化体育活动等日常管理,为进城农民提供细致的生活服务,消除进城农民与当地城镇居民之间的无影隔阂,才能让进城农民真正感受到成为当地的新市民。
(5)兼顾进城农民潜在的政治权利诉求。一些文献关注到了进城农民的政治权利,但这种诉求不仅停留在是否参加工会、党员组织等方面,而且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逐步满足进城农民“信访、申诉、社情民意表达”等参政议政方面的潜在需求,增强新市民化社会治理的参与意识,不仅是民主政治的要求,也有助于真正吸纳新市民化的城市融合。此外,政治权利的保障能够提升进城农民的社会地位,不仅有助提高财产和人身的安全感,而且有助于市民化后获得新的社会资本,增强城市的主人翁地位。
参考文献:
[1]Rise J,Sheeran P.The role of self-identity i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a Meta-analysis[J].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2010(40),5:1085-1105.
[2]何雪松,楼玮群,赵 环. 服务使用与社会融合:香港新移民的一项探索性研究[J]. 人口与发展,2009(5):71-78.
[3]Lu G X. The social distance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migrant workers: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08(8):172-186.
[4]吕 佳,陈万明.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测量指标体系构建[J]. 江苏农业科学,2014,42(12):478-480.
[5]刘传江,程建林,等. 第二化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J]. 人口研究,2008(9):48-57.
[6]徐建玲.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度量: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2008(9):65-70.
[7]沈映春,王泽强,焦 婕,等. 北京市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J]. 北京社会科学,2013(5):138-143.
[8]Shahsk K,Corley K G. Building better theory by bridging the quantitative-qualitative divid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06,43(8):1825-1835.
[9]Mills J,Bonner A,Francis K. The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vist grounded theor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2008,5(1):25-35.
[10]Charmaz K. 建构扎根理论:质性研究实践指南[M]. 边国英,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3.
[11]Getz D. Event tourism:Definition,evolution,and research[J]. Tourism Management,2008,29(3):403-428.
[12]Glaser B,Holton J. The grounded theory seminar reader[M]. Mill Valley:Sociology Press,2007.
[13]胡鞍钢,马 伟. 现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从二元结构到四元结构[J]. 清华大学学报,2012(1):16-29.
[14]张建丽,李雪铭,张 力. 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与空间分异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82-88.
[15]张 斐. 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 人口研究,2011(6):100-109.
[16]周 密,张广胜,黄 利.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测度[J]. 农业技術经济,2012(1):90-98.
[17]王晓丽. 从市民化角度修正中国城镇化水平[J]. 中国人口科学,2013(5):87-95.
[18]魏后凯,苏红键. 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2013(5):21-29.
[19]蔡瑞林,陈万明. 城镇化进程中文化的断裂与传承[J]. 中州学刊,2014(11):111-116.王 翠,刘世洪,刘 伟,等. 农业高新技术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 江苏农业科学,2019,47(15):32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