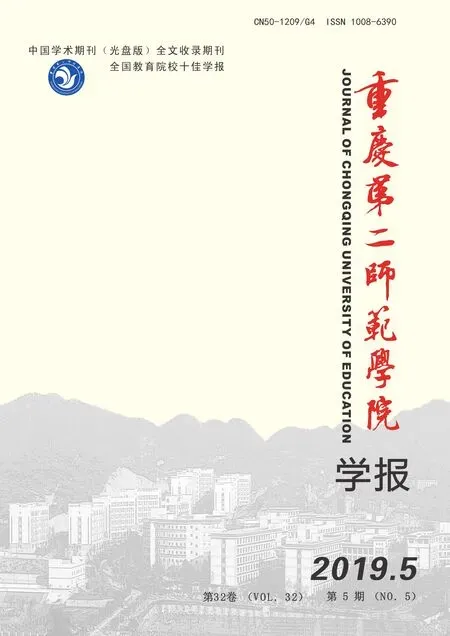张素含《蜀程纪略》的历史地理价值探析
赵成智, 石令奇
(西南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所, 重庆 400715)
道光甲申年(1824年),张素含受四川隆昌令张莘田之邀,在子侄陪同下,前往隆昌执教。在2000余公里的漫长路途中,张素含写下3万余字的《蜀程纪略》(含诗作137首),著成我国纪游文学史上的名篇。由于张素含仕途不显,清代及后世的史料中关于他的生平和著作未见记载,唯有《蜀程纪略》手抄本流传下来,在1991年由枣庄市峄城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并加以注释,集成《峄城文史资料》第四期《蜀程纪略》,引起了学术界一定程度的关注。其中,孙天胜《中国纪游文学史上的杰作——张素含〈蜀程纪略〉的文史价值》主要是从文学的体例出发探索书中的文史价值,任婷《清代四川游记的地理认知研究》也将此书作为重点考察对象,但这两篇文章对此书历史地理学价值的揭示和发掘尚存在余地。笔者不揣浅陋,将地方史志与《蜀程纪略》的相关记述加以比勘,进而揭示此书的历史地理学价值,以就教于方家。
一、张素含入蜀及其对蜀地山水的情感体验
(一)张素含入蜀缘由与《蜀程纪略》的写作
张素含,字霜三,清嘉庆至道光间山东峄县(今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左庄乡)人。或因其仕途不扬,清代官方文献中关于张氏的记载很少,但从《蜀程纪略》的记述中大致可以推断出他生活的主要时期。《蜀程纪略》开篇记载:“道光甲申年间,族弟莘田为四川隆昌令。诸侄随仕,课读无人。十月初,有书来招。天寒道远,颇费踌躇。而万里人来,又难令空返。不得已,于月之二十八日启程。”[1]1这里所说的“族弟莘田”,据《峄县志》记载:“张聘三,字莘田,敬恒季弟。嘉庆初,援例授知县。十年,补四川隆昌县,旋擢打箭炉同知。在任十年,民夷便之。以积劳迁龙安府署盐茶道篆。前后在川盖四十余年。”[2]590正是由于族弟张莘田的邀请,才成就了张素含这部《蜀程纪略》。以现今的眼光看,《蜀程纪略》保存还算完整,体例与文笔皆堪称上乘,故在清代纪游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蜀程纪略》共3万余字,其中包含诗作137首,书中多处出现里程数、地名、名人故里、题刻文迹、怪石奇峰、仙踪奇异、物产异俗等,是研究沿途历史自然与人文地理的重要史料。此外,张素含自宝鸡进入陈仓道,经凤县入连云栈道进入留坝县,再由褒斜道出褒城进入金牛道,自宁强一路南下进入成都后辗转到达四川隆昌,从中也可考察张素含由陕入川的交通路线,为研究清代蜀道交通地理提供了史料支撑。
(二)张素含对蜀地山水的情感体验
巴山蜀水位居西南一隅,由于山高谷深、丛林密布等自然因素,巴蜀地区一直以来与外界相对隔绝,故时人曾感叹:“天下已治蜀后治,天下未乱蜀先乱。”[3]613张素含生平初次入蜀,对蜀地高耸入云的山峰、阴森可怖的森林都感到心有余悸。刚入蜀地,张素含即写下“森森古木噪归鸦,一步栈云一忆家。山到七盘犹北望,不知身已在三巴”[1]114的诗句。张氏对于蜀山的感知不出山形险峻、形如削出、鸟道斜盘、凡历七曲折等意象,甚至借用岑参诗句“平生驱驷马,旷然出五盘。江回双岸斗,日出万峰攒”[1]115来描绘蜀山之巍峨险峻。
张素含对蜀水的描写较为细致,他在行至筹笔驿处记载:“近视之,水色深黑,令人望而却步。”[1]117可见,张素含起初对巴蜀之地并没有多少好感,反而对于蜀地的自然风貌心生恐惧。因此,张素含入蜀初期对蜀地的感知无外乎人烟稀少、深山老林,而在其诗中也多用野店、老树、山深、寒泉、冷杵等意象,借此抒发内心的孤寂和恐惧。如《益昌怀何易于》:“城临鸟道人烟少,地接蚕丛虎豹多。”[1]128再如《泛嘉陵江》:“寒猿三咽征夫老,杜宇一声岭树愁。八曲渝歌听不得,初春风物似深秋。”[1]121
李白有诗云:“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4]65历史上蜀地道路崎岖兜转,虽有蜀道可供行走,但其路途凶险坎坷,令人望而却步,这一情形在张素含的笔下也多有反映。他曾写道:“进入石牛道,路随涧转。涧旁多十里香。枝叶交荫,纷垂涧底。水穿石窦,淅沥有声。人行涧侧,坎腻油滑,螺盘垒转,十分曲折。”[1]134此外,张素含还借用杜甫的诗句“人渐番夷杂,梯犹碧落通”[1]116将蜀道之险刻画得极具画面感。
不过,在摆脱初临蜀地的惊恐后,张素含渐渐适应了蜀地的自然气候和地理风貌,其诗文风格也由原本的沉郁变为明快,开始对蜀山、蜀水、蜀道产生流连忘返之感。如他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奇景难再逢,欲去频回盼”[1]120,“人云蜀道难,我云蜀道易。眼孔放开时,险巇皆平地。初历金牛峡,已惬寻幽意。渐入剑门峰,云水滴苍翠。一鞭细雨中,心胆了无悸。无须羡王尊,叱驭浑闲事”[1]148。在行至魏城驿时,张素含不由喟叹魏城烟火稠密,山水秀美;过绵州时,他感叹此地水净沙明,一碧万顷,到处鱼鳞晒日,水荇牵风。由此观之,在这期间张素含已经被蜀地秀美的风光所吸引,由衷发出“江村风物、尤觉宜人”的感慨,并赞扬蜀地烟火数家,不啻当世武陵,竟产生徘徊不忍去的想法。除记录对蜀山、蜀水、蜀道的体验外,张素含还记录了蜀中的美食。如他在书中曾写道:“(昭化)县南有丙穴,每二三月有鱼,长八九寸,从山穴流出,味极美。”[1]129
二、张素含《蜀程纪略》的历史地理价值
(一)有关交通地理的考察与认识
1.交通路线
纪游文学一般采用日记形式记录沿途的见闻,张素含在《蜀程纪略》中却并未直接载明具体日期,而是以里程作为行程的记录。据考察,张素含入川路线如下:峄城—柳泉—徐州—砀山—商丘—宁陵—睢县—开封—郑州—巩县—洛阳—新安—渑池—灵宝—潼关—渭南—临潼—西安—咸阳—马嵬—武功—岐山—宝鸡—凤县—留坝—褒城—勉县—宁强—广元—剑阁—梓潼—绵阳—德阳—新都—成都—简阳—资阳—内江—隆昌。其中,西安至成都这段路程,张素含翻越了秦蜀古道的陈仓、连云栈道、褒斜、金牛,并记录其亲历蜀道的心境。如经过褒斜道:“二十里,二十里铺,褒斜谷口,武侯由斜谷取郿即此。十五里,青桥铺。自青桥铺至此,俗谓二十四道马鞍桥。冈峦起伏,经二十四上下,皆内依绝壁,外临黑龙江(褒水的别称)。肩舆翻掀,惴惴有春冰之恐。”[1]92经过栈道:“二十里,阎王碥,一名麻坪寺,系云栈中第一险阻。路盘山腰,上逼危崖,下临黑龙江,人马踏石棱上,石缺处架木补之”[1]94,“过鸡头关,即出北栈。烟开云敛,一望平原,觉神界忽敞,别有天地。忆自宝鸡入栈以来,不下六百里,高者入青天,下者入无地”[1]100,“出沔县西门二里许,又入南栈。道旁有坊,题曰‘重入云栈’”[1]106。过金牛道:“出大木戌西行里许,入石牛道,路随涧转……人行涧侧,坎腻油滑,螺盘垒转,十分曲折。”[1]134可见,张素含对蜀道的描写多为山随路转、路似羊肠、内逼危崖、外临大涧,这既表明了道路的险峻,也表明了作者对于蜀道交通的心悸。
2.交通工具
正如前文所述,蜀道崎岖险远,加之张素含一行人员和行李较多,马车当为首选,并且峄城至长安这一段路程较川陕道路相对平坦宽阔,适合车马通行,从陕西入蜀的道路狭窄崎岖,并不适合车马行走。对此,《蜀程纪略》记载:“出长安西行,路不容车,由此,舍车易肩舆。”[1]45张素含自陕入川始,肩舆一词多次在文中出现,如“肩舆入褒斜,人行白云上。乱山插翠微,势欲与天抗。岩径仅如丝,石顽不肯让……”[1]90,再如“危绝阎王碥,肩舆几倒翻。千盘走蚁磨,一线转云根”[1]95,又如“冈峦起伏,经二十四上下,皆内依绝壁,外临黑龙江(褒水的别称)。肩舆翻掀,惴惴有春冰之恐”[1]92。这里的肩舆应该是其后发展为四川地区特色交通工具的滑竿,肩舆比传统的车轿底盘高,能很好地适应四川崎岖的地形,且其制作简便,大路小径皆可通行,因此在四川山区使用较多。此外,为了适应四川交通路线的需要,张素含也不得不临时更换交通工具,如行至朝天镇时,“由此买棹嘉陵,顺流而西,绿水三蒿。青山满眼,较之云栈蹉跌,劳逸不啻霄壤”[1]120。再如“出广元,水程迂远,兼有紫石挂溪,恶滩险阻难行,复舍舟易肩舆。数里外,又入大涧”[1]127。在山路颠簸之余,张素含对于嘉陵水道亦有别致的体验。从《蜀程纪略》的记载可见,张素含自陕至川一路行来不断变换交通工具,由马车换乘肩舆,由肩舆换乘舟棹,再由舟棹换乘肩舆,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其入蜀的艰辛。
(二)有关历史自然地理的考述
1.对隆昌气候的考察
在我国历史上,明清时期气候较为寒冷,学界称之为“明清小冰期”“明清宇宙期”等。即便如此,一些地区的小气候依然逆大势存在。且看张素含对四川隆昌气候的记载:“(隆昌)冬无严寒,夏实酷暑,聚蚊成雷,夜不能寝,兼之地近漏天,多雨少晴,尤令人郁郁不乐。按:大漏天在雅州,小漏天在叙州。所谓漏天者,即山壁之大石穴也。云兴即雨。每夏秋间一月仅晴得三五日耳。地多水田,其谷宜稻。无霜、雪、冰、雹,树叶四时不凋。且节气尤早,豌豆、芥子皆十一月开花,麦子正月秀穗。虽仲冬之月,山花满涧,宛似三春光景。”[1]175可见,清代中后期四川隆昌多雨少晴,气候湿热,以至于树叶四时不凋,即使寒冷的天气,仍旧花草繁茂,这明显与“明清小冰期”的气候大势相背离。事实上,检阅明清诸多地方志和相关文献可知,这一时期四川很多地区都有关于大雪的记载。如《灌县志》载:“(乾隆五十一年)冬十月十二日两日并见五十二日大雪。”[5]419从热带作物种植线的南移和标志性植物荔枝的灭绝不难看出,明清时期的寒冷气候确实对四川地区影响深远,但据张素含的记载,隆昌似乎是个例外,值得关注。
2.对动植物的记述
关于大熊猫等的记载。清代四川地区在经历了众多战乱以及官方的“黄木采办”“乾嘉垦殖”之后,尽管森林覆盖率有所降低,但并未达到毁灭的程度,巴蜀地区仍然被“森森古木”所覆盖。蓝勇教授在对长江三峡历史地理的长期研究中发现:“明清时期直到民国,三峡地区野生鹿科动物分布依旧很广,主要种类有鹿、麂、獐、麝、麋、麑、麅等。”[6]43张素含《蜀程纪略》对蜀地动植物的记述与蓝勇教授的论断可以相互印证。如张素含记其在隆昌地区的见闻:“兽有虎,有鹿,有猴,有獐,有麅,有水獭,有羚羊,其最著猱。出夔州府,深山中好食生铁。近山居民,昏夜稍不戒,釜甑辄被食去。”[1]178这种“深山中好食生铁”的动物应为大熊猫。清代中后期长江三峡地区确实存在野生大熊猫,蓝勇教授经过考证认为:“历史上长江三峡气候温暖湿润,森林茂盛,甚至生活着野生印度犀、独角犀、亚洲象和大熊猫等珍稀动物。”[6]42大熊猫好食生铁的特性也多见于历史文献,《史记》卷一百一十七郭璞云:“敠,白豹也,似熊,庳脚锐头,骨无髓,食铜铁。音陌。犛音貍,又音茅,或以为猫牛。犛牛黑色,出西南徼外,毛可为拂是也。”[7]3025据此推断,清代中后期四川夔州府确有野生大熊猫出没,而从“昏夜稍不戒,釜甑辄被食去”的记载也不难看出,清代四川地区森林遭到大量砍伐后,大型动物领地缩减,时常与人类发生冲突。
关于松鼠、猿以及吐绶鸟的记载。《蜀程纪略》云:“二十五里,黄沙店。有‘仙留胜地’坊,相传青衣道士居此。其地产松鼠,状似田鼠而小,尾大如身,穴居树上,食松子,饮松间之露。”[1]103《广元道中》诗云:“浓纤螺翠沾衣湿,断续猿声隔水闻。笑指山腰谁结舍,樵歌起处犬争狺。”[1]127值得一提的是,张素含在经过汉州州南所见到的吐绶鸟:“(铜官山)其地有吐绶鸟,一名吐绶鸡,状如雄鸡而趾高,身褐色,顶有绿毛,顶下一嗉,无毛,色如霁蓝,晶莹可爱。每日天和则向日吐五色丝团,荣光夺目,须臾吞之,吞则复吞。真珍禽也。”[1]158吐绶鸟,又名角鸡,也称黄腹角雉,常年生活在湿润温暖的亚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和针叶阔叶混交林中。历史上四川地区吐绶鸟较多,文献中多有记载。清人黄廷桂在《(雍正)四川通志》载:“(夔州府)吐绶鸟,大如而五色可爱。”[8]246如今,吐绶鸟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浙江、湖南、江西等地,四川地区已经很难见到。
关于蜀地植物的记载。《蜀程纪略》云:“草木唯荔枝、橘柚、橄榄之属最多。山木唯桤树、枇杷、棕榈、马尾松之类最多。山果无枣无楂,六畜无驴,五毒无蝎子,草虫无蚰子。按:荔枝,唯涪州者最佳。昔杨贵妃酷嗜荔枝,由子午谷七昼夜至长安,即涪州荔枝也。花有僧鞋菊,开当九月,花蓝色,酷肖僧鞋。有铁树,独干无枝,叶如凤毛,花似鸭脚,开必成攒,每攒朵七,自下而上,开至四十九朵而止。有映山红,色似榴花,叶类月季。夏秋之交红遍山谷,尤为可爱。有茶花,花似牡丹,叶类耐冬花,开当严寒,弥觉娇艳,颓垣蔓草间处处有之。其余若丹桂、杜鹃、兰蕙之属,不可枚举。又有草名蛤蟆叶,好生厕处,叶如秋海棠,叶之反正皆有芒,一着肌肤,立即疼肿。”[1]178此处所述之蛤蟆叶,学名车前草,一年生草本植物,叶和子均可入药。据药典记载:“车前子,性味,味甘,性寒,无毒。”[9]479据此可知,任婷《清代四川游记的地理认知研究》所述“通过张献忠被蛤蟆叶所误伤,立志对此草斩草除根的这件趣事,描写了这种植物的有毒性质”[10]21,将蛤蟆叶列入有毒性植物不确,张献忠应为叶芒所伤,并非中毒。
3.对异虫、异鸟的记录
关于红毛蜈蚣的记载。四川隆昌湿热的气候适宜毒虫生长,据《蜀程纪略》所载,张素含在隆昌执教过程中就曾与红毛蜈蚣遭遇:“春仲,偕诸侄读书于禹王宫,更定后,阶下忽起金光一线,长数丈,复荧荧作碧绿色。诸侄大骇,急燃灯照之,有虫状如蚯蚓而有毛,其行甚骤,所过之地有流光。有寺僧见之,吐舌曰:‘此红毛蜈蚣也。’其物最毒,园中菽菜及厨中食物一经行过,食者辄毙。岁久者,雷必击之。毛乃其足,光则其毒也。热之以火,火光皆作绿色。”[1]177-178又载:“地多异虫。有亮虾,尾际有光,状如萤火。每月朗风清,澄波涟漪之际,望之如渔火、星星,晶莹可爱。”[1]177
关于鸟类的记载。清代四川地区鸟类品种繁多,张素含《蜀程纪略》中记述了杜鹃、桐花凤、相思鸟、竹鸡、点灯鸟、九头鸟、洋雀等的生活习性、形态特征、相关传说等。如:“隆邑多异鸟。有杜鹃,状似春莺而喙直。云是望帝之魂所化,其音云‘不如归去’。鸣则眼中滴血,雌雄相应音节最惨,集必拣最高枝,悲极则倒挂于树。群鸟环而哺之,犹有君臣之分焉。有桐花凤……有相思鸟,状如黄豆雀,爪嘴皆淡红色,生有定偶,两两相随,仿佛鸳鸯。有竹鸡,状如雌鸡而小,善斗,喜居翠竹中,鸣则‘呼呢滑滑’。又有鸟,名点灯,捉哈蚤,状如鸠,而趾高,毛黑色,黑夜鸣不休。相传者,有夫妇为蚤所苦,呼夫点灯,捉之。时久雨屋颓,夫妇压毙,遂化为鸟,飞则相随,鸣则相应。乍听之,若令人可笑;细聆之,又令人可怜。隆邑间有之,富德尤多。有九头鸟,一身而九头,每夜半至,如群雁齐鸣,当中一首流血,见之者以为不祥。川人闻声,必击铜器,惊之远扬。院宇稍留血迹,其家必有奇祸。有洋雀,状类画眉而大,翠羽黑眉,比鹦鹉尤为鲜洁。其余若翡翠、文雉、画眉、白头翁之类,尤不可枚举。”[1]177
4.对盐井和油井的叙述
清代四川井盐生产与前代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盐铁官营的桎梏有所松动,清初井盐业任人自由开凿,故井盐成为四川民间的自有产业,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蜀程纪略》记载了四川石桥井(今四川简阳西北石桥镇)的采盐工艺:“百二十里,石桥井,其地有盐井。井孔仅能容拳,深二三十丈,及四五十丈不等。以竹去节,入井中,牵挽顷时,始得水一桶,以火熬之即成盐。穿井时,先从宽处取势,数尺后,露出巨石,然后用铁锥一柄,上搭木架,用绳提冲,所有石渣,以铁爪抓之,再冲再抓,计得一井,亦不知费几万缗矣。”[1]171这种借用重力惯性提冲的方法较为原始,不但效率低下而且资费沉重。因此,按照就地取材的原则,一般盐井会顺势选在离“火井”较近的位置。因为四川地区处于板块断裂带上,山体内部不稳定,地表会形成裂缝,而地表下层的矿产资源往往会裸露出来。《蜀程纪略》记载:“邑有火井在城南九十里,其地名‘自流井’。孔方圆五六寸,深四五丈。井气如雾,沸沸上腾,以火引之,火焰顿起。相连有盐井。若熬盐、以泥作锅,腔旁留数小孔,以竹去节,吞孔中,使火从竹筒中引去,四周遍支盐灶,火根离竹寸许,甚细,至外渐大,光芒倍如常火。如不用,以水泼之即灭。最可异者,火从竹出,竹筒冷而不焦,若用泡皮装之,以针刺孔,作作有芒,数千里外皆可装去。相连又有油井,只可燃灯,不可烹调。可见天地之大,无物不有。”[1]175这里的“井气”是地下某种可燃气体,应为天然气。清代丁宝桢《四川盐法志》中也有“火井”的相关记载:“(富顺县)火井一在县西九十里,井深四五丈,圆径五六寸,有气上腾,以竹去节入井,投火引之即发。”[11]130-131此处的“油井”只可燃灯不可食用,说明了该地曾出产石油。

表1 《蜀程纪略》所涉巴蜀地区动植物、矿产一览表
(三)对巴蜀文化地理的认知
獠人作为清代巴蜀地区的特殊群体,张素含《蜀程纪略》多有记载:“百四十里,资州,系周大夫苌弘故里。州界荒夷,汉苗杂处。地有獠人,巢居岩谷,因险凭高,号曰阁阑。男则蓬头跣足,女则椎髻穿耳,以生处山水为姓名。又有濮夷,尻际有尾,长二寸许,若损其尾,则立毙。常于树上作屋,若偶地上居,则预穴以安其尾。夫死,妇不归家,亲死不葬,用柳棺置之山坎,听其骨化魂消而已。”[1]174此处所载“濮夷”应该是獠人的一种,都是指生活在山林之中的异族。獠人生活在树上的原因,有关学者曾做过论证,如鲜于煌认为“三峡地区的少数民族‘獠人’还在树上‘巢居’以避群害”[12]191。獠人部落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中形成了本民族独有的生活习性和民族信仰,汉獠之间也常发生冲突。如《四川通志》载:“刘信,南溪人,历官广西,恭政有廉名,獠人叛,信讨之,亲冒矢石遂死于阵。”[8]519又如:“牟葢,长宁人。嘉祐初,獠人谋内宼,葢引兵趋之,捕斩七千余级。铃辖司上闻诏,赐钱钞三十万,并锦袍银带,寻为本州刺史。”[8]369
西南地区自古就有“信巫鬼,重淫祀”的传统,这也是中国南方民族的群体特征。蓝勇教授《西南历史文化地理》一书就对西南地区民间信仰有所考述,认为“西南地区各民族信鬼神和重淫祀的传统与荆楚民族的影响和相同的自然环境有关,因楚地自古便有信鬼好巫之称”[13]181。张素含在隆昌的见闻也说明了这一点:“(隆昌)其邑南界黔省,西接番夷,汉苗杂处,巫觋成风。男覆白巾,女赤下体,顽梗尤为难化。”[1]175此外,蓝勇教授通过对西南地区风俗的考释认为明清时期西南民间城隍庙、土地神之类的神祀十分盛行[13]187。张素含对巴蜀地区土地信仰的记述较为翔实,他不但记述了某种风俗仪式,而且体现了地理差异,如“巴俗最敬土地,隆昌尤甚。凡塑土地皆戴纱帽,不知是何取意。且祠前旗杆有竖千余根者,问之土人云:‘巴蜀土地最灵,凡有祈祷者,须杀雄鸡一只,用鸡血粘鸡毛一撮,糊入壁上,还愿时,竖旗杆一小对。’适有新建土地小祠,祠颇修洁,像亦成趣,祠外旗杆如猥毛,祠前鸡血满墙,祠内欣喜欲狂”[1]176。
三、结语
张素含的《蜀程纪略》对川陕地区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等方面进行了探求与考察,记录了许多珍贵的地理信息和情感体验。《蜀程纪略》关于巴蜀地区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的记述,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史、方志等的不足。此外,《蜀程纪略》这类游记所记录的内容大都为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这种近乎田野考察方式的记录也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因为考察记录较为真实,能大致反映某一时期的地理概貌。因此,考察清代游记的历史地理价值对于揭示这一时期的区域历史地理问题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