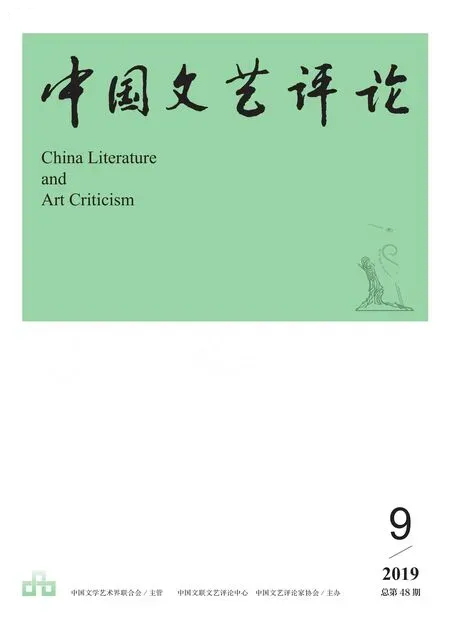王国维“境界”说的理论结构与审美精神转向
刘发开
“境界”说作为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意蕴丰厚的核心观点,也是一个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创造性美学范畴,对其内涵的发掘和阐释历来聚讼纷纭。笔者不揣浅陋,从王国维“境界”说所蕴含的“真”与“实”的审美基质、“不隔”与“不代”的审美尺度、“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审美境界、“众芳芜秽”与“以血书者”的审美旨归等四个维度,对其美学意蕴的整体结构作出探析与辨识,并考察“境界”说蕴含的审美精神转向、时代意义及其对当代中国美学和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构建的镜鉴价值。
一、“真”与“实”的审美基质
《人间词话》第一则即提出:“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在王氏看来,词的格调高低取决于有无境界,而境界之有无,最为关键之处即在于其是否体现了“真”、达到了“真”。王国维之所以如此标举“境界”、崇尚“真”,是因为在中国传统美学和文论发展历程中,“真”在很长历史时段内是被遮蔽的、隐而不彰的。尽管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以诗为宗,甚而将诗神化,却一度淡忘了“真”这个最基本也最紧要的审美基质。“真”的意涵至少有三个层面。首先,“真”是一种“真性情”,是人之性情的本质,尤其是天才性情的本质。王国维在《叔本华与尼采》一文中借叔本华的天才论,反复强调天才乃是“不失赤子之心”的一类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可以将赤子与天才的称谓互换,即凡天才皆赤子、凡赤子皆天才。王国维在此标举的“赤子之心”相当于李贽标榜的绝假纯真之“童心”,他认为人的本质是真,倘若涉世被染则假,故“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给予李后主、纳兰性德以极高评价,在他看来,李后主和纳兰性德生长于深宫大院,均未涉世过深而被尘世污泥浊水所染,反而成为“能写真景物真性情”的基础和条件。二人的共同之处正在于保存了这个“真”,所谓“阅世贵真、境界贵深”是也。

再次,“真”还是一种“真功夫”,即对“真景物”“真感情”鲜明真切的传达功夫,往往表现为对审美对象的传神描写。作者具有了天才式的“赤子之心”,观物写景都投注真挚的感情,而若不能具备恰切的传达和表现功夫,不能对审美对象进行传神的描写,则将文不逮意,亦不能有真境界。王国维对如下两句诗推崇备至:“‘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前句中的“闹”字,将明媚春光下红杏枝头花团锦簇、竞相绽放的景象活灵活现地描绘出来,也将游人踏春的兴致充分传递和激发出来;后句中的“弄”字,则将月光倾泻、花影婆娑的清幽之境和作者舒闲散淡的生活情趣点染得极为恰切而传神,故能“境界全出”。再如他称周邦彦的“叶上初阳干宿雨, 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深得“荷之神理”,也是从对审美对象的传神描写中感而言之的。可见,有了“真景物”“真感情”还不够,还要有真切传神的描绘与传达的“真功夫”,如此才能达到“写真”“体真”与“传真”的统一,这是境界之有无与高低的关键要素。
再来看“实”。诗人对宇宙人生“入乎其内”,其实就是去深入体验那些有关我们自身生存和外界生命的真实际遇,从而将客观事物作为一种受审美主体精神浸染的、非对象化的实体来看待。具体而言,“实”又包含两层内涵:其一,是创作者的“忠实”。《人间词话》云:“词人之忠实,不独对人事宜然,即对一草一木,亦须有忠实之意,否则所谓游词也。”王国维认为一个词人首先要做到对生命的忠实,这里的生命不单指人的生命,而是对人事尤其对一草一木都要忠实,即以仁爱忠厚之心对待自然万物;并且纵使人事变幻、草木枯荣,对这种生命的无常性也要热爱,也要忠实。中国当代诗人海子在表达对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热爱时,曾提到有这么两类抒情诗人:“第一种诗人,他热爱生命,但他热爱的是生命中的自我,他认为生命可能只是自我的官能的抽搐和内分泌。而另一类诗人,虽然只热爱风景,热爱景色,热爱冬天的朝霞和晚霞,但他所热爱的是景色中的灵魂,是风景中大生命的呼吸。”王国维在此格外提出对“人事”的忠实,特别是对“一草一木”的忠实,实际上也是要求词人对人类和大自然的秘密的热爱,对自然景物的生命、呼吸和灵魂的热爱和忠实。
其二,“实”还意指一种“实境”。王国维在中国传统美学理论基础上,吸收了西方新的美学观念,以创作方法将文艺划分为造境与写境、理想与现实等不同类型,所谓“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在王国维看来,“写境”并非照搬自然和生活,而需对自然和生活中的各种“关系、限制之处”加以扬弃和突破,以审美理想加以甄选、提炼和改造;而“造境”也并非随意编造、杜撰和捏合,而需遵循艺术规律和自然规律。因而,在大诗人那里,“写境”必是“邻于理想”,而“造境”则“合乎自然”,二者又颇难区分,二者的融合正体现了艺术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内在统一性,蕴含着造境与写境、理想与现实的辩证法。
二、“不隔”与“不代”的审美尺度
王国维在评价前代词人词作时,史无前例地提出了“隔”与“不隔”“代”与“不代”两组概念,可视为两种审美尺度。他列举了姜白石的数句写景之词,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等,指出这些写景之作“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并指出“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王国维在此敏锐地指出了词人“写景之病”,可谓睥睨千古、一针见血。所谓“如雾里看花”即从读者的心理反应和审美感受视角揭示词人“写景之病”,更易为读者所接受和理解。王氏进而又举例说明“隔”与“不隔”之别,认为“不隔”之诗包括陶、谢、东坡之诗,延年、山谷之诗则在稍“隔”之列;而如“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诗句,以及“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等词,其妙处即“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他还举数例说明何为写情之不隔与写景之不隔,认为不论是写景还是抒情,若能达到“语语都在目前”“语语明白如画”、形象鲜明生动、表达情真意切,便可称为“不隔”。反之,若在创作时感情虚浮夸饰、遣词造句矫揉造作,使读者在欣赏时犹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一头雾水、不知所云,便是所谓的“隔”了。
王国维之所以如此标举“不隔”,是因为中国传统诗词艺术在发展流变过程中,虚饰浮夸之风未泯、美刺投赠之篇盛行、繁冗隶事之文大盛,诗人已经不再切身投入、拥抱和体认生命的本真与存在的真实,而是持一种玩味心理、吟咏姿态“为赋新词强说愁”。如此一来,富于自然生命力的审美理想便沦为脱离于生命本真的不及物的语言游戏。在王国维看来,这种漠视生命本真的诗词艺术显然是偏离诗词审美理想的。正是在此意义上,他对那些“为美刺投赠之篇”“使隶事之句”“用粉饰之字”者甚感哀叹,进而呼唤明澈自然、能引起读者直观或艺术直觉的“不隔”之作。因为只有达到“不隔”的诗词,才能使作者在审美创造中自由地抒发情感,使读者在审美感受和理解中得到充沛舒展的精神愉悦。相反,若用“红雨”“刘郎”等字代指“桃”,用“章台”“霸岸”等字代指“柳”,而非直接说“桃”和“柳”,就不仅会因过于“陌生化”而阻断和破坏读者的审美感受,而且诗词本身也将在这种修辞练习和语言游戏式的陈潭死水中溺身而亡,从中也可窥见中国传统美学和诗词艺术中“隔”的流弊之深。同时,王氏明确提出“词忌用替代字”,并揭示出“代字”的两层意涵:表层上指字词的调换,用一些修饰词、引申词替代词的本义,这样必然导致诗词中语言雕琢、晦涩而非质朴自然,从而阻碍鲜明生动形象的生成,使读者有“雾里看花,终隔一层”之憾;而在深层次上,“代字”却映射到了词人创作的幽暗心理本质,即对事物本来面目和生命本真的漠视与回避,故而在字词调换、词藻堆叠上下功夫,这也反映出作者在创作中的一种心理躲闪或不诚恳。王国维在此并未将“代字”和用典停留在作为一般艺术技巧层面,而是将其提高到如何使文艺作品达到有境界的高度,实属难能可贵。
王国维进一步指出:“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与多数诗论者偏重于标举传统的意蕴深婉曲折的审美风格不同,王国维对清新疏朗、自然真切之作格外倾心。从他对《古诗十九首》“写情如此,方为不隔”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他之所以如此推崇《古诗十九首》,就在于这些诗歌完全是所见所感、直抒胸臆,一切都直接就是情,而不是源于情,不同于后来的“缘情而绮靡”。由此可见,王国维力主“不隔”与“不代”,至少是在两个层面对诗词艺术创作提出了审美尺度:一个是在作品内容层面,要求达到情景之真,即所写之情与所写之景须是真实的、直面事物本来面目和生命本真的;另一个是在艺术表现层面,要求活泼自然、平淡舒朗,摆脱虚饰造作之痕迹和雕琢晦涩之流弊。当然,王国维并不否认传统诗词对含蓄蕴藉的“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的追求,而是将其作为语言层面的遣词造句、诗词表层的总体艺术风貌这两个层次之上的第三个层次,足可见其对传统诗词艺术真谛的深厚传承与切身体味。
事实上,王国维的“不隔”与“不代”审美观不仅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论中的“自然”(庄子)、“风骨”(刘勰)、“直寻”(钟嵘)、“妙悟”(严羽)、“直致”(司空图)、“现量”(王夫之)、“神韵”(王士祯)等诸理论一脉相承,而且充分吸收了西方美学中重视审美直观、艺术直觉作用的美学观念营养,是一种融汇中西的美学范畴和美学标准,体现了继承性与开创性的统一。
三、“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审美境界
从美学角度看,王国维视境界为“文学之本”,认为纯粹的境界是最美的,或者说,境界是纯粹的美的世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第三、四则提出“境界”有“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之分,称“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为有我之境;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则为无我之境。他还对二者的内涵加以阐释,指出“有我之境,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认为“无我之境”乃“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二者分别对应“优美”和“宏壮”。
事实上,作为审美境界的不同层次,“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区别也很明显:首先,在审美主体的观物方式上,“有我之境”采取的是“以我观物”的方式,诗人带着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观照外物,并将其思想情感投射或倾注到外物身上;而“无我之境”采取的是“以物观物”的方式,诗人的感情色彩融化或稀释于外在事物或自然景物之中。其次,在审美客体的外在呈现上,在“有我之境”中,经过“以我观物”的审美关照,所观之物便附着上了诗人浓重的感情色彩,成为诗人情感的寄托物;而在“无我之境”中,经过“以物观物”的审美静观,所观之物则以隐蔽的状态呈现,达到物我不分、陶然相忘的境界。第三,在美感性质的差异上,“有我之境”由于是由动到静的转捩瞬间所得,给人的美感是“宏壮”的;而“无我之境”则是在静中所得,给人的美感是“优美”,二者在审美境界的获得时机与美感属性上有所不同。
关于“优美”和“壮美”的区别,王国维显然受到博克、康德、叔本华等西方美学家的影响,并曾在《〈红楼梦〉评论》中作出具体阐述,此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无我之境”,并非指不附带任何主体个性或主观感情的“无我”,而是指在“我”心中,“无丝毫生活之欲存”,能够保持情感的克制,不作有意的情感宣泄,并且与外物“无利害之关系”,以内心“宁静之状态”沉浸其中,达到物我合一的化境,此时即为“优美之情”。陶渊明《饮酒》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以及元好问《颖亭留别》中的“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即传达了这种淡远心境融于静穆景物之中的境界。这种与物俱化的境界作为一种生命体验,表面上看是对外物的沉浸,实则是主体意识与客体对象之间的界限消解和对外在利害关系的审美超越。从另一角度看,“无我之境”并非完全超脱于生命之外,而是一种对景物有着深刻的生命体验,进而与景物浑然一体,达到物我合一、天人合一、情景合一的审美境界。从西方美学的视角看,这种“无我之境”显然吸收和融汇了康德关于审美判断无利害的思想。在康德那里,审美判断并非从既定概念出发,而只能是主观的,因为美感是一种无利害的快感,“只有对于美的欣赏的愉快是唯一无利害关系的和自由的愉快,因为既没有官能方面的利害感,也没有理性方面的利害感来强迫我们去赞许”。可见这种无利害的生命快感体验是促成“无我之境”的关键。
而所谓“有我之境”,指的是“我”带着欲望和意志观物,写出的作品会黏附实用的、现实利益的色彩,且“此物大不利于吾人”,于是在我的意志与外物之间形成较为强烈的争执和冲突,导致“吾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直到“我”暂时忘却欲望,沉醉于景色之中却不会产生占有景色之欲,或者说直到“我”的意志强力挣脱各种欲求而获得独立之时,一种深切的壮美感才油然而生。这就是“动之静时思之”的含义,其“动”即个体生命欲望与自然发生冲突而引起的争执与波动,而“静时”则是一种于暂时的平静中获得的审美静观状态,进而也体现出审美超越性。冯延巳《鹊踏枝》“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以“我”之“泪眼问花”,看雨横风狂中乱红飞落,字里行间流溢出一种无限惆怅之情、无可奈何之意,“我”的伤春情感在“乱红”飞舞中得到渲染和增强,故是一种“有我之境”。而秦观《踏莎行》“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将日暮春寒、杜鹃啼血之景描绘得甚为深切,这种种“外物”如“孤馆”“杜鹃”“斜阳”,对漂泊蓬转的“我”是一种“大不利”的刺激和强烈的生命体验,从而创造出一种无限凄婉愁苦的悲壮之境界,故而也是一种“有我之境”。
概言之,“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包含了“境界”说审美意蕴中争执与超越的不同层面:一方面,由于生命的欲望和意志得不到满足,造成物我关系的紧张和争执,并在这种生命的紧张和争执之须臾宁静瞬间生发超越性的“壮美之情”;另一方面,审美主体在与审美客体的“物我合一”中获得审美超越,从而达到充满生命意志与生命体验的愉悦和宁静,故而生发“优美之情”。当然,这两种审美境界也并非是截然区分的,王国维曾用“意余于境”和“境多于意”来概括,认为二者虽然时常相互交错、各有偏重,但又不能有所偏废。
四、“众芳芜秽”与“以血书者”的审美旨归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第九则中洞观古今、自许甚高地提出:“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王国维何以断言以沧浪的“兴趣”和阮亭的“神韵”为代表的古代美学文论“犹不过道其面目”?而他随手拈出的“境界”二字又何以能“探其本”?此中似有真意。王国维还提出:“若夫真正之大诗人,则又以人类之感情为其一己之感情。彼其势力充实,不可以已,遂不以发表自己之感情为满足,更进而欲发表人类全体之感情。彼之著作,实为人类全体之喉舌”,这里的“人类之感情”“人类全体”,并非指中国传统美学中基于群体性的悲天悯人的宣告,而是指对生命本真的个体化洞察,即对人类情感之真切、生命之无常与灵魂之苦痛的个体化体认和观照,进而以“一己之感情”体察和担荷“人类全体之感情”。王国维评价南唐中主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古今独赏中主“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二句,只因它的写景抒情绮丽迷幻、愁苦难辨,这正是中国传统美学让人只觉处在一种淡淡的哀愁和莫名的隐忧之中,而难见透彻的真性情、真感情进而折射出人类全体之感情的症结所在。“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二句则不然,因其能传达给读者一种“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强烈感受,不仅忧而复愁,而且痛而及苦,是以一人之喉舌代替“人类全体之喉舌”吐露的心语,是一种对生命本真和灵魂苦痛的深切体验。
在指明后主“不失其赤子之心”,方使词至他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后,王国维进一步指出后主词的真正意义之所在:“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其词“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在王国维看来,后主词之所以能超越前人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即在于它是“以血书者”,达到了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的境界,而这种境界则源于对生命本身的一种赤诚和热诚。王国维在《列子之学说》中指出:“释迦、耶稣等等常抱一种热诚,欲以己所体得之解脱观救济一切。”而究竟何谓“以血书者”?在尼采那里,“血”不仅指肉体的血,也指精神的血:“你将体会到,血就是精神”。王国维引尼采的话为评价后主之词作注脚,显然又未局限于尼采的原义,那么王氏这里的“以血书者”又当作何解呢?
结合艾布拉姆斯“文学活动四要素”说,可推知这里的“以血书者”至少包含四个层面意涵:首先是作品层面,即作品在遣辞达意、形象塑造中所蕴含的元气淋漓、力透纸背的“血气”;其次是事实或世界层面,即作品中所记录和描绘的内容是一些现实中浸透着血泪的苦难,从而构成一种个体或群体性的痛苦记忆;其三是作者情感或精神层面,即作者在创作时处在一种基于生命体验的极度苦痛、悲伤和绝望的情感状态,而以此种“结沉痛于中肠,哀极而至于伤”的真感情进行创作,以至情至性的热情和激情对作品灌注所有心血,其作品方具有人类高贵之精神,方可称之为“以血书者”的文学,如《离骚》是屈原“以血书者”,《红楼梦》是曹雪芹“以血书者”,《追忆似水年华》是普鲁斯特“以血书者”,《战争与和平》是托尔斯泰“以血书者”……大凡古今中外伟大作品,无不是作者以心血浇灌而成;其四是读者层面,即面对“以血书者”的作品,庸碌颓废的读者难以从中读出高贵的精神,只有那些拥有丰沛生命力、敏锐感知力、深刻洞察力的读者才能读出文字背后的痛苦灵魂、情感血气和高贵精神。以上四个层面又是紧密关联、相互依存和渗透的,相对而言,第三和第四个层面或许更符合王国维的本意。
对于“以血书者”的文学,饶宗颐曾将其称之为“流血的文学”,以与“流泪的文学”相区别,指出“词则贵轻婉,哀而不伤,其表现哀感顽艳,以‘泪’而不以‘血’”;他还列举了表现伤春之泪、伤别之泪、亡国之泪、怀旧思乡之泪、无可告语之泪、徒呼奈何之泪、回肠荡气之泪等七八种泪的词句十数首加以说明,以辩驳王国维的“以血书者”之说,认为词中佳句乃“不以泪书者”。在饶先生看来,词这种文体宜“哀而不伤”,以“泪”抒怀足以表现词人的哀感,不必“泪尽而继之以血”。但在王国维看来,词中仅有涔涔的泪目仍觉不够,因为“以泪书者”和“以血书者”之间不仅是程度的差异,更是性质的不同,如果说“以泪书者”只是一种表现忧伤情感的惯常书写方式,那么“以血书者”的文字才能直抵最高的“真”与“实”,才是对在场生活、个体生命和生存现实的深切体认与深刻洞察,对个体生命价值的空前重视与深挚热爱,对人类罪恶、人间疾苦以及个体灵魂苦痛的勇敢担荷。这种“以血书者”的文字既是“写实”的,又是“理想”的,既是“入乎其内”“与花鸟共忧乐”的,又是“出乎其外”“以奴仆命风月”的,有对“国有内忧外患、人为衣食奔波”的“忧生”“忧世”之生命历程、价值与意义的深切体验。这种“以血书者”作为至情至性之真感情的最深刻体现,也是“境界”说的深层本质和终极审美旨归。
五、审美精神转向及其时代意义
王国维能够提出“境界”说并赋予其丰厚美学意蕴,既与他及时吸收了西方美学思想的丰厚营养有关,也与他基于民族文化本位对中国传统美学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关系重大。王国维接受西方哲学与美学的影响和熏染,可以从三个维度来审视:一是理论概念上的借鉴和运用,如“优美”“壮美”“直觉”“游戏”等;二是美学体系与审美分析方面的影响,如借鉴叔本华美学思想对《红楼梦》进行评论与分析;三是关乎审美理想与哲学观念层面的根本性问题,如对尼采“以血书者”观念的化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懂得西方美学的人才能更好地研究中国美学。不可否认的是,从康德的审美无功利学说,到席勒的“审美自由王国”说,到叔本华的“纯粹无意志”美学,再到尼采的“强力意志”哲学,都对王国维的思想和美学观产生深刻影响,但由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以及近代社会历史语境的影响,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也经历了一个“由信仰叔本华到怀疑、扬弃,再到融合德国古典美学和儒家美学而思考美学问题的发展变化过程”。如果说在王国维早期的《〈红楼梦〉评论》中仍然可以清晰地找出他对西方美学思想,尤其是对叔本华美学思想的机械镶嵌痕迹,那么到了1908年的《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已经将“西学义谛”烂熟于心,以独具之慧眼返观其人生体悟及国粹艺文,并在对传统美学弊病的体察和超越中达成学理再创,所谓“庶几水中之盐味,而非眼里之金屑”是也。正是基于深厚的中学功底,加之受到西学尤其是康德、席勒、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影响与激发,才驱使着王国维渴望在主观抒情类作品中再现“最完全之世界”“形而上学之需要”“终身之蕴藉”,从而为传统的“境界”美学内涵注入了崭新的生命活力。
在此,王国维“境界”说已经蕴涵了新的审美精神转向,即站在世纪交汇和时代转折点上的王国维,其思想和审美观正处在一个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期,由于西方美学的摄入和触发,使其“境界”说形成了对传统美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西方古典和现代美学思想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融会贯通中实现脱胎换骨,具备了“新的眼光”,并最终达成了自身在生命维度和审美维度上的双重转向。在生命价值维度上,“境界”说以“真”和“实”为前提和基质,即以具有“赤子之心”和真性情的创作者对生命的在场和生存的洞察,对生存实在、生命本真的直面,毅然进入生命的本真,从而创作出“以血书者”的文学作品。在王国维看来,只有这种作品才是最高的“真”,才能达到对人间罪恶和个体灵魂苦痛的担荷,也只有这种文字才能达到对生命本真的深挚热爱和对生存实质的深切体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境界”说以其丰富的审美意蕴超出了传统“境界”的含义,进而摄入了生存和存在的本体意识和深层本质。
与之相映照的是,在审美精神维度上,“境界”说传达出王国维对南宋白石之后词风转变的警觉和反拨。自姜白石起,词作“一变为即事叙景”,借吟咏物景寄托当世之忧,抒怀达意让位于描摹刻画,词风也由疏转密、由亮转隐、由快转沉、由阔转细、由浑转精,遂成意象派式的清苦幽怨、冷艳远晦,对此,王国维以其词论和词作予以有力反拨和纠正。与此同时,王国维也在“境界”说中表达了对唐、五代、北宋词所谓“生香真色”的那种质朴、酣畅、雄健、沉着、真切、清新疏朗、生意盎然、精力充盈的美学风格的追求和崇尚。与前者的疲倦姿态相比,王国维追求和崇尚的正是一种包含了对生命的热爱的健康之美、充盈之美。这样一种美的崇尚和审美精神转向,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样一个西方文明大肆入侵、中西文化交汇激荡、中国濒临民族存亡绝续的重大关口,在那样一个积贫积弱的时代和病恹恹的社会审美氛围中,无疑具有开时代风气之先、引领时代审美精神风尚的重要意义,可以说在审美精神取向上做到了“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放眼当今时代中国学术研究境况,面对诸如“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等时代新论题,如何打破西方文论的重重魅影,弥合西方、传统与现代裂痕,重构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仍是一项值得深入探究的课题。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文论重感性评点、轻理论分析,除了刘勰《文心雕龙》、叶燮《原诗》等少数系统性的文艺理论著作,其余多是诗话、词话、诗文评这种随感式、印象式批评,缺乏西方文论中的逻辑性和实证性分析,从而造成现代学术理论发展上滞后于西方。这种观念有其逻辑上的合理性一面,但又是极其片面之辞。因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典文论话语系统已经变成僵死的‘故纸堆’,成为一堆毫无价值的‘烂铜废铁’”;相反,中国古代文论资源区别于西方重逻辑的语言和分析的方式,而在审美领域中对生命体验和美学意蕴的直观把握更显其独特的美学价值,故而依然是一脉取之不竭的美学富矿,对全人类的美学而言亦是一份独特而宝贵的遗产。诚如季羡林所言,“我们中国文论家必须改弦更张,先彻底摆脱西方文论的枷锁,回归自我,仔细检查、阐释我们几千年来使用的传统的术语,在这个基础上建构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然后回过头来面对西方文论……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并且应“首先认真钻研我们这一套根植于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文论话语,自己先要说得清楚,不能以己之昏昏使人昭昭”。季先生此言乃是基于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肺腑之言与智慧之言,其目的在于融汇中西并建构一套“根植于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文论话语”,可谓卓识之见。
由此反观王国维的美学范畴创造,他并非一味地对所谓的“国粹”抱残守缺、泥而不化,而是在西方美学思想初入中国的文化转折期即及时接受、吸收和借鉴异质文化,以其作为观照中国传统美学和文艺创作的“外位性”视角。与此同时,他又没有成为唯西方美学马首是瞻的奴仆,简单挪用、直接照搬和单纯接受西方美学的理论和概念,而是在观照中国古代美学与近代现实中对其加以改造和转化,利用“西方的美学思想和方法论总结了中国人自己的审美经验”,让“西方逻辑的方法和中国古有的重审美经验的批评方法交相辉映”。特别是他并不将以艺术直觉、灵感、印象式评点等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方式视为低级的、原始的、腐朽的或不科学的“理论僵尸”,而是放大这种具有民族文化特色批评方式不可替代的优越性,以中国传统的词义阐释方式和诗话词话言说方式为“模子”,重新激活中国古代的“意境”论和“境界”论,并赋予其蕴含时代内涵的丰富美学意蕴,在中国美学理论谱系中开拓出了具有世界意义的理论贡献。这种坚守民族文化本位、以我为主、汇通中西的研究取向,正是王国维文艺美学思想穿越时代、烛照当下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从中也显示出他与中国传统美学“血肉般的联系”。当然,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孕育和形成于国势日蹙、民族危亡、质疑传统的时代背景下,其对西方美学思想的接受、理解和阐释也存在一定的误读和局限。即便如此,王国维以中西美学和文论话语进行相互参证,重释、激活中国古代美学和文论范畴,发掘并创造性转化出现代美学话语新内涵的创举,仍不失为一个化铁成金、革故鼎新的美学范式创造之范例,对于推动中国美学和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构建也是一个成功先例,应当引起新时代中国美学和文论研究者的借鉴和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