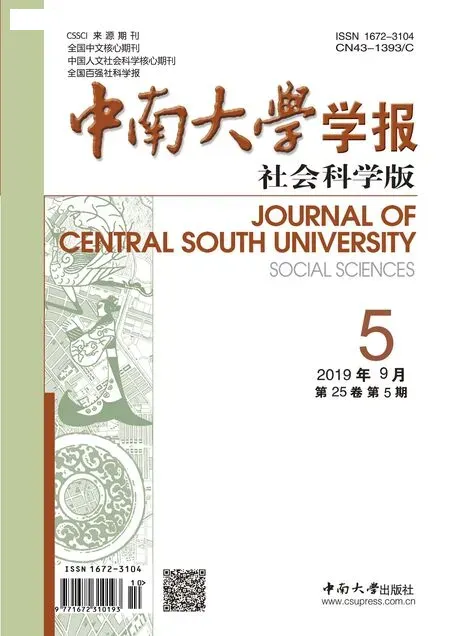论汉语四声的发现与民间歌者的关系
——补论佛经转读与四声发现无关
鞠文浩
(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广东广州,510275)
近年来,四声的发现与民歌的关系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如刘跃进先生提出“四声的发现,不仅肇始于佛经的转读,江南新声杂曲的影响也是不能低估的”[1],吴相洲先生亦认为“四声八病源于民间又回到民间,与民间歌诗传唱有着密切的关系”[2](57)。尽管如此,民歌在发现四声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仍未得到学界的充分认识,时至今日,学界对于这个问题的主流看法仍是:四声的发现主要受佛经转读的影响,同时,清谈、民歌以及文人的诗歌创作等因素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实,这个看似周全的观点与事实相去甚远。实际上,在发现四声的过程中,佛经转读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而除了人们对于汉语声调的认识逐渐加深这一内在因素外,决定四声发现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是民间歌者。
一、吠陀三声的性质及其与 汉语四声的关系
“四声的发现受了佛经转读的影响”,这一观点最早是陈寅恪先生在其《四声三问》一文中提出的。先生称:
(汉语声调)所以适定为四声,而不定为其他数之声者,以除去本易分别,自为一类之入声,复分别其余之声,为平上去三声。综合通计之,适为四声也。但其所以分别其余之声为三声者,实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也。[3]
文中对这一观点作了简要论证:
据天竺围陀之声明论,其所谓声svara者,适与中国四声之所谓声者相类似。即指声之高低言,英语所谓pitch accent者是也。围陀声明论依其声之高低,分别为三:一曰udātta,二曰svarita,三曰anudātta。佛教输入中国,其教徒转读经典时,此三声之分别当亦随之输入。至当日佛教徒转读其经典所分别之三声,是否即与中国之平上去三声切合,今日固难详知,然二者俱依声之高下分为三阶,则相同无疑也。
这一观点及其论证自提出之日起,就不断受到反驳,直至今日仍有学者撰文力证其非。周法高先生指出,“吠陀三声”在公元前已经失传,中国僧人不可能接触到它,自然也没有办法将其应用到佛经转读中[4];饶宗颐、俞敏二先生指出,佛教禁止用“吠陀三声”诵经,中国僧人不可能在转读佛经时使用这种“外书音声”[5-6];戴伟华先生指出,中土的佛经转读使用的是汉语,与印度声明论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7];陈顺智先生指出,南朝及隋唐的音韵学家、诗律学家在讨论四声时,没有一人提及它与佛经转读的关系,而六朝文献中也找不到任何关于印度声明论的记载,这说明四声的发现本就与佛经转读无关[8]。他们都是从史实的角度,论证佛经转读并未受到“吠陀三声”的影响,因而也不可能成为汉人“依据及摹拟”它来划分平、上、去三声的契机。这些观点都是很中肯的。
但也有学者认同或有保留地认同陈寅恪先生的观点,并对其观点做了补证。平田昌司认为吠陀诵法在佛教中未被完全禁绝[9]。卢盛江赞同此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吠陀诵法可能进入了中土,且一定程度上融入了中土的佛经转读[10-11]。但诚如平田昌司所言,“中国人有围陀三声的知识这项假设,很不容易证实”[9](53),晋宋齐梁的文人和僧人确实对梵语有一定的了解,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种了解涉及吠陀三声。卢盛江认为《高僧传·经师论》提到的“三位七声”,核心就是吠陀三声,但他并没有提出可靠的证据来支撑这一观点。关于“三位七声”的具体含义,学界一直众说纷纭,目前看来,应该跟吠陀三声没有太大关系。另外,卢盛江也没能解释“为什么六朝音韵学家在讨论四声时,无一人提及佛经转读和吠陀三声”的问题。总之,要证明佛经转读乃至吠陀三声在汉语四声发现的过程中起到了作用,目前还缺乏切实有效的证据。
其实,无论吠陀诵法有没有传入中国,它都不可能成为四声被发现的重要因素,因为从原理上看,平、上、去三声的划分,并非“依据及摹拟吠陀三声”。兹略作补论如下。
首先,吠陀声明论所谓之“声”(svara),与汉语声调的性质完全不同。汉语的声调是字音本身固有的特征,而吠陀的“声”则是一种诵读方法。简言之,汉语四声之“声”是声调,吠陀三声之“声”是声腔。举例来说,汉语中我们说某字为平声,是指这个字的读音本身是平声,而吠陀诵法中重音音节用udātta读,不是指这些音节本身具有udātta的调子,而是指在诵读吠陀经典时,重音音节要刻意地读成高调(udātta)。这是一种出于追求音律效果而人为规定的发声方法,不是语言本身的特征。梵语本身是没有声调的,而汉语作为一种有声调的语言,不可能摹拟一种无声调的语言来对自己的声调进行分类。
陈寅恪先生认为吠陀三声是语言的调子(即“声调”),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十诵律》卷三十八“明杂法之三”记载:
佛在舍卫国。有二婆罗门,一名瞿婆,二名夜婆,于佛法中笃信出家。本诵外道《四围陀》书,出家已,以是音声诵佛经。时一人死,一人独在,所诵佛经,忘不通利,更求伴不得,心愁不乐,是事白佛。佛言:“从今以外书音声诵佛经者,突吉罗。”[12](饶宗颐:按突吉罗,即梵语duskrta,义为ill-done。《翻译名义集》卷七“突吉罗”条,善见云:“突者,恶也,吉罗者,作也。”“作恶”之谓。[5])
佛陀禁止用《四围陀》之“音声”诵读佛经,这个“音声”是指诵法之音声,而不是语言之音声,当时瞿婆、夜婆诵读佛经的语言应该是与舍卫国的其他佛徒相同的。如果认为这段话说得不够清楚的话,那么《五分律》的记载应能对我们理解吠陀三声乃诵读音调这一事实有所帮助。《五分律》卷二十六“第五分杂法”云:
有婆罗门兄弟二人,诵阐陀鞞陀书,后于正法出家。闻诸比丘诵经不正,讥呵言:“诸大德久出家,而不知男女语、一语多语、现在过去未来语、长短音、轻重音,乃作如此诵读佛经。”比丘闻羞耻。二比丘往至佛所,具以白佛。佛言:“听随国音读诵,但不得违失佛意,不听以佛语作外书语,犯者偷兰遮。”[13](饶宗颐:按偷兰遮者,《翻译名义集》七“善见云:偷兰名大,遮言障。……明了论解:偷兰为麄,遮耶为过。”谓大过也。[5])
“听随国音读诵”指可以用各地方言来诵读佛经,依印度当时的情况,各地方言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各国语言”,佛陀规定佛经可以用各种语言来读,但不能作“外书语”,可见“外书语”并不是语言。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则更加明确地指出了佛陀禁止的对象是吠陀诵法,其第六卷云:
时诸苾刍以缘白佛。佛作是念:“苾刍诵经,长牵音韵,作歌咏声。有如是过。由是苾刍不应歌咏引声而诵经法。若苾刍作阐陀声诵经典者,得越法罪。若方国言音,须引声者,作时无犯。”(义净注:言阐陀者,谓是婆罗门读诵之法,长引其声,以手指点空而为节段。博士先唱,诸人随后。)[14]
这里已说得很明白,吠陀三声是歌咏之声,而不是语言之调,如果语言本身有声调,那佛陀并不会禁止用它们来诵读经法。
根据平田昌司的介绍,印度古典戏剧学著作《戏剧论》中列举了四种朗诵台词时使用的调子:udātta、anudātta、svarita、kampita。其中“svarita、udātta适合于滑稽、艳情等情绪,udātta、kampita适合于英豪、激烈、惊心动魄等情绪,anudātta、svarita、kampita适合于悲哀、可恶、恐怖等情绪”[9](53)①。从这一记载来看,udātta、anudātta、svarita显然不是语言的“声调”,而是朗诵的声腔。
《声明论》对udātta和anudātta的解释是:
The vowel that is perceived as having a high tone is called udātta or acutely accented.The vowel that is perceived as having a low tone is called anudātta or gravely accented.②
“is perceived as”(被视为、被当作)一语也透露出udātta和anudātta是人为规定的音调的事实。如果它们是自然的语言声调,那这里应该直接写成The vowel that has a high tone is called udātta,而不需要加上“is perceived as”。
其次,吠陀“三声”的划分原理,并不是按音调高低分成三阶。确切地说,只有udātta和anudātta是按高低分,svarita只是一种特殊的语音现象,而不是一个音高类别。俞敏先生对此有深入探讨,他指出:
严格地说,svarita并不能跟udātta和anudātta平列,算三种……印度的“老师宿儒”也有根本不承认有svarita这种东西的。[6](42-43)
尉迟治平先生也说:
svarita并不是一种正式的调子,只发生在下面这种特殊情况下:
sāvitrí upakhyana → sāvitrýupakhyana 娑玮特莉的故事
由于语流音变,带重音的元音i变为半元音y,和不带重音的元音u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个新的音节,即trí + u → trýu。在一个音节里,高调后紧接着低调,形成了过渡性的滑音,变为先高后低的降调。[15]
可见svarita只是重音音节与非重音音节缩合到一起时,发生的同一音节内音调降低的语音现象(这种现象可能只在诵读吠陀时出现,缩合而成的新音节本身没有降调),在吠陀诵法中,它并不具备与udātta和anudātta等同的地位。我们可以这样认为:udātta是高调,anudātta是低调,但svarita并不是“中调”,它不是一个介于udātta和anudātta之间的音高类别,而是一种udātta与anudātta相遇时产生的变音。吠陀声明论中将svarita解释为“混合音”,而这一解释也没有强调其音高的意思。声明论中只有udātta和anudātta是强调音高的,从词根来看,它们与svarita有本质的区别。梵文中dā这个词根有“提高”的意思(笔者不懂梵文,此处依据的是饶宗颐先生的论述[5]),故udātta意为“高调”,an是反义词缀,故anudātta意为“低调”,而svarita没有dā词根,从构词上讲,它与udātta、anudātta不在同一语义范畴。陈寅恪先生认为吠陀“三声”是依“声之高下”而分,这个观点本身不能成立。
另外,吠陀声明论中到底有没有“三声”这样的说法,也还需要再讨论。因为声明论中虽提到了udātta、anudātta和svarita这三个概念,但并没有明确表露出把它们视为并列三类的意思,而且在实际的吠陀期语言中,“混合音节”所占的比例极小,很难把它定性为一种与重音、非重音并列的音节种类③。
再次,汉语平、上、去三声的划分依据也不是音高本身,而是音高的变化,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沈约在《答甄公论》中以春夏秋冬四时之象比拟平上去入四声,体现了当时人对四声的认识,以及四声的分类原理。他说:
昔周、孔所以不论四声者,正以春为阳中,德泽不偏,即平声之象;夏草木茂盛,炎炽如火,即上声之象;秋霜凝木落,去根离本,即去声之象;冬天地闭藏,万物尽收,即入声之象:以其四时之中,合有其义,故不标出之耳。[16](102)
“不偏”“如火”“去根离本”“闭藏尽收”这些用词明显都是在比拟调形,而不是音高,可见在当时,汉字声调的分类依据是其升降变化,而不是“声之高下”。唐代释处忠《元和韵谱》称“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直而促”[17],他在这里描述四声的听觉特征时,也没有强调它们声音高低的区别。
陈寅恪先生称“至当日佛教徒转读其经典所分别之三声,是否即与中国之平上去三声切合,今日固难详知”,但从周、隋、唐初的梵汉对音材料来看,声明论的“三声”是不能与平上去三声“切合”的。周、隋、唐初僧人音译的佛经中,上声字既可以对译重音音节,又可以对译非重音音节。如mahāprajāpáti译为“摩诃钵啰阇簸帝”,以上声字“簸”对译重音音节pá,kinára译为“紧那罗”,以上声字“紧”对译非重音音节ki。去声字既可以对译非重音音节,又可以对译混合音节。如mahāprajāpáti以去声字“帝”对译非重音音节ti,pūrnámaitrāyanīputrá译为“富啰拏迷低黎夜尼弗多啰”,以去声字“夜”对译混合音节ya。可见,声明论的三声与平上去三声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对应关系④。
总之,陈寅恪先生提出平上去三声实依据及摹拟印度声明论之三声的观点,最重要的论据是声明论的三声与平上去三声“俱依声之高下分为三阶”。但事实上,无论声明论的三声,还是汉语的三声,都不是依据声音高低来划分的,而且它们一个是“声腔”,一个是“声调”,性质上也完全不同。因此,从原理上讲,汉语四声分类法不可能是依据及摹拟印度声明论制定的,而佛经转读对汉语四声的发现,也没有直接的影响。
二、汉晋乐谱体式与四声的发现
古人讨论四声,鲜少提及其发现过程,但仔细翻检旧籍,仍能找出零星相关记载,而这些记载则全部指向一个事实:四声发现于民间。
其中,直接记载有一条,李概《音韵决疑序》称:
平上去入,出行闾里,沈约取以和声之,律吕相合。[16](104)
他已明确指出,“平上去入”之分,是出自民间的。这条记载的可靠性,可以从三个方面论证:第一,李概生活的年代距离周颙、沈约等人不远⑤,对于当时之情况,了解得比较充分;第二,如果四声不是发现于民间,或文人有此共识,那么主流文人很难凭空论断四声出自民间;第三,李概此论,不必主观作伪,因为将四声的发现归功于民间,对他本人没有任何好处,而且中国文人虽然喜欢将某些观点或发明假托于往圣昔哲,但基本不会假托于民间。因此,李概之言应有所依据,而非凭空杜撰。
间接记载有两条:一是钟嵘《诗品》称“至如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18]。前人多认为“蜂腰”“鹤膝”是“八病”中的两病,但在中唐以前的文献中找不到依据。本文先不讨论它们的真实含义,仅从钟嵘的行文来看,“蜂腰鹤膝”应与“平上去入”有关。而《南史》称沈约等人“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19](1195),亦可见“蜂腰”“鹤膝”的制定的确需要用到四声,而它们又“闾里已具”,说明闾里之间早有平上去入之分。二是甄琛指责沈约《四声谱》“不依古典,妄自穿凿”[16](97),沈约答复称“昔周、孔所以不论四声者……是以《中庸》云‘圣人有所不知,匹夫匹妇,犹有所知焉。’斯之谓也”[16](102)。他先说圣人不论四声,是因为四声之象暗合四时,不言自明,接着引用《中庸》的句子,应是退一步而言,哪怕圣人不知,“匹夫匹妇犹有所知”,以此来反驳甄琛“妄自穿凿”的指责。说明四声者,圣人即使不论,也知其合于四时。圣人即使不知,“匹夫匹妇犹有所知”。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四声已为当时民间的“匹夫匹妇”所了解。
另有一条记载,可作旁证。《梁书》称:
(约)又撰《四声谱》……高祖雅不好焉。帝问周捨曰:“何谓四声?”捨曰:“‘天子圣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20](243)
“天子圣哲”四字,正对应平上去入四声,周捨以此来回答萧衍的问题,或许带点推荐四声的意思。对于四声,萧衍到底是明知故问,还是真不了解,此处暂不讨论,但周捨向他解释之后,他仍不愿使用,说明他对四声之分并不认同。而《隋书·音乐志》记载“帝既素善钟律,详悉旧事,遂自制定礼乐”[21],《梁书·武帝纪》则称其“不听音声,非宗庙祭祀、大会饗宴及诸法事未尝作乐”[20](97),可见他本人善雅乐而不好俗乐,那么他不喜欢四声,很可能与四声之分出自民间俗乐有关。
不少学者已注意到四声与民间存在密切的关系。詹锳先生依据沈约《答甄公论》以及李概《音韵决疑序》的说法,提出“四声之论乃根据当时民间之口语现象归纳而成”[22](174)。吴相洲先生亦认为四声出自民间,但他并不认同四声是由口语现象归纳而成的。他说:
当时闾里使用四声和讲究蜂腰、鹤膝等声病最有可能的是民间歌者,只有他们才知道什么样的歌词便于入乐歌唱,也懂得什么样的歌词便于入乐歌唱。[2](57-58)
吴先生的观点很有道理。四声姑且不论,民间日常交流所用的口语不可能也不需要制定出“蜂腰”“鹤膝”之类的格式,而民间歌者因为需要考虑歌词入乐歌唱的问题,所以在长期实践的过程中加深了对于文字声调的认识,进而发现四声,并利用它制定出相应的格式。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既然如此,那么民间歌者对于文字声调的“认识的加深”,具体又是怎样实现的呢?
刘跃进先生在讨论永明诗歌时曾作出一个推测,这个推测对于我们理解民歌与四声发现的关系,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他说:
新声杂曲对于永明作家的影响尤为直接。他们不仅大量摹拟创作了具有江南民歌风味的乐府小诗,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歌者之抑扬高下”之间,会不会注意到“四声可以并用”(顾炎武《音学五书·音论中》)这个基本的音乐规律呢?换一句话说,在歌唱中同样一个字,是可以“随其声讽诵咏歌”而有不同的音调,其结果“亦皆谐适”(江永《古韵标准》)。我想,对于善识音律的永明诗人来讲,这种基本的辨音能力应当是具备的。[1]
文中引用了顾炎武与江永的观点。顾炎武《音论·卷中·古人四声一贯》称:
四声之论,虽起于江左,然古人之诗,已自有迟疾轻重之分,故平多韵平,仄多韵仄。亦有不尽然者,而上或转为平,去或转为平上,入或转为平上去,则在歌者之抑扬高下而已。故四声可以并用。[23]
江永《古韵标准·例言》称:
四声虽起江左,案之实有其声,不容增减,此后人补前人未备之一端。平自韵平,上去入自韵上去入者,恒也。亦有一章两声或三四声者,随其声讽诵咏歌,亦有谐适,不必皆出一声,如后人诗馀歌曲,正以杂用四声为节奏,《诗》韵何独不然?[24]
两位先生皆认为古诗之所以能够四声通押,是因为歌唱时字调可以随其配乐曲调的抑扬起伏而变化。在原理上,这种观点是成立的,但实际上古诗中入声字一般不与平上去三声字通押,因为入声不只是一个调类,同时也是一个韵类。因此,顾炎武在《音论》中又说“平上去三声,固多通贯,惟入声似觉差殊”。
但不管怎么说,古诗入乐,歌者在演唱时可以自主改变诗中字调的抑扬高下,使之合于相配的乐调。这是事实,顾、江二氏对此的理解并无问题。在这点上,乐府诗也是与古诗一样的。因此,刘跃进先生认为,永明诗人在摹拟创作乐府诗的过程中,可能会认识到,同样一个字是可以唱成不同音调的,而这种认识对于他们发现四声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一观点很有道理,但有些地方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首先,无论歌唱,还是创作乐府诗,民间歌者都是绝对的主力。如果民歌中真的有某种因素能促使四声被发现的话,民间歌者注意到这一因素的机会要远多于主流文人。从这个角度看,民间歌者发现四声的可能性要比主流文人更大。其次,在歌唱时,一个字的唱调可以比它的声调曲折很多,歌者可以人为拉长它的发音,并做出与其文字本音不同的抑扬起伏。因此,文人或艺人在歌唱和创作乐府诗的过程中直接发现四声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沈约、钟嵘、李概等人的论述又确实反映出四声的发现与民歌有重要的关系,那么民歌之中到底有什么因素,或者说它到底以什么方式,促使人们发现了四声呢?
这个问题或许可以从六朝乐谱中找到答案。《道藏》洞玄部《玉音法事》一书,上卷记载《步虚吟》三首,乃晋代道教之乐歌,歌中每字之下皆以曲线及小字标明唱调。经逯钦立先生考证,此即汉魏六朝乐谱旧式,与《汉志》所谓“声曲折”体式略同[25](97-104)。兹录其第一小节之谱(见图1)。

图1 《步虚吟》第一首乐谱节选
谱中以曲线表示唱调之抑扬起伏,又以文字标明相应位置的实际发音(此举应是为了帮助歌者理解并掌握唱调的起伏变化),其标明之文字,逯钦立先生认为可分为两类:
如“下亚哑”、“贺俄阿”、“何下”、“下下”等为数最多。且各成定组,状写声节。此谱中通用之字,姑名之曰甲类。又如“爱艾哀”,则专于“太”字下用之,“乌误悟”,则专于“无”字下用之。此等字为数最少,且因辞变换,并不固定。要须与本辞为叠韵。此谱中特殊之字,姑名之曰乙类。甲类仅状歌声,乙类且叶辞韵……[25](103-104)
这种分法已得其崖略,但仍稍显粗糙,分成三类应更加合适:第一,“贺我阿”“亚哑牙”等为助音字,表示此处应唱“he”“e”“ya”等音。这类字有声而无义,在歌唱中起调整节奏的作用,与本字(稽、首、礼、太、上等字)没有关系。第二,“下”不是助音字,其本身不发音,只表示此处唱低音或降调。第三,“衣宜义”“哀艾爱”“于御汙於”等字,表示本字的唱腔,即本字发音拉长之后的抑扬起伏。本字发音拉长,实际上是拉长了韵母,因此“衣宜义”“于御汙於”等字发音皆与“礼”“虚”等字的韵母相同,唯声调不同。
其中,第三类字的使用,可以使歌者加深对文字声调的认识,进而发现四声。因为这类字本质上是利用它们自身的声调,来表示歌曲中相应位置的唱调,而这些唱调有高有低,有升有降,有平有侧,串联起来即组成整段唱调的起伏曲折。在标注这类声字的过程中,歌者是完全有可能意识到汉字声调的区别,并总结出它们升降变化的特征的。另外,第一类中“亚哑牙”等助音字也具有韵母相同而声调不同的特点,这些字对于四声的发现,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由于年代久远,相关材料稀缺,“齐梁之前的民间歌者如何发现四声”这一问题,很难有一个全面、具体的结论,但根据上文论述,有两点是可以基本确定的:①汉语四声是由民间歌者发现的;②歌者在乐谱中标注文字的唱调,对他们发现四声起了重要的作用。
另外,齐梁之前,民歌中已有“平调”“侧调”“上声”的说法,詹锳、逯钦立二先生都认为声调中的“平上”“平侧”之名有可能来源于此[22,27]。
《乐府诗集》卷四十五引《古今乐录》记载:“《上声歌》者,此因上声促柱得名。”[28]《古今乐录》为南朝陈代僧人智匠所编,其时四声说已流行于世,“上声”成为一个专称,其含义是固定的。然则“上声促柱”之“上声”,应该就是指四声中的上声,而且梵汉对音的成果显示,中古汉语的上声是短音⑥,确实有“促柱”的特征,可见“上声歌”的命名,正是利用了四声中上声的特性。
既然如此,那么齐梁之前的民间歌者,至少应该已发现了“上声”,而他们当然不可能只发现“上声”这一个声调。因为声调平上去入的变化特征本就是在对比中体现出来的,再结合“平调”“侧调”的说法,不难确定,“四声”确实是由民间歌者发现的。
三、周颙与《四声切韵》
刘善经《四声指归》称“宋末以来,始有四声之目,沈氏乃著其谱论,云起自周颙”[16](80),饶宗颐、逯钦立等学者皆据此判定四声乃是周颙在刘宋末年发现的[5,27]。但这一观点很难经得起推敲:如果周颙在宋末已发现四声,那萧子显著《南齐书·周颙传》为何未记载此事?《南史》又为何将“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放在永明十年周颙“转国子祭酒”之后[19](895)?文献记载中为何整个南齐朝都无人提及四声,而萧衍登基后还有“何谓四声”之问?李概言及四声从民间进入文学创作时,又为何完全不提周颙?这些问题都说明,周颙不可能在宋末就已发现四声。
《四声谱》久佚,沈约原文究竟是怎样写的,已不可考,但仅从刘善经的转述来看,沈约所谓“起自周颙”者,未必是“四声之目”,也可能是“四声之谱”,而根据前文的讨论其实不难判断,沈约的本意正是后者。《文镜秘府论·论病》称“颙、约以降,兢、融以往,声谱之论郁起”[16](396),可见起自周颙的,的确是“声谱之论”。所谓“四声之谱起自周颙”,是指周颙著《四声切韵》,率先使用四声来划分韵部,为后来沈约著《四声谱》,将四声应用于文学,打下了基础,但四声并不是周颙发现的,四声之名亦非由周颙发明。
值得注意的是,《封氏闻见记》称:
周颙好为体语,因此切字皆有纽,纽有平上去入之异。永明中,沈约文辞精拔,盛解音律,遂撰《四声谱》。[29]
饶宗颐、逯钦立都认为“体语”即慧琳《一切经音义》所言之“体文”,亦即梵文辅音字母[5,27]。周广荣、卢盛江二先生也赞同此说[11,30]。他们都认为周颙“好为体语”是受了梵文悉昙学的影响,并因此将《封氏闻见记》的这段记载,视为悉昙学影响汉语四声发现的证据。但实际上“体语”并不是“体文”。因为“体文”不是可以“为”的东西,“周颙喜爱作梵文辅音字母”这句话不能成文,而且慧琳《一切经音义》是将梵文“阿”等十二字称为“声势”,将“迦”等三十五字称为“体文”,“体文”对应的是汉语中的声母,而声母是没有“平上去入之异”的。如果将“体语”理解成“体文”,那这段记载的前后文就不连贯了。台湾《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将“体语”释为“用反切法表达的隐语”,并举《北齐书·徐之才传》“之才聪辩强识,有兼人之敏,尤好剧谈体语,公私言聚,多相嘲戏”为例[31],这一解释是可靠的。周颙喜好的“体语”与徐之才喜好的应是一回事,都是反切隐语,因此才会“切字皆有纽”。《封氏闻见记》的这段记载只是说周颙以“平上去入”对切字进行分类,为后来沈约撰《四声谱》打下了基础,它并没有声称周颙是四声的发现者,更未涉及梵文悉昙学的内容。
刘善经称“宋末以来,始有四声之目”,这一说法与四声出自民间并不冲突。如果此论言之有据的话,那完整的“四声之目”或许是在宋末出现于民间的,但它的形成则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至少“平侧”“上声”等名称在刘宋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四、结论
“吠陀三声”的性质与汉语四声完全不同,而佛经转读对四声的发现也没有直接的影响。齐梁之前,民间歌者已经发现四声,永明末年,周颙率先采用四声来划分汉字韵部,著成《四声切韵》,后来沈约又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四声谱》,制定出“四声律”⑦。在这一过程中,民间歌者的贡献是认识到四声的存在,并拟定了它们的名称;周颙的贡献是以主流文人身份认可了“四声”的合理性,并据此编写出韵书;沈约的贡献则是正式将四声应用于文学创作。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四声才得以进入文学领域,并在诗歌创作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 《戏剧论》(Natyasastra,一译《舞论》)相传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古印度学者婆罗达(Bharata,一译婆罗多)所作,黄宝生《梵语诗学论著汇编》对其部分内容进行了翻译,可参看。
② 吠陀《声明论》,即波尔尼仙所著之《文法书》,又称《波尔尼仙经》,本文对它的分析皆依据饶宗颐先生《印度波尔尼仙之围陀三声论略——四声外来说平议》一文中节录的印度学者Śrīśa Chandra Vas的英译本。
③ 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一文对此有论述,可参看。
④ 本段例证皆转引自尉迟治平先生《周、隋长安方音再探》一文,唐初译音可参看施向东先生《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语言研究》1983年第1期)文后所附的“玄奘译著对音字表”。
⑤ 李概生卒年不详,《北史》本传记载:“(概)为齐文襄大将军府行参军,……除殿中侍御史,修国史。后为太子舍人,为副使聘于江南。……还,坐事解。后卒于并州功曹参军。撰《战国春秋》及《音谱》并行于世。”(《北史》卷33《李概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11-1212页。)北齐文襄帝高澄于兴和二年(540年)始任大将军,李概应是在此之后担任他的行参军。高澄死前并未称帝,不可能立太子,因此,李概任太子舍人,应是在文宣帝高洋天保(550-559)年间,此时据沈约去世大概有40年。
⑥ 参见尉迟治平《周、隋长安方音再探》、施向东《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
⑦ 关于“四声律”,拙作《从“五声”到“四声”——齐梁声调分类之衍变》有论述,可参看,载于《人文杂志》201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