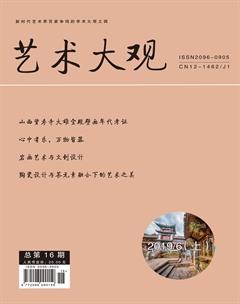宋代文人画品评标准研究
任玉婵
摘要:“逸品”作为品评标准的出现发展和确立,给文人画明确了审美内涵,因文人画的题材居多,形式多样,品评标准尤为重要,本文将侧重于从品评标准试析宋代文人画的审美内涵及精神性。
关键词:逸品;文人画;审美内涵;精神性
一、宋代文人学士画
在中国绘画史上,宋代是一条明确的分界线,宋代以前和宋代之后的绘画技法及其美学思想都经历着绘画的新旧交替,相互交融,绘画大家也是层出不穷,画派与画派之间的斗争也极其频繁,文人画在宋代是一个新生画派,他们的美学实践和艺术理论改变了宋代院体画家们的审美观念及品评标准。文人画从而进入人们视野,逐渐成为时代主流,可以说宋代以前的中国画是不断寻求技法的精益,历经文人画以后则是不断创新,历经实践,从而使绘画和精神达到高度契合,对后世的文人画与文人画理论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谈到宋代文人画首先提到的是宋代文人学士画,一场文人发起的运动,奠定了日后文人画发展的基调,其中北宋李公麟的中国画,以不反映现实为主,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体系,其中文人画体系包括了人格、学问、才情、思想等四个方面,其中的人格则是代表了文人画的要求,也是画家们对于人格的向往。才情涵盖了:诗、音乐、文学以及文人们偶尔的多愁善感。思想上主要是当时所推崇的道家思想,一种哲学的体系。
苏轼在《东坡题跋·跋宋汉杰画》中提出,“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这是“士人画” 的首次提出,苏轼也是第一个较全面的阐明文人画理论的人,他对文人画体系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宋代以后的文人画是沿着宋代文人画的理论规范一路走来的,是在宋代的艺术名家的基础上继续拓展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著名元代四家的作品中也受其影响,在此基础上发展深刻,从形式上皆以:笔、墨、诗书画印、构图的空间性留白为主,其精神性以:情景交融,借景抒情,寓意于物等意境达到“墨分五色,与画同源”。
二、文人画品评标准的出现及发展
南宋谢赫最早对绘画进行分品,在其《古画品录》中将二十七位画家分为六品。继谢赫之后,唐代李嗣真将“逸品”一词用于书画品评,在《书后品》中,将“逸品”列于“九品”之上:李斯居首,王羲之、王献之、钟繇、张芝次之。这个时期“逸品”作为最高品评标准。这也是“逸品”一词在唐代作为书画品评标准的最早出现,是品评创作者艺术修养和其作品优劣的审美标准。李嗣真的品评标准与南宋谢赫有异曲同工之妙,谢赫在《画品》中将陆探微列为榜首,品评标准更注重创作者技法,可见这个时期的审美标准更偏向于艺术的作品技法、专业、成熟等等标准,与后来理解的“逸品”存在着差别。其后,唐代张怀瑾在《画断》中将品评标准重新定义:“神品”“妙品”“能品”,以这三品品评书画,其中“神品”品评标准和李嗣真提出的“逸品”品评标准则为同一等级。
“逸品”的再次提出则在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中,朱景玄在“神品”“妙品”“能品”品评标准之外在列“逸品”,“逸品”并不是作为榜首提出,而是在三品之外,王墨、李灵省、张志和三人被列入“逸品”之中,并评价“此三人非画之本法,故目之为逸品”,评价虽高,但却将其列为三品之外,可见这个时期的品评标准仍然注重画家技巧,不过和李嗣真《书后品》中“只”注重作画技巧的审美标准进步许多。继朱景玄之后,张彦远的《历代名画录》将品评标准分为“自然”“神”“妙”“精细”“谨细”五个品评标准,虽然未将“逸品”列入其中,但这里的“自然”和“逸品”有着共通之处。所有张彦远也算“逸品”的推崇者。
到了宋代,黄休复的《益州名画录》将品评标准分为“逸格”“神格”“妙格”“能格”四格,与《唐代名画录》不同的是黄休复将“逸格”列于其他三格之上,“能格”最低,其品评标准是画家对生物的观察能力和作画的技艺能力是否达到标准;“妙格”次之,需要画家本身融入自然、合乎自然;“神格”则需要画中的意向符合画面中显示的形象,和人物画的传神相关但不等同;而“逸格”则要求符合三格的同时更高于三格,和精神性相关,要求更为严苛。这个时期确立了“逸”的审美内涵和品评标准的地位,往后对书画的品评标准也建立在此基础之上。
文人画的品评标准和画家本人“人品”一直有着相关联系,宋黄庭坚在《濂溪诗序》中提道:“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可见宋代对“人品”的定义及要求,把“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这类高洁品性融入作品之中,也是在向世人展示画家们超脱世俗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因而宋代文人们格外注重品性的修养,他们选择坐石邻水,与竹同游,在与大自然的“神遇”中获得精神的自由和超越。喜欢画元气淋漓的景色,追求高远、深远和平远的山水构图,以此体会和领悟玄远微妙的道,实现与道合一的精神理想。
三、“逸品”对宋代文人画的影响
宋代文人们通过笔墨的宣泄,洗涤自身的灵魂,以创作来抒发心中淤积,陶冶情操。但文人画的形式多样,因此品评标准的出现才显得尤为重要。文人画的创作题材广泛,他们所关注的事物皆能入画,一直以来文人们对创作题材的品位清雅,对审美对象有着独自的生命体验,创作形式也多种多样,每个人的审美趣味也不尽相同,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急需一种品评标准,指明一个方向,而品评标准的“逸品”使得他们在精神上远离尘世,在品行上保持着清旷荒寒、淡雅清疏的高洁。通过绘画审美标准“逸”的追求实现在精神上对世俗生活的超越。
在品评标准“逸”的影响下,画者在努力提升自身技法的同时更注重修身养性,毕竟中国画较之西方油画的造型艺术不同,文人画更主张表现的是“画中气韵”,这需要画家们不能只强调形似,更是要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突出对情感的表现。受“逸品”影响,文人画在笔墨技巧、章法上更为巧妙成熟。南宋李迪的《风雨归牧图》描绘的是一幅极具风俗意味的山水画,在题材的选取上富有野味情趣,着重表现了两个牧童在牛上的趣味性,使用简洁的背景将二者更好烘托,牧童、牛、树、岩石、等景物都被置于风雨主题的氛围之中。在作画技巧上,李迪用色清谈细腻,对牛和牧童的造型把握精准,笔墨精细,有工有写、有虚有实、密而不乱,可见李迪的深厚功底。上述提到“逸”的审美需求要求画家们不止技艺精湛,更需要达到“虚境”和“实境”相结合,也就是在绘画中达到精神和气韵皆能展现其中的绘画作品;北宋刘松年《四景山水图》中,分别描绘了春、夏、秋、冬四时的景象,画面以人物活动为中心,对亭台楼阁进行精心描绘,笔墨苍劲,季节渲染十分得体,春、夏、秋、冬每一幅都各具特色,例如描绘春景画面中便是桃李争艳、小草极富生机;描绘夏景则是夏山如碧、绿树成荫、几片小荷婀娜多姿;描绘秋景则是老树经霜、落叶知秋,其中画面的右下的几株点缀的红枫和右上的快掉完的红枫让整个画面秋营造的意境更上一层;描绘冬景则是高松挺拔、苍竹白头,整幅画面并没有运用大面积的白表现冬天的景,但刘松年却在画面营造出茫茫一片的朦胧氛围,冬景反而更加凸显,刘松年以一颗空灵虚静的心,深刻理解着大自然的无言之美,画面中线条清润,景色层次悠远,描绘了一幅远离尘嚣的四景,也表现了画家寄情于山水之中,融入大自然的自由超脱的心境;北宋苏轼的《枯木怪石图》中,怪石盘踞画中左下,枯木占据画面右半部分,用笔方圆相兼,使得画面中怪石如同漩涡一样,坚实有力,画面带来一股昂扬向上的正气之感,这幅画也是他在美学上的实践,相交于以往的“神形兼备”,这幅画则更注重意向性描绘,是文人画新道路的开创。可见,这些作品都是受品评标准影响且符合“逸”的审美需求。
“逸”的品评标准地位确立以后,文人们会从造型、题材、形似、笔墨等等来考究绘画作品,对题材的选择、画面的要求、自身品性的修养都有不同的理解与表达,画家在创作时也更注重对画面意境的营造,人格性情的表现。在本身技艺高超的情况下更注重格调高妙、超凡出尘、品性高洁等特质,只有这样才能引起“君子”共鸣,从而精神上得到满足。
四、结论
“逸品”的产生及发展给文人画带来了新的审美方向,也给宋代和宋代之后的文人画指明了方向。“逸品”是一种新的审美需求,作者是否能达到这个品评标准,则需要他们不断创新,保持自身品性高洁的同时把对生活的感悟传达在画面上,和观者达到精神上的高度共鳴。自“逸”的评品标准确立以后,宋代文人画甚至往后的中国画无不以“逸品”的审美内涵发展着,因而“逸品”的发展和确立对宋代文人画有着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傅慧敏.中国古代绘画理论解读(经典版)[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
[2]苗根源.极品山水—中国古代山水画论及画法图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3]张顺琦.中国绘画中的“逸”之品格[J].安康学院学报,2008(01):68-69+74.
[4]程刚.宋代文人的易学与诗学[M].北京:方志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