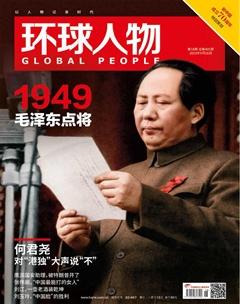路遥最后的辉煌与黯淡
许晓迪
路遥最后的时间,定格在1992年11月17日。如果他仍活着,今年70岁。对一个作家来说,正是沉入丰满、深刻的年纪。
陕西作家大多是写作的“苦行僧”。柳青写《创业史》扎在皇甫村3年,陈忠实写《白鹿原》一直蛰伏在西蒋村。相比而言,路遥的“苦”,是一种殉道式的残酷劳动。
写《人生》时,他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每天工作18个小时,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写《平凡的世界》的6年里,他找来10年间各类报刊的合订本,逐日逐月地翻看;多次来到矿场,和工人同吃住、共劳动。在招待所的小房间里,他大口大口地吐血,苟延残喘地和小说里的男女老少生活在一起。写完最后一个句号,他将笔头丢到窗外,看着镜中的自己,神情憔悴,两鬓斑白……
在那个中国文坛被西方各种现代主义的写作思潮“武装到牙齿”的时代,这部现实主义的长篇三部曲,被批评家们打上了“陈旧”的标签。路遥一度郁闷到极点,甚至跑到柳青墓前大哭了一场。他最终咬牙走了下去,用“过时”的劳动给历史留下一份深厚的记录。
1991年3月,《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听到消息后,路遥躺在木板床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眯缝着眼睛微笑着说,嗬嗬,这下狗日的做日塌了,有些人一满(陕西方言,一直的意思)看见我不顺眼,这下怕再张狂不起来了……
在《路遥的时间》里,作家航宇真实还原了这个瞬间的路遥:刚强、自负,以及掩盖在粗口之下的孤独、愤懑。在路遥生命最后的两年,航宇如亲人般陪伴、照顾着他,并记录下作家在这段艰难日子里的抗争、痛苦和无奈:
他是为了帮助兄弟找工作不惜亲自跑工厂的哥哥;是躲进招待所整理文集、“赖在”医院不肯走的作家;是名头响当当、手头空荡荡的穷书生;是疼痛得在病床上打滚、呼喊着救命的病人……
在书中,航宇写到了这样一幕:一天中午,下起了毛毛细雨。路遥站在作协院子里的一棵树下,一口饼,一口黄瓜,再一口葱,吃得津津有味。雨丝淋湿了他的头发,可他全然不顾。看到站在传达室门口的航宇,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我分明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在发颤,不争气地差点流出了眼泪。”航宇写道:“他为什么要过着这样一种简单的生活呢?他为什么不好好珍惜自己的身体,去吃一顿他喜欢的饭菜呢?”
这就是路遥留在中国文学史的形象,土布衬衫,旧牛仔裤,黑不溜秋的凉鞋,像个蹬三轮的。他最崇敬的作家柳青也是如此,身穿对襟袄,头戴瓜皮帽,儼然一位关中老农。然而,就是这两个看起来和舞文弄墨的作家毫无干系的陕北人,以罕有的宏观视野,为中国当代城乡、阶层的社会变革史,留下了生动纷繁的记载。
如今,再难看到这样的“大”作家了。贾平凹说路遥是一个有大抱负的强人,像逐日的夸父,气势磅礴却倒在干渴的路上。在《路遥的时间》里,我们读到了这条路上的诸多莽丛荆棘,也读到了一个伟大作家最后的辉煌与黯淡、脆弱与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