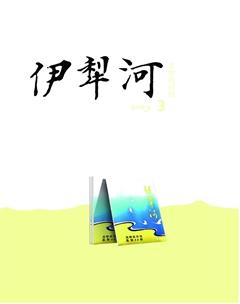废墟
李达伟
我们都在躲避废墟,我们的内心深处都在拒绝着废墟,我们是在一些废墟上看到了自己,看到了那些正在成为废墟的心灵与精神。而允许废墟侵入现实,那可能也是另外一种意义的对于精神世界的暗示,也是对于自身的暗示。我们在需要不断警醒自己时,是可以出现在某个废墟面前,实实在在的废墟,让它在精神世界里产生激荡的波浪。精神世界开始发生震荡了。精神的河流开始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涨落。精神的河流制造了一些废墟。精神的河流也在用不断上涨的流量把一些废墟遮掩起来。但废墟侵入现在,往往是一种貌似无力的介入,我们的精神在废墟前面无动于衷。
废墟:废弃的路。铺满了砖块。只剩下一些砖块。我出现在了那条路上。路被掩藏起来。路被厚厚的落叶覆盖。上面可能会有一条蛇。我是看到了一条蛇从落叶上面慢慢游走。蛇可能不会想到会有人的出现。它可能正在享受着那些厚厚的落叶堆积在一起,所释放出来的腐殖层的独特气息。我们对视了一秒。仅此一秒就已经足够让我震颤不已。我不想与一条蛇继续对视。我忍受不了那时候空气里的焦灼慌乱的气息,那样的气息与眼前的场景之间是不应该有着任何的联系,眼前的场景本应该是为了让人至少暂时忘却焦灼与慌乱的,而竟然适得其反。那样的废弃的路,还有那样一条蛇的出现,让我毫不怀疑这是一条通向废墟的路。路本身已经组成了废墟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样一条路的存在,会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对可能会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有了充分的想象。是出现了一截断墙,严格而言,是一个残关,残关上的字迹模糊,残关旁边长着青葱的草。残关所暗示我们的是这里曾是一条古道的必经之处。同时它也暗示我们这已经是废弃的残关。我们只会偶然出现在这里。但在我第一次出现时,我其实还是没有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我的想象世界里并没有出现残关,想象中出现更多的其实是一片原始,或者至少是繁茂的自然,里面有着一些我所熟悉的,或者是陌生的植物,然后在面对着这样的自然时,内心的慌乱与焦灼转瞬消失,但实际在一个残关面前,内心的慌乱与焦灼却加剧了。那时我抑制不住的是把自己与眼前的残关放在一起,我只是残关的一部分,把残关作为参照系时,我该把自己放在哪里?而与我不一样的是,那条蛇随意就可以滑入残关的某个破洞之中。
希望成为一个天生的观察者(只可惜我不是),特别是在面对一个又一个废墟之时,我甚至有了终其一生去捕获有关“废墟”的种种冲动,但我也深知,这确实只是短时间里的冲动,我一直处于这样的冲动,往往缺乏对事物持久的热情与兴趣,这时我眼前一片空白,似乎这样才是正常的。天生的观察者将是什么样子的?
废墟:一段斑驳的墙体,上面有着各种涂鸦艺术。那些涂鸦艺术家选择了那堵墙,他们毫不吝啬自己的笔墨以及思想的喷发,他们在那个小小的墙体上尽情挥洒,墙体表现出了惊人的承受力,那些饱满的奔放怪异的艺术竟然让墙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显得很坚固。涂鸦艺术是语言的一种形式,那是貌似静默却能让人明显感觉到不沉默的世界。涂鸦艺术与语言艺术,二者之间是应该有一些联系。本是废墟的墙体,本是早晚如果不是自己倒塌的话就会被推翻被拆掉的墙体,因了那些涂鸦艺术的存在,而暂时延长了生命,而暂时在那个周围都是废墟的世界里显得格外惹眼。眼前的涂鸦艺术创造者,应该是知道他所在那个墙体上创作的东西早晚要被彻底清除,这是一个有那么一些人特别热衷清除的时代,一些人清除了记忆,一些人清除了灵魂的记忆与应该有的样子。我在眼前孤立的墙体上看到了那个无名的艺术家在用这样的方式抗拒着一些东西。艺术家可能是在抗拒时间的消亡与人性的弱点,只是艺术家最终所会看到的将是抗拒的无力与无效。我想描写一下眼前的这个墙体,这个墙体在整个的废墟之内,也是之外。墙体的周围就是碎石头被乱切的水泥,以及水泥里面的铁(已经被扭曲,但还没有断掉,也似乎无法断掉的铁),这应该是一個才被制造出来的废墟,那里没能看到任何的杂草丛生,不知道那些丛生的杂草还会不会从废墟之上生长出来,更不会长得繁盛,可以略微把废墟本身的丑陋覆盖遮掩。
远离尘嚣。远离生命最喧闹的场。生活得如同废墟,生活如同废墟之上的生命,这样的表述多少有些突兀和不妥,应该是生活暂时进入了废墟,废墟暂时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思考开始围绕着不断重复出现的“废墟”展开,思考时而是向外的,时而又是沉入内部的,此刻,我更愿意沉入内部。在那个废墟前面,我真正有了远离尘嚣的感觉。置身日常生活中随处都是喧闹的尘嚣时,我竟麻木了,我竟没有任何想逃离的渴望。我真的麻木了。远离尘嚣,我只是暂时的远离尘嚣。只是在那个废墟前面,一切显得那般静谧,那里没有尘嚣,或者那里的尘嚣属于过去,尘嚣被废墟所掩埋。我继续寻找自己所想要的废墟。废墟所给我的竟不再是僵化与麻木,而是给了我极度的自由与舒适。绷紧的思想在废墟面前如废墟本身一般突然有些松动有些垮塌。
废墟:废墟所在位置,我需要想想才能真正分辨我所要触及的那个废墟,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不断有废墟在内部累积起来。有些废墟之间的差异显得异常微小,它们分布于那些世界之内,它们同样在我的内心深处占据着不同的位置。我需要一点点的时间。废墟在一个坡上,只是很小的废墟。出现在废墟前面之时,我气喘吁吁,那里可能看到我日常生活着的世界的整体,错落的建筑,建筑是生活的主体,我生活在其中某些建筑物内部不是很大的空间里。那时,在那个位置还能看到那个局促的空间之内的我,以及像我一样的人。我们在这个城市之内,面对着纷繁的生活所带来的各方面的冲击,在遭受着其中好些让我们倍感无奈的冲击之时,我们更多时候无奈,更多时候妥协,可能更多时候还要忍受一些人无端的中伤,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在一些时候(即便这样的时候很少)的抗争,我们在抗争着日常生活的庸碌。而这个坡上,有一个废墟,这是我不曾想到过的,那时我只是无意间出现在这个坡上,无意间发现了这个废墟。我是为了暂时远离尘嚣,其实我也知道尘嚣是我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们往往能做到的只是暂时避开。如果眼前出现的是废墟,我也知道自己暂时远离了尘嚣,暂时远离了由于各种事情纠缠而略显慌乱的情绪。那是什么样的一片废墟?至少曾经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片废墟?在这里似乎我的重述将没有多大意义,意义只在于那个坡,而坡上有一小片废墟而已(但当重新出现在那个位置,并重新看待那个废墟之时,我才发现那小片废墟的意义,其实就是它提供了一个可以认识自我最好的位置)。
风景与废墟。废墟对思想的影响(风景对思想的影响,自然对思想的影响,一片枯叶对思想的影响,一条河流对思想的影响),废墟对思想的突兀性与停顿性与思考的绵延性的影响似乎要超过风景所给予的,至少在我把更多思想和注意力放在废墟之上时,是如此。常常觉得自己是以困惑的姿态(废墟远不只是定义的那般简单)打量着那些废墟,准确些说应该是打量着那些时间。废墟与时间。废墟就是时间。只是时间未必就是废墟。风景与废墟之间的联系,随时在发生着,我们把众多的废墟建造成为一片现实的风景。有些风景很自然地就存在着,而废墟作为一片风景时,废墟往往要经受着一些人为的重建。但有那么一个废墟,人们没有对它进行任何的重建,也没有对它进行任何的保护(人们的用意里面就没有保护这样的想法,人们只是希望它消亡,人们根本没有去思考如果把它保护下来的话,它的意义所在)。
废墟成为一种风景。人们并没有去修复它。那个风景所最让人着迷的就是废墟本身,以及废墟正在继续消亡的过程。废墟最终会消亡,只是无法预知它所消亡的具体时间。络绎不绝的人群,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看一片废墟的真正消亡。我出现在了那个作为风景(与内心的风景和自然的风景不一样),说得再具体点就是景点存在的废墟面前,由于络绎不绝的人群的影响,一些震撼人心的力量被弱化了,我竟也如很多匆匆过客一样感叹几句,似乎就只剩下了几句不痛不痒的感叹,感叹时间的力量与意外所携带的摧毁力量。一些无序杂乱地堆砌在一起的石头,一些倒在石头,抑或就是在石头上的涂鸦艺术。涂鸦艺术里,可以看到时间较为清晰的痕迹,也可能什么都看不到,只能感受到一个混沌模糊的时间感。作为风景的废墟的存在,像极了行为艺术。废墟就摆在那里,许多人不断地来到那里,他们希望通过不断前来,能看到废墟消亡的过程。有些人开始抱怨,他们觉得多次来到那里之后,废墟依然如故,而且没有要继续消亡下去的意思。他们习惯了停止生长,却无法习惯停止消亡。似乎有那么一些人可以从消亡的过程中解恨。作为风景的废墟,由于它停止了消亡(其实只有废墟自己知道,它像极了人,一个不断在衰老的人。但有时候它也像极了一棵古老的大树,那棵大树没有任何异常,现在可以把它具体到某棵古树上,一个很小的村子,那棵古树的存在醒目而让人感到安慰,突然间,古树就死了,没有任何征兆。废墟又与这棵古树有点不一样,废墟本身就显现出了消亡的征兆,废墟本身也是消亡的一部分,只是人们所希望的可能是被拔地而起,被从地上迅速且彻底地抹去痕迹),人影慢慢变得稀落,然后就剩下我一个人(可能只是回忆中的错觉,我应该不会是最后一个人)。没有人再去管那个废墟,那个废墟对于那些人已经没有多少的利益。然后这时我就出现了,我也是想来看看废墟的真正消亡的,我也发现,这个废墟暂时是不会消亡的。我与众多的人所表现出来的一样,我所希望自己能在某些时间里,至少在认识上能与一些人有所区别,但这样的希冀也最终没能实现。我自己成了普通大众的一员,我对于世界的认识变得异常普通。我离开了,不再去关注废墟,我把时间更多放在了关注内心之上。内心在现实与虚构面前,经受着多次的震荡与涌动。而某一天,从别人的口中听到了那个废墟彻底消失的消息,那时我并没有因为曾经所希冀的所觉得不可能实现的竟然实现了而感到吃惊,我竟变得异常平静,我竟没有去关注那个被彻底抹掉的废墟之上重建起来的东西。成为风景的废墟,或是悲剧的风景,或者无法得到任何诠释与解读的风景。诠释与解读,在一些时间里,也会失去一些力量。那时,我不再去关注诠释与解读。那时,我打开了那些有着众多废墟的书,我终究没能把废墟彻底放下。
许多废墟就是未知的世界。我扼制不住那颗探寻的心,而最终发现,很多时候,探寻许多的废墟本身就是徒劳的。废墟本身就是掩藏了一个已知的世界,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废墟,一个已然倒塌或正在倒塌的世界(我们没有人会去说废墟永远存在),一个充满疑问的世界。一片废墟,一个又一个废墟,一部疑问集,一群被疑问充斥的人。我们在面对着充斥内心的那么多的疑问,我们自知乏力,却仍然继续探寻,在探寻的过程中,一个又一个的疑问继续出现。疑问集已经变得很厚。在翻开那些大部分都是没有答案的疑问时,我继续沉陷于一个被谜所遮蔽的世界之中。更多时候,我是妥协了,至少这次我在面对着那个废墟之时,我是妥协了,我是承认自己无法把废墟表面的蒙尘清除,哪怕只是暂时的打扫干净,这次我只知道那是一个废墟。废墟的过去,未知的过去。废墟的现在,就是一个废墟,废弃的瓦砾,倒塌的墙体,似乎原来是一些建筑物,里面原来所生活著的到底是人还是别的生命?这样的疑问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主要是已经无从探寻。我想解开那个谜团,只是谜团最终只是谜团,只是加重了我对于那个废墟的探寻。疑问有它的意义,众多疑问的存在,会让我们已经变得淡漠的心变得有所波折。我们似乎已经无法回避那些疑问,如果我们真回避了那些疑问,可能也将意味着我们内心的麻木与死寂。众多的废墟,似乎它们的意义就是让心能够随时澎湃起来。像感伤,像是美的另外一种绝美的姿态,像不断探寻废墟内部的世界。我开始慢慢关注心的发展。
废墟:废弃的瓦砾,倒塌的墙体,没有烧毁的痕迹,建筑之内,只有被无法移除的墙体,这样我也无法知道墙体之下的世界。那时我出现在某个山谷之中,我朝周围看了看,都是倒塌的墙体,以及破碎的废弃的瓦砾。在这个废墟的场内,至少可以知道的是有过一些生命的存在,只是我无法说清楚是人还是牲畜,只能是这二者之一。我相信叙事者。在与叙事者交谈的过程中,我尤为相信。我忘记了叙事者的模样。在那段短暂的交谈时间里,我只是重视交谈的内容,而丝毫没有去在意讲述者本身。讲述者将会变得有些沮丧和气愤,但讲述者也可能会显得多少有些自豪,讲述者至少让讲述的对象集中在了讲述的内容之上。他说在那个山谷之内有一片废墟。我说我知道,在未与他进行交谈之前,我就已经在那里出现过,我出现的理由真如上文所写那般简单。在没有讲述的陌生世界里,我就真正只看到了废墟,真正只知道那应该是一片废墟没错。讲述者说在那些已经成为废墟一部分的建筑物里,原来是养着一些狩猎来的动物。人们并不吃那些动物,只是把它们当成美的一种表达方式(在它们身上,美绝对不是以一种方式呆板地呈现着,美在那些动物身上变化多端,美的种类,足以让我们观看的人感到不可思议)。动物们纷纷饿死在那个建筑物之内。动物们纷纷绝食。人们并不知道该如何饲养那些动物。人们看到了美的凋零,美的最终化而为一,很单一的美感,最终在那些颓丧饥饿的动物身上已经看不到任何的美感。美感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消亡。负责搜集美感的人,最终也抑郁而终。在这之前,动物们也纷纷抑郁而终,它们是强烈地感知到了狭小与幽闭于一个空间之内的痛苦。自由在消散,自由在那个空间之内消散。在讲述者口中,饲养者突然意识到了自由对于美的真正重要,只是他无能为力。我在脑海里制造着这样的场景:动物们化为自由的精灵从建筑物的缝隙处逃了出去,而那个负责饲养动物的人最终竟也成了某种集各种美于一身的动物,只是在他化而为动物之时,就彻底在那个世界之中销声匿迹。但这只是讲述者的片面之词。我所面对的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废墟,将是没有被任何解读的废墟,那时任何的解读也终将没有任何意义。孤独的建筑物,孤独的废墟,孤独的一部分(一个空壳般的废墟)。那些建筑物并没有被建在平地,而是在山谷陡壁之上,当初在建造这个建筑物时,必然是付出了众多有关美学上的思考与认识。只是那里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建造建筑物的地方。我再次出现了。我在讲述者口中,了解到那个建筑物的始末,以及那些有关建筑物本身有一点点传奇意味的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