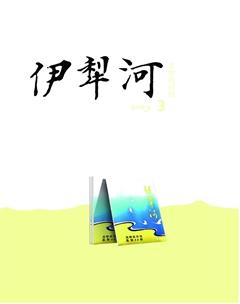相逢与告别
若非
到达落烟东收费站,天就黑了下来。
立秋下了车,与荣芳隔了一个车窗,你开车小心点。荣芳说,嗯。也没有多的话,就算告别了。不消两分钟,荣芳就驾车驶入了高速。她突然又有一些后悔,和立秋的分别,太简单平常了,應该多说上几句的,毕竟人海茫茫,尚不得知下一次相见会是何时。
荣芳走后,立秋一个人站在收费站外,心里有种不舍,眼睛时时瞄着出站通道,好像那里随时都会驶出荣芳的车。
约摸二十分钟,手机震动了一下,荣芳连续发来两条信息。说,立秋,我在服务区加油。又说,我这一生中最幸运和最遗憾的事情,都与你有关了。
原本,立秋并没有打算谈恋爱的。
立秋在沙溪财政学校读书,是1990年左右的事情。沙溪财校是全省财政干部的摇篮,从这里走出的毕业生,服务在全省各个财务岗位上。学校有中专部和大专部,立秋是大专部的学生。因为受老师喜欢,他没有住宿舍,住在很关心自己的张老师的两居室租房里。
读的是财政学校,但立秋对自己的主业并无兴趣,他醉心于文学创作、学生会活动,组织学生活动、编辑出版校刊、写作投稿,每一样都做得风生水起,是同学和老师眼中的大才子。大一结束,他就成了学生会主席,校刊主编,小有名气的校园写作者。他因此成了校园名人,有许多人认识,也有许多女孩喜欢。
但他确实是没有恋爱打算的。立秋是落烟人,父辈是沙溪迁过去的,但是年代久远,已然在落烟扎地生根。落烟离沙溪很远,无论坐汽车直达还是到省城转火车,也都得走上十几个小时。立秋亦知道自己的归宿,毕业后必然要返回落烟,被安排在某个乡镇的财政所工作,所以他心无旁骛,一心只等待毕业。
第三年的秋天来临得特别明显。开学后没多久,学校的树叶一片一片落下来,铺在地上。下午,张老师说,立秋,下课早点回来,有人来家里吃饭。他们虽然住在校外,住处也有厨房,但极少做饭。大多时候他们在学校食堂吃,偶尔逢着周末或有朋友时就在住处自己做,开小灶。张老师要安排吃饭,又不是周末,定然是有重要人物来了。
立秋到了门口,听见家里传来正在流行的歌曲《一无所有》:我要抓起你的双手,你这就跟我走,这时你的手在颤抖,这时你的泪在流……进了门,便见一个年龄与张老师相仿的女子,带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坐在客厅灰土土的沙发上。张老师赶紧介绍,说这是立秋,我学生,和我住一起。介绍到那小姑娘时,立秋眼睛一亮。小姑娘生得清秀,皮肤白,眼睛大,很好看,就是站起来时,看起来有点矮,瘦瘦的。
张老师说,这是荣芳。
立秋便慌慌张张,说,我是立秋。
见立秋慌慌张张的样子,张老师说,立秋,快去做菜,菜都洗好了的。别说,立秋做菜还真不错,不然张老师也不会把这个重任交给他。他们一起生活有一年了,立秋的小炒和火锅,都让张老师赞不绝口。
立秋炒到第二个菜的时候,荣芳就走进了厨房,怯生生地说,你什么都会做吗?
立秋回头看了她一眼,有些不好意思,赶紧转回头,说,也不是,都是慢慢学。
荣芳端起炒好的菜,放到客厅的茶几上,回到厨房,我最喜欢肉末茄子。
立秋说,这个我会,但今天没有买这个菜。
荣芳又端起第二个菜,嗯。
边吃边听,立秋也就大体了解了情况,和张老师年龄相仿的女子是荣芳的姐姐,是张老师的好友。荣芳到沙溪财校读书,作为姐姐的,带她来拜访张老师,请他以后多多关照自己的妹妹。张老师和荣芳的姐姐聊天时,立秋就边吃菜边打量荣芳。荣芳偶尔一抬眼,看到立秋的眼神,赶紧低下头。谁都没吭气。
吃完饭,立秋收拾碗筷,荣芳就说,我来洗吧。她抢到洗手池那里,去接立秋端着的锅。以后你做吃的,我负责洗碗就行了,我不会做菜。立秋一乐,好啊,我就喜欢做吃的,但我很烦洗碗。荣芳说,那就这么定了,不过我姐不在,我哪里还好意思来吃饭?立秋想想也是,没再说话。
天黑下来时,张老师送荣芳和她姐姐出去,立秋就站在阳台上,看着他们走出院门。一会儿,张老师回到家里,立秋就半开玩笑地说,老张,你是不是喜欢那个姐姐?张老师手一扬,找打啊你?立秋避开,人家让你多关照荣芳,你多喊她来吃饭吧!张老师说,那小姑娘还没成年,你不会是看上人家了吧?立秋说,我这是心疼你老人家,以前都是我做菜,你洗碗,如果荣芳在,你不是乐得清闲?张老师想了一下,也不是没道理。
少女荣芳那时候离正式满17岁尚欠两个多月,是个十足的未成年少女。
荣芳从一出生,就注定和财政脱不开干系。她出生于财政世家,父亲是县财政局局长,母亲是财政局干部,姐姐哥哥都已经读完书到了财政部门工作。她初中一毕业,就被送进了沙溪财校,被既定了未来,也是毕业后到财政局工作。
荣芳和立秋未来的命运,是如此相似。不同之处在于,荣芳家境殷实,生活费是班上最高的,每月的钱花不完。但立秋就不一样了,他大多用来挥霍的钱,来自于自己的写作,一首诗可以得到十来块钱稿费,一个月发上几首,也是不少的收入,偶尔获个文艺奖,得有一两百元奖金,瞬间说话就硬气了。
荣芳读到立秋的诗,说,你酸得哟。
立秋问,你什么意思哦?
荣芳边洗碗边说,就是觉得酸。
说是这么说,下次来吃饭的时候,荣芳竟就自己写了一首,趁着立秋炒菜,窜到厨房,塞到立秋衣袋里,立秋,你给我看看。
立秋问,什么?
荣芳说,诗,我写的。
立秋说,你不是说我写诗很酸吗?
荣芳说,你看不看嘛?话这么多!
立秋说,看,当然要看。
他们洗完碗,张老师就说,立秋,你送荣芳先回去。立秋“啊”了一声,想问什么,但看看张老师怪怪的眼神,和荣芳姐姐假装看书的样子,便觉得不好再问,跟着荣芳一前一后出了门。
不远处就是沙溪河。河两岸长满了高大的法国梧桐树,也不知道在这个偏远的地方什么时候被人种下的这些树,已经长得无比高大茂盛,在深秋里洒落一地金黄。立秋和荣芳一前一后地走着,河水就缓缓摇晃着他们俩的身影。
荣芳突然站住,立秋。
立秋说,嗯?
荣芳说,你为什么叫立秋?
立秋说,我立秋那天生的。
荣芳说,那你要是立春、立夏、冬至生的,岂不就叫立春、立夏、冬至了?
立秋说,可能我爹妈真会这样起。
荣芳咯咯一笑,那你要是清明出生呢?
立秋说,那也许就叫清明了。
荣芳还在笑,立秋反应过什么来,摸摸脑门,不说话。
风一吹,流水里他们的倒影,晃了几下,碰在一起。
快到学校时,他们就拉开了距离,隔开个十来米,荣芳在前,立秋在后。到了校门外,荣芳止住步伐,回头看立秋,冲他使眼色,立秋不动。
荣芳压抑着嗓子,立秋你回去吧!
立秋说,没事,我送你进去。
荣芳为难地说,不了,我到这就行。
立秋看了看四周,确定荣芳不会有什么事,便说,那好。他们就分别各自回去了。
路上,立秋打开一张折叠的小纸,读荣芳给他的诗歌。荣芳的诗歌标题,就叫《立秋》。看到标题,立秋心里乐了一下。
荣芳写着几行娟秀的小字,很好看。
立秋
一枚落葉
飘扬、舞蹈
落于我的眼眸
激起一阵柔软的涟漪
风起时
雨落下
暖暖地,滋养着我的青春
如果你不推开门
就不会邂逅
我守望的眼睛
末了,有一句落款。“荣芳写于1991年10月14日,沙溪财校。”
立秋看着那些好看的小字,沉吟着,不知不觉,就回到了家。
荣芳的姐姐来得勤,有时候领着荣芳来,有时候单独自己一个人来。
有时候,立秋一进门,看见她在,吓一跳,再看张老师,一脸尴尬,立秋便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很尴尬。几次之后,立秋就形成了一个习惯,每次回家前,先在门外仔细听听家里有没有其他人,再敲敲门。
荣芳迎来17岁生日。张老师说,立秋,你今天去买菜,晚上荣芳来过生日。他给了立秋一些钱,立秋就小跑着出了院子。时已寒冬,大风一吹,立秋打了个哆嗦。
买菜的时候,他留意了一下,买了两个茄子。他记得,荣芳喜欢吃肉末茄子。提着菜回到家,荣芳和姐姐已经到了。茶几上摆着蛋糕,是张老师买的。还有糖,饼干,也是张老师买的。
张老师和荣芳姐姐埋头共同看一本什么书,挨得很紧。
立秋进了屋,荣芳就跳了起来,我帮你洗菜。
立秋说,没事,你坐着吧。
荣芳说,不,我就跟你洗菜。她转头看了一眼沙发上的张老师和姐姐,低声说,我感觉自己像个电灯泡,这哪里是来给我过生日啊,分明是方便他俩见面。
立秋也回头去看,笑了,怪不得你这么积极帮忙洗菜。
荣芳说,你这话不对,以前我也帮忙洗菜的。
他们一人一边,围着一个半大的盆,在冒着热气的水里洗菜。洗着洗着,立秋的手,就碰了荣芳的手一下。荣芳什么也没察觉,立秋便又碰了一下。荣芳的脸忽地红了,你干嘛?
立秋有些不好意思,问,你多少岁了?
荣芳说,明晚满17。
立秋不解,明晚?
嗯,我生日是明天。荣芳说,明晚我得回家过,所以今晚先来你们这里,其实就是我姐想来,给我过生日只不过充当了个借口。
立秋又扭头看了一眼张老师和荣芳姐姐,你觉得,他们在干什么?
荣芳说,看书,一进门就在看了,一本书,倒是没看到他们翻了几页。
立秋说,谈恋爱的人都这么无聊吗?
荣芳说,不知道。
立秋说,他们会结婚吗?
荣芳说,不知道。
立秋问,你会谈恋爱吗?
荣芳说,不知道。她立马又抬眼看了一眼立秋,重新说,不知道,我还小呢!
洗完菜,立秋抡起菜刀切菜,荣芳就在旁看着。谁都不说话,厨房只有切菜的声音。然后开始炒菜,立秋负责炒菜,荣芳负责陆续端到茶几上。两人打着配合,晚餐很快做好。
张老师像突然发现他们似的,啊,做好了,那就开饭吧。
四人围坐在茶几边,就开吃了。荣芳第一筷子尝了肉末茄子,边咀嚼边看立秋。他笑,她也笑。她含着东西,说,嗯,这茄子可以。立秋不说话,只是乐。张老师说,可以你就多吃点,今天是你生日,我们都是沾了你的光。他嘴说着话,但并不看荣芳,也不看立秋,他眼里只有荣芳姐姐了。
吃完饭,他们又各自吃了些蛋糕,立秋和荣芳就如往常一样去洗碗了。洗碗时,立秋的手肘,不自觉地碰了一下荣芳的手肘。荣芳不说话,低着头,跟没事似的。立秋再碰,荣芳就避开了。立秋再碰,荣芳没再避,反而拐了一下,用身子撞了一下立秋。
她说,你走开。
立秋就拿着两个清洗好的碗,一脸笑走开了。
收拾好残局,立秋对张老师和荣芳姐姐说,张老师,姐,我先送荣芳回去了,你们俩慢慢聊,我晚点再回来。
荣芳姐姐说,立秋,没事,等下我送她回去。
荣芳说,姐,我不要你送,我自己走。
荣芳姐姐说,你这小孩。
张老师赶紧说,就让他们去吧,立秋这么大了,不会有事的。他说着,催着立秋,去吧去吧,路上小心点。
他们决定上沙溪河边上走一遭。落叶早就没了,夜色中的河水寂静无声,河边很冷清,难得见上个把人,也都匆匆地走着。
荣芳哆嗦着身子,使劲踱着步。立秋没话找话地问,你说这河里有鱼吗?其实他知道河里有鱼。
荣芳说,当然有,但我没吃过,不知道什么味道。
立秋说,找机会我做给你吃。
荣芳说,真的吗?
立秋说,那当然是真的,就当我补你个生日礼物了。
荣芳说,那我可等着了。
立秋说,等着吧。
他们离开河岸,学校就离得不远了。
我可以送你进去,立秋说,送到楼下。荣芳没说话。到了大门前,荣芳照例停下来,让立秋走。立秋不走。荣芳只好往里走,立秋也往里走。荣芳快,立秋就快,荣芳慢,立秋也慢。一直到宿舍楼下,荣芳回头,看到立秋站在夜色阴影里,冲自己笑,荣芳,以后我都要送你到楼下。荣芳惊慌地环顾四周,你要死啊,这么大声,赶紧回去。一转身,溜进了宿舍楼。
荣芳生日后没多久,一年就结束了。一个学期也眼看要结束了。
下午时,张老师把立秋从教室叫出来。你叫上荣芳,下午来吃饭吧!张老师说。立秋问,你怎么不自己叫?张老师说,我这把年纪了,去叫她吃饭,容易起误会。立秋说,你怕误会,我就不怕误会?张老师说,不会,你堂堂学生会主席,名气大着呢,就算你们俩谈恋爱也不会有人相信,何况你们没有谈不是?
立秋想了想,那好吧!又说,你这是要讨好小姨子吗?张老师作势要打立秋,别胡说八道。立秋逃开,你去买菜啊,我可不想這么冷的天跑来跑去。张老师留下一串“好好好”,走了。
上课前,立秋跑到荣芳班窗外。荣芳看到窗外的立秋,有些意外,有些慌张,看了他一眼,埋着头,不动。立秋只好找一个正要进门的学生,同学,麻烦帮我叫一下荣芳。那人进去,大声喊,荣芳,学生会主席找你。全班人都刷地盯着荣芳,荣芳的脸就红了,低着头,赶紧跑了出来。
你找我干什么?荣芳没好气地说,羞死人了。
张老师叫你下课后去吃饭,他已经买菜去了。
好。你以后可不能这样来找我了,被人看到不好。
好,下午家里等你。
立秋逃了后面两节课。张老师没课提前回来,正撞见立秋拿着鱼竿,从院子里跑出去。
你给我站住。张老师把他叫住,你没课?
立秋眼珠一转,没有。
张老师说,信不信我明天就找班主任?
立秋赶紧说,好吧,我逃课了。
张老师问,干什么?
立秋丢下一句“有重要事情”,跑了。边跑边说,把菜洗好啊。张老师要骂一句“你学好呀”,立秋已然跑得不见了踪影。
下课后,荣芳上了立秋和张老师家。张老师蹲在地上洗菜,让荣芳坐。荣芳问立秋呢,张老师说,拿着鱼竿跑了,也不知道去哪里,你等下,他再不回来,我给你做。他喃喃地说,这家伙,今天还逃了课,被我撞了个正着。荣芳就说,我去找找。
荣芳在河边的桥墩下,找到正在钓鱼的立秋。那天很冷,风吹得桥墩委屈地嚎着,立秋蹲在地上的背影,让荣芳有些心疼。荣芳走近。我猜你在河边,你倒是会找地方,让我找了好一会儿。
立秋“嘘”了一声,示意荣芳别出声。荣芳就突然紧张起来,在旁边蹲着,眼巴巴地望着水面。约摸坐了十来分钟,浮漂一晃,立秋赶紧拉线,一条河鱼上钩了。立秋站起身,得意地掂量了一下,感觉鱼有个把斤的样子,开心地说,走,你的生日礼物有了。
荣芳边走边说,这么冷,你钓这鱼,就为了给我礼物啊,不划算呢,这么冷的天,可以明年春天再补也不迟。
立秋说,谁让我今天有时间呢。
荣芳说,张老师说你还逃课了?
立秋说,老师上课太无聊了。
荣芳跳起来打了立秋的肩膀一小拳头。她毕竟太小了,拳头软软地落在立秋肩上。她说,你长本事了呀!
立秋乐,不疼。
那晚上,他们喝上了新鲜的河鱼汤。荣芳只是低头喝汤,不做声。张老师感概万千,说立秋跟他住了一年多,愣是不知道他做鱼也这么在行。立秋说,老张你要是喜欢,以后你多买鱼呀。张老师丢过去一根鱼刺,你倒是想得美。
又到了洗碗时间,立秋用手肘碰荣芳,荣芳白了他一眼,向旁边移了两步。立秋移步过去,荣芳就拐了他一下,你走开,不要挨擦挨擦的。她说这话时,脸很红。
立秋照例送荣芳回去,他们照例要走一段河堤。荣芳问立秋,你说春天河里鱼会不会更多?立秋说,不知道。荣芳说,你做的鱼很好吃。立秋说,那我以后都给你做。荣芳说,那你可记得了。立秋说,记得。
去往学校的路,是三米来宽的马路,蜿蜒着爬到半山,就是学校大门。准备上山时,荣芳说,我带你走另一条路吧。立秋竟然不知道还有另外的路。荣芳说,跟着我,不会错。小路在另一边。是很狭窄的小路,要穿过很多低矮的房檐,有些破旧的小卖店,能够看到坐在不远处吃饭的一家子,听到路边房子里传来的低声细语。很安静,也有点黑。
路窄的地方,他们的身体就碰在了一起。走着走着,立秋就去抓荣芳的手,荣芳手一甩,立秋抓了个空。眼看不远处就是出口,立秋竟然有些心慌,他再去抓荣芳的手,荣芳依然一甩,身子不经意撞了立秋一下,立秋就顺势撞在了墙上,有些疼,他“啊”一声。荣芳赶紧问,怎样,疼不?黑暗中他们看不清对方的脸,只听得见荣芳焦急地询问。立秋说,疼。荣芳伸手来摸立秋的头,立秋顺势就把那手抓住了,紧紧地,荣芳挣扎,没挣扎开。走了不到十米,小路走完了,立秋赶紧松开了荣芳。荣芳快步向前,和他拉开了距离,一前一后地进了学校。
后来,荣芳想起立秋,最常想起的,是紧紧跟随在身后的细细碎碎的脚步声,不大,但听得真切,很有节奏感。那声音让她感到安全,知道在不远的身后,有一个人一直在。他们持有某个固定的距离,那是一个安全的,亦能确保安全的距离。她喜欢那脚步声,也喜欢那距离。
后来,立秋想起荣芳,最常想起的,是数米开外的那个清瘦单薄的背影,和偶尔扭转回来的脸庞。她不说话,但她的眼神里,有信任。他曾经享受过学生会主席和校刊主编的荣光、权利,但这些都不及走在荣芳身后时有成就感。他会觉得自己是有用的,心里是满足和温暖的,他喜欢这种感觉,却又不止于这种感觉。
后来,时间很快就到了假期,立秋回到了落烟。走之前的晚上,他们照例一起吃饭,立秋没有送荣芳,因为荣芳姐姐正要接她走,她们家就在沙溪,离得不远。张老师和荣芳姐姐低声热烈地讨论什么的时候,荣芳问立秋,你明天走吗?
嗯,一早就走。
我不能去送你。
没事,我没事。
有多远?
十几个小时吧,早早走,晚上睡觉前汽车该能到。
荣芳充满忧愁,太远了。
是啊,太远了。
听说落烟很穷。
立秋点了点头,没说话。
他们又到阳台上站了一会儿。立秋伸手去摸荣芳的手,荣芳避了一下,立秋就抓着她的中指,不放。就那么站着。冷风吹着他们。后来,荣芳就被姐姐叫走了。立秋一直站在阳台上,看到他们走到院子里,看到他们走出院子,看到天黑黑的。冷风让他打了个冷噤。
转年春天的时候,张老师和荣芳姐姐要结婚的消息,就传开了。
立秋问张老师,老张,真的假的?
张老师说,百分之千是真的啊!
立秋去到学校,慌慌张张就去找荣芳。这是他第二次到荣芳所在的班级找荣芳。荣芳看到他,又一脸慌张,扭过头,假装没看到。同学们大多认得立秋,立秋便叫其中一人,麻烦叫一下荣芳。荣芳红着脸出来,小声嗔怪他,都说了不许来找我。
张老师和你姐要结婚了。
我知道啊。
他们要结婚我就不能住那里了。
这又有什么关系,你本来就有宿舍的。
那我就不能做吃的了。
立秋看着荣芳。
荣芳一愣,感觉有什么梗在嗓子里,很难受。正好到了上课时间,荣芳被人流裹挟着,进了教室门。
立秋那几日郁郁寡欢的,见什么都不顺眼,吃什么都不合口。他又去找过荣芳一次。荣芳不愿意他到班级门口去找她的,他却去了。荣芳看了他一眼,出了教室门,就一直往前走。立秋紧紧跟着,他们穿行在课间站满学生的楼道间。立秋,都说了不要来班上找我,不好。张老师要结婚了,我就得搬出来。搬出来就搬出来吧,你住到宿舍,也是一样的。可是我不能做饭了。不能做就不能做嘛,在食堂吃。不一样的。哪里不一样?我。你回去吧。
张老师一忙起来,就无心关注立秋了。立秋心里惶惶恐恐,时常心不在焉。张老师忙里偷闲,像突然发现立秋,立秋你要没事,帮我收拾一下,我要在这房子里结婚了。立秋说,我明天就搬走。张老师笑,不急,哪有那么快,还有两个月呢,只是得提前准备,也算是个小装修,你差不多再搬走不迟。出门前,立秋对张老师说,我下课后去买菜,你叫荣芳她姐吃饭嘛。张老师不解地看着他,你这是?老张,我这不帮你们创造机会嘛。
荣芳姐姐自然是带着荣芳来的。饭吃得很平常。饭后回去的路上,他们走那条黑乎乎的小路,立秋试探了一下,终于牵住了荣芳。立秋说,张老师说我可以待到他們快结婚的时候再搬。荣芳说,嗯。立秋说,你多去吃饭吧,不然我搬走了就没地方做饭了。荣芳说,嗯。
荣芳隔三岔五就往张老师家去。她已经叫张老师姐夫了。他姐夫长姐夫短地叫,张老师很高兴,安排立秋负责招待好荣芳。张老师沉浸在即将大婚的喜悦和紧张中,哪里顾得了他们俩。
他们饭后往回走的时候,刚进学校没多远,迎面就走来了一个黑影子。荣芳。那黑影子冲荣芳喊道。荣芳一惊,老师。立秋立马晃了,杵在数米开外,不知是走是回。黑影子就是荣芳的班主任老师。班主任问,大晚上的,你去哪里?荣芳说,我,我,散散步,老师您也散步啊?班主任说,大晚上,别乱走,赶紧回去。荣芳说,好,好。说着赶紧小跑着,往宿舍楼去了。立秋尴尬地杵在哪里,看到荣芳跑了,赶紧折回身,逃走了。
张老师很快就要结婚了。立秋说,你来,我们吃最后一顿饭,以后可没机会了。荣芳说,好。
班主任找到荣芳时,荣芳正盘算着下课后去找立秋。班主任把荣芳叫到办公室,荣芳,你是好学生。荣芳心里就虚了,老师,请问您找我什么事?班主任说,最近,我听到了很多不好的话,关于你的。荣芳说,我,我。班主任追问,你是不是在谈恋爱?荣芳更慌了,我,我没有。班主任说,很多人都告诉我,你和学生会的立秋走得很近。荣芳说,我们是朋友,他跟我姐夫住在一起。班主任说,我不管你们什么关系,别让我看到你和他在一起,不然我就告诉你爸了。荣芳爸是班主任的同学,也是沙溪财校的毕业生,不仅荣芳爸,荣芳的哥哥姐姐妈妈,都和班主任认识。
荣芳出了办公室,就犹豫了。她终于没有去找立秋。立秋那天炒好菜,还没等到荣芳。菜凉了,还没等到荣芳。张老师忙完,看着桌上的菜,咦,懂事,等我吃饭呢。立秋慌忙站起来,老张,你够了,现在才回来,菜都凉了。张老师说,没事,热一下。立秋说,你自己热吧,我突然胃不舒服,不想吃东西了。
班上是不能去了,不然荣芳真得急。午饭时间,立秋就早早在路边等着,学生们很快就排了长长的队。眼看着荣芳过来,立秋一个箭步赶上去,正好排在荣芳身后。他说,昨晚菜都凉了,你没去。荣芳说,有事。立秋问,什么事?荣芳说,你别问了。打完菜,立秋端着餐盘,看到荣芳坐在不远处,他就坐在旁边的餐桌上,拿眼睛看荣芳,荣芳一直低头吃饭,没抬头。立秋心里很酸,只吃了一半,端着餐盘走了。
张老师的婚礼简单,倒也温馨。招呼完客人,立秋送荣芳回去。在那条小路上,立秋再去牵荣芳,荣芳就不干了。荣芳说,以后我们还是离远点吧!立秋问,为什么?荣芳没说话,自顾自地走。有一阵子,她听不到任何声音,以为立秋生气了没跟着,走到宿舍楼下,一回头,立秋站在不远处,死死地看着自己。她心慌,不敢说话。
立秋终于是忍不住了。他很生气。那种闷气,说不清理由,堵在心里,难受。毕业临近,未来飘渺。他心里的气,也便汹涌起来。那天他打好饭,搜寻到荣芳,就坐在不远处。他想也没想,堵着气,便坐到了荣芳的对面。荣芳吓了一跳,愣了一下,端起盘子,饭也没吃,跑了。要知道,那可是他们第一次在学校食堂坐在一张桌子上,时间不过三五秒。
荣芳怕,怕被人看见,看被人瞧出来他们之间虽然没明说但彼此心知肚明的关系。立秋也怕。学校管得严,马上要毕业了,这时候出纰漏,对自己影响很不好。可是他就是生气,什么也不管了。
也许这就是结局吧!立秋想。他这么想时,便开始打包行李,买车票。待天黑下来,他心慌慌的,行李已经打包妥当,只待明日走人。他心里乱,下了楼,往沙溪河边去。
荣芳找到立秋,你还真会找地方。立秋那时候坐在桥墩下,是早前他钓鱼被荣芳找到的地方。我问了你室友,他们说你出来了,我不知道你在哪里,就到处找。荣芳说,我不是故意不理你。
立秋没接着这话题。他说,我明天早上走。荣芳哦了一声,有多远。立秋说,你以前问过了。荣芳说,我还想再问一遍。立秋说,不管远不远,你也不可能去。荣芳沉默了一会,谁知道呢。
后来他们再也没有说话。夜色一下子就覆盖了他们的脸。日夜不息的沙溪河,日夜不息地流着。
回去的小路,很短。他们都心慌。心里梗着话,谁都不说。快要走完时,荣芳终于忍不住,转身抱住了立秋。立秋,我不想你走。她哭出来。不停地哭。立秋一时不知所措,我在,我在的。他说着,紧紧抱住了荣芳。
很多年后,立秋一直难以忘怀的,是那天晚上的拥抱。那是他们在一起期间,最亲密的接触。
第二天清早,立秋拖着沉重而杂乱的行李离开时,在校门看到了荣芳。我请了病假,送你去车站。荣芳固执地去抢立秋的一个背包。她小小的身子,背着立秋的背包,显得有些笨拙。
你走我前面。荣芳说,我看着你走。
立秋说不,我喜欢走你后面了。
荣芳嘟着嘴,犟在路边,一直以来都是你送我,这次,我送你。
立秋就应了。他慢慢走在前面,时而回头,看荣芳一眼。立秋快,荣芳就快,立秋慢,荣芳也慢。他们上了公交车,下了公交车,跻身于车站拥挤的人流中。人一挤,他们就散了,越来越远。
立秋回到落烟,夏天突然变得盛大起来。盛夏时,他到了落烟一个边远的乡镇财政所工作。
所里只有四个人,都是男的,一个所长,一个副所长,两个办事员,立秋是其中一个办事员。除了立秋,其他都是中年人。所里业务少,他们最大的消遣,就是打牌,打麻将,喝酒。喝醉了他们就唱歌,不是流行歌,是一些当地小调、山歌。副所长最喜唱山歌,声音也好。
到的第一晚,大家为立秋接风,菜很简单,酒却很多。是一种叫苞谷烧的酒——这种酒用苞谷酿制,喝起来暴性很大,也很烈,立秋抵不住几杯,就热,困。迷迷糊糊时,大家就怂恿副所长唱歌。副所长假装推辞二三,便唱:赌你来,赌你穿过九层岩。麻杆大桥赌你过,十二花园赌你来。立秋听不懂,感觉歌词也没啥意思,就是那曲调悠悠的,绕来绕去,让人起鸡皮疙瘩。唱罢,其他人不满意,要求他来个带劲的。副所长清了清嗓子,压低声音唱:洞门小妹矮咄咄,一对奶奶像牛角,哥哥有个烂脾气,不摸奶奶睡不着。立秋听着,面红耳赤,也不知道是酒精作用,还是山歌撩人。
财政所离城三十余公里,路况极差,往返很不方便。如果没什么特殊事情,立秋一般半月回次家。他给荣芳写信,从镇上寄出去,普通信件,五天左右,才能到沙溪财校。荣芳回信,问他,你会来看我吗?差不多六天后,立秋的回答写在信笺上,会的。
谁都没有提彼此之间那种不曾言明的事情。
荣芳给立秋寄信,是特快。特快自然比平信快。她每天都去收发室,问自己的信件,收发室老头慢慢就认得她了,冲她说,又来啊,没你信呢!她也不说话,低头就翻找,自然是没找到立秋的信的,失落着走了。往后,老头也不说没有信的事情,只说,来了一堆,你翻翻有没有。她依然在那里翻,很认真地找立秋和自己的名字。没有。还是没有。
没有立秋的信,她就想,立秋是不是不理我了,越想越难过,越难过越想。五六次后,立秋终于来信了,说,过阵子,我去看你。她又心花怒放,想着立秋,很快就能来了。但第二天,又一如既往地去找信。
立秋请了半天假,回到落煙城中,正好赶上最后一班去往沙溪的车。晚上十来点,车到沙溪。刚出站,荣芳就跳了出来。我就知道你会来,她几乎是哭了。立秋心里很难过,嗓子涩涩的,几乎说不出话,你怎么在这里等着,这么晚了。荣芳说,你信里说今天要来的,下午三点我就来车站等你了,我不敢走,总觉得再等上一会儿,你就到了。立秋说不出话来。荣芳说,幸好你来了。
立秋要哭。荣芳推着他,走,我们吃凉面。沙溪小吃众多,凉面是其中一绝。立秋说,好。
车站离学校远,他们牵着手,在路上走。看见一家小旅馆,立秋犹豫了一下,要不,住这里?荣芳拖着他往前走,不好。又走过一家,立秋想住,荣芳不。走走停停,离学校就越来越近了。正巧,熄灯前,他们进了大门。立秋,也就有些不情愿地住进了朋友的宿舍。
信函里断断续续地谈话,并未在现实生活中承续下来。荣芳问得多的,还是落烟的情况。她早已找身边的人探过,知道落烟这个地方,边远,贫穷,远不及历史悠久的沙溪。她不敢想象自己生活在落烟的境况,她是家里老小,又是女孩,遥远的地方不敢想。但心底里是想在立秋身边的。
她问,你在落烟过得好吗?
还好,只是比较无聊。
那你平常都干什么?
写作,睡觉,打麻将,也喝酒。
真无聊。
立秋沉默了一会,你去找我玩。
荣芳慌忙摆手,不行的,我爸妈要是知道我去那么远,铁定打死我。
立秋就不说话了。待到分开的时候,立秋问,你都不会去落烟?
荣芳愣在那里,我不知道。
到分别时,立秋和荣芳,都感到一种伤感。谁也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落烟和沙溪,离得太远了,谁也不知道,这一别,又要等多久才能相见,甚至是否还能相见。他们小心翼翼地分别了。
立秋再次回到落烟,回到那个小小的财政所。依然写作,依然和同事们打牌打麻将喝烧酒,依然和荣芳通信。只是渐渐地就有了一种疲倦感。荣芳依然一次次去收发室翻找信件,这件事已然成为一种习惯,但那种以往找不到立秋的信的失落和找到信时的欣喜感竟也不知不觉间淡了。
所长看立秋年轻,不太能和其他人打堆,便寻思着给他介绍对象。不远处的中学正好有几个刚从师范毕业的老师,长得不错的也有,其中一个,看着挺合适。所长和校长老熟人打了个招呼,两堆人就凑到了一起吃晚饭。
依然是简单的菜,由立秋操刀。中年男人女人们只顾着嗑瓜子、聊天、打牌。菜上齐了,财政所和学校的联谊就正式开始了。酒喝开来,大家就把立秋忘了。立秋倒也乐意,毕竟和这些中年男女都聊不来。
那姑娘来得晚,连连抱歉,说回了家一趟,正好母亲有点事,耽搁了。中年男女们身子一缩,就腾出了一个空,正好在立秋身边,说,没事没事,小江老师,你快坐。所长已然微醺,站起来,舌头有点不灵光了,介绍道,来来来,小江,我给你介绍,这是我们立秋同志,刚毕业来参加工作的,你们年轻,多聊聊。说完向立秋使了使眼色。立秋觉出什么,脸一下红了,再看小江老师,她的脸也红了。
原来两人都不知道那顿饭的意义,直到相互看过了,聊过了,才知道着了同事们的道道。小江老师说,立秋,听说你喜欢文学书籍?立秋说,有一点。小江说,我也是,以后我找你借书。立秋不好推却,便答应了。
立秋给荣芳写信说,所长给自己介绍了个姑娘,莫名其妙就见上了,姑娘在学校教书,就是镇上的人,来找过自己几次,都是借书。原本是把自己的生活告诉荣芳,荣芳回信说,这也好,毕竟她离得近,可以照顾你。立秋看了信,字写得很工整,就是信笺有些皱巴巴的样子,看不出荣芳写信时的情绪。
落烟的海拔比沙溪高很多,冬天,比沙溪来得早。风呼呼吹着所里的小门,发出恐怖的声音。立秋想着,荣芳的生日快到了,就给她写信,告诉她,要去陪她过生日。他算过了,荣芳十八岁生日的时候,不逢周末。这也就是说,他得请上至少两天假,但也意味着荣芳不会被叫到家里过生日。
荣芳回信是几天后。荣芳说,好。就一个字。很干脆。
荣芳写这个干脆的“好”字之前,她写过两封信。一封里,她拒绝了立秋,让他不要来了,先说路途远,又说天气冷,最后说,我不可能去落烟的,就算想,我爸爸妈妈也不会同意,而且我还太小。另一封,她答应了立秋,却又说,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这两封她都不满意,撕了,写第三封时,她想了很久,心里很为难,最后狠了心,写到,好。这“好”里,意味多了。
上车的时候,立秋心头涌起一阵悲壮。他心里有种奇怪的感觉,这一程,从一开始就是悲壮的。荣芳依然逃了课,在车站接到又冷又饿的立秋,带她去吃当地有名的羊肉粉。他吃粉,她就那么看着。然后顺着沙溪河岸,一直往下走。她没有再问他落烟的事,他亦没有多话。
晚上在一家看起来不错的餐馆吃饭,点了六个菜,一瓶白酒。那是他们一起吃过的最贵的晚餐,但菜并没有想象中的好吃。他们吃了一半菜,喝了三分之一酒,都有些微醺。聊了很多,酒精让他们说了许多暖人暖心的话。
看起来如同往常。
夜越来越深时,他们都有归去的意思。立秋试图留荣芳找一家旅馆,荣芳拒绝了,他们一起往学校走。路,是以前的路。人,似乎也是以前的人。他们之间的距离,还是那么几米。到了宿舍楼下,荣芳就在阴影里站着了。荣芳转身,对立秋说,立秋,谢谢你陪我过十八岁生日,我很感动,能遇见你,我也很幸运。立秋想说话。荣芳又说,但是,立秋,以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她说完,转身就跑进了宿舍。
立秋在荣芳的楼下站了许久,他不记得站了多久,只知道自己的腿似乎是肿了。荣芳在阳台上看过,看了一眼,没敢再看第二眼。她没有哭。
凌晨时,立秋就被朋友拉走了,住在朋友的宿舍里。
回去的路是火车从省城转,因为当天汽车返回。立秋下了床,天还没亮。火车是上午九点五十五,他就着冷水洗了把脸,就出了门。直奔火车站而去,头也不回。也不敢回头。
荣芳赶到火车站,立秋的那趟车已经快开了。她拥挤着买了一张站台票,去找立秋。她原本不去送立秋的,虽然心里很想,但她知道不能,快刀斬乱麻,才是最好的办法。可是终究是没忍住,跑了出去。
站台很挤,很多送站的人,在寒冬里张望着即将远行的列车。荣芳踮着脚尖,寻找立秋的身影,但她并不知道找到立秋能干什么,她怕立秋看见自己,却又希望立秋看见自己。她甚至很绝望地想,立秋要是坐在另一边,那就真的永远看不着了。
荣芳一直都没有找到立秋。
火车启动时,立秋站起来了一下。他一直是坐着的。车上很吵闹,他就那么闷闷坐着,等车开。车启动时,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站起来了一下,然后看到了站台上人群中瘦瘦的荣芳。寒冬里,她显得更瘦了。
立秋的心里很酸。荣芳在到处张望,但并没有看到自己。他心里想,算了吧。和沙溪,和沙溪火车站站台上的荣芳,作了无言的告别。
回到所里没几天就下雪了。这几日立秋都没睡好,精神状态很差。小江来还书,说好书要分享,见立秋话少,也就自讨没趣地走了。雪越下越大,地面铺满积雪的时候,邮差就把信送到了所里。
荣芳寄来一张站台票,没有只言片语。
立秋沉默良久,想哭,眼睛干涩,没有水分。他给荣芳写信,告诉她他看到站台上的她了。就这样,也没有说多余的煽情的话。像一种答复。
荣芳没有再写信来。
后来很多年,立秋偶尔想起和荣芳的分离,心里都会有一丝丝难过。他一直没弄明白和荣芳分开的原因。他几乎就要忘记这个叫荣芳的人了。
2018年春天,荣芳去省里开一个商业会议,邻座的男人自我介绍来自落烟。荣芳心里有细微的触动。每次在路上看到路标写着“落烟”,心里都会有种类似的触动。她心里知道,在落烟,有一个曾对自己很重要的人。
茶歇时,荣芳和来自落烟的男人聊天,我有个很要好的朋友就在落烟。那人说,是吗?真有缘!荣芳说,只是,很多年不见了,也不知道现在怎样。那人就问他,人是干什么的?荣芳说,我只知道他最初回了落烟,不知道后来离开没有,如果没变化,应该在财政部门。那人说,叫什么名字?荣芳想了下,立秋。那人起身打了个电话,一会儿,拿着手机回来,我给你找着了。
那人在便签上写下立秋的电话,荣芳接过来,也就放在了手提包里,一时不知道该不该打。好几天后,荣芳打电话过去,立秋正在忙。领导忙着要材料,他已经加了一晚上的班了,手机静音在侧,一心应付领导的材料。等到忙下来,看到陌生来电,再打过去时,荣芳又忙了。工厂那几日有大订单,几十个工人忙得焦头烂额,荣芳也跟着忙。电话来时,荣芳一时不知道是谁的,她忘记存了,但来电显示“落烟”,让她突然明白过来。
她在吵闹的车间接起电话,喂。
立秋在另一边,喂,我看到您的未接来电,请问你是哪位?
荣芳说,你猜猜。
立秋说,猜不到。
荣芳说,你仔细听听。她走到相对安静的地方。
立秋沉默了半晌,试探地说,荣芳?
那天荣芳实在太忙了,聊了几句,就挂了。后来他们加了微信,断断续续地聊些天。彼此的这漫长的生活也就渐次地展露出来。
荣芳毕业后,进了沙溪财政局,干了两三年就离职了,开始做生意,到处跑。这期间,她结婚了,生活看起来很好,孩子听话,生意也不错,有一家规模中等的工厂,四五十个工人,成为了常人眼中的成功女性。
立秋并没有和学校的小江老师在一起。工作的第二年,因为写作上的优势,他得以离开了那个小镇,到县财政局工作。二十五年里,他结过三次婚,有两个孩子,分属于第一任妻子和第三任妻子。他从县局又到了市局,当起了中层干部,过着一个中年男人最为平常的生活。
谁也没有提往事。有一天,荣芳微信上说,这么多年,常常在路上看到落烟的路标,但神奇的是,从没去过一趟。
立秋说,那就来看看吧!看看这个地方,也顺便看看我。
荣芳说,算了吧,相见不如怀念。
立秋说,懷念可以,别等到只能悼念。
荣芳准备来落烟时,立秋刚开完一个烦躁的课题会。荣芳说,我出差归程,想转道去看看落烟。立秋说,好。
宴席是立秋提前订好的,房间也是,在城郊的一个山庄。那里做特色菜,环境很好,适合小聚。他约了些朋友,都是些庸碌尘世中交心的友人,以世俗中最好的阵势招待荣芳。在去落烟东收费站接荣芳的时候,他心里一直反复想,这么多年没见的人,会长成什么模样?是风韵依然,还是早已被时光消磨了容颜成为一个平凡的大妈?但无论是什么样子,这一场见面,属非见不可,有些话,需得当面重新提起。
荣芳驾一辆看起来不错的宝马从高速下来,停在了路边,电话响起时,也就看到了不远处站着的立秋。见面的一瞬间,相互笑了一下。立秋说,我们去吃饭。荣芳说,好。立秋说,听我指路。荣芳说,好。
到山庄预定好的房间,围餐桌对面坐下,他们才仔细打量起对方来。彼此都老了许多,相视时,又能从如今的容颜里记认出依稀的模样。
荣芳保养很好,比以前高,身材也好,皮肤白皙,穿一件黑色的长裙子,头发松松地扎着。看着看着,立秋的心里,就起了波澜。遥远的细节,涌上心头来,牵手时的紧张,拥抱时的激动,恍若昨日。不得不说,他突然就冲动了。
在荣芳眼里,立秋苍老了许多。她知道他快五十岁了,样子却不太像。苍老,只是和记忆里那个人相比较的。她坐在那里,感到安全。
约好的人,陆续到来,很快,五六个人,也就围满了餐桌。聊上没几句,来的人,也都慢慢觉出来他们之间微妙的关系。
开饭前,荣芳说,立秋,你坐我旁边吧!
立秋有些不好意思。
大家就起哄,去吧去吧,又不是没挨着坐过。
立秋就扭扭捏捏过去了,挨着荣芳坐。
荣芳分享一些奇怪的小吃,来自于某国。她前不久刚国外旅行归来。挨着劝大家品尝时,她说,好东西就是要分享。
大家就说,你们的故事也要分享,我们今天,就拿你们的故事下酒了。说时,一瓶茅台酒上了桌。
荣芳不喝酒,喝白开水。立秋是喝的,酒过三巡,大家还起哄,让他们说故事。立秋不说话,一句不说,荣芳也是,说我们没什么可说的。再喝过三巡,立秋依然不说话,荣芳倒说了。
细细碎碎的,都是些遥远的旧事,试探,跟随,碰撞,别离……荣芳说来平淡,听者便时时饮上一小杯。气氛渐渐活跃,立秋插话进来,对其间的一些隐约的细节作了补充。
他一直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分开。荣芳提到最后分开的话题,点了一句。
立秋喝了杯中酒,那时候是真难受。
听者便问,那是为什么?
立秋说,不会是有了新的人了吧?
荣芳沉思片刻,那时候就是怕,怕遥远的距离,怕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的贫穷与偏僻,怕家庭的阻拦,而他也正好没有给我那种能让人奋不顾身的动力。
立秋叹了口气,继续喝酒。
这么多年,就想着,有朝一日要来落烟看看,这回终于是来了,地方见着了,人也见着了,我不遗憾。这话,荣芳是发自内心的。
立秋一贯少语。倒是听者问,那时候要是不分开会怎样?
立秋就笑了,荣芳也笑。立秋说,谁知道呢?或许早离了。
荣芳说,如今看来,分开不见得是什么坏事,那时候美好的事情,如果走入婚姻,柴米油盐、鸡毛蒜皮,谁能保证感情能一直保鲜?也许真如他说早离了,也可能依旧深情地在一起,更多可能是麻木地彼此扛着一段感情。你看分了,不见得多坏,至少现在想起来,都是美好。这么多年不见,最初那种干净美好还在。像突然之间一个亲人失而复得。现在的感觉,真的像亲人一样美好,他像个哥哥。
她边说话便给立秋夹菜,还真像从未失散的两人,像恋人,也像亲人。
立秋大多时候不说话,他从侧面看荣芳,很好看,更甚于曾经。心里的感觉,很复杂。
饭毕,夜有些深了。友人们寥寥打笑,便散去了。把山庄的寂静,留给他们俩。
他们顺着山庄的小路散步。荣芳穿了细细的高跟鞋,走了没多久,便有些撑不住。立秋看着她,累了吧?她便挽了他的手臂,脚疼。曲折小道平缓幽深,有的地方漆黑一片,行人寥寥。感觉有些累了,便打道回房。有一段小道,没有光,很像沙溪财校外的那条捷径。立秋心中一动,一把牵住了荣芳。
剩下的路,就变得非常漫长。明明住处不远,立秋却觉得很远,他着急地牵着荣芳走,他在追赶着什么。房门洞开,立秋就翻身抱住了荣芳。荣芳一怔,没有反抗。他吻她,心跳很快,她有一时的无措,随后有微微地抗拒。他将她放倒在大床上。一种近似于疯狂的冲动,狠狠地冲击着他的内心。他抚摸她的脸,颈脖,胸部,撩开她的裙子,吮吸它们。
荣芳的眼神复杂。惊异?妩媚?幸福?厌恶?好像都有。她在迎合他,却也似乎在抗拒。她环住他脖子的手臂,竟然有一丝丝的颤抖,是恐惧,还是激动?立秋不得而知。
有一刻,立秋的脑子一片空白,随后往事无端涌起,无数声音交织。我这是在干什么?这阔别二十五年的相见,难道只是为了完成当年的遗憾?这场性事,是从联系上的那一天开始,就注定了的吗?之后呢?一别两宽,藕断丝连?他管不了那么多了。
然后那自问的声音消失了。荣芳微微的呼吸声,渐次大了起来。她神色中有迷离,又有挣扎。她试图在决定什么。她的手开始使劲地推着立秋。立秋,立秋,不行啊。立秋疯了似的。她推,他不为所动,固执地探取她的身体。她心生悲哀,像坠入无边的大海,呼救,却无人应答。她几近于放弃,不行啊,哥。
立秋怔在那里。什么?
荣芳喘了口气,不行啊,哥。
立秋久久看着身下的荣芳,她身上的衣服,几乎是要脱完了。荣芳有些犹豫,放开了推他的手。立秋没有动,他看着荣芳的脸,慢慢地,一滴泪落在了荣芳的脸上。
清早,他们在山庄吃了简单的早餐,便去城区和附近的一些景点,去看过如今只隔着四十分钟车程的立秋最开始工作的那个小镇,也去立秋的中学旧址坐了坐。天快黑时,立秋送荣芳上高速。
在荣芳走后的落烟东收费站外,立秋突然心里很难过,很难过。此刻,荣芳正在离立秋生活的落烟越来越远。他们离得越来越远了。
立秋拦了辆出租车,在车上给荣芳发短信,说,注意安全,到了说一声。他又突然变得平静,像在叮嘱一个远行的亲人。
时代已经拉近了落烟与沙溪的距离。当年横亘在他们之间的大山、河流,当年连接他们的山路、桥梁,都已经在时代变迁里被高速替代了。但他们之间,已然被定格在一个固定的距离,遥遥相望,想来温暖、安全,不会离得更远,也不会靠得更近。立秋想,他和荣芳之间,也许真的就如同亲人了。
他明白过来,这时代裹挟着每一个人奔涌向前,身后的路注定是回不去了。
两个小时后,荣芳抵达沙溪。她给立秋发微信,我到了。立秋說,好。
那时候,立秋在客厅看电视。天色已晚。妻子在卧室陪孩子说话,声音隐隐约约传来,家里很安静。立秋关了电视,走进卧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