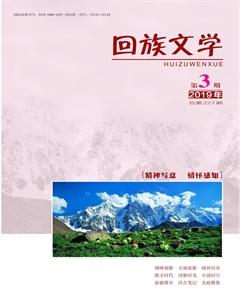走隆德
题记:现代性迫使人们不停地删除,可就血亲而言,隧道里的基因是无法更换的。尽管有人不屑于这种血浓于水的原始乡愁,可,作为生者,在愈加严重的代际隔膜中,至少应该有一次庄严的生命呼唤。
一
为了母亲的微笑,小妹断然决定走隆德,这消息尽管来得仓促,却并不削减我将“出发”的喜悦。想了许多年的还乡之旅终在今日得以实现,想象中,老屋的柴门,是要摸一把的,老井的古水是要掬一捧的;最好能在老家的泥土院里感受一下黎明的晓月和夜晚的星空;如果再好一点的话……嘿,二十日走,三十日归。时间紧迫来不及多想,快快将大脑扫描一遍,一些零散的记忆浮上了心头。
我的祖籍在隆德。父亲卖身葬父离家后,奶奶天天站在梁头上等他回来,等盼了四十年;后来,奶奶眼睛哭瞎了,临死一月,直立山头天天喊着我父亲的小名儿,望着他离去的方向,长长短短地、一声一声,呼唤着远去的孩子,直喊到咽了气……而我的父亲,到奶奶离世也没能回去……这些心酸的往事都是听姑父讲的。我姑父姓靳,叫靳民居,常以身为陕人而滔滔不绝。他活着的时候只要有机会说话,不管问不问,他都会拉着怅怅的秦川调儿用他沙哑的声音讲述过去那些天朝黄历和隆德旧事。
他说隆德由于处在陕西宁夏甘肃三角中心,明初属于陕西平凉静宁州,清代归甘肃管辖,后来才划拨给宁夏的。他说民国九年,老家发生过一场八点五级的地震,当时房屋倒尽人死过半。震后第二日,老天余威不减,山城境内扬风搅雪飞沙走石,冻死者难计其数,流離惨状口不忍述……他说大姑就是因饥饿时吃了发芽的土豆毒死的;三叔最可怜,因误烧了人家的麦场,活活被打成了傻子,后来抓进监狱,是出狱后走在回家的路上病死的;还有一个小媳妇穷日子过不下去,就喝毒药自杀了……在苦难的记忆打捞中,知道老辈人早已离世,去看的亲人,是这棵苦树上稀稀拉拉吊的几个“小果子”,无奈人还没有迈出一步呢,心就像被什么东西给咬了一口,无端的痛疼感莫名袭身,一鞭子,一鞭子抽打在我的身上,我那些未曾见过面的亲人们呀,这是怎样的一次寻亲呢?
临行前,上网查看,又一猛棍打上头来——父亲生前所住的那个杨沟乡已不存在了,地图上抹去了它的名字,村民按照国家“吊庄移民”的政策都拔“萝卜”挪到了别处。没等我回过神来, 十年前去过老家的大妹、二妹便吹起冷风——咱们的“苦根”,长在寸毛不生的石头上,那难走的路,土厚如墙,行车如牛,那时我们进庄子,是智雄弟用手刨土,才刨出来路。
二
从新疆出发,在银川落地。
没料到想了几十年的回乡路,真正付诸于行动,仅仅用了两小时。
下飞机后,成群的喜鹊迎面飞来。大伯的儿子陈智雄来接我们,一见面,就风趣地对着那些热情的鸟儿说:“知道、知道,别叫了……”
“你长得太像姑妈了,深眼窝,卷头发……”小妹一见到智雄弟,很快就和他聊起来。
第二个见到的亲人,也是一个卷头发,深眼窝……他是我大姑的儿子,长得极像我的父亲,七十年代初,他去过新疆,在我家住了一年多,只听他远远喊了声“妗子——”就扑到我母亲身上。
“妗子”,隆德话的意思是舅妈,因我父亲在长辈中排行老二,所以,老家的人称我母亲为“二妈”。
亲人们相聚。
十年前托大妹送我彩色香袋的堂姐来了,忙前忙后,为我们端水递茶的弟媳妇来了……
我们没有抱头痛哭,在相互的对望与寻觅中,我走过去抱了一下我的堂姐,堂姐名叫陈巧蕊,是宁夏石嘴山市龙湖区王站村的新迁户。她盖了新房,娶了媳妇,穿戴整齐,上下一新地站在我的对面。可,我那时,握了她的手,拥了她的身体感到自己热切的心慢慢往下沉。我千里来看的姐姐,在我心目中,是一个高大的堡垒,是龙头,是坚强的战士。但是我抱住了她的肩,却抱不住她那孱弱抖动的心。她用那种呜呜咽咽、含糊不清的语言回应了我。我感到自己被一种叫作“苦寒”的东西给猛击了一掌,冷气袭身,我倒退一步,心上又觉抽了一鞭子。
我哪里能不知道,这个大我两岁的姐姐,当前正是我这个家族阵亡空地上的排头兵……她个子比我高,力气肯定比我大,她的存在是对我的掩护。拉她坐在自己身旁,一种血亲冷热之交错的刺痛让我内心涌起无比的怜惜与悲伤。
她告诉我,父亲回乡的那一年,大伯正在乡里当干部,家里穷得朝不保夕。父亲买了一双鞋、两双尼龙袜送给她,她高兴得一夜睡不着觉;父亲见家人用缺了口的大黑碗洗脸,就去集市上买了一个新脸盆,可,大妈哪里舍得用,擦干净,摆在桌子上当装饰品。临走,父亲留下五百元钱,抓了十个小鸡娃,让小心养着……那夜,她高兴地挤在大伯和父亲的怀里睡着了。
我们这次来,最高兴的是小宝子。
小宝子已年过半百,最佩服的人是我大伯,他说,当时他因为嫂子虐待,不堪忍受,实在没办法,曾去求过大伯。那时,大伯是村上的支书,他想报名参军,大伯不同意,就睡在大伯的炕头上,哭了一夜。半夜时,大伯要看他的脚,问是不是平的,他一赌气,走了。后来,他在火车站背煤,挣了五十元钱,自个儿去了新疆,在二妈家住了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有人给他脸子看……”
小妹问:“你恨大伯吗?”
小宝子说:“才不呢,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如何伟大?”
“他口碑好!威信高。县上、乡上开会,大伯从不做记录,坐在会场上,只管埋头睡觉。有一次大伯到省城去开党代会,主席台上点他的名,问他为什么开会睡大觉?大伯把头一抬,只‘嗯了一声,又作睡眠状。四围的人解释说‘这个人,你们不用管,你看他闭着眼,回去传达时,上面没有想到的,他都能给村民讲得明白得很。”
月亮上来了!
这是2010年的中秋节。
我们在故乡温热的怀抱中说一阵,哭一阵,追忆着父辈人不堪回首的往事。那个团圆日,我们说了很多话,也流了许多泪,等母亲给晚辈们发过“红包”后,便切入了此次回乡的正题。
问:屋呢?
答:搬了!
问:坟呢?
答:不知道!
又问:那么,咱爷爷叫啥哩?
又答:咱不知道!
沉默……等着,想了一会儿,这一次点了名:
“小宝子,你的妈妈叫什么名字?”
“嗯……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吗?不知道……这么说,千里来寻的根,前面是空的?那么,知道名字的,年龄最长、最老的人是谁呢?
小宝子拉长了秦音,那就是……大伯陈有裕了。可是,大伯他……埋在新疆呀?
那年,我大伯得了癌症,当医生将肝癌晚期的结果告诉他时,大伯断然决定去新疆!一生为人谨慎,办事稳妥的大伯,明知自己大限已至,为什么要抛尸他乡呢?我想来想去,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太想念他的弟和他的妹了,他们手足三人活着不能相见、死后是要埋在一起的。果然,西域大漠收留了他们——父亲刚刚去世,大伯就死了,紧接着,姑母也死了,自此,大树西迁,兄妹三人埋骨天山。
三
很显然,这是一趟没有线索的寻根之旅;在我故乡的深处,没有可读的家谱,没有可祭的祠堂,没有可叩拜的老人,也没有可以寻查的历史,没有可寻的答案。可,乡愁是扎在人心上的刺呀!
七十多岁的老母,跟父亲结婚五十多年,这是她第一次回家来拜见公婆。半个世纪的峥嵘岁月,一万八千个含辛茹苦的日子……哗啦啦倒下来,一起堆在了这位老人的心上,山路弯弯细雨蒙蒙,气蒸云海十八旋……自银川到隆德四百多公里的追思路,高度在海拔两千九百四十二米,我们坐着大巴车,越黄河,钻隧道,翻过了红军长征途中的最后一座山,走了六个多小时,于中午两点二十分到达了父亲的出生地——隆德县城。
到家了。
冷风嗖嗖却热泪滚滚。
这个苦甲天下,穷困冠首的小县城,并不像人们传说中的那样破败。相反,它,清凉,静穆,气象如晓月中的旧梦,虽是秋高且抹着一层新绿,气候与地貌类似天山脚下的木垒河,让人感到亲切,优美,一见如故。
回乡来,天放晴,淅淅沥沥的小雨,也停了。偷偷捏着一把汗,祈祷天公作美有奇迹发生,简单地吃过午饭后,我们挥车上路向六盘深处的杨沟乡驶去。
智雄弟也是第一次带着媳妇回乡,他是村子里唯一考出去的大学生。当年在县城里求学走的就是这条路。据说那时他步行走,从天亮要走到天黑才能到家。他说旧时山地上长的野生蕨菜为贡品,被一代一代的人挖光,地皮露出来,荒得很。小妹拿着照相机一面拍照,一面感叹着“回去,要打听一下,宁夏这个姓陈的政协委员叫个啥,把家乡的路修得这样好,要不是他修的这条路,我们恐怕寸步难行呢。”
快到村头了,马上,马上就要到家了,让人发愁的是天色渐灰,下起小雨。
眼见,雨点越下越大,汽车在崎岖的盘山路上开始打滑。远远看见埔堡在云间挺立,表弟指着老家的房子说:“看,就在那”。那时,路边的野狗、野猫开始飞窜,有一些不认识的鸟儿和野鸡在车前闪晃,就像是进了一个野生自然保护区……大约走了四十分钟后,车子在一个三岔路口停了下来。
下车探路,分头去敲那些掩映在树丛人家的门。
所有的大门都不开。
一村人悄然,山林问仙道。我打着雨伞往前走,门上的对联还没有褪色,水井上还有木盖,一扇一扇的门却敲不开。
紧紧关闭着的门,铁锁上了锈,整个村子都是空的!
正要转身,忽见一穿着长靴的男子向这边走来,仿佛从桃花源“冒”出来的武陵人,我们赶快上前求问,他告诉我们说:“这是闫庙村,杨沟村往西走,翻过梁,就到了。”
匆匆忙忙上车来,全身冷得瑟瑟发抖。在我们的心上,这剩下的几里路真是太长太长,眼见天一点一点黑下来,心切切,泪汪汪,路却越走越危险。祖先的家,近在咫尺,触手可及,双脚却不能抵达……车尾打着弯,往下滑, 这可怎么办呀!“苍天呀,我可是带了父亲一起回家的呀!”
司机不敢往前开。
智雄弟急了,指着近在眼前的山梁喊:“看——就那里,老房子……”啊呀!看得见,望得着,眼睁睁就是过不去!
大家急得转着圈,又努力了半天,还是不行!如果宁……可能会……天幕将落下,黑云压阵,雨注如泻,我求呀求,神灵没有降灵。
全部的人,从车上跳下来——
一句话也不能说,直直立在雨中,向同一个方向望过去:我们望呀望,望断天涯,眼前是穆苍苍,青萧萧,层层叠叠崎岖不平的一往秦川;烟云翻卷着清辉笼罩着秋草,和着农田、瓦房、乡间路与天公一起落泪。这是生命分裂的地方,也曾是古战场,汉长城行奴役下苦劳的地方。
古诗源《陇头歌》这样写着:“陇头流水,呜声呜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
好一个肝肠断绝啊——当年我爷爷下世,穷得不能入土,儿子以身葬父,换得两张卷席送亡人入土时,肝肠断绝!后来,我奶奶在盼她十六岁的儿子回家,盼得两眼望穿,双眼望瞎都不能回来时,肝肠断绝!现在,我们千里还乡情切切,泪汪汪,却进不了家门,肝肠断绝!
老祖宗啊——我们回来了。埋着爷爷奶奶的山头,生我父养我父的老屋……你们的儿媳,孙媳,代替父亲而来的孩子们,现在正在被清雨浇身,朔風刺骨,却只能以爷爷奶奶那样肝肠断绝的心情,对着祖先长眠的方向面西而泣……长天共洒泪,揭不开那密密层层的雨帘。秋风同回眸,望不断那千沟万壑的山堑!
这可真是应了一首诗:
八百里秦川长呀
两千里家路远
霜发坟头梦难舍
泪磅礴
断肠人天涯跪相别
山不让路,我们没办法,急匆匆。母亲拔了两棵带根的草,智雄弟刨了一包带泥的土,几个人垂首而立,默默地向着祖山鞠了三个躬,还没等转身上车,我们就被黑暗的莽园吞没了……
回到宾馆,母亲又记起父亲临终前的话。
“七个孩子交给你……成人……”
“你那时……”
“我不想活了,死在家里,又担心娃娃害怕……”
“想不到呀!”母亲哽咽起来。
我们心酸的,又哭了一会,就睡了。
半夜醒来,打开床灯,突然发现墙上有李白《将进酒》草书一首:“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天呐!如此绝诗,谁人抄写在我的床头?那一夜,我睁着眼睛到天明——
四
第二天,太阳刚露头,隆德新华书店的女经理,就来为我们送行。智雄弟急着回银川上班,我们坐大巴到西安,本来说好是先送我们的,结果,突然有变,银川的车要先走,这下慌了手脚,智雄弟与弟媳,大包小包把我们送上车,一个飞去扔来一包热鸡蛋,一个奔来捧着两个烫烧饼……然后拥抱、握手、垂泪,忙忙乱乱地分开了。
告别时,我和小妹不甘心,又跳下车,想在写有“隆德”二字的石碑前留个影。那时,隆德大桥、六盘山、白象河触目可见,背景意义深远。看见脚边有朵粉色的小花孤零零地站在地上摇摇摆摆;一束橘黄的沙棘花突闪过去,听见胸腔里低音的呜咽——小松树,大垂柳,金色的红太阳……我们走了!
就在我们急匆匆六神全忙,饥不择食地拿着照相机狂轰乱炸时,突然,车窗外,爬出一个小孩的头喊着“车走了,车走了……”
多么熟悉的乡音啊!
是那种略带一点陕音的秦川长调:“车——走——了!”
听到这一声烫人的、清亮的童声乡音,我和小妹同时抬起了头,两股长泪从脸上滚落下来……飞速地跑上车后,跌在座位上,快快抱住那小男孩的头猛亲一口:
小老乡,叫什么名字?
中一人!
啥?
就是“中国的一个人”。
好家伙!谁起的名?
我爷爷!
你爷爷是干啥的?
我爷爷叫中宏天,是用毛笔写大字的!
你爸爸呢?
叫中文章!
哦——我的天呐!
再见了,隆德。
来不及听一曲父辈们咏唱了几千年的秦腔!顾不得瞧一眼祖辈们烽烟深处坟头上的无字碑……突觉着忘记什么又留下了许多……小老乡不停地从口袋里摸东西,摸出一把豌豆送给我,我放在手心,金子般的发亮,一数,九颗。分小妹几个,然后包起来,装进纸袋。一会儿,中一人的父母走过来,送给我们一捧沙棘花,这一束“黄梅”还未拿定细看,窗外,一片夺人的锦绣便匆匆闪过。眼睛赶忙移出去,又是观光又是记录,顾不过来时,速将一只手递去,喊着妈妈——赶快拍照!霎时,车子已驰过了两个道口。
隆德,再见了!
故乡的茅屋、刺柳、整洁的草垛,雾锁的青山,紫褐色的油麻堆,还有红瓦房、兰花花……你不是破败的黄土坡,你是我生命中的青纱帐,是我血液里的寂静源。
此乃天地有感呀神灵回显,当天夜里,我竟然奇迹般梦见了父亲;梦见他目光中闪着希望之光向我走来,我惊喜交加,身不由己地大声高喊着“爸爸回来了——”直到把自己喊醒来:后人呀,如果你再一次降生于此地,请感知我今日之心头大憾,懂我为此而死不瞑目的苦衷。
五
父亲走的那天,我幽魂般在街上乱跑,一直等他咽了气,我才回到家。未见他最后一面,也没有哭,我失魂落魄地坐在门槛上想,想了几个月,终于想明白了。我想,在那生死诀别一刻,父亲如果有话要说,他,最想对我要说的话,一定是要我替他回老家去看看。
这个遗愿,在我心中怀揣了三十年;我没有一天不想这件事。可,父亲的故乡,非寻常之地,就像我父亲的为人,虽然清贫,却异常尊贵。
想我父亲活着的时候,从不与人套近乎。出差在外,也没有去过子女的家。他老人家一辈子不欠人情,不借人东西,不在别人家吃饭,不看邻人吵架,不愿打扰旁人,不给孩子添麻烦……自我出嫁后,父亲虽是常常去我住的那个县城里开会,并不通知我;既是我知道后专门去请他,他也不会来。不料,父亲的生地也像父亲的为人这般,倔强而固执,使人随便不能靠近。
或许,正是因了父亲这份清贵,世上有了两个令我揪心的圣地,一是父亲的坟头,二是祖籍的墙头。时光如水,父亲的坟头我可以年年去,去为他培土、祭扫、修墓,去见他的坟场一天天的变化,目睹它怎样由一开始的数十家阴宅变成现在的近千家阴宅……如何由原来孤单的一棵树变成了如今的葱葱密林……可,不知为什么,祖籍的墙头,我却无缘触摸,迟迟不能如愿?
还好,六月是丰厚的,又一年夏天,偶遇佳机,外出学习期间我在宁夏停留了几日。可,当飞机在银川落地我断然决定再走隆德时,唯一能带我进村的表弟陈智雄却一脸犹疑。他说国家1991年就开始移民吊庄,沟里一个人都没有,你去了,狼吃了咋办?再说夏季草深树密路都找不到。后来,见我态度坚决,就提前预告道:“姐姐你执意要去的话,我们只能远远地站在山坡上看一看。”
我说,好好好,就站在梁上看看吧。
新疆有个木垒,宁夏有个隆德,这是我父亲生前住过的两个地方。从木垒到隆德,相距大约两千多公里。可两处的山势地形却惊人地相似。都是依山而居,一样的冬暖夏凉。
再走隆德,又见青烟薄雾,袅袅云衫;桥依旧,雨依旧,清凉依旧。一个人抱着暖手袋在隆德宾馆等人,回头看那宾馆的床头詩,已不是李白的《将进酒》,而成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外面风寒,室内阴潮,墙上酒诗火辣。
作家咸国平来了,热情地带我们去了艺术街,公柳园,那时,天上的细雨时滴时停,路上积了一滩一滩的水,一条街几十家画舫,我们一间一间看。隆德不愧是艺术之地:梅也有,菊也有,新诗旧词,琴棋书画……红牡丹,大公鸡,山水,牧童……看得我又惊又喜又骄傲!心里想,爸爸的故乡真是不简单——人人都懂书法,家家都有画廊,青山臂举蓝天,柳树头顶云伞,各个清流少年威挺将军气度不凡。
转悠累了,我们坐在故乡的夜店吃火锅。服务员是腼腆内敛的宁夏小姑娘,透着女儿厚厚的拙朴,沉静中略带单纯,微笑中含有隐忍。故乡的风,拂面如洗抚着我疲惫的心灵。就这样,随着夜幕的轻轻闭合,我们走完了隆德县城的一条街。
六
带着父亲回乡来,到了山梁的岔路口,又走错了。
车,陷进了路边的土坑,一个轮子卡在树桩上,不能动。乌云罩上心头,快快跳下来开始想办法。幸亏老乡咸国平认识供电所的人,赶紧打了电话等他们来。
我左右转着圈,不知所措。
一时走不了,独坐梁上,呆望。听到布谷鸟的叫声,沿坡而上。一拐弯,眼前豁然开朗,直愣愣,站在梁上傻了眼:猛吸一口清气,放眼四看,绿呀!春树、槐树、杨树……无边的苜蓿地,台梯式的绿毯子连在一起;向左看,果林里有野桃,野梨,野杏儿……累累挂满枝头;右边的坡梗上,黄的刺玫,紫的小菊,粉的山大王,一坡一坡铺上去,星星一样闪着亮光;崖的缝隙中盛开着紫白色的山菊花,田野中,大豆正在开花,麦子正在出穗,苞谷节节拔高;一只山鸡“噗嗤”落在脚下,它鲜红的尾巴,一翘,一翘,与边上翻飞的彩蝶争奇斗艳,满眼都是新鲜。可,回乡的路,咋就这样难啊?眼看到了家门口,却看不见老宅子的影,摸不到老墙上的土 ,又是肝肠寸断呀!
记得那一年九月,我们娘儿三,兴冲冲走到这里,在此,被无情的暴雨拦住,站在雨中,望着对面的山梁内心多么悲凉!这会儿,我默默地祈祷着,真想趴在地上给老天爷磕几个头。
正愁着,一个背草的人过来了。
赶快上前去求问,老人才一说话,我就被他熟悉的乡音感动了!眼前说话的人,突然变成了我的父亲……黑衣衫,深眼窝,发卷,背驼,神情肃穆。
老爷爷,这是杨沟乡吗?
不哦,喔再向前走五里路,咱就到了……
正问着,供电所来了七八个人,他们抬的抬,挖的挖,一会儿就把车子从坡上弄了下来。老乡们非常热情,非要护送我们一程,快到地方时,他们齐刷刷从车上跳下来,我们拍了一张合影照。之后,我们朝右走,他们往左一拐,上了公路。
说是下了坡就到了,但,智雄弟一直找不到原址,他不知朝哪个方向走,急得不停地抓头,我们更是两眼摸黑,绕着林场的白房子转了几个弯,天上开始滚黑云,我的心,又捏了起来。
进了一个荒村。
残墙上,开着一树黄色的迎春花。朝下看,院子里,到处都是红花绿果,拨开齐腰深的草,避开荨麻,一步一探地走过几条荒无人烟的空巷。门,关闭着,悄然无息的村子里没有鸟,没有动物,没有一个可以询问的人。
我们沿着一条小路往前走,路过菜地,萝卜、菠菜、葱、蒜……看得十分诱人,弯下身子拔了几根芫荽含在嘴里,香气冲鼻。
看见一家院子里挂着窗帘,树一样高大的牡丹花正在怒放。像有人的样子,弟和弟媳开了门,刚抬脚进去就听见女的喊声——“嗷啊!这么大的杏子……哇——石榴!快来看!酸枣,草莓,樱桃,花椒树……”“呵呵,我的爷爷呀,这里的花儿可真多……满得很!”智雄弟边赞边数着,芍药、金针、玫瑰、月季,马莲花……我进去一看,发现还有兰花、菊花、百合花;花丛中,有几棵柏树和松树,花园四周的泥台上,爬满了粉白两色的喇叭花,黑石豇窝子倒扣着枣木拐棍立在墙根,花布门帘,是那种淡蓝色的竹子,洗得干干净净。窗台上放着婴儿的奶嘴,玩具,香皂盒,漂亮的紐扣……还有一把梳子和一面小圆镜。
一拉灯,还亮着。人呢?厨房的门,被风刮开了,用麦草编制的锅盖放在灶台上,暖瓶,坛子,辣子罐,升子,计量器,一样也不少。落满干苜蓿的柴房里,有窗,有炕。墙上糊的年画是“宝灯良缘”、“珍珠塔”等。农具房里,整整齐齐摆着连枷、耙子、耧、耕子、磨、犁头、锄、背篼、铁锨、铲子……作家咸国平,手抚摸着这些农具感叹道:看不到喽,这些打粮食的农业工具现在都成了博物馆的文物展览了。临走,他抓起门口的扫帚,把院子认认真真扫了一遍,我想给主人留下一件礼物作纪念,在背包里摸了半天 ,找出一支笔 ,坐在门槛上,写了一个便条塞进门缝里,用白帘子挡住,出来了。
七
正午的天空,一会儿晴朗,一会儿阴云,草太深了,又找不到路,转了一圈,智雄弟焦躁起来,突然想起了老乡提到的林场,又快快返头,朝那一排白房子走去。
推开大铁门,荒草萋萋,所有的房子都敞着窗户。几十年不住人的荒凉,我们一间一间看。走到最里面,是一个教室,讲台上,有粉笔和一个铜式的铃铛,黑板上写着六年级学生的名单。一看课表,智雄弟高叫一声,“啊呀,找到了!”“唰”地拿了望远镜就往外跑。
我不明白,站在原地爬在墙上看了半天,才发现厚厚的课表底下,有作息时间表,上面盖着一个红章子,落款是“杨家沟公社赵家沟大队完全小学”。
随即,便也一步跨出来,赶快追着问,找到了吗?他把望远镜递给我,说:“看——就是那……你对着梁看,是不是塬?房子?”我接过望远镜,朝那茫茫绿海一望,隐约看见一些土墙,他说,你再看看有没有铺子?堡?咱家就在一个铺堡的旁边。
原来,这秦川大地的七沟八梁上,找一座古堡实属不易。当地人说法不一,深处为垴,两山相夹为岘,三山两道为岔,沿川道沟河而住为庄,以阶台居住成村落者为塬。那高高低低的丘陵梯田,像缠着清一色的绿带绕山而转;每隔一个山头都有一个堡子;每一个堡子边上都有山民栖息,且,多是顺沟建房,就势而居。所以到了夏天,川道山梁都被长草覆盖,绿茵茵一片外来者难以辨认。
智雄弟紧着的眉头终于开了。他一面擦着汗一面喊:来、来、来,快吃午饭,吃完了,进庄子。于是,我们席地而坐,望着对面的山梁,咀嚼着香甜的食物……大家嘻嘻哈哈笑了一阵,最后商量决定让驾驶员留下,把车开到大路上等我们,其他人徒步前行。
陇西盆地,由于地壳运动的变化和地震的影响,七道梁,八条沟,一梁一个庄,一沟一窝树,全部掩映在秘密的森林里,刚一下坡,一条大峡谷就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噗、噗、噗,跑到沟底,一看,哦啊!还不错,居然弯弯曲曲淌着一条河。赶快把双脚踩在石头上,摸一把水,爽!再摸一把好清凉!又看见一片沙棘林,惊喜地穿过苜蓿地,树,越来越多,草越来越深。空气新鲜,风景不错,弟和弟媳激动地站在河边拍照,作家咸国平,唱着歌,早已大步跨着上了山梁。
八
想了几十年的回乡路,终是如愿。
奶奶的沟呀,爷爷的梁!孙儿回来了……栖栖遑遑站在斜坡下,举头向上看,几滴雨点打在我的脸上,空气变得凝重起来。是逆风吗,还是因为要向上攀登的阻力在作怪?感觉行脚重似千斤双腿迈不动。一会儿,随着雨点的飘落,阴沉沉的天空中,突然飞来一只大鸟,在我头上“鹄儿”、“鹄儿”叫。
我吃力地向上爬,才拿棍子拨开一棵缠住我的树,密密匝匝的草又抱住了我的腰。我艰难地沿着树沟往上攀,几片白嫩的槐花落在我的肩上。雨滴打湿了它的叶子,我的心,起伏不定,像天上的云朵一样翻滚起来。
抬头向上望,快到第二个台阶了,梦幻般却见一束沙枣花摇晃在我的面前,一把拉过来,开得正旺呢,贴在鼻尖闻一闻,香似槐味——又疑心是不是看错了,再拉过来看一遍,枝上有刺,叶有银粉,也是白黄相间的小铃铛……又是一个想不到啊。
就这样,我,一进三退。我一走一叩首、一步一惊心地走完了一沟树,又走完了一坡草。大鸟一直跟着我,我走一步,它叫一声。听着“鹄儿鹄儿”的呼唤,我恐惧地瑟瑟发抖,感应着无人可知的血亲之疼,那“鹄儿”两字,原是我父亲的乳名,它是鸟吗?那呜沉沉的一噎,凄厉地惨叫一声,落在了我看不见的地方。
九
祖先的老宅子,在梁上第三个台阶。
智雄弟,三步跨作两步,在梁上飞奔,我随其身后,也踏着荒草飞奔起来。他一边跑一边呼喊,风把声音传给我:
“这是三叔疯了以后点火的地方……”
“这就是老房子的院墙……”
他一面跑,一面指给我看,这是祖先落脚的窑洞,这是驻扎军营的地方……四四方方的堡子,被野蒿覆盖着,留下二三百米的残垣断壁。我们从东边跑到西边,又从西边跑到东边——故园里的土墙、烟道、麦场、水窖、老井、菜地、野蒿……
“嗷——嗷——”风中,有什么东西在嚎叫。
老宅子,找到了!
骤雨怒泄,天空破裂。“轰隆隆”滚雷响,“噼噼啪啪”的大雨倒下来……那阵,冷风似刀割,暴雨如鞭打。我心畏懼,垂手默立,且泣且祷:老天爷啊!就让我们在这里多待一会儿,好吗?这是我奶奶想父亲哭瞎了眼睛、呼唤我爸爸回来的山梁。我似乎可以感知到奶奶喘着粗气的呼吸;这是我三叔受人欺凌被人打傻坠落地狱的现场,我似乎可以感知到他被侮辱被损害的心灵呼叫;这是我的祖辈们最初的诞生之地,我似乎由此而倾听到人类生命最古老的歌谣!
陇上烟雨蒙蒙,悄然无息。
雨中,那一排白房子,孤立风中如泣如诉。那是大伯为村民修建的学校,今已人去楼空,留一袭素白供后人瞻仰……这横栽墙根的七棵核桃树,它是父亲五十年前从新疆带去的种子。今吾父归天,七子四散,核桃树却依然挺立,正予我避风挡雨……
山雨天沐。我的眼,不能睁开,头不能抬起来。我的泪水伴着雨水流淌着,跌入鞋帮里,咕咕溢出来,我全身湿透,我手脚冰凉,我灵魂出窍,混成前世的秘密与这片乡土结成了一体。
岿然不动的黑土墙呀,我是在最后一刻才看见了你!
亲亲的黑土墙,我多想扑过去抱一抱你:失落多年,尘封多年,遗弃多年,你被掩埋得多么净洁呀,多么尊贵!追踪溯源,陈姓到今约有三千零五十年的历史,在来源不同的四个祖群中,我是舜帝的后裔?白永贵的后裔?刘矫的后裔?以及侯莫陈氏的后裔?
不知道。
感叹我觅源无痕,来路不明——所见血之尽头,只有这清新如洗的黑土墙。它,幽深如漆,庄重如山。如此摄人魂魄!如此鲜明夺目!
呜呼!足也。
青山淹没了我的历史源头,蒿草掩埋了我的祖脉古道,却永远抹不去我血亲记忆中这座历久弥新的黑土墙。
陈霞,女,新疆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新疆作家班学员。出版有《回家》《天风吹固的冰火》《画心》《荒原上的孩子》《天山脚下》等散文作品集。现定居新疆昌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