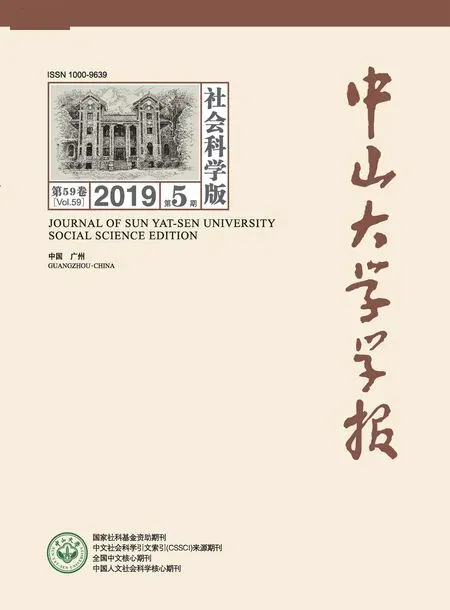明朝海防战船欧化变革的历史考察*
谭 玉 华
明朝军事技术变革与欧洲军事革命相互呼应,素为中外学者所关注,相关讨论甚至超越学术范围,成为公众话题。明朝军事技术变革,以火器为重点,以欧化为特征,即明末焦勖《火攻挈要》所论:“世之论兵法者,咸称火器,论火攻者,咸慕西洋,此言固为定论。”(1)[意]汤若望授,焦勖述:《火攻挈要》卷中《火攻根本总说》,海山仙館丛书,道光丁未镌,第26页。而在火器变革之外,明朝军事技术变革还涉及陆上军事工程和水上战船(主要指海防战船),三者共同构筑了“欧洲军事革命图景的中国映像”。欧洲影响下的明朝军事技术变革研究,长期聚焦于佛郎机、鸟铳、红衣大炮等欧式火器,研究成果汗牛充栋。而军事工程与海防战船的技术变革研究,久未引进“欧洲因素”作为观察变量。2011年以来,情况略有改观,有学者开始关注炮台、铳城等军事工程的欧化问题(2)郑诚:《守圉增壮——明末西洋筑城术之引进》,《自然科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庞乃明:《欧洲势力东渐与晚明军事工程改良》,《东岳论丛》2011年第7期;冯震宇、高策:《〈守圉全书〉与明末西方传华铳台技术》,《自然辩证法通讯》2013年第6期;Tonio Andrade, The Gunpowder Age: China,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in World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212-213.;也有学者试图探讨欧洲技术影响下的战船变革,尤其是蜈蚣船的原型问题,争鸣不已(3)参谭玉华:《汪鋐〈奏陈愚见以弥边患事〉疏蜈蚣船辨》,《海交史研究》2019年第2期。。 2016年,欧阳泰梳理了明末清初舷侧舰炮技术的创制问题,坚持认为外在的战争环境和对手(欧洲势力)是明清战船变革与否的决定条件(4)Tonio Andrade, The Gunpowder Age: China,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in World History, pp.206-210.,印度学者罗伊也持类似观点(5)Kaushik Roy, Military Transition in Early Modern Asia, 1400-1750: Cavalry, Guns, Government and Ships,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5, pp.131-132.。 两人都把明朝战船变革视作欧洲军事革命的外溢,强调明朝战船变革的全球史意义。然而,明朝战船的欧化内涵十分丰富,单纯的个案研究,很难达到窥斑知豹的效果,不易捕捉历史全貌。本文旨在澄清欧洲技术影响下,明朝战船舰炮和船舶两个方面的变革过程,及与之密切关联的海战模式演变,复原明朝战船欧化的历史过程。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转换研究视角,从内在技术传统上着眼,分析明朝战船“重利炮,轻坚船”技术偏好形成的原因。
一、佛郎机引入与炮击战术初显
正德嘉靖之交,佛郎机入明,与发熕、鸟铳等成为舰载火器的主流,将中国传统碗口铳和手铳排挤到次要地位。至万历朝,神飞炮、百子铳和威远炮等又相继装配海防战船,舰炮数量增加,威力增强,向重炮方向发展。船舶方面,则引入东南亚蜈蚣船专以架设佛郎机,普遍使用东南亚叭喇唬船,发明桅杆帮接技术。炮击战术初显威力。
(一)战船装备新式舰炮
第一轮战船变革引进和创制多种新式舰炮,其中尤以佛郎机最为重要。佛郎机属于小型后膛火炮,母铳子铳组合使用,以铳架支撑,操纵灵活,发炮迅捷。早在正德十六年(1521),佛郎机就已被仿造,装备广东海防战船,用于屯门海战(6)(明)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卷9《佛郎机》,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21页。。 嘉靖二十八年(1549)安南范子仪叛乱,俞大猷造船备战攻打安南,佛郎机已是战船的主要火炮,“大兵船一只,要用佛郎机铳二十门;中哨船一只,要用十二门;小哨一只,要用八门”(7)(明)俞大猷著,廖耀全、张吉昌点校:《正气堂全集·正气堂集》卷2《议征安南水战事宜》,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2页。。此后,佛郎机在明后期舰炮中的主力地位日益巩固,而把明前期的碗口铳排挤到次要地位。
与此同时,佛郎机衍生出发熕、神飞炮等新式火炮。发熕属前膛炮,长管,圆鼓腹,带耳,铳身纹饰繁复,铳尾圆突。“每座约重五百斤,用铅子一百个,每个约重四斤。”(8)(明)郑若曾撰,李致忠点校:《筹海图编》卷13下《经略五》,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99—900,899—900页。发熕体大,需用四轮铳车支撑转运,其铳车不起缓冲、消解后坐力作用。发熕固定安装于船首斗头位置,后坐力全为船身吸收,以致于“放时火力向前,船震动而倒缩,无不裂而沉者”(9)(明)郑若曾撰,李致忠点校:《筹海图编》卷13下《经略五》,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99—900,899—900页。。
发熕为佛郎机的改进型,“其制出自西洋番国”,“嘉靖年,始得而传之,中国之人更运巧思,而变化之,扩而大之以为发熕。发熕者,乃大佛郎机也”。从形制推测,发熕应是佛郎机去掉母铳,保留子铳,适当加大加长子铳而成(10)类似改造佛郎机为前膛炮的情况,在明代并非孤例。万历朝,叶梦熊曾经在塞上,将一百五十斤子铳和一千斤母铳的大将军铳(神铳),去掉母铳,把一百五十斤子铳增重为二百五十斤,延长其长度为六尺,达到其原长的三倍,径直放置到滚车上发射。其改造思路或借自发熕。见(明)王鸣鹤编,袁世忠校:《登坛必究》卷29《火器》,万历刊本,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第2页。。 从对音推测,“发熕”为葡语的falcão的音译,falcão就是采用子母铳结构,依靠V形支架单杆支撑的回旋炮,也即佛郎机(11)Filipe Castro eds., Early Modern Iberian Ships Tentative Glossary, Austin: J. Richard Steffy Ship Reconstruction Laboratory, 2017, p.42; Smith R. C., Vanguard of Empire: Ships of Exploration in The Age of Columbu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54.。
发熕体重力威,性能远在碗口铳和佛郎机之上,因而大受明军水师青睐。嘉靖年间,发熕即已遍装闽粤战船,福船、广船“所恃者有二,发矿(熕)、佛郎机”(12)(明)郑若曾撰,李致忠点校:《筹海图编》卷13上《经略五》,第857—858页。。 嘉靖三十九年(1560)成书的《纪效新书》(18卷本)记载“福船应备器械数目”,内含“大发熕一门”,已有法定意味。而海沧、苍山等中型福船,仅备大佛郎机和鸟铳(13)(明)戚继光撰,马明达点校:《纪效新书》(18卷本)卷18《福船应备器械数目》,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8年,第469—474页。。万历七年(1579)成书的《苍梧总督军门志》存《战船操演布列图》,显示发熕作为标准的船首炮,似已成为当时大型战船的标配(14)(明)应檟、凌云翼、刘尧诲:《苍梧总督军门志》卷15《水兵制与兵夫列船式》,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第162—164页。。
然而,发熕笨重,加之其发射震损船体,不利水战,限制了其在大型战船的装备和使用(15)(明)何汝宾:《兵录》卷12《铜发熕》,抄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不具页码。。 至隆庆万历朝,部分发熕由于“载放无法,置之不用”(16)(明)涂泽民:《涂中丞军务集录二·行监军道(水防火器募兵)》,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第5册卷354,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813页。, 隆庆四年(1570)福建漳州水战之器,“惟佛郎机、鸟嘴铳。若发熕、大将军,则未可轻用”(17)万历《漳州府志》卷7《兵防志》,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明万历元年刊本,第19页。。 另外,部分发熕从大型战船转移至专门小型战船之上。
神飞炮是一种采用子母铳制的大型后膛炮,有准星照门,是佛郎机的“汉化增强版”。神飞炮最早见于戚继光万历十二年(1584)成书的《纪效新书》(14卷本)(18)(明)戚继光撰,范中义校释:《纪效新书》(14卷本)卷12《舟师篇》,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58、271,258、271,259页。。 “神飞炮三号,母铳大者一千斤,次者八百斤,三号六百斤。子铳大者八十斤,其它两式依次减杀……水战则枕于舟舱,后用活机以便升降。遇坚阵巨船,照准一发,横击二三十丈,触之立成齑粉矣。”(19)(明)毕懋康:《军器图说》,《四库禁毁书丛刊》子部第29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348页。神飞炮每门可达千斤之重,是佛郎机之中最大的一型。万历年间,每船装备神飞炮一二门不等,既有发熕的威力,又有佛郎机填装、发射快捷灵活的优点(20)(明)戚继光撰,范中义校释:《纪效新书》(14卷本)卷12《舟师篇》,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58、271,258、271,259页。。崇祯年间,东南战船“每一号船,可用神飞炮四门,佛郎机五门,百子炮九门”(21)(明)陈仁锡:《陈太史无梦园初集》漫集《东南舟师》,《续修四库全书》集部 别集类第138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74页。。
威远炮是在大将军炮基础上去除铁箍后的大型前膛炮,高二尺八寸,重有百二十斤、二百斤两种,有准星和照门,威力极大。万历二十九年(1601),浙江提议增造威远炮,一号一百四十四座,二号二百六十二座,用以装备福船之外的草撇、苍、罾、铁、渔、沙、哨、军民唬船(22)(明)范涞:《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卷6《修理战船》,《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482号,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第798页。。 这样不管兵船大小,均配一门大型前膛火炮。
不过需要说明是,神飞炮和威远炮这两种大型火炮,似乎仅装备于万历年间受倭寇潜在威胁比较大,距离朝鲜、日本较近的江浙沿海战船,并未普及到整个东南沿海。而且,目前亦不见其在海战中发挥作用的文献证据。
百子铳是介于佛郎机和手铳之间的小型火炮,虽重不能手擎,但可以就地支撑,灵活摆动,调整发射方向与角度。其兼具明朝传统火器和欧洲火器的双重特征:支撑百子铳的四足铳床与支撑碗口铳的铳床类似,这代表着其传统特征(23)戚继光直言百子铳即虎蹲炮,不过他在记录时,仍有意识地把百子铳与虎蹲炮相区分,而且舰载百子铳的组装方式、使用方法与虎蹲炮存在显著不同。;单杆V形支架支撑百子铳,放时执尾牵挽,望准照星的使用方法,显然是受了欧洲舰载回旋炮的影响。

嘉靖万历年间的这波舰炮更新,至万历抗倭援朝战争时达到高潮,以佛郎机炮的引入和仿制为中心;发熕、百子铳属于佛郎机的“汉化改进型”,其中发熕重量在五百斤左右或更多;神飞炮则属于佛郎机的“汉化增强版”,达千斤之重;威远炮是传统陆地火炮的改进,重可达二百斤。舰炮种类增加,威力增大,使用重炮的趋势增强。
(二)引入东南亚战船与创制帮接船桅

叭喇唬船与蜈蚣船类似,也是一种东南亚的快速桨帆船。“叭喇唬船制造,起于番夷海贼”,“夷人出哨海上,多用此船”(31)(明)郑大郁:《经国雄略(武备考)》卷8《叭喇唬船》,潭阳王介爵观社刊本,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本,第21页。。 官军仿制“始自浙中”(32)万历《广东通志》卷9《藩省志九·兵防总下》,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本,第29页。,嘉靖三十七年(1558),浙江舟山之战,总兵俞大猷手中就有叭喇唬船(33)(明)郑若曾:《筹海图编》卷9《大捷考》,第624—625页。。叭喇唬船被引入东南海防战船体系之后,一直到明末都是海防战船的重要辅助船型。
除引入以上两种特殊船型外,明朝战船出现了帮接桅杆。通常,战船船体不大,桅杆短粗,极少拼接延长桅杆,也不使用牵拉固定桅杆的稳索。但大规模造船运动,木材消耗严重,长大桅木稀缺,价格高企,个别桅杆采用帮接技术。早在嘉靖十六年(1537),陈侃使琉球封舟,“大桅原非一木,以五小木攒之,束以铁环”(34)(明)陈侃撰,袁家冬注释:《使琉球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第22页。。 隆庆年间,为剿灭海盗曾一本,福建造船也有帮接船桅之议:“照得各州县制造巨舰陆续告完,惟合用大桅间有申请欲行帮接。本院因未经见,难以主裁节,会各镇道多方采访,有称往年封夷大船,用桅长至十七八丈者,大抵亦用帮接。今巨舰大桅,必须与船相称,若拘执一根成材,恐难寻觅。”(35)(明)涂泽民:《涂中丞军务集录三·行廵海等道(船桅)》,《明经世文编》第5册卷355,第3824页。涂泽民对帮接船桅的犹疑态度,恰恰能够证明其技术仍属初创,并不普及。万历三十四年(1606),夏子阳使琉球,造封舟,时因“地方大材砍锯略尽”,议用合桅(36)(明)夏子阳:《使琉球录》,张生主编:《钓鱼岛问题文献集》(明清文献),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01页。。至崇祯朝桅杆帮接更为常见,《天工开物》记载桅杆使用端直杉木,“长不足则接,其表铁箍逐寸包围”(37)(明)宋应星撰,潘吉星译注:《天工开物》卷下《舟车第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52页。。桅杆帮接,其强度必然减弱,为了增强桅杆强度,船舶也偶尔装配稳索。崇祯十年(1637),珠江口明朝水师战船就使用稳索(38)Mundy Peter, 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in Europe and Asia, 1608-1667, Cambridge: Hakluyt Society, 1907, p. 203.。此时,帮接船桅,使用稳索的技术已经司空见惯。
(三)炮击战术威力初显
明初至正德年间,战船武器装备,火器与冷兵器平分秋色。“神机、碗口”作为常规火器,普遍装备于各类战船之上,数量随海战需要增减。碗口铳腹浅管短,铳口开敞呈碗状,铳腹填装火药,铳口填装炮弹,或石或铁,封堵严实,采用铳床发射,炮弹获得的加速度小,相应的威力也小(39)成东:《碗口铳小考》,《文物》1991年第1期。。碗口铳的重量不大,“洪武五年水军左卫进字四十二号大碗口筒”,重15.75千克(自铭二十六斤),口径110毫米,全长365毫米(40)王兆春:《中国火器通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1页。。菲律宾巴拉望岛东北莱纳(Lena)沉船,为弘治年间的一艘中国商船,其出水铜碗口铳5件,体型亦不大(41)Goddio F., Crick M., Pierson S., et al., Lost at Sea: The Strange Route of The Lena Shoal Junk, London: Periplus Publishing London Ltd., 2002, pp. 239-241.。作为舰载远射火炮的碗口铳,与手铳大小相配,混合使用,威力有限。水战主要依赖投掷类火器焚烧敌船、冲犁、跳舷接战等战术。“海中战法,攻船为上,若以我大船犁敌小船,触之无不坏者。”“恃火器。火器之中,亦惟火毬、火药桶,投之入贼舟,即时焚毁而至妙也。”(42)(明)郑若曾著,傅正、宋泽宁、李朝云点校:《江南经略》卷8《火器论中》,合肥:黄山书社,2017年,第561页。嘉靖初年,中葡海战“(葡萄牙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炮火,而是来自敌人的试图强制登船”(43)Guilmartin Jr J. F., Portuguese Sea Battles, Vol.1, The First World Sea Power, 1139-1521, Kindle Edition, 2011.“Veniaga island(贸易岛,即屯门岛) June to September, 1521”.。
嘉靖朝以后,发熕、佛郎机、百子铳、神飞炮、威远炮、鸟铳等火器的引入,相较原有的碗口铳和手铳,显著增强了战船火力,舰炮有向重炮发展的趋势,导致海战在原有的冲犁、火攻之外,又明确把“炮击之法”作为一种主要战法。水军斗船,“其制胜者有三:一用大船犁小船,而用火药瓶烧之,取胜者。一用大炮击碎其船,而取胜者。一用火箭,烧其篷帆,而取胜者”(44)(明)陈仁锡:《陈太史无梦园初集》漫集《东南舟师》,《续修四库全书》集部 别集类第1382册,第274页。。而且,铳炮的作用变得比较突出,“海寇所恃,全在于铳,吾亦以铳为应。中军大船之前,仍用次等船载佛郎机大铳数架以镇之。两翼中船之前,亦用再次船载铜将军大铳数十架以列之。其小船亦各载鸟铳、铅筒数百,以备于四面”(45)(明)郑若曾撰,李致忠点校:《筹海图编》卷13上《经略五》,第883—884页。。
不过从战争实践来看,虽然装备以上诸种火器,但海战战术的重要性次序,仍是以火烧船,以船冲犁最重要,海战以冲沉贼船为首功,而斩级擒俘则次之(46)《兵部为官兵血战擒贼渠魁事》第二十二号,《明清内阁大库史料》第一辑明代,沈阳:东北图书馆,1949年,第518页。。 而以炮伤人,以炮毁船的情况,并不多见。隆庆三年(1569),闽广剿灭海盗曾一本诸次海战,可略窥不同战术应用之大概。是年五月,枳林澳一战,官军冲击贼船六十余只,贼尸焚溺浮海者不下二千余数,显然是冲犁和火焚战术的结果(47)(明)苏愚:《三省备边图记》之《枳林破海寇记》《南澳平海寇记》,《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2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897,902页。。 六月,官军在南澳备草百石,设火船于港口,举火焚毁贼船十一只,最终剿灭曾一本,官军和曾一本所持发熕、佛郎机等器似乎并未发挥多大作用(48)(明)苏愚:《三省备边图记》之《枳林破海寇记》《南澳平海寇记》,《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2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897,902页。。
二、红衣大炮的应用与炮击战术的成熟
17世纪初,荷兰人东来,其船铳数量与威力比之葡萄牙船更多更大,几场冲突使得明朝认识了其性能特点,并且专以“红夷”大炮称之。海防问题严峻的东南沿海,迅速把红衣大炮应用于海防战船,并且突破大型火炮装备战船的数量限制。为了应因红衣大炮装备海防战船的需要,出现专门化的熕船,并创制出舷侧炮技术,炮击战术更趋成熟,已与欧洲船舶的炮击战术十分接近。
(一)舰载红衣大炮数量的突破
红衣大炮是16至19世纪之间,大西洋沿岸诸国陆续装配的前装重型滑膛炮,入华并经中国人仿制后, 种类多达近百种,其重量、精度、威力各方面都有大幅提升。尤其是红衣大炮气密性好,可以在比较封闭的下层甲板空间发射,而不至于烟雾弥漫,影响炮手视线。
早在天启年间,红衣大炮就通过澳门葡人进入中国,很快实现自造自铸(49)胡晓伟、陈建立:《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藏明天启四年红夷大炮的探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等编:《文物保护研究新论》,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163—168页。。红衣大炮当时主要用于对后金作战,也不排除装备和应用于战船。至崇祯年间,红衣大炮明确出现在海防局势紧张的闽粤沿海的各类大型战船。崇祯五年壬申(1632)七月,海贼刘香具有广东极大之船,每船红夷大铳十余枚(50)(明)陈仁锡:《陈太史无梦园初集》车集《浙寇新防议一》,《续修四库全书》集部 别集类第1382册,第431页。。 此外,崇祯年间,南京工部郎中董鸣玮造龙骨炮船,其制“仿之闽海,一船可安红夷炮八门,百子炮十门”(51)(明)范景文:《南枢志》卷159《遵旨酌议制造铳船》,《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453号,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第4180页。。“仿之闽海”一语,清楚显示福建战船使用红衣大炮比南京龙骨炮船更早。
红衣大炮在战船上的应用,突破了以往发熕、威远炮、神飞炮等大型火炮在战船上的数量限制。从崇祯年起,海盗和官军船只就开始装备多门红衣大炮。如,崇祯六年(1633),明荷料罗湾海战,荷兰战船对厦门港内明军战船发动突袭,击沉二十五至三十艘大型战船及十五至二十艘小型战船。其中大型战船,分别装备十六门、二十门、三十六门大炮(52)江树生:《热兰遮城日志》第1册,台南:台南市政府,2002年,第105页。。而荷兰台湾长官汉斯·蒲陀曼(Hans Putmans)的记载也可佐证郑芝龙舰队装备火炮数量不少,“按荷兰模式建造,庞大精致,装备精良的帆船及舰队,还在船上装配了一部分能被拖动、带有环栓、置于双层甲板的大炮”(53)[荷]包乐史:《中国梦魇——一次撤退,两次战败》,刘序枫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9辑,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005年,第139—167页。。崇祯八年(1635),在剿灭刘香的战役中,郑芝龙的战船,“每船可安置大铳二十四位,炮声一发,裂云穿浪,卒成馘阵之功”(54)《兵部为登莱巡抚曾化龙提报登镇兵马船只实数并请措给饷银等事行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45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1—92页。。穆迪在珠江口目击的明朝水师战船帅字船或帅船,船侧有炮廊,通过舷窗伸向外面(55)Mundy Peter, 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in Europe and Asia, 1608-1667, p. 203.。从图绘来看,该船采用双层火炮,单侧船炮数量十四门,上层七门,下层七门。其中下层火炮安置于全封闭式的火炮甲板之上,是红衣大炮的可能性最大。
然而,装备十几门、甚至多至三十六门红衣大炮的战船并不普遍。如此多的红衣大炮,其单炮重量也不大。而且极有可能存在红衣大炮与发熕混淆的情况,中国长城博物馆藏崇祯元年铸造前装滑膛红衣大炮,长1.70米,重420千克,但自铭为“发熕神炮”(56)黄一农:《明清独特复合金属炮的兴衰》,收入陈玨编:《超越文本:物质文化研究新视野》,新竹:“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3—136页。。因此,战船所载动辄十门或几十门大炮者,当只有部分为红衣大炮。
通常情况下,战船只装备一件到二件红衣大炮。例如,郑成功的龙熕、副龙熕,就各以一船专载之(57)(清)阮旻锡撰,厦门郑成功纪念馆点校:《海上见闻录定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2页。。 顺治十四年(1657),浙江地方官提议“水艍、犁缯船,每船需用红衣炮四位”,比万历朝编《两浙海防类考续编》记录的“福船止用铜发熕一位,佛郎机三门”的火炮配备要重大。对此,清浙江巡抚陈应泰认为“事关海战制胜,不可不讨论万全”(58)《浙江巡抚陈应泰揭帖》,《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51年,第173页。。说明战船装载多门红衣大炮非普遍现象。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进攻热兰遮,其大型帆船约六十艘,各装有两门大炮(59)[荷]揆一:《被忽视的福摩萨》,厦门大学郑成功历史调查研究组编:《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增订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3页。。这种单船装配红衣大炮一至两件的情况,延续到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的澎湖海战,虽然明郑“炮船安红衣大炮一位,重三四千斤,在船头两边安发熕二十余门不等,鹿铳一二百门不等”,但明郑船只还有名“三熕”“四熕”者,因其载炮数量而得名(60)(清)姚启圣:《闽颂汇编三·攻克澎湖》,《台湾文献汇刊》第2辑第3册,北京:九州出版社等,2004年,第36页。。而清军水师鸟船也是“双战棚,两重炮位”(61)(清)陈良弼:《水师辑要》不分卷,《续修四库全书》史部 政书类第86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32页。,颇能代表当时战船舰炮的一般情况。
(二)熕船的创制与舷侧炮技术的成熟
天启崇祯朝的舰炮变革,火炮数量更多,体量更大,威力也更巨,因之也带动了船舶的深刻变革,促成了熕船的创制及舷侧炮技术的成熟。
早在嘉靖年间,福船之中就出现了专门载放发熕的小船(62)(明)俞大猷著,廖耀全、张吉昌点校:《正气堂全集·洗海近事》卷上《呈总督军门张》,第815—827页。,船底铺泥,泥上铺垫紧实的糠,用长木头在船舱中编排成筏,放在糠上,前后置栏格,护以牢索,筏上置坚木熕床。关键是“床与筏固,筏与船固”(63)(明)涂泽民:《涂中丞军务集录二·行监军道(水防火器募兵)》,《明经世文编》第5册卷354,第3813页。。 这些专门载放发熕的小船,可以看作熕船的原型。天启年间,广东海盗也有专门载放发熕的水底熕船(64)(明)陈仁锡:《陈太史无梦园初集》车集《浙寇新防议一》,《续修四库全书》集部 别集类第1382册,第431页。。
崇祯年间,随着舰炮数量越来越多,重量越来越大,舰炮作用日益突出,装载火炮的战船逐渐被赋予了“铳船”“炮船”“熕船”等专属名称。例如,崇祯年间,南京设立水标营,守御褚正行制造海船十八只,铳船七只,唬船四只,十桨船一只(65)(明)范景文:《南枢志》卷159《遵旨酌议制造铳船》,第4179页。。 顺治十七年(1660)、十八年,郑成功攻漳泉,取台湾,铳船、熕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成为对付清军战船、荷兰夹板船的重要武器(66)(清)彭孙贻、李延昰:《靖海志》卷3“庚子年”“辛丑年”,《台湾文献丛刊》第35种,台北:台湾银行印刷所,1959年,第54、57页。。
为了解决大型火炮移动不便、后坐力震损船身等问题,熕船配套采用了铳车、舷窗、炮孔、火炮甲板等,形成了与欧洲船舶相近的舷侧炮技术。红衣大炮最初也如发熕、无敌神飞炮一样,固定于船首斗头位置。但随着铳车、驻退索的应用,这些问题圆满解决。何汝宾指斥“红衣大炮震损船体”,都是“心口讹传,未曾经练之说。”他提出“在大船上,用车轮架安置停妥(红衣大炮),装药试放,船不震动,且声亦不大震”(67)(明)何汝宾:《兵录》卷11《火攻集说》。。铳车的引入,解决了制约明军水师战船装配多门红衣大炮的技术瓶颈。
熕船火炮数量增加,除少数安装于首尾,大多迁移至船舶中部船舷两侧。而红衣大炮或发熕体型巨大,重心较低,难以越过船舷伸出船外。因此,船舷两侧开挖舷窗、炮孔,施放红衣大炮。“船下层(主甲板)左右约开铳孔,或三十处,或二十处,安置红夷大炮,每门重二千三四百觔者,用一车轮架乘之,便於进退装药。此等大炮,每船一只,或六门或八门,左右排列;余孔亦列千觔与五百觔之铳,必要五百觔为率者,方沉重不跳且送弹端直。至上层战坪如用百子、狼机等炮。大约一船要兵百余名,大小铳共五六十门,多多益善。”(68)(明)何汝宾:《兵录》卷11《火攻集说》。除开挖舷窗、炮孔外,面对动辄二三十门大炮,战船还采用了双层火炮,即,在主甲板之上的官舱顶部(或称战台)再增设一层火炮。前揭郑芝龙战船和珠江口明军帅船均采用此种双层火炮,明末郑大郁《经国雄略》所绘福船与嘉靖万历诸福船图相比,明显设置了舷窗、炮孔及双层火炮甲板(69)(明)郑大郁:《经国雄略(武备考)》卷8《福船》,第7页。。郑成功水艍船火炮也采用分层设置,上施楼堞,绕以睥睨,面裹铁叶,外悬革帘,中凿风门,以施炮弩(70)(明)吴伟业:《吴梅村全集》卷25《梁宫保壮猷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 627页。。康熙二年(1662),张学礼出使琉球,其封舟采用了双层火炮,“上层列中炮十六位、中层列大炮八位”(71)(清)张学礼:《使琉球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2页。。 同时,双层火炮技术不但应用于东南沿海地区,而且也深入到内河。康熙十三年(1674),吴三桂叛,伪总兵杜辉,造飞船,“中分三层,上中两层左右各安炮位三十六,下层左右各置桨二十四,其行甚速”(72)(清)孙旭撰,张富祥整理:《平吴录》,车吉心主编:《中华野史》清朝卷1,济南:泰山出版社,2000年,第129页。。铳车、舷窗、炮孔和双层火炮的设置共同构成了战船的舷侧炮技术。
(三)炮击战术的成熟
红衣大炮装配战船,专门熕船的创制,舷侧炮技术的成熟,对海战影响巨大,舰炮对船的破坏和人的杀伤力已经相当可观。
天启七年(1627)八月,郑芝龙与俞咨皋部战于福州将军澳,郑芝虎使用斗头炮将明水师马胜船打穿,延着火药桶发火。但此战明军所沉敌五只战船,均为烧沉。崇祯元年(1628)六月,郑芝龙与俞咨皋再战于厦门,明军孙雄船被郑芝熊尾送炮打沉(73)(清)江日昇撰,陈碧笙点校:《台湾外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24,34,343页。。
崇祯六年(1633),明荷料罗湾海战和与刘香之战,是明末福建沿海最大规模的海战,已经出现个别“放炮打沉贼船”的情况(74)(明)邹维琏:《达观楼集》卷18《奉剿红夷报捷疏》,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乾隆三十年刊本,第39—52页。。 崇祯八年,郑芝龙于广东田尾洋剿灭刘香,双方战船均有被炮击沉者多艘(75)(清)江日昇撰,陈碧笙点校:《台湾外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24,34,343页。。
顺治十八年(1661)农历四月,郑成功在台江海域与荷兰军舰展开海战,郑成功船队以大型战船六十艘,每艘各装备有二门大炮,包围了荷兰战船赫克托号、斯·格拉弗兰号,白鹭号、玛利亚号等四只平底船。战斗过程中,“荷兰战船赫克托号首先爆炸沉没……中国大船紧靠斯·格拉弗兰号和白鹭号二号船的尾部,英勇的中国士兵向敌船甲板和船舱上开炮射击,中国军队还奋不顾身地用火船去烧毁荷兰甲板船,火船内装着火药和引火东西,因船小灵活,容易驶近敌船燃火,火船发火后,火船上士兵再跳水泅回。这时有一只火船用铁链扣住斯·格拉弗兰号的第一斜桅,使火延烧起来”(76)陈国强:《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的伟大斗争》,《厦门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此次战斗,以炮击船、以炮击人的作用变得非常突出,火烧敌船亦起了重要作用,但常规的跳船接战则没有出现。
康熙十九年(1680),清军收复海坛之战,万正色战船“炮火齐发,击沉贼船十六艘”(77)(清)佚名:《清代官书记明台湾郑氏亡事》卷2,“康熙十九年二月癸未,提督万正色奏克海坛”条,《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6辑,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 年,第13页。。康熙二十二年(1683)澎湖海战,炮击战术变得更加重要,海上交战发铳为先,“焚寇之船莫如火,碎寇之船莫如炮”(78)(明)何汝宾:《兵录》卷11《火攻集说》条。。 当时报告清军死亡三百二十九名,带伤者一千八百余名,悉被炮火攻击。清军大小战船,被炮打坏甚多。而清军用舰炮击沉的郑氏大炮船八只(79)(清)施琅撰,武宏丽等点校:《靖海纪事》上卷《飞报大捷疏》,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346—354,346—354页。。
这个时期也发展出了舰炮对射的战术,“凡水战,彼此望见,即发斗头熕。将近,或发左边炮;转舵,发尾送炮,再发右边炮”(80)(清)江日昇撰,陈碧笙点校:《台湾外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24,34,343页。。这与当时欧洲战列舰偏舷齐射战术已经高度一致。
不过,以舰炮决胜负的情况并未出现,在一般的海战事例中,多样化的炮击、冲犁、火烧、跳船、肉搏等仍是常规战法。火攻之法,尤备受推崇,火焚仍是主要的海战战术。即便澎湖海战,清军用火桶火罐焚毁大炮船十八只、大鸟船三十六只、赶缯船六十七只、洋船改战船五只,远多于舰炮击沉的区区八只(81)(清)施琅撰,武宏丽等点校:《靖海纪事》上卷《飞报大捷疏》,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346—354,346—354页。。 这个时期欧洲人的记载也显示,明末战船上的炮很小,不知道怎么瞄准(82)[葡]曾德昭著,何高济译,李申校:《大中国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9页。,类似的记载也见于穆迪的航海日志(83)Mundy Peter, 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in Europe and Asia, 1608-1667,p.203.。
三、战船变革的“重利炮,轻坚船”
在大西洋沿岸,15世纪最后几十年,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欧洲船舶出现了可以击沉敌船的舷侧重炮。16世纪,随着舷侧炮技术的成熟与发展,以撞击和强行登船为特征的海战方式逐渐被偏舷齐放的战术所取代,17世纪激烈的海军军备竞赛,各种新型战舰不断涌现,炮火越来越猛烈,速度越来越快(84)许二斌:《14—17世纪欧洲的军事革命与社会变革》,《世界历史》2003年第1期。。 面对欧洲坚船利炮,明朝战船变革在方向上,大体能与欧洲船舶变革保持一致,明朝在16世纪才开始在战船上应用发熕、神飞炮、威远炮等重炮,17世纪初才开始使用红衣大炮,采用舷侧炮技术,炮击战术日益突出。但是,明朝战船在舰炮和船舶两个方面的变化,均滞后于欧洲船舶,且呈现出明显的“重利炮,轻坚船”的技术偏好:即舰炮技术变化频繁,与欧洲舰炮的变革节奏、方向一致;船舶技术变化迟缓,有限的变革也多是应因火炮需要的产物,未发生欧化变革。
(一)舰炮变革的快速性和选择性
明朝战船与欧洲船舶接触之初,就迅速引进、仿制佛郎机和红衣大炮用于实战;在引进、仿制欧洲火炮的同时,对与之密切关联的架炮技术、锻炮技术、舷侧炮技术也一并引进吸收;舰炮还衍生出发熕、神飞炮、百子铳等佛郎机的“汉化改进版”和“汉化增强版”,最终形成了以欧式火炮为主导的舰炮格局,推动了明朝舰炮重炮化趋势。而且,在舰炮与船舶的互动关系中,舰炮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佛郎机的引入导致了蜈蚣船的仿制,红衣大炮的引入导致了舷侧炮技术的成熟,熕船的创制。明朝战船的舰炮变革,显著增强了战船威力,呈现鲜明的欧化特征,呼应了欧洲舰炮的重炮化趋势。
明朝舰炮对欧洲舰炮并未全盘吸收,而是具有特定的选择性。例如,欧洲船舶的超大型火炮长管射石炮(bombard)、大型加农炮等非常普及。这些超大型火炮航行时作压舱物,战时布列于甲板,对欧洲跨洋商船形成军事优势十分关键。但明朝战船始终排斥这类火炮,而是选择佛郎机这种非主流小型火炮作为引进对象,以致欧洲人对明朝战船火炮形成了“普遍较小”的印象。这与明朝战船普遍体型较小有关,大型火炮将增加船舶的无效载荷,提高船舶重心,威胁船舶稳性。再如,17世纪欧洲的舷侧炮技术通常是多层设置,炮孔较多。但明朝战船的舷侧炮,多是双层,普遍炮孔量少。入清之后,部分战船炮孔实用功能弱化,转向装饰作用,甚至采用图画炮孔。这与明朝战船对结构强度、水密性、稳性要求高紧密相关——开挖炮孔、使用多层火炮必然损害船舶结构强度和稳性。另外,欧洲火炮以锻造为主,明朝火炮以铸造为主,明朝对欧洲火炮的仿制,长期未引进锻造技术。直到万历朝叶梦熊、赵士祯等才尝试锻造火炮,而且锻造技术一直不是明朝火炮制造的主流(85)(明)何汝宾:《兵录》卷11《火攻集说》。。
(二)船舶变革的迟滞性与从动性
与舰炮不同,船舶对欧洲技术表现出相当的漠视和排斥。整个16世纪,葡萄牙人与明朝保持了相对稳定的贸易关系,甚至发生了几次一定规模的冲突。但明朝知识界并未把欧洲船舶和东南亚船舶区分开来。当时留存的官方文献和私人著述,对葡萄牙船往往以番船称之,对其技术独特性通常只是寥寥数语,一笔带过。更有甚至,作为屯门海战的直接参与者汪鋐,张冠李戴,把东南亚的蜈蚣船误作葡萄牙船(86)(明)汪鋐:《奏陈愚见以弥边患事》,(明)黄训编:《名臣经济录》卷43,《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44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3页。。显然,明朝政治和知识精英,对葡萄牙船的特殊性没有认识,不能与东南亚船相区分,更遑论对葡萄牙船技术的引进和学习了。对欧洲船舶的漠视一直持续至荷兰、英国商船来华,经过几场大规模的海战——1633年明荷料罗湾海战、1637年明英虎门之战、1661—1662年郑成功攻台之役,还有诸如1624年明荷在澎湖的对峙,人们才把欧洲船从东南亚船中剥离出来,并以马来语“夹板”一词命名,对其船型、结构、帆装、火器等有了具体描述和深入认识,但“引进、仿制和改造”等技术交流的常规步骤,在船舶技术领域并没有出现。明朝从未购买欧洲整船,战争俘获数量极少,欧洲船舶的船型、结构、属具等对明朝战船几乎没有影响。
在漠视和排斥欧洲船舶技术的同时,明朝船舶技术沿着自身传统缓慢发展,引进同属“南中国海传统”的东南亚小型桨帆船蜈蚣船、叭喇唬船;创制桅杆帮接技术和稳索设施,应对桅材资源短缺;创制熕船和舷侧炮技术,应对舰炮数量的增加。这三组技术变革,看似是对欧洲船舶技术的模仿和回应,但细究之下,与欧洲船舶只是神似或形备,其变革仍在明朝战船技术传统范畴之内,沿着传统技术路径演进,其基本的船型、结构、属具等未发生欧化变革。以最具欧化色彩的舷侧炮技术为例,其技术构成要素在嘉靖年间的鹰船中就能找到,后者已有舷窗、铳孔之设。“其旁皆茅竹板,密钉如福船旁板之状。竹间设窗,可以出铳箭,窗之内、船之外,可以隐人荡桨。”(87)(明)郑若曾著,傅正、宋泽宁、李朝云点校:《江南经略》卷8《沙船论一》,第565页。双层火炮也是以明朝海船传统的多层甲板为基础的。
四、中欧战船技术传统的兼容与排斥
同样是面临外来技术冲击,战船两个平行的技术领域反响差异缘何如此之大?缘何明朝战船呈现出“重利炮,轻坚船”的技术偏好?即面对作为有机整体的欧洲“坚船利炮”,明朝战船在有效地吸收改造欧洲火炮技术的同时,却长期回避排斥欧洲船舶技术。显然,从夷夏之防、儒家思想的保守性或制度角度,无法对此给予合理解释。而回归技术角度,从技术传统的兼容与排斥着眼,提供了欧洲技术冲击下,明朝战船变革“重利炮,轻坚船”技术偏好形成的一种新解释。
(一)明朝传统火炮与欧洲火炮的兼容
明朝舰炮的技术传统与欧洲火炮的技术传统的兼容性要强,前者容易接受后者。首先,从火器结构的角度来看。明初战船形成了碗口铳和手铳大小相配的火器结构,在抗倭和对安南的水战中,这种火器结构日益得到巩固。明中晚期,欧洲火器佛郎机、鸟铳、红衣大炮传入,并未对原有的火器结构构成冲击,反而增强了原有的基本火器结构。传统火炮技术展现了极强的接受能力和改造能力,不但把佛郎机、鸟铳、红衣大炮纳入已有的以碗口铳和手铳为主的火器结构,还创制出发熕、神飞炮、百子铳等新式火炮,接受了与火炮关联的锻造技术、架炮技术以及舷侧炮技术。
其次,从制造技术的角度来看。作为“重工业”的制炮,其生产环节较多,但中欧制炮的技术差异,主要在成型领域:明朝以铸造为主,欧洲以锻造为主,其它铜铁冶炼差距并不大。即便在两种技术传统差异最大的“成型”环节上,明朝传统的铸造技术并不排斥锻造技术——以佛郎机和红衣大炮为模,即可铸造仿制。所以,欧洲火炮容易被传统舰炮接纳、融合、改造、吸收。而且,明代中晚期的所有兵书,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设立卷册章节记录欧洲火炮情况,甚至出现了《火攻契要》这类专门的欧洲火炮技术的编译类著作,实现了欧洲火炮的技术传承。最终欧洲火炮轻易取代传统火炮,占据舰炮主导地位。
(二)明朝传统船舶与欧洲船舶的排斥
明朝战船的技术传统与欧洲船舶的技术传统差别很大,彼此排斥。首先,明朝传统船舶与欧洲船舶之间帆装难以兼容。受地球自转影响,大西洋东岸海域深阔,风气和柔,极少海洋性风灾气候,对船舶的驶风性能要求极高,所以欧洲船舶往往有巨大繁复的风帆,可以使用强度较弱的三节桅杆。而东海和南海所在的太平洋西岸,属于深海大洋,风涛多险,受海洋性季风影响大,暴雨强风等灾害性天气高发。因此,中国海船发展出便于快速缩帆,驶风避险的硬帆纵帆,而排斥欧洲帆船复杂的难以操控的软帆和横帆。
其次,明朝传统船舶与欧洲船舶之间操控系统难以兼容。16世纪以来,由于地中海航路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控制,切断了欧洲各国从亚洲直接获取香料等商品的途径。大西洋沿岸的海上贸易目的地,从地中海向美洲、印度和东南亚扩展,而非洲的经济状况很难满足当时欧洲国家的贸易需求。纵横跨越大西洋的航行安全系数略高,对船舶的操控性要求不高,其风帆只是提供动力,不影响船行驶的方向。偶尔舵失灵时,才升起后帆,使船尾转动(88)[葡]费尔南多·奥利维拉著,周卓兰、张来源译:《商船制造全书》,澳门:澳门海事博物馆、葡萄牙海事学院,1995年,第301页。。而东海和南海岛屿众多,暗礁丛生,兼以群岛星罗棋布,半岛、大陆弯环怀抱,沿岸海屿断续,很像一个内湖;又加之海禁影响,对外贸易萎缩,海上货运的目的地以周边沿海地区为主,一般不过马六甲,海上贸易完成一个航行周期的时间短,补给方便。以上多岛礁和航距短的特征,使得建造大船既无必要,也不便利,反而是中小船型操驾灵活,易于驱避,适宜多岛礁环境,成为明朝海船的主流。海船体型以中小为主,操控性好,帆、桨、橹并用,便于趋避,甚至帆舵联动,帆装兼具操控船舶的作用。
最后,明朝传统船舶与欧洲船舶之间结构差别巨大。欧洲船舶主要以跨海远航为主,航行周期长,补给不便,往往需要体型巨大的船只,保证长时间航行的给养和单次航行的利润。加之航行海域安全系数高,其船以水平隔舱为主,装货量大。东海和南海海上行船颠簸不稳,船载货品又以鱼类、陶瓷、大米、食盐等大宗散装固货为主,极易发生货物移动导致船舶翻沉,对船舶稳性要求很高。中国海船采用了能够固定分割货物、方便货物转运、提高船舶稳性、类似集装箱功能的密实的横隔舱结构(一米左右)。同时,复杂多礁的海域环境要求海船结构坚固,建造选用铁力木、荔枝木、柚木、梢木等上好木料,用材坚厚,甚至福船还发展出了多层船壳板技术。
欧洲海船的复杂帆装、体大难驭等特征,在东南亚海战和短途贸易中,不但没有技术优势,反而成为致命缺陷。在历次对抗当中,东南亚苏丹政权往往利用兰卡桨船(lancaran)形成对葡萄牙大船的优势;明朝水师往往能够因以制敌,利用诸番舶“大而难动”的缺陷,用火攻、登船等灵活机动的战术,取得对欧洲船舶的胜利。例如,崇祯六年九月初六日,福建漳州古雷、吉钓湾,一次对荷兰的小规模海战中,明军三十余名,攻大船收功,但最终却被“夷贼各下小艇,四面包围”而被反杀(89)《兵部题行〈兵科抄出福建巡抚邹题〉稿》,厦门大学郑成功历史调查研究组编:《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增订本,第19页。。葡萄牙、荷兰等国在亚洲海域的贸易或殖民活动,往往要征用当地戎克船、兰卡桨船或使用各类中小船型(yatch)或快艇(flute)。嘉靖二十八年(1549),俞大猷谈及澳门葡人船只情况时,直言其“所恃者龙头划”(90)(明)俞大猷撰,廖渊泉、张吉昌点校:《正气堂全集·正气堂集》卷15《谕商夷不得恃功恣横》,第384页。,龙头划也是一种中式帆桨并用的中型船只,说明当时葡人已经普遍接受和使用了中式船舶。
总而言之,海船建造是传统社会最复杂的工业门类之一,牵涉面广,生产链条长,技术难度大,各个环节彼此依赖,互相制约。欧洲船舶技术与明朝船舶技术分属两个独立的技术系统,彼此都有一套满足航海需求十分成熟的技术体系,各自环境依存度高,技术传统差异大,很难形成彼此借鉴,相互学习的局面,反而彼此漠视,相互排斥。明朝战船船舶技术的变革,不是欧洲船舶技术冲击的结果,而是船舶技术传统发展,应因舰炮需要的结果,是明朝战船技术传统范围内,对原有技术传统的改进、强化或弱化,并不触及明朝战船的技术传统的根本,未引发船型、结构、属具上的欧化。
结 论
面对欧洲技术冲击,明朝战船“重利炮,轻坚船”的技术偏好,植根于明朝火炮、船舶技术传统与欧州技术传统的兼容和排斥。这种技术传统之间的兼容与排斥决定的战船“重利炮,轻坚船”的技术偏好,反映第一轮西学东渐自发状态下“嫁接式”技术引进的一般逻辑:明中期开始的欧洲技术引进,以实用为目的,以实物、技术的应用为主,有技术无科学,有实物引进无知识传承,缺乏格物致知的过程。军事技术的引进是不完整和缺乏根基的,无法在新环境下形成独立的技术体系,获得延续。外来技术要想存续下来,进行技术复制,必须依赖和融入“嫁接的受体”——传统技术体系之中。外来技术与传统技术兼容的程度,决定了其被接受的程度。
明朝中欧战船技术传统的兼容与排斥,延续至鸦片战争前后。尤其在船舶技术领域的相互排斥,此时的战船延续着明清两代战船在结构、属具上的一贯特征,体型更小,帆装仍以简易折叠纵帆为主,追求快速灵活。同时期的东来欧洲船舶为全帆装船,船型修长,帆装更趋繁复,船舶速度更快,且实现了战船与商船功能的彻底分化,但其船型、属具等方面的特征与16世纪以来的欧洲商船并无大的区别(91)辛元欧:《试论西洋帆船之发展》,《船史研究》1993年第6期。。 中欧战船技术传统的差异,决定了鸦片战争前后,在旧有的技术体系之下,“嫁接式”地零星购置和仿制西洋帆船,只能浅尝辄止,半途而废。
直到洋务运动,军事技术引入,完全抛弃旧有的技术传统,采取复杂的外来技术系统“移植”,其既直接引进实用的火炮、船舶,也引进生产这些火炮船舶的器械工具及生产体系和外国人才,更传播相关科学知识培育人才。它是一整套的生产和配套体系的改弦更张,与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不可同日而语,其结果自然也不同。
——亚克兴角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