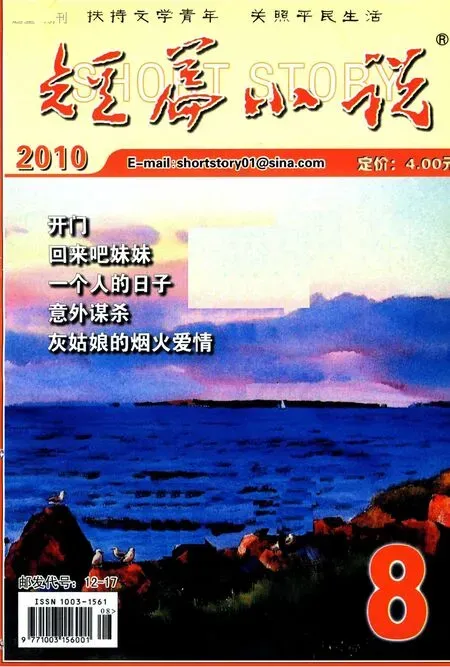乡村匠人
◎王振东

油 匠
黄土洼村前有一条官道,向西通到镇上,往东可达泌阳,村里的油坊就在这条路的北沿儿,油匠师傅叫王石头。
油坊是三间草房,东头那间安一盘石磨,中间盘一个锅灶,西间放一台油榨,这些都是磨油最基本的设备。
王石头已经当了十年油匠,起初他给老油匠打下手,后来老油匠老了,村里便让他接替老油匠磨油。那时,和交公粮一样,村里每月必须给公社粮管所交三次香油,每次王石头都是从村里的保管室领取芝麻,磨成香油后,把香油挑到镇上,交给粮管所。
王石头为人厚道,技术精湛,磨起油来似小媳妇绣花,一丝不苟。先把芝麻淘洗干净,控出水分,然后倒入铁锅里炒。炒芝麻最关键,油香不香,就看这一步。炒轻了,磨出的油不香;炒重了,油有一股子焦糊味。只有炒得不轻不重,磨出的油最香。这样的火候,只有靠王石头自己把握了。他磨出的香油颜色橙红,不混浊,闻着有一种特别的香味。将炒好的芝麻用磨拉成糊,摊到铁篦子上蒸,蒸好后用棉布包成圆饼,用钢圈把圆饼箍紧,把箍好的圆饼一个挨一个竖放于榨道里,慢慢旋紧榨道里的木桩,香油就会顺着榨道流入下面的桶里。
由于油坊开在路边,路过的人有时会拐到屋里,看王石头磨油。刚炒好的芝麻焦香,不自觉的人难免抓一把尝尝。王石头就抱拳施礼:“这芝麻姓公,要是我家的,大伙随便吃。不然这个吃一把,那个吃一把,到头来油出不够数,我没法给村里交差,请大伙理解。”话说得入情入理,想吃芝麻的人只好把口水咽回肚里。
这天,老婆在做午饭,见王石头从油坊回家了,就不错眼珠地看着他,瞅得他心里直发毛。王石头怕老婆,一看这架势,结巴道:“咋……咋了?”
老婆哈哈大笑:“看把你吓的,我又不吃你!”
“那你为啥这样看我?”
“你说,每次去粮管所交油,是不是就你一个人?”
“是。”
“收油的人验得严不严?”
“起先收油的老张验得可严了,后来见我实诚,人也熟了,就不验了,说我交的油免检。”王石头像小学生一样,如实说了,不解地问老婆,“你问这弄啥?”
老婆捧过油罐,往锅里放了一撇子油:“你瞧瞧,咱家每年就分这二斤棉籽油,一年到头连一滴香油都吃不到。”
王石头说:“村里磨的香油都交粮管所了,哪家不是吃棉籽油啊!”
“咱和他们不一样。”
“都是一个村的,咋不一样?”
“你的脑袋就是榆木疙瘩!当着油匠,就不会想法弄点儿香油吃?”
“咋弄?领出多少芝麻,磨出多少香油,保管员都会过秤,一斤一两都不能马虎。”
“当了十年油匠,没有弄回来一滴香油,却没少闻你身上的油味!”老婆埋怨道。
王石头挠挠头笑:“谁叫咱俩是两口子哩。”
“我想好了,等你下次去交油,咱得弄瓶香油吃。”
“那是集体的油啊!”
“啥集体的个人的?你就听我的。”
王石头想说“不”,却被老婆那凶恶的目光给压了下去。
转眼又到了交油的日子。老婆拿出一瓶米黄色的液体和一个空瓶子对王石头说:“去粮管所的路上不是有块苞谷地吗?苞谷地有一口废机井,我先把这瓶小米汤和空瓶子放到机井旁,你到那里后先倒出一瓶香油,再把这瓶米汤倒入油桶,搅匀……等没人时我去拿。”
王石头十分震惊:“这……这是损公肥私,逮住可不得了啊!”
“这办法是神不知鬼不觉。别怕,不会有事的。”
“只兴这一次,下不为例啊!”
“中。”说罢,老婆挎住藏了米汤和空瓶子的篮子出了门。
这边保管员也称完了油,王石头挑起担子去了粮管所……
午饭,全家人果真吃到了香油。
“看看,听我的没错吧。”老婆一边把半碗凉拌黄瓜端到王石头面前,一边显摆道。
王石头笑笑,那笑有点儿不太自然。
过了半个月,王石头见老婆的心情格外好,就鼓起勇气说:“你知道那瓶香油是咋来的吗?”
老婆狐疑地望着丈夫。
“其实我根本没有倒集体的油。那天你说过之后,我寻思着,无论如何咱不能那样做,就到粮管所求老张,说你病了,想吃香油,让他帮忙给买一斤。老张十分不解,说你为村里磨着油,咋连香油都吃不到?我说那是集体的东西,一两一钱都不能动。老张很感动,自己掏钱给咱弄了瓶香油。我把油藏在了地里,等你那天把米汤放在苞谷地后,我就调了包……”
老婆惊得张大了嘴巴。
“早几天我不是进了趟城吗?我去医院卖了一次血,把老张的钱还上了……”
好半天,老婆点着王石头的头,嗔怪道:“你真傻呀!”说完,把瓦罐里仅有的五只鸡蛋做成荷包蛋,“他爹,快补补身子吧!”
席 匠
那时,乡下不少人家常常是吃了上顿儿没下顿儿。吃的紧张,用的更别提了,吃饭用的粗瓷大碗,裂了烂了,就让锔匠钉钉接着用;铺的,也不像现在都是席梦思,铺领席就算不赖了。所以就有了席匠。
黄土洼的刘才就是一位席匠。
编席用的是高粱秆。那时,高粱是村里的主要作物,种的较多,既种白秆高粱,也种红秆高粱,籽粒磨了吃面,秸秆破篾编席。席是村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铺床需要席,晒粮需要席,连结婚娶媳妇也需要席。铺床晒粮用白席即可,娶媳妇得用花席,除铺床、围床用花席外,还用花席装点迎亲牛车,牛车到家后,新媳妇走往洞房的路面,均以花席铺地,就像如今的红地毯。一到农闲,方圆几十里的人家都请刘才编上几领,一年的用席就齐备了。
刘才的编席手艺是跟着爷爷学的,因为自小聪明伶俐,十八岁时就能单独外出揽活儿了。刘才人实诚,不像有的席匠急于赶工挣钱,干活毛糙,他编席从不偷工,从剥皮、破篾、浸泡、碾轧、刮篾到编织等二十几道工序,每道工序都用心去做,精益求精,没有半点儿马虎。刘才手艺精,编出的铺席晒席纹理清晰,光滑柔软,密实耐用;花席图案精美,栩栩如生,既编织“囍”、“福”、“寿”等字样,还编织“福寿双全”、“喜鹊登枝”、“年年有余”等图案,像一件件艺术品。最令人叫绝的是,他编的席,兜水不漏。一次他编好一领席收工吃饭,女主人顺手把一岁多的儿子放席上去盛饭,谁知儿子一泡尿撒在上面。女主人赶紧拎着席的四角去屋外倒尿,竟滴水未漏,倒完尿,席的背面还是干的。
一天,杏沟村陈家请刘才到家编席。陈家有个闺女,名叫喜枝,面容姣好,鼓胸细腰,两条粗黑的辫子垂于腰际。刘才见了,心中暗喜,忍不住要多看几眼。喜枝钦佩于刘才的人品和手艺,想方设法给刘才做好吃的。一来二去,彼此有了好感。编完席回到家,刘才就让父亲托媒人提亲,两人订了终身。秋里麦子刚种上,刘才就迫不及待地破篾编席,一下子编了十领花席,准备腊月迎娶喜枝。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一天,驻扎在镇上的日本鬼子开展冬季大扫荡,气势汹汹地闯进了杏沟村。日本鬼子进村就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村人闻讯,纷纷逃难。可喜枝晚了一步,被几个鬼子堵在家里……一个黄花闺女遭此屈辱,一气之下,悬梁自尽了。失去了心爱的姑娘,刘才像疯了一样,找鬼子报仇,硬被家人拦了回去。他恨透了日本鬼子,发誓一定要报仇雪恨。可仇还没报,鬼子就投降了。但他对日本人的恨,永远刻在了心里。后来,刘才成了家,有了儿子刘全。刘全十多岁时,他就教儿子学编席,他要让儿子和他一样成为一个出色的席匠。
刘才六十岁那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与外界交往日渐增多,土特产大量出口。因刘家席密实美观、色彩艳丽、柔软轻便,建国初曾作为本土特产进京参加过展览,故被县外贸公司定为出口的拳头产品。有这样的好政策,刘才决心大干一场,与外贸公司签订了长期供货合同。他带着儿子和他的徒弟,不分白天黑夜赶活儿。因为是出口产品,刘才编席更加精益求精,每道工序,他都严格把关,稍有瑕疵,就会返工,甚至销毁。一次,刘全将几片有缺口的篾子编到了席上。他发现后,不由分说将那几片篾子扯了下来,并立下规矩:如果发现谁再以次充好,弄虚作假,扣发当月工资。屡教不改者,解除雇用关系。重罚之下,谁也不敢再弄虚作假了。
这天,刘才到县外贸公司办事,无意间听业务员说,他编的花席全部出口到了日本。顿时,他的血直冲脑门,摇晃了一下,险些跌倒。他踉踉跄跄地找到外贸公司主任,要求取消合同。主任说:“取消合同就是违约,违约是要赔偿违约金的。”刘才说:“我宁愿赔偿违约金,也不会再供货!”刘才家的花席出口占全县土特产品出口总额的四成以上,如果花席出口受阻,他这个主任就别想干了。见刘才态度坚决,主任只好请主管外贸的副县长出面做工作。副县长说了“为了中日关系,要以大局为重”等一大堆官话,可刘才死活不同意,最后副县长承诺花席不再出口日本,只出口东南亚。刘才这才同意继续供货。
县里给日商也签有供货合同,取消订单也要赔偿违约金。这位副县长当面承诺不再往日本出口花席,实际上背着刘才继续给日商供货。得知这一消息后,刘才怒火中烧,搬出仓库里的所有花席,一把火烧了。然后对着日本方向大骂一通,气绝身亡……
刘才说啥也不知道,在他死后不久,儿子刘全就成立了花席编织公司,专门和日商做生意,花席也慢慢成为民间工艺品,刘全也成了花席编织传承人。去年,刘家花席还被列为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哩。
泥巴匠
那年月,乡下人日子过得紧巴,住的清一色草房,土坯砌墙,茅草结顶,不但砌墙用泥巴脱成的坯,勾缝也用泥巴,泥脊、搪墙用的还是泥巴,一座房子从上到下都离不开泥巴。泥巴匠应运而生。黄土洼的孙有才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但凡能称为“匠”的人,都有点儿手艺,如木匠、铁匠、剃头匠等等。孙有才能被称为泥巴匠,和泥掂泥自然不在话下,关键还会干砌墙、搪墙、苫草、泥脊等技术活儿。不但会干,干得还好,能服众。这可不是吹出来的,全是熬出来的。起初他也是个小工,和泥,掂泥,搬坯……干啊,熬啊,终于有了掂瓦刀、使泥抹的资格。瓦刀、泥抹是泥巴匠“吃饭”的必备工具。能掂瓦刀使泥抹就意味着是大工了,或者说是匠人了,就可以领头包活儿,就是大家口服心服的领导了。
孙有才成了香饽饽,谁家要盖房,得提前预约,晚了就被别人请走了。他领着一二十个小工,村里村外包活儿,谁和泥,谁搬坯,铺派得井井有条,房屋盖得快,质量又好。主人家满意,完工酒就备得丰盛,孙有才和小工们也喝得痛快。
有一次,孙有才被十里岗的仝三请去盖房。挖地基时,仝三的邻居拦着了,说仝三没留足封道。在乡下,盖房都要留足封道。孙有才好言相劝,但两家互不相让,竟动起手来。孙有才猛地往两家人中间一站,高声说:“你俩可听说过‘六尺巷’的故事。大清康熙年间,有个大学士叫张英,一天张英收到家信,说家人为争三尺宽的宅基地与邻居闹翻,要他利用职权打通关系,赢下这场官司。张英看罢信,笑了笑,然后回信一封,并附诗一首:千里来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接到信后,明白了个中道理,主动让出三尺宅基地,邻居见了,也让出三尺,这就成了‘六尺巷’。老话说,千年搁街万年搁邻,互相让让,比啥都强。”
仝三和邻居听了,都有点儿不自在。仝三马上把地基往里挪了挪。邻居也表示,将来他家盖房,也留足封道。就这样,一场械斗被孙有才化解了。
“才哥这泥巴匠,高!”
“有才真有才!看你把他两家‘搪’的,都没话说了。这叫泥巴匠的泥抹——两面光。”
“这就是领导才能,要是才哥当了队长、支书,能把事办得,谁都不会有意见。”
众人纷纷夸赞孙有才。
后来,孙有才真就当上了支书。
孙有才在为人盖房时,一不留神从房顶滚了下来,摔断了腿,治了几个月,骨头是长着了,却成了瘸子,再也爬不上房顶了。后来,大队支书年龄大了,就推荐有威信、又有领导才能的孙有才当支书,公社同意了。
当了支书的孙有才,果然把手中的“泥抹”用得得心应手,把“墙”抹得更光滑了。
这天,大翠和二梅妯娌俩因一只鸡蛋来找孙有才评理。原来,妯娌俩住在一个院子里,嫂子大翠住堂屋,二梅住东屋,两家的鸡窝并排垒在西墙根。两家不睦几年了。早上大翠摸过芦花鸡的屁股里有蛋,可中午从地里回到家,发现鸡窝里空空的,料定鸡蛋被二梅偷拿了。大翠就骂,二梅上去把大翠的头发拽掉了一绺。
孙有才一听,心里有了数:“为了把案断得公平,我得先看看现场。”
孙有才来到大翠二梅的家,在院子里转了一圈。二梅赶忙端出自家的蛋筐让孙有才看:“支书,俺家母鸡下的是红皮蛋,她家母鸡下的是白皮蛋,俺这蛋筐里有白皮蛋吗?”
“你俩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这就召开支委会,专门断这个案子。”说罢,背着手走了。
过了一天没见动静,二梅到大队部打听。孙有才说:“我正准备到你家断案。”
孙有才带着支委一班人来到二梅家,二梅慌着递烟倒茶,支委们有说有笑,只字不提鸡蛋的事。说着说着天就黑了,民调主任夸张地伸了个懒腰:“快饿死了,撤吧,明天再说。”孙有才说:“不急。”二梅的丈夫随柱看出了端倪,赶紧让二梅做饭。一盘炒鸡蛋,一盘拍黄瓜,一盆手擀面条。“时候不早了,这回真该撤了。”民调主任打着饱嗝说。孙有才这才站起身,对二梅说:“别看一只鸡蛋,也得断清楚,不能让你家背黑锅。明天继续断鸡蛋案。”
第二天下午,孙有才果真又带着一班人来到二梅家,一边喝茶吸烟,一边闲聊,还是不往正事上扯。二梅只好又炒了鸡蛋拍了黄瓜,支应他们吃饭。吃完饭一抹嘴,孙有才还是那句话:“这不是一只鸡蛋的事,鸡蛋虽小,名誉事大,咱一定得把案子断清。”
第三天,孙有才准时坐在了二梅屋里……半筐鸡蛋见了底,二梅心疼得牙根疼,对丈夫说:“明天要再来,还得去买鸡蛋。”随柱眉头皱成了疙瘩:“为啥他们不去嫂子家,偏偏一连几天来咱家,来了又不提鸡蛋的事……坏了,这是孙有才在羞辱咱呢。”
二梅两口子脸臊得不行,马上来到堂屋,二梅“啪”地打了自己一耳刮子,一把鼻一把泪地认起错来。大翠见了,拉着二梅的手:“好妹子,咱是亲一家,不能为一只鸡蛋伤了弟兄妯娌们的情分。往后咱还是亲一家。”
其实二梅两口子不知道,孙有才已经对大翠进行了批评教育。
饭场上,民调主任绘声绘色地说:“咱支书不愧是泥巴匠出身,就是会搪,不费啥劲就把大翠、二梅这两面‘墙’给搪光了!”
剃头匠
黄土洼把一些手艺活儿做得精的人称为“匠”。你家具做得好,木匠;你席编得好,席匠;你房子盖得好,泥瓦匠。匠是大家对他们手艺的最高赞誉。宁国忠头剃得好,是个剃头匠,包着八个村子的剃头任务。
宁国忠家在村西头,两间破草房,光棍儿一个,无牵无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宁国忠的家当是一个炉子,一只搪瓷盆,一个小木箱,外加一个凳子。到了村里,不用吆喝,孩子们早替他把信儿传到了村里的角角落落,他只需把剃头挑子安放在村中固定的地方,烧上一盆热水,打开箱子,取出推子、剪子、剃刀,还有一个装有掏耳工具的竹筒,然后揞上一锅烟吸,静等大家来剃头。
那时的发型比较单一,老年人剃光头,青年人剃平头,小孩子剃“茶壶盖”。平头和茶壶盖头比较好剃,难的是剃光头和刮胡子。难,是对一般人说的,对宁国忠来说,好比如今的天宫实验室与神舟飞船自动对接一样容易。剃光头时,他先把顾客的头洗一遍,然后一手扯着磨刀布,布要扯得紧绷绷的,另一只手拿剃刀在布上来来回回一磨,“唰唰唰”,电光火石一般。刀磨好了,左手把头皮撑开,右手持刀从上往下一刀一刀地刮,不到一袋烟工夫,一只圆圆的“葫芦”便亮在人们面前。
刮胡子是最见功夫的。剃须之前,宁国忠先拧了个热毛巾焐在顾客脸上,待须孔张开,用刷子蘸上皂沫在脸上细细抹过,右手悬腕执刀,拇指按住刀面,食指、中指勾住刀柄,无名指、小指顶住刀把,左手抚脸撑开皮肤,剃刀便在顾客脸上细细扫荡,就连耳轮耳廓和眼皮上细细的绒毛也不放过,当你还在惊叹他的手艺时,顾客脸上再也摸不到半根须茬。此时,顾客往往舒服得闭上了眼睛,似睡着一般,等着享受掏耳和捏肩捶背服务。
掏耳是个细致活儿。掏耳筒里挖勺、绞刀、镊子、耳绒这四样物件各有其用。他扳着顾客的头,将耳朵眼对住日头,左手轻捻耳廓,先用挖勺将耳耵挖出来,再用绞刀在耳朵眼里转上一圈,用镊子将剩余耳耵夹出,最后用耳绒轻轻转动,掸去细屑,几个步骤娴熟自然,像他吸烟一样顺溜。
捏肩捶背是收官之作。剃头、刮须、掏耳做完,顾客已是耳目一新,红光满面,再经摩顶、放髓、捏肩、展臂、捶背,整个上半身骨节放松了个遍。最后一着是敲顶,左手掌覆在顾客头顶,右手握空拳在掌背上轻轻地敲,只听“嗒,嗒”几声脆响,收布、理领,再瞧那顾客,真真是容光焕发,再无刚坐下时的颓唐面目。
这一通活儿下来,一般人额上可能已沁出汗珠,可宁国忠却面不改色,气不发喘,接着为下一位顾客剃头。
人们都说,让宁国忠剃头是一种享受。
有一天,日本鬼子实行夏季扫荡后在镇上驻扎下来。因为战事繁忙,小鬼子已经许多天没有剃头、洗澡,浑身又臭又痒,这下终于可以把自己打理打理,好好放松享受一番了。洗过澡,小队长龟田还想剃剃头、刮刮脸,就让汉奸许二歪找个手艺好的剃头匠来。那时,宁国忠已在镇街上开了个理发馆。许二歪就是镇上人,当然知道宁国忠的活儿好,就把他找了来。宁国忠打心里不想为小鬼子服务,可在刺刀的威逼下,只好违心地去了。一套活儿下来,龟田竖起了大拇指:“哟西!”接下来,小鬼子争着抢着让宁国忠剃头。
宁国忠原想剃一天就算交差了,谁知龟田说队伍里正缺个剃头的,要他随叫随到,不然就“死拉死拉”的。
这天,龟田又要剃头享受了,便让许二歪叫来了宁国忠。小鬼子驻扎的地方是一个天井院,很大,原是财主李杰民的房子。前屋及东厢房住的是士兵,西厢房是伙屋和马厩,后屋是龟田的住室和办公室。宁国忠已经多次来这里了,不只是龟田,这院里上上下下的人,他都熟识。他都为他们剃过头。
龟田有个习惯,一套活儿下来,因太过舒服,要靠在椅子上眯一会儿,慢慢品味服务带来的快感,这时候你不能喊他,只需轻轻收拾好东西,蹑手蹑脚走就行了。
龟田坐在办公室中间的椅子上。剃完头,宁国忠用热水湿了毛巾,拧一拧,轻轻焐在龟田脸上,几分钟后拿掉毛巾,用刷子蘸上皂沫在龟田脸上细细抹过,然后拿出剃刀,在磨刀布上磨了几下,左手撑开皮肤,剃刀便在龟田脸上沙沙移动。龟田的眼皮抖了抖,吸一口气,呼出,整个身体惬意地松弛下来。
剃刀依次经过额头、鼻翼、嘴唇、下巴、咽喉,然后轻轻一抹。龟田的脖子上立时现出一道口子,就像孩娃哭叫时咧开的嘴,粉红色的泡沫从那道口子里冒出来。龟田似乎熟睡了一般,什么声音也没发出。
宁国忠匆匆收拾好工具,出了门,轻轻把门带上。到了前屋,笑盈盈地朝士兵们弓弓腰,转身走出门去。
宁国忠从小镇消失了。
再次回到小镇时,宁国忠带来了一队人马,这队人马当天夜里就把龟田的据点给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