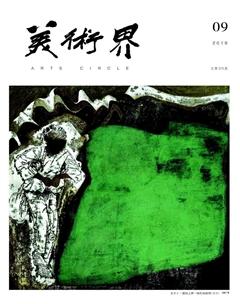贵州苗族服饰图案造型分类及语义研究
王兰英
【摘要】苗族服饰图案是苗族文化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图案内容和造型形式能够反映苗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几何体造型和非几何体造型的分类方式可以囊括所有的苗族图案造型,以便更好地区分图案是为了装饰还是作为某种包含了特殊意义的符号,也能够更好地理解造型的语义,本文拟从几何体造型和非几何体造型对贵州苗族服饰图案展开研究。
【关键词】图案;造型;语义;分类
苗族服饰上的图案形成是苗族人民对生活、对理想的高度概括和具体表现,它记述了苗族的发展历史和生活状况。几千年以来,贵州苗族服饰上的图案还保留着历史的痕迹,透过这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图案造型我们可以找到隐藏在图案背后更深层次的含义。贵州苗族村寨大都在深山老林中,过去因为经济不发达、交通相对落后,很多苗族村寨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从而保留比较完整。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对苗族服饰图案造型的传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直到今天我们走到贵州的各个苗族村寨还可以看到几千年以前的苗族图案通过人们身上穿戴的服饰展示出来,成为了活的、生动的“历史展示”。
根据不同的角度我们暂且将图案造型按两种方式来分类:一种按衍生含义可以将苗族服饰图案归纳为普通图案和宗教图案。普通图案是由基本的方形、三角形、平行线条等几何形体组成,一般作为服饰图案的装饰纹样。而宗教图案包含了祖先崇拜、图腾崇拜、生殖崇拜造型以及万物有灵的思想观念,是人们精神生活、思维方式以及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体现。宗教图案从特殊的角度以独特的方式记载了苗族文化发展的脉络和进程,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另一种分类方式按照造型形态可以将苗族服饰图案分为:几何图案造型和非几何图案造型。其中几何图案造型在苗族服饰中占的比例比较大,很多图案造型都是由基本的几何形体通过反复排列、变化组合而成,苗族村寨中常见的植物和动物经过苗族妇女的精心编织创造出形态比例优美的几何图案。非几何图案造型包含的范围也很丰富:各种动物、植物花草、人物及生活小场景都成了苗族人民描绘的对象。不过这两种分类方式不能完全地分离,相互之间有交叉,比如几何图案和非几何图案中包含了普通图案和宗教图案,下文将按照第二种分类方式进行阐述。

一、几何图案
几何图案在苗族的服饰图案中所占比例比较大,它们构成了苗族服饰图案主要的造型形态。苗族服饰中的几何图案造型有些是标准的点、线、面、体的装饰纹样,这些纹样经过组合和变形形成了各式各样的装饰图案造型,本文将其称为装饰几何图案。它们通过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的排列方式组成有节奏、有规律的图案造型装饰在苗族服饰的衣襟、领口、袖口、裙边等地方;而有的几何图案造型则是采用自然界中具象物体经过夸张变形而成的几何化图形,这类几何图案造型既有物体本身的物理特征,又增加了几分生动、幽默和乐趣,甚至有些具有某种特殊的宗教含义。在贵州,从很多地方的苗族服饰中,我们能够轻松提取出十字形、双线形、三角形、拐子形、菱形、心形、圆形、方形、螺旋形等基本的几何体造型。
这些几何形体经过排列组合形成了复杂且丰富多彩的几何图案造型,并通过二方连续、四方连续以及各种装饰骨骼组合的构成方式在苗族服饰衣袖、肩颈、裙子边沿等地方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图案造型样式,成为苗族服饰图案一大特色。基本几何体经过巧妙变化可以形成几十种同一形体、不同花型的图案造型,如图1的图案即从苗族服饰上提取,它们由基本体菱形、三角形、线条等组成了各不相同的几何图案造型,这样的图案造型在贵州凯里、六枝、兴义、黄平、贵阳花溪等地的苗族服饰中极为常见。
(一)装饰几何图案造型
几何图案造型中,有些图案只是为了服饰装饰得好看而制作。作为装饰的几何图案纹样,出现在苗族服饰的衣袖、肩口、裙沿边上,经过简单图形的重复组合、连续变化形成了有韵律、有节奏的图案造型,形成苗族人民日常服飾的装饰和点缀。苗族图案题材十分丰富:有纯几何形体,也有动物、植物、花卉等,丰富的内容、精致的制作是苗族妇女对身边事、身边物的高度提炼和简化,以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执著。图2是贵阳花溪高坡的苗族服饰图案,纹样主要以菱形几何体为基本元素,经过四方连续的构成形成了花瓣形式。花溪的苗族图案最大的特点是在前胸和后背有比较大的菱形几何刺绣图案,服饰主要为旗帜式,人称“旗帜服”。服饰花纹样主要为白色和红色穿插而绣,底色一般为蓝色,以挑绣的工艺制作,色彩鲜明,层次丰富,是典型的装饰几何图案。
(二)寓意几何图案造型
寓意几何图案造型不仅具有装饰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们具有某种特殊的历史含义和宗教含义。这些图案造型大都模仿大自然中的物体经过抽象变形成为几何化的形体,从图案造型的表面形体来看,它们具有物体本身的自然属性特点,能够大体分清楚它们属于哪一类型的物体。苗族人认为鸟曾经孵化出了他们的祖先姜央,对于他们来说是有恩情的,因此为了纪念鸟,苗族服饰上会有各式各样的鸟的造型图案。另外,在苗族文化中鸟还代表了男性,具有生殖崇拜的意义。同样在贵州凯里、台江、丹寨等地流行的回纹、漩涡纹也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几何图案,虽然它们是同一个花纹但是不同的地方称呼不太相同,有些地方称呼为水旋,有些地方称呼为牛旋,有的还称呼为蕨菜花。这些纹样的含义会根据说法不同而有不同的含义,有人说漩涡纹是牛头上的旋代表了祖先,又有人说是一种像漩涡的植物治好了苗族姑娘的病被绘制了下来,还有人说是苗族祖先对长途迁徙过程中跋山涉水的艰辛的纪念,代表了圆满急转。又如图3,阿城认为此图案为洛书的原始造型,是华夏文化的源头,这个图案和考古挖掘的新石器时期玉版图形一致,它们都指向了天极,是人类崇拜宇宙的一个标志。蛙的造型在苗族服饰图案中也大都以几何化的形式出现,蛙的肚子浑圆、产子繁多具有很强的生产能力,因此蛙纹在苗族文化中是具有生殖崇拜象征意义的。



二、非几何图案造型
苗族服饰上非几何的图案造型非常丰富,很多花卉植物、飞禽走兽以及人们想象中的动物、植物、人物造型都表现出具象和半具象的造型特征,有些属于纯写实的造型,还有想象塑造的造型形象。造型生动形象地反映了苗族人热爱生命、热爱自然的高度情怀和朴素的审美情趣。
花卉植物的图案造型在苗族服饰刺绣、织锦、蜡染中是比较常见的,苗族人喜欢荷花、玫瑰花、石榴花、八角花、灯笼花、桃花、鸡冠花、葫芦、牡丹花、茶花、向日葵等植物花卉作为刺绣图案。这些花卉植物大部分是苗族人民身边非常熟悉的野生之物,不过由于苗族妇女手工艺的运用手法不同、地理环境差异、植物生长差异,使得同一种花卉植物类图案呈现出丰富多彩、个性鲜明的风格特点,也表现出了不同于其他地方的造型形态。花卉植物纹大部分是采用挑花、平绣、蜡染工艺,与其他图案造型综合使用,常常用于腰带、衣袖、领带、衣衽、围裙等作为装饰,如图4。
天上飞的鸟类,水里游的鱼类,地上跑的老虎、狮子、家禽等都是苗族妇女心中理想的图案造型。在苗族服饰中鸟类的图案类型十分丰富,不仅有几何型,也有具象型。在传统图案造型中,鸟往往和鱼、石榴、桃子等组合在一起,共同表示了生殖的含义。鱼的繁殖能力是比较强的,在苗族人民的观念中,鱼是多子多产的象征,是生命力的象征,因此鱼被当成了生殖能力旺盛的崇拜形象。在苗族服饰图案中,鱼的造型往往比较肥大,有漂亮的尾巴和纹饰,且非常生动,一般为两两嬉戏或四条相互追逐。老虎和狮子图案造型一般在小孩的肚兜、帽子上表现比较多,主要是希望小孩长大后能像老虎狮子一样威猛、勇敢。另外,这类凶猛的动物往往还和人物图案一起出现,表现一种农耕狩猎的生活方式。

苗族人民塑造出来的吉祥图案造型一般都具有某种神秘色彩和历史传奇故事,有蝴蝶、龙、英雄人物。蝴蝶是苗族的文化的始祖之一,苗族歌曲里唱到:“枫树生妹耪,枫树生妹留,……枫树生耪留,有了老妈妈,才有你和我,应该歌唱她。”苗族人民认为妹表示妈妈,榜留指蝴蝶,因此他们称呼蝴蝶为“蝴蝶妈妈”。苗族的蝴蝶纹与汉族的蝴蝶纹相比较,其造型更具有装饰性,几十上百种蝴蝶造型被赋予了神秘的色彩:人面兽身的蝴蝶造型、人面蝶身的蝴蝶造型、蝶身鸟足的蝴蝶造型等,千姿百态、优美动人。蝴蝶纹有些也被简化成了几何体,形成一种装饰纹样运用在服饰中,但更多的是一种拟人化的、半具象半抽象的图案造型,具有强烈的装饰性,在苗族的文化中广泛使用。
龙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被视为一种能兴风唤雨、翻江倒海、能走能飞的神物,老百姓为了祈求吉祥、风调雨顺创造出了龙的形象。苗族龙不同于汉族龙,它没有固定的模式,不依附权贵,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龙的形象也不被任何人占有,龙的造型像虫、像牛、像猛兽。苗族龙被作为祖先崇拜的象征,它的造型没有固定的标准,苗族妇女往往按照自己的理解来描绘龙的形象。从服饰图案上我们可以将苗族龙分为:角龙、飞龙、卷龙、头龙、双头龙、骨龙、蚕龙、蜈蚣龙、回身龙、蛇龙等。
人物造型在苗族的服饰图案应用中也是非常普遍的,一般带有故事性和情节性,人物的形态都带着某个动作和思考,一般与老虎、狮子、龙等造型一起出现,这些图案场景并非现实生活中的再现,而是苗族人民的理想化创造。如图5所示苗族服饰图案,画面中一个人站在一条单头四身的蚕龙头上,面向牌坊,头仰天空,似乎若有所思。学术界对此有多种解释,杨培德认为这座牌坊是苗族的庙宇,而庙宇下面的人则是苗族的祖先姜央;而阿诚认为这座牌坊是天盖、下面用四根柱子撑起表示天极,而这个人物则是天极神。
总之,苗族图案造型的分类有多种方法,但是不同的角度分类的方式各有不同,从分类方式中找到一种更适合语义解读的路径才是最终目标,对苗族服饰图案进行不同角度的分析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领会其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
注释:
*本文为2019年度贵州省理论创新联合课题“贵州苗族服饰图案造型的解读”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GZLCLH2019- 287)。
参考文献:
[1]阿城.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M].北京:中华书局,2018.
[2]钟涛.苗绣苗锦[M].贵州:贵州民族出版社,2009.
[3]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18.
[4]汪禄.苗族侗族服饰图案[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