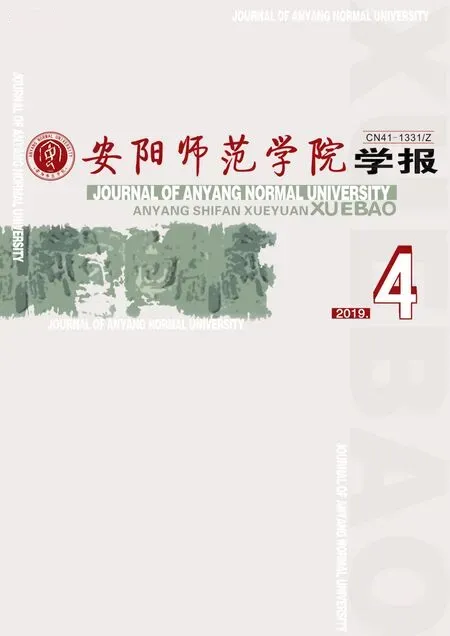元代崂山道士刘志坚诗词题刻考述
孙立涛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刘志坚(1240-1305),元代博州(今山东聊城市东北)人,道号“云岩子”,是丘处机的第三代传人。明人黄宗昌《崂山志》载:“(刘志坚)倜傥有材干……弃家入道,师事东平郭至空……遂唯而笃行,辞郭而东至崂山。私喜曰:‘机缘在是矣’。即山麓南阿为椽,虎狼旁午……岁余,徙入深涧……凡一言一行,必践其实。”[1](P50-51)刘志坚在崂山结庐修行之时,“洞祁真人闻之,特赐‘云岩’为号。元大德八年,敕封‘崇真利物明道真人’。”[2](P316)
刘志坚主要在崂山西北麓的华楼山地区修行和传道,逝后门人将其葬于华楼山凌烟崮,墓址至今尚存,元代集贤大学士赵世延为其撰作的《云岩子道行碑》亦流传至今。在刘志坚的经营下,元代崂山道教曾兴盛一时,传道期间他还将大量全真道先辈的诗词和修炼要诀镌刻到了山石之上,后署“云岩子上石”字样,且大部分遗留到了今天。所以,崂山华楼山地区道家诗词题刻中很大部分都与刘志坚有关。但本文述及的“刘志坚诗词题刻”,其内容均与刘志坚本人联系紧密,或是其他道人专门赠与刘志坚的词作,或是刘志坚亲自所作的诗歌,此外本文还就文献中题为“云岩子作”的多处崂山题刻进行辨析。
一、兖州董师父赠云岩子《酹江月》词刻
在崂山华楼山凌烟崮南侧,镌刻着两首兖州董师父赠送给云岩子刘志坚的词作,一首为《酹江月》,另一首为《上丹霄》。
《酹江月》词刻文字为阴刻楷书,字径约20厘米,共竖排14行,其文为:
充州小东门董师父赠云岩子。
酹江月。

大德四年三月初三日。
这首词刻的落款只有题刻时间“大德四年(1300)三月初三日”,没有记载上石之人。在其旁侧还有“丹阳师父题长生师父《沁园春》”词刻,落款为大德四年(1300)三月十六日,二者镌刻时间只差十余日,且在雕刻字体、技法方面也一致,据此推断两处石刻应是由同一人上石的。“丹阳师父题长生师父《沁园春》”词刻后署名为“云岩子上石,书刘志德”,那么这首“充州小东门董师父赠云岩子”《酹江月》词刻也应是由他们主持上石的。
词刻中的“董师父”具体为谁,并不十分清楚,只知他为“充州”的道门弟子。虽然题刻中写为“充州”,但在元代并无此地名,“充州”应为“兖州”之误。《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载:“兖州,唐初为兖州,复升泰宁军。宋改袭庆府。金改泰定军。元初复为兖州,属济州。宪宗二年,分隶东平路。至元五年,复属济州。十六年,隶济宁路总管府。领四县:嵫阳,曲阜,泗水,宁阳。”[3](P1368)可见在元代,兖州属于山东地区,距崂山不远。兖州董师父赠与崂山名道刘志坚诗词,从中又可看出,当时山东各地道教间的往来、交流应是比较频繁的。
这首《酹江月》词刻在当代与崂山文化相关的著作中也有收录,如王集钦的《崂山碑碣与刻石》、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的《崂山志》、王瑞竹的《崂山诗刻今存》、崂山风景区管理局与崂山区文化新闻出版局新近出版的《崂山摩崖集萃——华楼篇》等,均有介绍。通过比较会发现,各著作间对这首词的断句分歧较大。除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的《崂山志》收录此词时未加标点外,其他几本著作对此词的断句均有不同。如《崂山碑碣与刻石》断此词为:“酹江月,清虚至道,愿同流客,客俱达真理,识破幻缘终久,假物外参寻知己,幽上山林,喧居廛市,动净常明,示纵横妙用,湛然消息无比,真空渺邈难量,微来不见透骨穿筋髓,表里灵光无曲委,道在先天而矣,这些功夫真实做就,暗合先师指,他时若解,顿然心上欢喜。”[4](P132)《崂山诗刻今存》对此词第一段断句为:“清虚至道,愿同流,客客俱达真理。”[5](P117)
学者间对此词的断句之所以出现差异,也许是对《酹江月》词牌未作充分的考察,其实《酹江月》是《念奴娇》词牌的别名,以《念奴娇》为词牌的历代文人作品有很多。当然,《念奴娇》词牌亦有变格形式,对崂山这首《酹江月》词刻断句时,可多选取几篇流传至今的《念奴娇》作品做参照。笔者认为《崂山摩崖集萃——华楼篇》对这首词的断句比较符合《念奴娇》词谱,笔者开篇介绍此词时的断句亦与此相同。另外,学者间对此词的断句产生分歧,恐怕还与对这首词的理解有着一定的关系。这首词中的一些用语较为生涩,读者可能不甚了解,或不同读者对个别之处的内容有着不同的看法。因当代收录此词的著作均未对其内容作出详细阐释,故笔者不揣浅陋,试对这首《酹江月》作出解析。
这首《酹江月》本是一首赠答词,是兖州道人与崂山道人相互交往中产生的,故词作的开篇就表明了两地在“清虚至道”方面密切交流的愿望,即所谓的“愿同流客客”,期望着在相互走访学习中,于修道上“俱达真理”,亦即两地道人共同修道成真,这可视为此词的第一部分。

第三部分为:“真空渺邈难量,微来不见,透骨穿觔髓。表里灵光无曲委,道在先天而矣。”这一段文字阐述了道术修行的艰辛与不易,“真空”意指修行的最高境界和层次,这对道行浅显者来说是“渺邈难量”、难以企及的,对于虔诚修道者来说,若不能悟此真道会有一种穿透筋骨的痛楚,故作者又进而感慨:表面上是一副“灵光”的修道者神态,而真道尚在天上,未全部参透——似在暗合自己道行尚浅,仍需继续努力修行。
最后一部分:“这些功夫,真实做就,暗合先师指。他时若解,顿然心上欢喜。”作者认为,虽修行成真不易,但仍要坚定意志,多用功夫,努力去做,参合先师前辈的指点,以求最终走向成功。“他时若解,顿然心上欢喜”一句设想修道成真之后无比欢喜的心情,亦显示了作者坚持道术修行的执着信念。
二、兖州董师父赠云岩子《上丹霄》词刻
董师父赠送给云岩子刘志坚的另一首词作为《上丹霄》,距《酹江月》词刻不远,文字亦为阴刻楷书,字径约20厘米,共竖排13行,其文为:
充州小董师父赠云岩子。
上丹霄。
炼神丹,凭志气,要坚牢。先锁下劣马猿猱。时中假炼,频加慧力痛槌敲。常交保护主人公,勿纵分毫。功要积,行要做,物要远,我人抛。得跳出四大形巢。虚空踏定,那里重头旧知交。始终不改志无移,德行清高。
云岩子上石。刘志德,朱志成。
由词刻落款可知,这首董师父赠送给云岩子刘志坚的《上丹霄》,也是刘志坚本人主持上石的,由刘志德、朱志成撰书。
从这首词的内容来看,主要是对道家修炼精神的阐述。词中首先说明道术修炼要志气坚定,切忌“意马心猿”,要频加努力,不应有分毫的放纵之心;其次说明道家修行要积累功能,抛弃世俗之物,彻底斩断人间各类情感的牵绊,确保德行高洁。这首词的整体含义虽然大体可知,但其中一些道家术语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恐怕不易理解,如“劣马猿猱”一词实际是“意马心猿”的另一种表达,“猱”也是猿一类的动物,古代文献中“猿猱”并用很常见。
另外,词中的“常交保护主人公”“得跳出四大形巢”两句用语较为生涩,参考其他相关资料,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其意。《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载曰:“不闻神仙之语:人似破漏房屋,主人不修补者,宫殿倒塌,坏其梁柱,是人有疾病无常者。”又载曰:“精血散者,性命也。一意者,为真主人也。”[6](P285-286)王重阳《赠董德夫》诗亦曰:“乘闲随步复寻真,冷淡清虚作主人。”[6](P31)以此看来,在道家语中“主人”似指“修道之身”而言的,那么这首《上丹霄》词刻中的“主人公”一语也应如是。至于“跳出四大形巢”如何解,笔者认为“四大形巢”或指内丹修炼术语所言的“四假凡躯”,与佛教语“四大假合”“四大皆空”类似。“四假”即“水、火、土、风”或“心、精、气、身”,道家认为人的肉体即是由“四假”聚合而成的,如《重阳真人授丹阳二十四诀》载:
祖师(王重阳)答曰:“……天有四时,人有四大。天有地、水、火、风,人有心、精、气、身……”丹阳问:“何者天有四时,春、夏、秋、冬也;人有四时,四肢四大是也。”丹阳问:“何名天有地、水、火、风,人有地、水、火、风?”师曰:“天有地、水、火、风者,金、木、水、火、土也;人有地、水、火、风者,心为火,精为水,气为风,身为土,乃是地、水、火、风也。”[6](P296)
此外,王重阳《金丹》诗亦言:“本来真性唤金丹,四假为炉炼作团。”《活死人墓赠宁伯功》诗言:“活死人兮活死人,自埋四假便为因。”《述怀》诗曰:“静中勘破五行因,由此能捐四假身。”《传神颂》云:“借他俗状做形躯,攒聚火风并地水。阳作骨骸阴作肤,眼耳鼻前安个嘴。”马钰和韵王重阳《引丹阳上街求乞》诗亦曰:“火风地水合为肌,只是愚迷走骨尸。”全真道人往往将人的肉身称为“四假凡躯”,也是他们在修行过程中力求摈弃的无价值之体,如王重阳《梦》诗言:“四假身躯贩白昼,算来何异寐时人。”《全真堂》诗曰:“一间闲舍应难得,四假凡躯是此因。”《苏幕遮·劝化醴泉人》词:“四假凡躯,恰似蚕知缘。各缚缠,夸做茧。裹了真灵,直待锅儿煎。”《水云游》词曰:“思算思算,四假凡躯,干甚厮玩。元来是、走骨行尸。”《望蓬莱》曰:“四假身躯宜锻炼,一灵真性细详猜。”马钰《满庭芳·重阳真人升霞之后》亦言:“四假凡躯弃下,真性超升。”丘处机也说:“四大假躯,终为朽物。一灵真性,自在无拘。”[7](P90)
由上看来,崂山《上丹霄》词刻中的“跳出四大形巢”亦应指跳出四假凡躯之身,即摆脱“走骨行尸”的状态而“真性超升”,真正达到修行成真的境界。另外,词中的“我人抛”“那里重头旧知交”之类的语言,笔者认为表达的是对世间人情关系的割舍之意,盖与王重阳、马钰等人为虔诚修道而斩断夫妻、儿女类家庭束缚的做法类似。
这首《上丹霄》题刻文字保存得相对清晰,故当今与崂山文化相关的著作对其收录时,在文字辨识上基本未有差异。差异主要出现在断句上,而断句方面之所以有误,大概是对这首题刻的体裁了解不够。学者或称其为诗,或称其为长短句,如王集钦《崂山碑碣与刻石》载录这首题刻时说:“不诗不词的长短句中,充满了做功积德的勉励之情。”[4](P145)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准确,“上丹霄”一词虽然常出现在道家诗词用语中(1)如王重阳《虞美人》:“仙音一派莹声招,此时还许、返本上丹霄”(参见王重阳著,白如祥辑校:《王重阳集》,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92页);《小重山》:“蓬莱须访旧王乔。重相约,同共上丹霄”(参见王重阳著,白如祥辑校:《王重阳集》,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181页)。马钰《遇仙槎》和韵诗曰:“心无喜与忧,化道崇真快。未敢上丹霄,且结金莲会”(参见《重阳教化集》卷三,载于王重阳著,白如祥辑校:《王重阳集》,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247页),等等。,但金元时期也本有《上丹霄》词牌名。如王重阳与马钰即有相互唱和的《上丹霄》词作,王重阳《上丹霄》词曰:“向终南,成遭遇,做风狂。便游历海上嘉祥。闲闲得得,任从词曲作诗章。自然神气共交结,认正心香。真清净,唯清湛,还清彻,处清凉。赤青红白又兼黄。五般彩色,近来围罩宝珠光。这回应许碧霄上,明耀无方。”马钰和韵曰:“遇风仙,心开悟,骋颠狂。黜妻屏子便迎祥。逍遥坦荡,恣情吟咏谩成章。就中行化觅知友,同共闻香。烹丹鼎,下丹结,中丹热,大丹凉。不须炼白更烧黄。自然玉性,万般霞彩射人光。上丹霄去住蓬岛,永永圆方。”[6](P240-241)有了这两首《上丹霄》的唱和之作,参照其体例格式与押韵方式,便很容易对崂山上这首董师父赠送给云岩子的《上丹霄》词刻予以断句了。
三、刘志坚“云岩子作”诗刻
在兖州董师父赠云岩子《上丹霄》词刻右下方的一岩石上,刻有“云岩子作”七绝一首,文字为阴刻楷书,字径约20厘米,共竖排10行。诗句镌刻长短错落,每句两排,其文为:
云岩子作。
先生有志不须愁,劳擒意马锁猿猴。白牛常在金栏里,免了伦回贩骨头。
姜玄童上石。
诗刻开头的“云岩子作”之语,表明这是刘志坚自己所作的一首诗歌被镌刻到了山石之上。诗刻落款为“姜玄童上石”,姜玄童应是刘志坚的门人。诗刻离“刘志坚遗蜕处”较近,或是刘志坚逝世后,门人姜玄童将他这首诗歌操办上石,以作颂念。
元代集贤大学士赵世延所撰《云岩子道行碑》等文献皆载,刘志坚“不知书”,故其所作诗歌不会很多,更没有个人文集流传。但《云岩子道行碑》又载其“弱冠西事永昌王,掌鹰房,倜傥负才气,有干材,不甘落人后”“雅不知书,言出理会。”(2)关于《云岩子道行碑》的详细内容,可参周志元:《崂山志》卷六《金石志》,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214-217页。以此可见,刘志坚虽然不识书,但有才气,能言会道,善用口语理会。他身前有多位擅长诗词创作的全真道前辈,耳闻他们创作的大量与修道相关的诗词作品定会受到感染,从他把多首道家诗词镌刻上石的做法上也可以看出这类诗词对其影响之深。在这种情况下,其“不甘落后”之心也一定会激发出他身具的才气,并促使他口作诗歌以攀附名道,也本属自然。
刘志坚这首诗歌在《云岩子道行碑》中也有记载:“尝作颂曰:‘先生有志不须愁,牢牵意马锁猿猴。白牛常立金栏里,免了轮回贩骨头。’”(3)此处所引刘志坚此诗,以周志元《崂山志》(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214-215页)卷六《金石志》中《云岩子道行碑》所记为底本,而清人黄肇颚《崂山续志》所载《云岩子道行碑》(题为《有元故崇真利物,明道真人道行碑》)中所记刘志坚此诗,在个别文字上与周志元《崂山志》所载不同,具体为:“先生有志不须愁,牢拴意马锁猿猴。白牛常在金栏里,免了轮回贩骨头。”详见(清)黄肇颚:《崂山续志》,山东省地图出版社2008年版,第153页。通过文字对比会发现,碑文中所载诗歌的个别文字与崂山“云岩子作”诗刻有出入。“云岩子作”诗刻“劳擒意马锁猿猴”一句中的“劳擒”在碑文中作“牢牵”;“白牛常在金栏里”一句中的“常在”在碑文中作“常立”;“免了伦回贩骨头”一句中的“伦”字在碑文中作“轮”。刘志坚素不知书,其诗歌当主要以口作口传的方式传播,这种口头诗歌一旦被书写于载体之上,个别文字难免因口音接近而导致差异。况且,赵世延虽作有《云岩子道行碑》,但其与刘志坚并未有交往,据碑文内容可知,此碑是刘志坚去世20年之际,赵世延应其弟子黄道盈所请并听其转述刘志坚事迹后撰作的。刘志坚这首诗歌能被载入碑文,恐怕也是黄道盈转述的结果,口头转述过程中个别文字亦难免出现差误。
至于哪个版本更准确,笔者认为《云岩子道行碑》所载与崂山“云岩子作”诗刻都有不妥之处,二者对此诗的转录皆存在文字误差。前已提及,刘志坚作诗的动机多半是受到名道诗词的感染而萌生的,他在将诗词镌刻上石时,一定会对多数诗词进行甄别和选择,这在无意间使其了解和学习到大量前人的诗词作品。可想而知,当刘志坚自己进行诗歌创作时,定会借鉴前人的诗歌艺术,在诗歌创作中化用前人的诗句或以此为典也在所难免。
事实上,刘志坚这首“云岩子作”诗刻确实有对全真道前辈诗词的借鉴成分。全真道祖师吕纯阳曾作有一首七言绝句,文为:“休夸年少骋风流,强走轮回贩骨头。不信试临明镜看,面皮底下是骷髅。”[8](P688)其中“强走轮回贩骨头”与“云岩子作”诗刻中的“免了伦回贩骨头”相似,但其中的“伦回”在吕纯阳诗歌中作“轮回”。以此反观“云岩子作”诗刻中的“伦回”及《云岩子道行碑》中的“轮回”可明显看出,刘志坚的这首诗歌末句写为“免了轮回贩骨头”才是准确的,即《云岩子道行碑》所记此句较为合理,而崂山“云岩子作”诗刻中镌刻的“伦回”则过于随意了。又,元代仙游山道士彭致中所集《鸣鹤余音》中收有一首马丹阳的《满庭芳》,词中言曰:“思今古,从前勇猛,尽葬在北邙山。不如心行善,无烦恼,养就朱颜。怕无常限到,意马牢拴。神炁休教败坏,锁白牛、常在金栏。修行事,自家性命,莫作等闲看。”[9](P268-269)其中的“无烦恼”“意马牢拴”“锁白牛、常在金栏”,与崂山“云岩子作”诗刻中的“先生有志不须愁”“劳擒意马锁猿猴”“白牛常在金栏里”有相通之处。此外,马钰《金莲出玉花·莱洲仓使卢武义》其二亦曰:“牢擒意马,紧锁心猿宁著假。”[10](P138)《满庭芳·赠曹八先生》词也言:“牢捉牢擒,争奈马猿跳健。”[10](P227)由这些均可看出,“云岩子作”诗刻中的“劳擒”作“牢擒”才准确,以“劳”代“牢”是谐音导致,而《云岩子道行碑》中的“牢牵”也因“擒”“牵”二字发音相近而误;“云岩子作”诗刻中言白牛“常在”金栏,与马丹阳《满庭芳》词句“锁白牛、常在金栏”契合,而《云岩子道行碑》作“常立”亦音误。
由上而论,刘志坚这首诗歌的准确书写应为:“先生有志不须愁,牢擒意马锁猿猴。白牛常在金栏里,免了轮回贩骨头。”与崂山文化相关的近现代文集对此诗也多有收录。如周志元《崂山志》卷六《金石志》即载有此诗,但差误较大,其中“牢擒意马锁猿猴”一句中“牢擒”误写为“牢拴”,“白牛常在金栏里”一句中“白牛”误写为“白中”,“免了轮回贩骨头”一句中的“免了”误写为“免使”、“贩骨头”误写为“凡骨头”[11](P200)。
刘志坚这首七言绝句的蕴意与其他全真道人类似的诗词基本相同,主要传达了一种修道理念,即控制心神、沉静专一。所谓“牢擒意马锁猿猴”,也就是说道家修行要意志坚定,戒除“意马心猿”式的躁动不安状态。其实“意马”“心猿”二词普遍存在于王重阳、马钰等全真道人的诗词及修炼要诀中,几乎成了用以批驳修道不专的术语。“白牛常在金栏里,免了轮回贩骨头”一句,多用道家修炼术语,不易理解。《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记载:
问曰:假令白牛去时,如何擒捉?诀曰:白牛去时,紧扣玄关,牢镇四门,急用先人钓鱼之法。又用三岛手印,指黄河逆流,掩上金关,纳合玉锁,如人斩眼,白牛自然不走。名机出水登彼岸之法。有十般定性命之法。诀曰:一名金关玉锁定,二名三岛回生换死定,三名九曲黄河逆流定。是名无漏果。圆者,皆共成于仙道。若定了宝时,休教滞了腰脚,昏了眼目。此是定三宝之法。[6](P283)
这里的“白牛”在道家术语中实指“元精”,以牛作比,盖是暗指人的性冲动如蛮牛乱闯一般。若让白牛不走,意即防止淫性冲动,其方法就是诀中所言的“紧扣玄关,牢镇四门”“掩上金关,纳合玉锁”“金关玉锁定”,最终使精气归源,此正合“云岩子作”诗刻中的“白牛常在金栏里”之意,同指道家修行所强调的锁定原始淫欲之心,以保心神清净。若能做到此,则可以“免了轮回贩骨头”。“轮回贩骨头”盖指常人在淫色之心的驱使下,过度纵欲而致骨肉枯竭,或如同行尸走肉般的非专一状态,最终将会走向死亡轮回之路,这也是吕纯阳在其七言绝句诗中警惕世人“休夸年少骋风流”的原因所在。除了吕纯阳的这首七绝外,后世全真道人的诗词作品中类似之语还有很多。以马钰诗词为例,其《满庭芳·骷髅样》词曰:“样子骷髅,偏能贩骨,业缘去去来来。驰骋伶俐,不肯暂心灰。转换无休无歇,腾今古、更易形骸。空贪寿,绕经万劫,终究打轮回。”《满庭芳·叹名利》:“堪嗟虚幻事,妻男走骨,自己行尸。又何须相爱,相恋相随。”《满庭芳·寄零口孙可道》:“幻躯摸样,走骨行丘。筭来骋甚风流。父母生你之处,杀你因由。”《满庭芳·赠潍州苗先生》:“休夸美貌,休夸年少,休夸惺惺俊俏……闲想轮回生死。闲闲看,丹经子书庄老。”这些词句无不在警示着修道之人戒淫戒欲,以真正做到静心真修。
四、文献所记其他“云岩子作”崂山题刻
除以上所述“云岩子作”诗刻外,相关文献还载有多首标记为“云岩子作”的崂山题刻。以周志元《崂山志》为例,其列举散刻于各崖石上的“元华楼诸真人丹诀”时,提到多首“云岩子作”诗刻。其中有一长篇诗歌为:“落魄红尘数十年,朝朝恣性日高眠……一朝得到长生地,须感当时指教人。”(4)此诗较长,中间部分已省,全诗可参周志元:《崂山志》,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199页。经查,此诗为北宋道人朗然子刘希岳《进道诗》的节选本,故所谓的“云岩子作”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云岩子上石”,并非诗歌作者为云岩子。除周志元《崂山志》外,清代黄肇颚《崂山续志》也言及朗然子刘真人在华楼山有此长篇诗刻,但如今华楼山所存刘希岳《进道诗》题刻只有最后几句:“夹脊双关至顶门,修行径路此为根。华池玉液频频嚥,紫府元君未上奔。常使气冲关节透,自然精满谷神存。一朝行到长生路,感谢当初指教人。”这几句诗刻位于华楼山沈鸿烈别墅东竹林内的巨石上,前面大部分诗句题刻并未见到。
周志元《崂山志》又列举“云岩子作”诗刻:“天纲空疏万象疏,一株松倒华山枯。寒云去后留孤月,腊雪来时向太虚。古洞龙蛇归紫府,十年鸾凤落苍梧。自从别却先生后,南北东西少丈夫。”[11](P199)这首诗实为吕纯阳《劝世吟》29首中的最后一首(5)参见《纯阳真人浑成集》卷上,载《道藏》第二三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第687页,诗刻中的部分文字与文献所载存在出入。,所以“云岩子作”也应指“云岩子上石”。黄肇颚《崂山续志》将此诗刻误认为朗然子刘真人(刘希岳)所作。如今,这首诗刻在华楼山地区亦未见到。
周志元《崂山志》再列举“云岩子作”诗刻:“修行不要意忙忙,常把心猿意马降。世事不贪长守分,外劳不动内阴阳。忘言少语精神爽,养气全神记忆强。若使昼夜还不睡,六贼三尸尽消亡。”[11](P199-200)这首诗刻至今可见,位于华楼山碧落岩下,文字为阴刻楷书,字径约15厘米,共竖排7行,前题“离山老母作”,落款为:“大德二年(1298年)云岩子上石。”故“云岩子作”也指“云岩子上石”。《崂山志》中部分文字辨识或不确,也可能是周志元认为题刻文字有误,从而进行了校对。如“常把”题刻作“常想”,“长守”题刻作“常守”,“阴阳”题刻作“隐阳”,“记忆强”题刻作“第一强”,“若使”题刻作“若是”。至于作者“离山老母”为谁,不可详知,或是借用古代民间信仰中的“黎山老母”而来。“离山老母作”诗刻的内容主要是对道家修炼方法的阐释,其中“六贼三尸尽消亡”一句不易解。陈撄宁《孙不二女功内丹次第诗注》言:“炼形之法,总有六门……惟此一诀,乃曰真空炼形,虽曰有作,其实无为,虽曰炼形,其实炼神,是修外而兼修内也。依法炼之百日,则七魄亡形,三尸绝迹,六贼潜藏,十魔远遁。”[12](P484)孙文昌等著《崂山与名人》中说:“六贼,指损身伤性的六尘,即色、声、香、味、触、法;三尸,指在人体作祟的神有三,即上尸青姑,伐人眼;中尸白姑,伐人五藏;下尸血姑,伐人胃命,每于庚申日向天帝呈报人的过恶。因此,道士于庚申之日彻夜不眠,以使三尸无由向上天言其过失;且清气入,浊心除,行之久则身神安,此即为宁庚申。庚申日为每年阴历的六月八日。”[13](P106)
周志元《崂山志》还列举另一“云岩子作”诗刻:“道人日用是如何,景灭情亡气自和。一粒丹砂炉里滚,两条银焰透烟萝。木人会唱环中曲,石女能吟白雪歌。兔角敲开圆满月,真人无梦笑呵呵。”[11](P200)这是华楼宫后山题为“三千师父作”题刻的一部分,位于鸿烈别墅北。周志元《崂山志》中的个别文字与题刻有异,题刻原文为:
三千师父作。匠人曲道明。
四十年中,采德一颗大光明珠,霹不破,忒胡论,无凤輍大,分付一个铜眼睛,鉽脚后跟,男儿眼中滴血,大不分付,恐怕断了后人。
道人日用是如何,景灭情忘气自和。一粒丹砂炉里制,两条银滔透烟罗。木人邪唱环中曲,石女能吟白雪歌。兔角敲开囼满月,真人无梦笑呵呵。
大德四年二月廿日云岩子上石。书刘志德。
此则题刻同样是由云岩子刘志坚组织上石的,镌刻于大德四年(1300年)二月廿日,刘志德撰书,文字为阴刻楷书,共竖排15行,字径约20厘米,曲道明操作上石。题刻概由序文和诗文两部分组成,文字较为晦涩难懂,其中夹杂着一些方言俚语或谐音字,如王瑞竹说:“胡伦:方言,意思为‘整个的’,写为‘囫囵’更准确。”[5](P90)这进一步增加了理解题刻内容的难度。题刻中诗刻部分主要是对道家修炼理念和内丹修炼之法的阐释,诗句中除含有较多的道家术语外,也夹杂着“石女”“木人”等佛家禅语。至于题刻作者“三千师父”为谁,亦不可详知。
周志元《崂山志》列举的“云岩子作”诗刻还有:“三十二上抛家计,纵横自在无拘系。来到崂山下苦功,十年得个真气力。”[11](P200)这首诗确实为云岩子刘志坚所作,赵世延《云岩子道行碑》对此诗也有记载,但最后两句作“来到鳌山下死功,十年得个真气力。”周志元见到的这首诗刻,在如今的华楼山上也未见到。
另外,周志元列举“云岩子作”题刻中还有“天有三才日月星,地有三才水火风,人有三才气血精”一句[11](P200)。这一题刻至今犹存,位于华楼宫后侧去华楼峰的山路之旁,其右下方有清代文士崔应阶的诗刻。此题刻文字为阴刻楷书,字径约40×30厘米,共竖排3行。王集钦《崂山碑碣与刻石》将其称为“离山老母口占”,并言此“为华楼雕诗中的最精炼者,易懂易记。”[4](P140)与之相似,王瑞竹《崂山诗刻今存》又将此称为“离山老母三才诗”,并言“离山老母,生平不详。”[5](P103)前已提及,华楼山碧落岩下有“离山老母作”诗刻,但言此处题刻的作者也为“离山老母”,不知何据。周志元《崂山志》称其为“云岩子作”,亦应指“云岩子上石”。其实,这三句题刻的内容,在道家相关文献中早有记载,为道家修炼要诀术语。汉代班固《白虎通义·封公侯》篇即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等,君、父、师”的记载[14](P131)。唐代张果老《太上九要心印妙经》载:“天有三,日月星,以应人之眼耳鼻;地有三,高下平,以应人之魂魄精。魂魄精者,以应人之精气神。”[15](P313)《重阳真人授丹阳二十四诀》亦载:“丹阳问:天有三才日、月、星,地有三才乙、丙、丁,人有三才精、神、炁是也。”[6](P296)以此可见,道家语“天有三才日月星,地有三才水火风,人有三才气血精”,应是历代道人在长时间的修道过程中逐渐感悟出的修炼术语,故言其为某位人士所作的诗歌恐怕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