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伪存真图通文史美术史论自立他山
——“鉴定与中国美术史研究”研讨会综述(下)
文/戴晓云
邵彦:近期所见书画鉴定个案两例
邵彦就个案中呈现在绘画、书法中的风格进行研究,而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她对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的“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上海博物馆举办的“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的展品做了两个个案研究。
邵彦首先分析董其昌的《山居图》(图八),指出程嘉燧认为这是董其昌早年作品的观点值得再思考。为了证明这个观点,邵彦几乎用了董其昌所有时段的作品,包括书法和绘画。从《行书论书卷》《纪游图册》《燕吴八景图册》《烟江叠嶂图卷》到《行书罗汉赞》,49岁的《罗汉赞》表明此时董其昌大字狂草成熟,对于从42岁的《燕吴八景图·西山秋色》(图九)到50岁的《烟江叠嶂图》发展成熟的长线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狂草快速奔跑的中锋线条,到山水画舒缓的长线皴,难度降低。
邵彦认为,《山居图》的时代应该重新归属,应为董其昌中期作品,不属于早期。董其昌早期的两件作品,一件是38岁作品、一件42岁作品,体现的主要不是遍学传统,而是从科举书法脱化的过程。
董其昌个人风格的形成足迹,主要体现在《罗汉赞》的成熟草书面貌、《烟江叠嶂图》的中锋长皴线。《山居图》皴法较《烟江》长皴线柔和,年代更晚些。
对于传为李公麟的《五马图》(图一〇),邵彦以《临韦偃放牧图》(图一一)和《孝经图》(图一二)为李公麟作品的标准器,综合黄庭坚的作品,对《五马图》进行了分析考证。
她认为《五马图》有明显裁割痕迹,原来可能不止五马。马旁“黄书”系伪添,笔力纤弱似明中期以后人书,书写位置古怪。后跋黄庭坚、曾纡书法皆真,黄庭坚书法为盛年佳作。黄庭坚跋纸张质地与本幅相同,但中间有裁割,年代相同,是否原配不得而知。人马画法精妙纯熟,属于画史孤品,无法置入现有线索。这些与她认可的李公麟《临韦偃牧放图》和《孝经图》画法有明显差异。
邵彦认为,《五马图》是北宋画,后添黄庭坚题,后纸黄跋有可能是移配。无法证明本幅是李公麟画,更倾向于是专业画家作品。亦无法证明是皇家马政档案,疑为屏风小样。
戴晓云:佛画鉴定个案和中国美术史研究
近年来,佛教美术(宗教美术)成为研究热点,由于这些文物的鉴定没有纳入传统书画鉴定的范围,因此与传统书画鉴定相比,佛教(宗教)文物鉴定问题更显重要。戴晓云围绕宗教画鉴定个案探讨中国宗教绘画的研究。首先以一幅明代嘉靖年间的道场画(图一三)展开,进而分析明代宗教绘画的时代风格特点,地区风格特点,比较了水陆画(传统)和民间宗教画(民间道场画)(新兴)的区别。
虽然此画的嘉靖年款画面漫漶,但经过分析,不存在改年款的可能性。题记上有年号“嘉靖”(图一四)。有些模糊不清,是不是后代的涂改和作伪呢?本幅是明代的还是清代的呢?这个问题可以从年号本身来考虑。“嘉”字上半部分的“吉”字没有漫漶,因此嘉字没有问题,清代有嘉字的年号就是“嘉庆”,而庆字的繁体是“慶”字,笔画比较多,作伪者想要把“慶”字完全刮干净也不太可能,因此嘉靖二字作伪的可能性不大。这幅画应该就是明代嘉靖年间的绘画。
戴晓云指出,明代的宗教绘画(包括卷轴和壁画)、金铜佛造像中人物的眉眼、造型、服饰和清代的相比,明代作品都相对生动,面色柔和,带有笑容,有的造像或雍容华贵,或庄严肃穆,但均较为自然,不刻板。嘉靖款的道场画人物自然生动,面带笑容。
古浪博物馆藏明代的水陆画共有42轴,根据题记,这些图是明代万历三十一年重修过,到清代雍正再重修。那么万历三十一年之前就绘制了。上述画作是明代的作品,具有上述描绘的明代时代风格。例如韦陀像中韦陀菩萨面带笑容(图一五),脸型丰腴圆长,造像生动,神采飞扬。
青海西来寺藏水陆画24轴,是明万历年间的画作,画风和人物造像也具有明代的时代风格(图一六),首都博物馆藏有万历年间慈圣皇太后造的水陆画40余轴(图一七),其绘制风格和青海西来寺的绘制风格完全一致。虽水陆画存在粉本的问题,但时代风格无疑是两馆所藏画风十分接近的根本原因,首都博物馆藏水陆画和青海西来寺水陆画具有相同的时代风格:西来寺藏水陆画的水陆缘起图和古浪博物馆藏的水陆画的水陆缘起图不仅人物绘制风格相似,而且人物形象也完全相同。

图八明 万历董 其昌山 居图上 海博物馆藏

图九董 其昌吴 燕八景图册之一 上海博物馆藏
公主寺位于山西繁峙,大雄宝殿有一堂明弘治十六年的水陆画(图一八)。其风格和嘉靖款道场画、古浪博物馆藏水陆画、青海西来寺所藏水陆画和首都博物馆所藏水陆画完全相同。由于公主寺绘制年代较其他几堂水陆画早,因此画艺更加精妙。
这些明代的水陆壁画和卷轴画,体现了明代的时代风格,画风端庄典雅,神态生动。共同点为人物脸型圆长,较为丰腴,眉毛弯弯;部分女仙脸上有三白脸色;所有人物柔和带笑,形象生动;均采取工笔重彩的画法;绘画形式类同,一般使用立轴的形式,神像旁有榜题,或还有功德主的姓名及所捐款项等具体内容。
但是,嘉靖款宗教画和其他的明代水陆画又有明显不同:嘉靖款道场画艺术性比同时期的水陆画差,人物造型和线条不如同期的水陆画,人物庄重典雅不足,同期水陆画的设色、线条和人物造型远胜于嘉靖款画作。比如弘治十六年的壁画采用了沥粉贴金的做法,显得富丽堂皇,色彩绚丽、古朴典雅。而嘉靖款画作则随意很多,甚至不讲究构图和对称关系。但嘉靖款道场画也有其优点,那就虽不够庄重典雅,但是比同期水陆画画得更野更活。
如上分析,这幅画和同时代的明代人物画有共同点,但又有明显区别。艺术风格和同时代的中原地区、北京地区的绘画艺术风格相差极远,具有明显的差异,那么为何和同时代的水陆画差异这么大呢?
戴晓云指出这是两种绘画系统,一种是水陆画的绘画系统,称之为传统绘画形式,承袭了传统的道释绘画形式;一种是民间宗教仪式上使用的图像系统,是民间形成的一种新的绘画,是配合民间宗教的一些仪式,在道场上使用的,其艺术具有民间性,不少具有年画的特点。这些新兴的绘画虽然和水陆画同时期,但艺术风格有差异,是由于宗教文化的形成和传承、绘画的传承和创新、粉本和画工不同。这些宗教画,大多分布在南方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些绘画和一定的宗教文化和宗教仪式配合使用,是民间教派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研究清楚这批宗教画的性质和题材,对民间宗教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弄清这批宗教画的性质,相关研究者使用图像作材料时,才不会用错。
道释画可以用艺术风格来判别,但鉴别有时候和艺术风格无关。戴晓云以《十王图》为例说明,由于“十王”在中国丧葬文化中特殊的地位,《十王图》的使用范围相当广泛。《十王图》既可能是佛教水陆的“十王”,也可能是道教黄箓的“十王”,还可能是民间宗教度亡仪式上的“十王”,也可能人们为了让亡人安心上路,把“十王”挂在墓中,道教徒悬挂道教性质的“十王”,佛教徒悬挂佛教性质的“十王”。这些《十王图》,可能出自一个粉本,但性质却完全不同。这种情况,在很多道释画中都存在,这是研究时尤其需要注意的问题。
尽管传统宗教绘画和新兴宗教有相似之处,同样具有明代宗教画的特点,绘画形式类同,一般使用立轴的形式,神像旁有榜题,或还有功德主的姓名及所捐款项等具体内容。但如前所述,它们在艺术风格上有很大的差异。由于道场画是配合一些宗教仪式用的,因此从绘画风格的差异,可以窥探其背后代表的宗教文化。这是读图分析其艺术风格和来源,从而为探寻宗教文化的类型提供历史证据的一个例子,也就是鉴定在佛教美术史研究上的作用。

图一〇 李公麟(传) 五马图 日本私人藏

图一一 李公麟 临韦偃牧放图(局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一二 李公麟 孝经图(局部) 大都会博物馆藏
朱万章:宋画鉴定的几个误区
朱万章谈了自己对宋画研究的几点心得。
首先,书画鉴定的基本问题是断代。一般说来,对于一幅古画的鉴定,首先确定其时代气息。画面透露出的“气韵”,是鉴定宋画的先决条件。这种“气韵”的获得是建立在对存世宋画的饱游饫看之上的。刘勰《文心雕龙》:“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运用到鉴定宋画可以衍变为“观千画而后识气”。宋画有一种共同的时代气息,即画面透露出的“气韵”,启功将其称之为“望气”。这种时代气息包括画面本身所蕴含的新旧程度、包浆、笔法、墨韵、赋色、材质、伤况、装裱等,甚至包括很多不可或很难言说的成分,因而在鉴定起来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不可确定性或模糊性,但只要对同时期的画作的共通性有所认知,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信息,就不会妨碍对画作本身时代的判定。
虽然所谓的“气韵”有一定的主观性,甚至有很大空间的不可捉摸性,但由于这是建立在对同时期作品共性的认知上,因而对于传统书画鉴定来说,目前仍是颠扑不破的不二之选。现在的不少书画鉴定实践,缺少这个环节的认知和积淀,轻言真伪,各说各理,因而有南辕北辙之虞。鉴定的关键一步最必须看原迹,任何精美的画册和高像素的电子图版都无法替代对画作本身的考察(图一九、图二〇)。
对于孤本作品的鉴定与比对,按照约定俗成的惯例,遇到没有同一人的作品作为比较参照的孤本,如果到代,且又无法拿出铁证证伪的前提下,一般便认定为真迹。辅助依据不可尽信。
画作本身以外的信息,如收藏印鉴、题跋、文献著录、材料、装裱及其他辅助依据,只能增加作品的文化附加值,也可以作为书画真伪的证据链之一,但不能作为判断书画真伪的直接依据。科技鉴定只能证伪。预设结论的证据链不可信。
对前人鉴定结论提出质疑的精神固然可贵,但须建立在论据充分的前提下。预设结论的证据搜索与推论不能作为书画真伪的依据,所有可能性都不能成为“证真”和“辨伪”的证据。宋画的鉴定存在作品优劣与真伪问题。一般情况下,一件有定论的宋画真迹其艺术价值是高的。但有时候并不尽然,有部分作品虽然是真迹,但不乏懈笔。也有的作品虽然画得很好,但却不是画家真迹。
朱万章认为,鉴定的先决条件是回到作品本身,但现在很多书画鉴定文章,并非建立在对作品原件的研究之上,而是抓住一点,加上各种推测,对已有明确鉴定结论的作品在没有铁证的前提下,轻易否定,对初入美术史研究之门的后学者造成困扰。朱万章建议,对待美术史上的名作,如果该作品前人已有结论,且这种结论已经被学界所广泛采纳,在确实拿不出令人信服的铁证证伪的前提下,理论上仍然遵循约定俗成的原则。

图一〇 李公麟(传) 五马图(局部) 日本私人藏

图一三 明嘉靖款 民间宗教道场画 私人藏
赫俊红:历史文献中的书画鉴定
历史文献可作为书画鉴定的辅助佐证。历史文献中有关书画家及书画作品的记载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纯文字的,如以集中记人为主的画史类著作,以及散见于笔记、杂记、诗文集和地方志等的有关记述;以记载作品的为主的书画著录书,如记录宫廷藏品的宋代《宣和书谱》《宣和画谱》,清代《石渠宝笈 秘殿珠林》初、续、三编,记录私家藏品的明清著录书约有六七十种。
另一种是图像的,以照相和珂罗版印制等技术,影印成书画作品的单幅或集册。这种图像记载方式出现在清末,民国时被集中在上海、北京的各大出版机构广泛采用。如上海神州国光社由邓实和黄宾虹主编的《神州国光集》21集、续集20集,文明书局刊印廉泉(小万柳居士)收藏而成的《名人书画扇集》60集,商务印书馆的《名人书画集》30集;而北京延光室、北平古物陈列所、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则依托清宫旧藏来影印,如《故宫书画集》47期、《故宫》44期。20世纪40年代末郑振铎编刊的《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8集。
面对如此庞杂的书画文献资料,首先要有辨析和质疑的鉴定意识。具体到某一书画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在梳理文献记载时,要注意两点:文献谱系查检,判断记述文献的承袭与变异;文献原真性,对最本源记述的追溯与采信。从此角度重新审视旧藏著录书画或现存书画作品,会发现诸多以往被忽视的问题,从而去伪存真,以正视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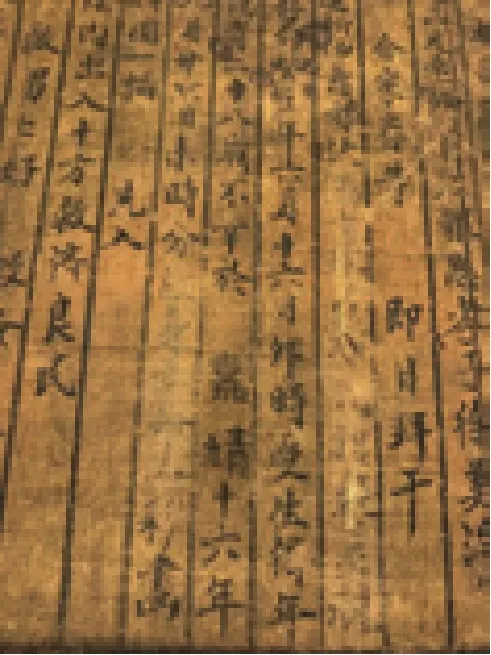
图一四 明嘉靖款民间宗教道场画(局部) 私人藏

图一五 明万历 韦陀像 古浪博物馆藏
以晚明画家马守真为例。1981年版《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俞剑华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767页)记其小传曰:“马守真(1548-1604),(明)女。一作守贞,小字玄儿,又号月娇,一署马湘,有小印曰献庭;善画兰,故湘兰之名独著。金陵(今南京)妓,居秦淮胜处。轻才任侠,与王穉登友善。以诗、画擅名一时。……”词条所附参引书目有《明画录》《无声诗史》《图绘宝鉴续纂》《列朝诗集小传》《书林纪事》。

图一六 明万历 水陆缘起图 西来寺博物馆藏

图一七 明万历 水陆缘起图 首都博物馆藏

图一八 明弘治十六年 观音和大势至菩萨图 山西繁峙公主寺壁画
词条编者参阅的上述5种书,前4种均成书于清初,后1种晚至1935年,写作者皆非传主马守真的当时代人,因此,这些记载又源自何人何处?与马守真相友善的吴门才子王穉登是否有过对马氏的记述?与马氏同时代的、后世的记载有哪些?历史文献中著录的马氏画作有哪些?对这些问题的追踪查检,便形成了关于马氏其人和其作品的两个文献查检表,即《晚明清初各种文本对马守真的记载》《明清鉴藏家对马守真画作的著录统计表》[1]。前者从王穉登于1577年的记述到卞永誉清初的记载共34项,后者从明末汪珂玉《珊瑚网画录》到民国关冕钧《三秋阁书画录》共著录作品26幅。
对上述文献的辨析对勘可知,王穉登写于1605年、马氏去世不久的《马姬传》,是对马守真其人其事的最早且可靠的记载,王穉登是以第一人称“余”来记述马氏身世才情及两人间的交往,此传1612年被潘之恒辑录于《亘史》卷十八“外纪•艳部”,明天启间刻本。
传中确切地记载了马氏的姓名字号:“马氏同母姊妹四人,姬齿居四,故呼四娘,小字玄儿,列行曰守真,又字月娇,以善画兰,号湘兰子。”传中还记载了马氏的年龄,即甲辰(1604)秋日马氏买楼船载婵娟从南京到吴门王氏客飞絮园,为王氏祝70寿时,马姬57岁,归未几便病故。如果按公元纪年,马守真的生卒年是1548-1604年。也就是说,王穉登《马姬传》中对马氏生卒、姓名字号等传略的记载,在历史文献谱系中是最早的、最可靠的、原真性记述,是应予以采信的。

图一九 宋 范宽 溪山行旅图 绢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二〇 宋 王希孟 千里江山图(局部) 绢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以此对勘上述《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中的马守真词条,显然“一作守贞”“又号月娇”有讹误。晚明清初其他人对马氏的片段记述基本源于王氏写作。而纵观马氏其人和其作品的两个历史文献查检表,分析发现类似“守贞”的讹误多出现在清乾隆及以后时期的马守真画作著录的题名或印章中。
归而言之,基于对马守真其人其作品的历史文献谱系的查检对勘,通过对其人生平传略记述(如生卒年、“守真”非“守贞”)的原真性追溯和采信,再从真伪鉴定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这些被旧藏家视为马守真的画作,便会发现其中存在着不少的伪作。1.通过马守真的生卒年(1548-1604)便可判为伪作的作品,包括金瑗记录的《女史马湘兰竹石积赏》《马守真兰竹》,张大镛记载的《马湘兰兰竹》。2.伪款印“马守贞”在清乾隆时及以后藏品上的使用,其中有《石渠宝笈》记载的《明马守贞画兰一卷》,陆时化记载的《明妓马守贞白描大士轴》《明马守贞水墨梅兰册》,葛嗣浵记载的《明马守贞飞白竹轴》,杜瑞联记载的《马湘兰白描兰花卷》(图二一)。
同样,类似的伪作也存在于现存作品中,如故宫博物院藏《兰竹图轴》,题款:“甲寅七月既望写于桃叶渡舟中 湘兰马守真”,甲寅当为1554年,马氏7岁,显然是伪作。再如故宫藏《马守贞竹石扇面》,题款:“天启癸亥夏五月……湘兰马守贞”;辽宁省博物馆藏《花卉图册》(图二二),其中一页的款识为“天启甲子秋日 湘兰女史马守真”。我们知道,天启癸亥是1623年,天启甲子是1624年,此时马氏已去世20年,故系伪作。

图二一 马守真 画兰卷(伪)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二二 马守真 花卉图册(伪) 辽宁省博物馆藏

美术史研究应回归到本体研究
书法和绘画是古代人们经常使用和创作的,留存量非常大,书画鉴定是鉴定中最常见的鉴定类别。书画鉴定的研究开展较早,体系较为成熟,其经验是其他鉴定门类可资借鉴的。此次研讨会以书画鉴定为中心议题,旨在借鉴书画鉴定成熟的理论和方法,为课题的顺利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宗教画的鉴定属于书画鉴定的范围,传世书画的鉴定理论和方法完全适用于此。
另外,我们必须明确,书画史和宗教美术史是中国古代美术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近年来其他学科对图像研究的关注,大多数集中在对宗教画、石窟造像和壁画、寺观造像和壁画等宗教美术作品上。这些研究美术史的理论和方法,应该和书画史一样。无论是传世书画还是宗教美术史(宗教图像)的研究,同样有本末问题,有基础研究和本体研究,本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让学界的目光集中在宗教美术研究的本体研究上。目前,许多研究舍本追末,在尚未清楚神祇定名、题材的性质、壁画本身和临摹复制品的区别,就把这些图像当作史料用于研究中,去证明自己的结论,这样会犯使用材料的错误。有的学者使用错误的学术史,对错误的学术史不加辨别,发表自己的议论,把研究建立在错误的学术上,最后得出错误的结论;有的在基础研究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借鉴西方的研究方法,从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或物质文化和视觉文化等角度去看问题。虽然使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无可责备,但在基础研究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就使用西方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属于舍本逐末,美术史研究中过度阐释的问题也会凸显。薛永年先生在《美术史的自立与他山》一文中指出,“我不赞成用中西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看待当下的美术史论研究中的问题。艺术史论研究,既有跨文化的一面,又有民族价值观和民族特色的一面。不过,需要明确的是,他者眼光,虽对我们有启发,但不能代替我们以自己的眼睛看世界,被动效仿搬来的鞋子,未必适合自己的脚。”“对此,我们更应该加强文化交流中的文化自觉,并且以卓然自立的精神在美术理论的建设中发挥他山之石的积极作用而避免外国专家也不欣赏的盲目追随。”[2]这是我们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应该持有的态度,也是宗教美术史研究中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
美术研究应立足于传统理论和方法,如果把立足于本土传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称为本,那么西方理论和方法则可称为末,研究中不可本末倒置。中国美术史研究的现状告诉我们,目前美术史研究更多应该在于自立,而不是他山之石。如果美术史研究的本体研究已经完成,那么借鉴他人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则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他山之石只有建立在扎实的基础研究上,才会结出硕果。
[1]赫俊红:《丹青奇葩——晚明清初的女性绘画》,第118、130页,2008年。
[2]薛永年:《自立和他山——美术史论的交流和借鉴》,《美术观察》201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