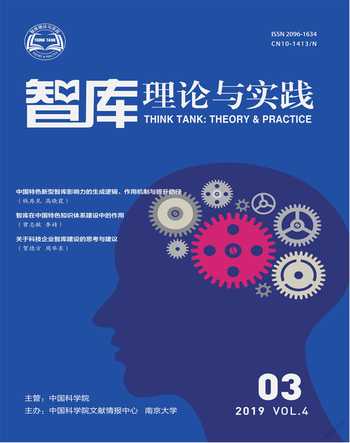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影响力的生成逻辑、作用机制与提升路径
钱再见 高晓霞

摘要:[目的/意义]影响力是智库的生命力和价值之所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影响力的核心是其作为政策研究与咨询机构的政策研究洞察力、政策设计的创造力和政策咨询竞争力。[方法/过程]本文通过文献研究和系统分析认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影响力的生成离不开国家治理中的需求拉动,知识运用过程中的内在驱动,以及政策网络中不同主体的协同联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影响力的生成还需要在政策研究、政策咨询和政策制定过程中逐步落地,形成政策话语的传播力、说服力和影响力。[结果/结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型智库要在治理进程中催生影响力,同时,要通过知识运用提升影响力,此外,还要在政策网络中不断扩大影响力。
关键词:新型智库 影响力 治理 知识运用 政策网络 政策话语
分类号:D601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19.03.01
影响力是智庫的生命力和价值之所在。影响力,包括政治影响力,也是评价智库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之一[1]。加拿大智库研究学者唐纳德·E.艾贝尔森(Donald E. Abelson)在其《智库能发挥作用吗? 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影响力评价》(《Do Think Tanks Matter?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Public Policy Institutes》)一书中认为,智库能否在政策制定共同体(policy-making community)中建立和维持强大的影响取决于这些机构怎样定义其使命(missions),取决于其领导者(directors)用以实现既定目标(stated goals)的资源和战略,而其所处的政治环境也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2]。默里·L.韦登鲍姆(Murray L. Weidenbaum,1927—2014)指出,智库对公共政策做出的最根本和最持久的贡献,是智力上的竞争意识(intellectual sense of competition)[3]。黛安·斯通(Diane Stone)从中观层面分析了智库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力,她提出,知识交流在政策研究机构中具有重要作用[4]。国内学者王莉丽认为,智库影响力的实质是舆论影响力[5]。朱旭峰则认为,智库影响力是通过直接或间接途径使政策过程或政策决策者的观点发生改变的可观测到的具体行为[6]。本文认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影响力主要是指其在政策过程中对于政策问题的洞察力、政策方案设计中的创造力以及政策咨询中的说服力。
1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影响力的生成逻辑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影响力的核心内容包括其作为政策研究与咨询机构的政策研究实力、政策设计能力和政策咨询竞争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影响力的生成离不开国家治理中的需求拉动,知识运用过程中的内在驱动,以及政策网络中不同主体的协同联动。
1.1 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影响力生成提供了广阔空间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政府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新型智库基于政策调查、政策研究和政策分析为政策过程奠定厚实的知识基础,广集民意民智,从而为政策制定及时提供智力支撑。治理强调的法治化、民主化和透明化为新型智库功能的发挥和影响力的生成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首先,治理的法治化内在地要求政府行政决策过程的程序化和规范化,从而为新型智库影响力生成奠定了法制基础。法治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托,其所强调的是制约权力的规则之治和程序之治。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意义上明确提出了要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强调了必须做到位的5个“法定程序”,即: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以及集体讨论决定。2019年5月8日颁布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从提高政府公信力的意义上强调了健全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机制的重要性。规定决策承办单位应当组织专家、专业机构论证相关决策的必要性、可行性、科学性等。并且规定:“专家、专业机构应当独立开展论证工作,客观、公正、科学地提出论证意见。”新型智库影响力的构建很大程度受益于治理的法治化对于政府决策所做出的专家论证的程序性设计和明确要求。
其次,治理的透明化意味着政府公共决策过程和结果等方面的信息公开,进而为新型智库影响力生成打开了信息通道。因为信息被认为是公共政策创新的命脉,这在客观上为新型智库设计科学的政策方案规划并且生成影响力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从目前中国公共政策制定的情况来看,咨询力度的扩大改善了政府决策的信息基础,推动了科学、民主决策的发展[7]。而信息公开和信息共享也为新型智库政策分析和政策咨询能力的提升和影响力的生成打开了信息通道。
第三,治理的民主化强调治理过程中的多主体协同参与,由此为新型智库影响力生成拓宽了渠道空间。新型智库正是作为治理过程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在政府决策中发挥咨询参谋作用而不断生成影响力的。在协同治理的背景下,智库分享了治理过程中合作性的知识权力和话语权力。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智库作为政策制定间接主体和决策辅助系统固然并不具备制定政策的决断权,但其作为咨询对象所拥有的话语权在决策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使政策从思想逐渐演变成现实。
1.2 知识创新基础上的知识运用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影响力生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不难理解,现代智库作为知识创新和知识运用而孕育的结果,其本身就是知识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ies)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创新、知识运用、政策研究、政策分析与政策咨询作为现代智库的中心工作,无疑也是直接关系到智库影响力生成与提升的核心因素。一方面,现代智库是知识运用、政策研究与政策分析实践发展而形成的政策研究机构;另一方面,它也是现代公共政策研究作为一门科学和一种职业不断成长的组织形式和重要载体。以色列公共政策学者叶海卡·德洛尔(Yehezkel Dror)认为,智库,就其独特的政策研究与政策分析组织意义而言,不但是政府设计(governmental design)的有意义的发明,也是各种政策研究成长的摇篮(breeding ground)……智库是政策研究的最纯粹的组织体现(the purist institutional expression of policy studies)[8]。实际上,任何能够形成政策的理论问题都离不开知识生产、知识创新和科学研究。换句话说,从理论研究发展到公共政策需要大量的知识运用、政策研究和政策分析。其实,知识运用理论就是致力于探讨政府公共决策中知识资源在知识共同体和决策共同体之间的流动。而对于其他政策参与者而言,是否有意愿接收智库知识运用的思想传递也成为衡量新型智库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从机理上讲,知识发展能力对政策民主化环境的实现是有促进作用的,既提升了社会公众的政策参与和民主监督能力,也无形中助推新型智库影响力的生成与扩大[6]。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呼唤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现代化。可以说,知识创新是新型智库的生命力和竞争力之所在。同时,在知识创新基础上的知识运用则直接推动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影响力的生成与扩大。
1.3 统一战线意义上的政策网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影响力生成提供了多元通道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职能改革与还权于民的呼声推动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勃兴。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又演变形成了新的“治理理论”。无论是新公共管理理论还是治理理论,其实都源于多元主义。在多元主义理论范式中,强调影响公共决策体系的社会力量多元性,认为影响决策的各因素和主体处于分散而不断变化的状态,而智库“只是越来越拥挤的思想市场的众多群体之一”,智库与利益集团、工会、人权组织、环境协会及其他非政府团体一样,其参与政治过程的目的在于“影响公众态度和政策决策”[9]。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相较于“铁三角”(Iron Triangle)模型中所谓的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和利益集团互动勾结的政策制定模式而言,多元主义模式更多地体现了现代多元社会中多元主体通过“竞争”达成“妥协”的一种民主政治取向。正如罗伯特·A.达尔所认为的,民主政治的最核心因素不是权力对权力的制约。在这些因素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社会团体、企业和公民个人[10]。传统政治民主化理论忽视了社会中的多元制衡机制的作用。在我国,统一战线是一种大联盟和大联合,其出发点是共同政治基础,其关键任务是达成政治共识,其目标和宗旨就是巩固和发展广泛的政治联盟[11]。从这个角度说,统一战线本身虽然并非纯粹意义上的智库,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体系中事实上发挥着新型智库的功能,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政策网络的效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统一战线不仅具有“凝聚人心”这一“最大政治”的使命,而且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不断“汇聚力量”的任务,发挥着基于元治理意义之上的多中心治理功能、协商式治理功能和网络化治理功能。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中,统一战线具有独特的地位,突出地表现在能够提供决策咨询平台、人才智力资源和资金政策支持[12]。统一战线在政策网络意义上发挥的智库功能主要体现在反映政策诉求、提供决策咨询、设计政策方案、反馈政策信息和实施政策监督等方面。
2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影响力的作用机制
众所周知,智库的首要目标是要通过在知识共同体中的知识创新、知识运用、政策研究和政策咨询影响决策公共体中决策层的政策决定。同时,由于智库影响力具有显性、因果性、直接(间接性)等特点[13],因而,智库也必然要致力于对媒体舆论和社会公众产生影响力。换句话说,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影响力的生成还需要在政策研究、政策咨询和政策制定过程中逐步落地,形成政策话语的传播力、说服力和影响力。
2.1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影响力的内外互动机制
影响力的作用机理是由内而外的。就新型智库而言,其影响力的生成和作用机理是基于自身的知识创新、知识运用在知识共同体内外建构互动机制,包括知识共同体与公众、决策共同体以及媒体之间的互动机制(如图1所示)。
首先,在面向公众的政策调查基础上发挥新型智库政策问题建构的公众影响力。与“专家治国”政治背景下的精英决策不同的是,在民主政治的理念和背景下,更加需要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的结合。政策问题识别、界定与共识的达成是通过公众参与的途径和民主协商的渠道来实现的。但是,在这一民主协商的过程中,智库专家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在智库实施的政策调查基础上,通过与公众的互动,在民主协商中构建政策问题,从而发挥智库在政策问题构建过程中的公众影响力。
其次,在“谋”与“断”的政策咨询互动中提升智库政策咨询的决策影响力。智库作为决策共同体中“决策层”即“决策中枢系统”的决策咨询系统或决策辅助系统,其所承担的政策设计和政策分析工作是政策决策者的决断依据。如果说,智库的政策研究、政策分析以及政策设计是一种“谋”的工作,那么,“决策中枢系统”的政策方案抉择则是一种“断”的工作。“谋”与“断”相互支持,相辅相成。智库作为“知识与权力之间的桥梁(bridge between knowledge and power)”[14],其稳固性依赖于政策调查的实证性、政策知识的真理性和政策分析的科学性。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中,知识共同體中的新型智库与决策共同体之间“谋”与“断”的频繁互动既体现了新型智库知识创新与知识运用的内在逻辑,也凸显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决策影响力作用的关键机制。
第三,在与媒体及公众的互动中扩大智库政策宣传的舆论影响力。现代社会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十分重视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政策宣传,使公众充分了解政策[15],进而也扩大了智库的舆论影响力。德洛尔认为,政策研究机构(智库)的研究成果应该是既全面又深入的,但是表达形式和语言应该容易为公众所接受;而且其目的应该是增加人们可以采取自主立场的机会,而不是向他们兜售这一个或另一个解决方案。所以,政策研究组织(智库)的研究报告,应该通过通信宣传工作,包括书面的报告、电视节目等各种手段广泛地传播出去[16]。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公众进行政策启蒙教育是现代智库的一项基本工作和功能。在卡罗尔·赫希恩·威丝(Carol Hirschon Weiss, 1926—2013)看来,也许社会科学研究最频繁地进入政策领域的方式就是通过这种被称为“启蒙”(enlightenment)的过程实现的。实际上,并不是一项单一研究的结果,也不是相关研究的结果直接影响了政策。而是社会科学研究产生的概念和理论观点渗透了决策过程[17]。其实,智库不仅针对普通民众,也面向决策者和社会精英进行政策宣传。
2.2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影响力的内部驱动机制
从哲学辩证法的角度来说,智库影响力的生成逻辑和作用机理根本在于内因。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影响力无疑也是生成于智库内部政策分析专家的知识创新能力的。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智库不只是简单的议政,而是以更加专业化的出谋划策即包括了政策分析和政策方案设计,当然也包括政策辩论和政策评估[18],不断施展影响力。
首先,依托知识共同体实现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体现洞察力和判断力。政府公共决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获取和运用公共知识资源的过程。在卡罗尔·威丝所概括的6种知识运用模式即知识驱动模式(knowledge-driven model)、问题解决模式(problem-solving model)、互动模式(interactive model)、政治模式(political model)、战术模式(tactical model)、启蒙模式(enlightenment model)中,问题解决模式强调知识运用的动力来自决策者的需求,并通过需求推动或者说是拉动政策研究。而知识驱动模式则强调知识本身可以能动性地推动知识应用于实际。在知识共同体理论视角中,知识是智库影响力的基石和核心要素之一。美国兰德公司创始人弗兰克·科尔博莫(Frank Collbohm)的理解,智库就是一个思想工厂和“战略思想中心”[19]。
其次,基于知识创新和政策分析促进政策咨询,激发创造力和说服力。在艾伦·B.韦尔达夫斯基(Aaron B. Wildavsky)看来,政策分析其实就是创造力(creativity)的同义词,它可以被理论激发,也可以被实践所强化[20]。为了发挥其在决策共同体中的影响力作用,智库在知识共同体中所进行的知识生产与知识创新不仅要有洞察力,而且要有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 1917—1980)所说的“政策切合性(policy relevance)”,用儒家的话语讲就是要能够“经世致用”,能够在知识运用过程中切实解决现实政策问题。在“决策共同体”理论视角中,政治决策体系是由多种力量构成的“决策共同体”或“政策网络(policy networks)”,其内部各种力量的互动形成不断流动的政策过程,决策者为处理复杂问题,不得不依赖“决策共同体”中由专家构成的“知识共同体”,而智库则是其中的一部分力量。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安姆斯特分校彼得·M.哈斯(Peter M. Haas)指出,“知识共同体”视角侧重于在特定的专门知识领域内达成共识的过程,并通过协商一致的知识(consensual knowledge)传播给其他行动者并由其他行动者执行。它主要关注的是一个知识共同体可能对集体决策产生的政治影响,而不是所提建议的正确性[21]。换句话说,知识共同体所提出的政策建议的正确性本身是知识意义上的技术性问题,而其对决策共同体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则是政治方向上的问题,自然更加受到关注。基于政治共识而形成的政策建议则更具说服力和影响力。
最后,通过成果转换推动政策创新,展示影响力和公信力。智库的知识权力只有在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互动和政策参与中才能转换成为对于公共政策决策的影响力,并且形成交往权力(communicative power)。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协同共治的新治理模式已经取代对抗模式(adversarial mode)和管理模式(managerial mode)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实际上,智库作为知识共同体中一种“知识精英”群体,在实际治理过程中,为决策共同体提供了广泛的智力支持,甚至形成了“政治求助于科学,决策依赖于专家”的格局(如图2所示)。如果说,基于知识共同体中智库的知识创新和知识运用有力地促进了决策共同体的公信力提高,那么可以说,也正是在政策咨询过程中通过知识共同体与决策共同体的互动合作中生成、发挥并且扩大了新型智库的影响力。当然,好酒也怕巷子深,新型智库影响力的落地也离不开交往互动能力以及传播营销理念和能力。
2.3 中國特色新型智库影响力的协同联动机制
现代多元复杂社会内在地需要多元主体的协作性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和网络化治理(governing by network)。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者克里斯托弗·K.安塞尔(Christopher K. Ansell)和艾莉森·L.加什(Alison L. Gash)提出,协作性治理是这样一种治理安排(governing arrangement),即一个或多个公共机构(public agencies)使非国家的利益相关者(non-state stakeholders)直接参与到围绕公共政策或公共项目的正式的、协商式的和共识性的集体决策过程 (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 process)[22]。在风险社会所面对大量复杂性问题的背景下,现代智库无疑是协作性治理和网络化治理中的重要力量。同时,智库参与国家治理也是公共政策制定科学化、民主化和规范化的必然要求。智库在协同治理中发挥影响力的作用机理是怎样的呢?詹姆斯·G.麦甘发现,政治与社会环境变化在为智库带来挑战的同时亦为其带来机遇,主要表现在:(1)经费的改变(changes in funding);(2)非政府组织特别是智库的扩张(the proliferation of NGO’s general- ly, and think tanks specifically);(3)全天候媒体公司的出现(the emergence of a 24/7 media);(4)技术进步更具体地说就是互联网的主导地位(technological advances, and more specifically the dominance of the Internet);(5)党派政治的发展(increases in partisan politics);(6)全球化的持续影响(the continuing impact of globalization)[1]。可见,智库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关键在于要有长期的、稳定的资金机制(funding mechanisms)以确保其能够通过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获得全面、独立的研究成果。德国学者马丁·W.蒂纳特(Martin W. Thunert)在讨论德国的智库时指出,在确保政治协商(political counseling)——即以专家为一方,以具有政治意识的公众(a politically aware public)和政治决策者(political decision-makers)为另一方而进行的不间断的双向思想交流(a constant two-way exchange of ideas)——方面,以实践为导向的研究机构(practically oriented research institutes)发挥着特殊的作用,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智库[23]。在我国,新型智库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与政治决策者以及具有政治意识的公众保持密切的互动和联动关系。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公共政策学教授马尔滕·阿拉德·海杰(Maarten Allard Hajer)等学者认为,智库是能够为决策议题进行话语建构的重要行为体[24]。所谓话语联盟(discourse coalitions),是一组故事情节(story-lines)的组合,说出这些故事情节的参与者,以及符合这些故事情节的做法都围绕某一话语而组织起来。话语建构是一种争论性的斗争,这种斗争是一种主导辩论结构的话语,并在(国家)实践中制度化,即取得霸权地位[25]。但是,智库话语权的基础是其在政策参与和交往互动过程中实现的知识权力,而知识权力的来源则是知识和信息的获取,特别是政府等公共权力部门实际治理和运作过程的信息。
智库借助于特定通道影响政策过程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其参与政策决策的现实限度。在精英决策体制和模式中,体制内的官方智库及其政策咨询无疑会受到人治思维的影响。一方面,由于认识上的偏差,我国政府决策人员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往往忽视甚至无视智库的专家参与、政策分析和政策建议。这使得智库的政策方案规划和政策分析成果因缺乏市场和环境而落入“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尴尬境地。另一方面,由于一些智库本身也缺乏足够的政策设计能力和政策市场营销渠道,导致我国智库的政策影响力一般较弱。
3 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影响力的提升路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型智库要在治理进程中催生影响力,同时,要通过知识运用提升影响力,此外,还要在政策网络中不断扩大影响力。
3.1 在治理进程中催生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影响力
一个国家的治理与善治,不仅要靠决策层的智慧与魄力,还要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过程中,借助于智库的力量与智力支持[26]。也正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新型智库得以大显身手,并且形成自身的影响力。
首先,在治理法治化的轨道上催生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影响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有机统一的。决策咨询制度作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方面,离不开新型智库的自身建设及其影响力的生成与扩大。但是,新型智库建设绝不能只为扩大自身的影响而采用不合法律程序的方式。
其次,在治理透明化的背景下凸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影响力。治理透明化意味着信息公开和信息共享的制度化和法治化,这也是新型智库获取那些进行政策分析所必要信息的制度化措施和法治化保障。在政策信息调查基础上进行政策设计和政策咨询既是智库专家的基本功,同时也是其进行政策分析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同时,也只有坚持经常性的政策调查研究,建构政策话语,才能增强其政策建议的说服力和影响力。
第三,在治理民主化的进程中增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影响力。民主通常是一项话语事业(discursive enterprise)……协商民主得益于一种科学讨论式的争论(a style of debate typical of scientific discussion)。[27]”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政策的民主化也是要通过政策话语体现的。通过话语的政策辩论和政策建言也因此具有了权力和力量,相应地就具有责任性,其职业伦理的基本要求则是要基于政策调查和知识创新向决策者诚恳建言并且需要接受监督和问责。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实施重大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制,也应明确决策者应承担的决策责任和智库决策咨询应承担的相应责任。
3.2 通过知识运用提升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影响力
可以说,智库的行动逻辑是基于审慎思辨的理论论证和政策分析而展开的。用中国古人的治学理念来讲,就是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首先,基于知识创新和知识运用提升新型智库在知识共同体中的判断力和影响力。知识是智库影响力的基石和核心要素之一。因此,智库提升影响力的基础必然在于通过知识创新促进知识运用。通常,智库专家会遵循“基础研究(basic research)→应用研究(applied research)→开发(development)→应用(application)”这一线性序列(linear sequence)的路径向决策者直接传递信息、知识和建议。其理念是,基础研究揭示了一些可能与公共政策相关的机会;于是进行了应用研究,以确定和检验基础研究的结果,以便采取实际行动;如果一切进展顺利,则开发适当的技术来落实这些研究结果;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应用。这个假设是,知识存在这一纯粹的事实迫使它朝着发展和使用的方向发展[28]。在智库的运作逻辑中,知识运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知识和政策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其次,加强话语政策分析提升新型智库在公共舆论场中的说服力和影响力。弗兰克·费希尔(Frank Fischer)被认为低估了话语分析的力量,因为他说,“话语政策分析师的方向……是一种怀疑和批判,而不是寻求真理本身(truth-seeking per se)”[29]。而马丁·雷恩(Martin Rein, 1915—2010)和唐纳德·艾伦·肖恩(Donald Alan Schön, 1931—1997)在《重构政策话语》一文中指出,政策话语通过个人、利益集团、社会运动和机构之间的互动将问题情境(problematic situations)转化为政策问题,设定议程,做出决定,并采取行动。我们认识到,政策分析是一种智力活动的形式,它可能作为更大的政策话语过程中运动的原因或结果[30]。美国波士顿大学政治学者费雯·安·施密特(Vivien Ann Schmidt)指出,“事实上,促成话语成功的因素包括许多与有助于想法成功的相同因素:与当前问题的相关性(relevance to the issues at hand)、充分性(adequacy)、适用性(applicability)、适当性(appropriateness)和共鳴性(resonance)……话语不但能表达一群行动者的策略性利益(strategic interests)或规范性价值(normative values),而且能说服其他行动者接受特定行动方案的必要性及/或适当性 (necessity and/or appropriateness)[31]”。新型智库专家作为政策分析者(analyst)通过话语政策分析要在公共舆论场中为社会正义事业作倡导者(advocate),为社会公共利益鼓与呼,为社会科学知识作立言者,为社会弱势群体作代言者,为政府公共决策作建言者(advisor),从而提升新型智库的说服力和影响力。
最后,坚持政策咨询的政治方向提升新型智库在决策共同体中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如果不考虑语言及其背后的意义世界,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就很难真正理解政策问题的由来和人们的诉求[32]。卡罗尔·赫希恩·威丝(Carol Hirschon Weiss, 1926—2013)在讨论知识运用的政治模式时坦率地指出,围绕政策问题的利益组合通常预先决定了决策者所持有的立场。或者是争论持续了一段时间并且意见已经变得强硬起来了。此时,决策者不太可能接受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证据。出于兴趣、意识形态或智力等原因,他们采取了研究不太可能动摇得了的立场。由此看来,政策过程中的政策问题识别与界定以及代表公共利益的政治共识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所进行的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如果作为公共政策分析者的智库专家自身缺乏社会公共道德,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和政治方向,那么公共政策分析也就没有意义了。评价一个政策分析者时,不应只关注其业务能力,更要考察其道德水平,选择正直、诚实、无私的专业公共政策分析人才,才能保证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合理与有效。
3.3 借助政策网络扩大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影响力
首先,在政策网络中通过协商式治理扩大新型智库影响力。在政策网络的协商式治理机制中,所有涉及问题领域的人都集中他们的才智、信念和判断来努力理解一个问题。在卡罗尔·威丝所说的知识运用互动模式中,政策研究及知识的运用只是一个复杂过程的一部分,同时也运用经验(experience)、政治洞察力(political insight)、压力(pressure)、社会技术(social technologies)和判断(judgment)。它不仅适用于面对面的情境(face-to-face settings),而且适用于通过中介(intermediaries)去收集和利用情报的多种方式[28]。实际上,决策者也是通过这一过程了解某一政策领域(policy area)的各种知识和意见。协商式治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实践形式,超越了自由民主的局限,让民主不再是停留于投票和选举这些操作性环节上,而是拓展到公共治理的全过程之中,使公共治理在坚持广泛民主性的基础上保证了参与的有序性。智库专家作为众多参与者中的一部分而进行相互协商(mutual consultations),逐步接近可能的政策方案。
其次,在政策网络中借助旋转门机制扩大新型智库专家的影响力。作为智力密集、人才荟萃的政策研究组织机构,新型智库自身建设特别是影响力的提升对人才的要求更高、更迫切。如果说影响力是新型智库的生命力所在,那么人才则是新型智库建设的核心和关键。在国家治理的政策网络体系中,新型智库的“智”来自人才流动的“旋转门”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常闭门”[33]。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统一战线的最大优势就是其所具有的人才优势,汇聚着大量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专业人才,他们是国家治理进程中党委、政府实施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的重要智力支撑。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发挥着“人才库”和“智囊团”的作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要在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政策网络体系中借助旋转门机制扩大新型智库专家的影响力。
最后,在政策网络中通过政策参与机制扩大新型智库在决策共同体中的影响力。英国公共管理学者斯特拉·拉迪(Stella Ladi)将智库理解为“与政府不同的组织,它们的目标是通过使用知识和建立网络,就各种政策问题提供咨询意见[34]”。的确,只有通过知识生产、知识创新和知识运用并且在政策研究中实现思想转变和观念创新,才能借助于政策网络中的互动、沟通和协同,在政策咨询过程中向决策共同体推广自己的思想产品,如政策设计方案等,不断扩大新型智库在决策共同体中的影响力。当然,智库专家在政策网络中的政策参与,绝不是要把知识和精力用来揣摩领导人的所谓“精神”,迎合某些领导人的心理需要,沦为领导人的“应声虫”,从事“御用咨询”,而是要通过政策调查,实地考察社会的现实问题和矛盾,实事求是地寻求解决政策问题的各种决策思路,从而在调查中获得发言权,提升政策话语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一句话,就是要在实践中求真知,以人民为中心,向决策者说真话。
4 结论与讨论
智库作为“连接知识与权力的桥梁”,其生命力和价值不仅在于学术影响力和舆论影响力,更是旨在实现决策影响力。在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影响力的生成、落地与扩大要基于自身发展的基本逻辑。在修炼内功的基础上,不断增强知识创新能力、政策设计能力和政策咨询能力,提升政策研究和政策分析的洞察力和影響力。同时,在政策咨询过程中提升话语的说服力和影响力。此外,在政策网络和政策协商过程中不断扩大自身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4.1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影响力生成于内部创新能力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影响力生成于内部创新力和判断力。其影响力生成与扩大的关键在于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分析和政策研究。智库专家作为公共政策分析者应根据外部制度环境的变化以及政策分析的内外交互过程要求来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发挥价值取向在公共政策分析中的重要作用,提高公共政策分析和政策咨询的有效性,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4.2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影响力提升应具有合法性和公信力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充分利用好大众传播媒体的优势,力图将自身的知识生产和政策研究与新媒体优势相结合,促进公众参与,彰显新型智库参与国家治理和政策制定的合法性。同时,在加强智库内外互动的过程中扩大新型智库的舆论影响力,提升其政策咨询的洞察力、说服力和公信力。
4.3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影响力扩大说到底必然源自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原则
现代治理体系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提供了制度性的框架。在这一框架中,公共政策作为民主政治体制中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的产物,其本质是实现公众意愿与公共利益,坚持以人民利益为中心,为弱势群体代言。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就意味着新型智库的一切公共政策研究必须是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的政策研究、政策分析和政策咨询。
参考文献:
[1] MCGANN J G. Report: scholars, dollars and policy advice[R]. Philadelphia: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2004: 1-39.
[2] ABELSON D E. Do think tanks matter?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public policy institutes[M]. Kingston and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2: 7.
[3] WEIDENBAUM M. Measuring the influence of think tanks[J]. Society, 2010, 47(2): 134-137.
[4] STONE D. Capturing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 think tanks and the policy process[M]. London: Frank Cass. 1996: 94-96.
[5] 王莉丽. 论美国智库舆论影响力的形成机制[J].国外社会科学, 2014(3): 13-18.
[6] 朱旭峰. 中国思想库: 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力研究[M].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22-23,96-97
[7] 王绍光, 樊鹏.“集思广益型”决策: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智库[J]. 中国图书评论, 2012(8): 12-22.
[8] DROR Y. Basic concepts in policy studies[M]// Nagel, Stuart S, et al. Encyclopedia of policy studies. New York: Marcel Dekker, 1983: 7.
[9] ABELSON D E. Do think tanks matter?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public policy institutes[M]. Kingston and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2: 49.
[10] 顾昕. 以社会制约权力: 托克维尔、达尔的理论与公民社会[J]. 公共论丛, 1995(1): 148-167.
[11] 钱再见.“人心”与“力量”:统一战线的政治使命与治理功能——兼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着力点[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5): 68-76.
[12] 钱再见. 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统一战线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研究[J].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6(3): 14-20.
[13] 朱旭峰, 苏钰. 西方思想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 基于社会结构的影响力分析框架构建[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4(12): 21-26.
[14] BULDIOSKI G. Think tank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urgent need of a code of ethics[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ot-for-profit law, 2009, 11(3): 42-52.
[15] 钱再见. 论政策执行中的政策宣传及其创新: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学理分析[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10(1): 11-18.
[16] DROR Y. Design for policy sciences[M]. New York: Elsevier Inc., 1971: 129.
[17] WEISS C H. The many meanings of research utilization[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79, 39(5): 426-431.
[18] 錢再见. 当代中国民间思想库及其功能实现路径研究: 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的分析[J]. 行政论坛, 2013(5): 54-59.
[19]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项目组. 中国智库影响力的实证研究与政策建议[J]. 社会科学, 2014(4): 4-21.
[20] WILDAVSKY A B. Speaking truth to power: the art and craft of policy analysis[M]. Boston, MA: Little, Brown and Co, 1979: 212-237.
[21] HAAS P M.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2, 46(1): 1-35.
[22] ANSELL C K, GASH A 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07, 18(4): 543-571.
[23] THUNERT M W. Think tanks in Germany[J]. Society, 2004, 41(4): 66-69.
[24] HAJER M A. Discourse coalitions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ractice: the case of acid rain in great Britain[M]// Fischer F, Forester J, et al. The argumentative turn in policy analysis and planning.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43-76.
[25] HAJER MA. The politics of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policy proces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61.
[26] 錢再见. 论新型智库的核心能力及其提升的创新路径[J]. 江海学刊, 2017(1): 105-113.
[27] GAMBETTA D. “Claro!” An Essay of discursive machismo[M]//Elster J.Deliberative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19-43
[28] WEISS C H. The many meanings of research utilization[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79, 39(5): 426-431.
[29] FISCHER F. Reframing public policy: discursive politics and deliberative practice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46.
[30] REIN M, SCHON D A. Reframing policy discourse[M]//Fischer F, Forester J, et al. The argumentative turn in policy analysis and planning[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45-166.
[31] SCHMIDT V A.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ideas and discourse[J].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8, 11: 303-326.
[32] 李亚, 尹旭, 何鉴孜. 政策话语分析: 如何成为一种方法论[J]. 公共行政评论, 2015(5): 55-73.
[33] 李建华, 牛磊. 新型智库建设热的“冷”思考[J]. 湖南社会科学, 2016(3): 23-28.
[34] LADI S. Think tanks[M]//Bertrand B, Dirk B S, et al.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science.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11: 2608-2610.
作者贡献说明:
钱再见:思路框架制定,论文撰写;
高晓霞:论文修改、完善、定稿。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e influence is the lifeblood and value of the think tank.The core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new think tank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its policy research insight, policy design creativity and policy consultation competitiveness as a policy research and consulting organization. [Method/process]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systematic analysis,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generation of influence of new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demand pull in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internal drive in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applica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different subjects in the policy network.The formation of that also needs to fall to the ground in the process of policy research, policy consultation and policy development to form the spreading force, the persuas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policy discourse. [Result/conclusion]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new think tank will have an influence in the process of governance, and the influence should be promoted through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addition, it is also expanding its influence in the policy network.
Keywords: new type of think tank influence governance knowledge application policy networks policy discourse
收稿日期:2019-05-12 修回日期:2019-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