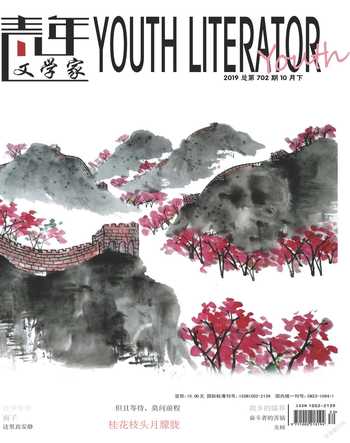从《生死场》对女性的书写解读女性悲剧
陈知训
摘 要:萧红在《生死场》中对女性的描写以及对女性悲剧的描绘是力透纸背的。在循环往复的生与死的轮回中,人们忘记了“人”的意义,自然而然地将一切压迫合理化,将一切悲剧消解在无限循环的乡村生活中。萧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女性的身体、感情和精神困境进行揭露,以唤起社会的关注和女性的觉醒。
关键词:《生死场》;萧红;女性;悲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30-0-02
1934年,萧红与萧军从哈尔滨跋涉至青岛,同年9月写下《麦场》,后被胡风更名为《生死场》。这部小说是萧红的代表作之一,同时也是她一生经历的缩影。由于创作处于特殊的年代,这部作品也被植入了特殊的民族主义的内涵。但这本书除了抗日宣传文学的成分,还有另一大视角值得解读——特殊时期的女性悲剧。
《生死场》中最宏观的框架,无非就是“生”与“死”的纠缠。不难看出整个作品中由“死不如生”——到“生不如死”的递进。故事的开头描写并无意义的乡下日子,农人们机械地为了生活而生活,进行日复一日的劳作和永无止境的聒噪,“死人死了,活人算计着怎样活下去”。而故事的后半段情节忽地转弯,由家长里短到社稷大义,不同的家庭之中表现出了不同样式的悲剧。二里半与麻面婆、赵三与王婆、金枝与成业,在战争里全然有着不同却相似的结局。但最不容忽视的一点是,无论是家事还是国情,女性总是成为悲剧的主人公和承担者。她们的身上总变化着生与死的故事,从身体、感情再到精神,无不以现代人无法想象的形式,经受着各种各样的折磨。
一、身体的痛苦,感官的覆灭
《生死场》中的女性悲剧,最先也最直观地体现在身体的痛苦上,这也是萧红极力想表达的一处。小说第六章的大半部分都在刻画一位产妇生产的痛苦。按理说,新的生命的降临,本应是值得喜悦的恩赐,可作为母亲却只体会到了灼热的痛楚。生育竟成了刑罚,产儿竟成了罪的本源,女性只是单纯重复着自己的工作和职责:
“她又不能再坐住,她受着折磨,产婆给换下她着水的上衣。门响了她又慌张了,要有神经病似的。一点声音不许她哼叫,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她仇视着一切,窗台要被她踢翻。她愿意把自己的腿弄断,宛如进了蒸笼,全身将被热力所撕碎一般呀!”
更特别的是,萧红还将人的生产和动物的繁殖放在了同处比较:
“房后草堆上,狗在那里生产。大狗四肢在颤动,全身抖擞着。经过一个长时间,小狗生出来。暖和的季节,全村忙着生产。”
“大猪带着成群的小猪喳喳的跑过,也有的母猪肚子那样大,走路时快要接触着地面,它多数的乳房有什么在充实起来。”
在萧红的笔下,人类的生产似乎就等价于最原始的生育,只是出于种族延续的责任,丝毫没有生而为人的温柔表现。而女性在这一过程中所经受的痛苦,几乎可以等同于刑罚。更令人感到凄凉的是,《生死场》中这些生育的女性只能麻木地接受这一切,沦丧爱意的同时,甘受着身体上的痛楚,沉沦在自我的安慰里,身体力行着女性的悲剧。
二、感情的坟墓,心灵的禁锢
身体的悲剧,还只是个开始。女性更深层的悲剧,是感情上的禁锢,是完全丧失自己细腻情感的深渊。作者对于金枝这一角色结婚前后的遭遇的描写,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情感一点一滴流失的过程。从恋爱中的少女,到人们口中流言蜚语的主角,再到婚后成为麻木的母亲,金枝几乎深陷感情的囹圄无法抽身,最后甚至摧毁了自己。
萧红描绘的金枝在恋爱中的状态,是小说为数不多的令人轻松又感到温柔的片段,不似其他的生生死死,沉重而压抑。
“姑娘假装着回家,绕过人家的篱墙,躲避一切菜田上的眼睛,朝向河湾去了。筐子挂在腕上,摇摇搭搭。口笛不住地在远方催逼她,仿佛她是一块被引的铁跟住了磁石。”
但是萧红紧接着就转变了文风,从棉长的温柔急转直下变成了暴烈粗犷而又令人惧怖的片段。
“五分钟过后,姑娘仍和小鸡一般,被野兽压在那里。男人着了疯了!他的大手故意一般地捉紧另一块肉体,想要吞食那块肉体,想要破坏那块热的肉。尽量的充涨了血管,仿佛他是在一条白的死尸上面跳动,女人赤白的圆形的腿子,不能盘结住他。于是一切音响从两个贪婪着的怪物身上创造出来。”
这些成業粗暴的动作,金枝只能忍受。似乎她只是成业的工具一般了,在甜蜜的谎言中溺死。无疑,金枝是深爱着成业的,从见面前内心的悸动中就不难看出来这一点。然而成业只是步了叔叔的前路,不想付出责任也不想付出深情。他所有的只是一句简单的要迎娶金枝的承诺,说得又大又空洞。
这就不难料想结婚后的成业将如何对待金枝。果然,婚后的金枝并没有过上自己意料中的幸福的生活。成业只是自己劳作,把金枝禁锢在家里,和漫无边际的家务琐事捆绑在一起。甚至在两人有了孩子之后,成业也没有改变他对金枝的态度。白天是整日的劳作和辛苦,晚上回家还要经受曾经深爱的人的打骂。当她明白过来,自己曾经纯洁爱情的憧憬已化为梦幻泡影时,她也愠怒着说出一句:“你像个什么?回来吵打,我不是你的冤家,你会卖掉,看你卖吧!”
她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她也明白这个的男人早已蜕变成冷漠炎凉的废物。但她千想万想都没有想到成业会摔死自己的骨肉,也葬送她全部的依赖。至此,她已彻底失去少女时温柔的情愫,这种感情上的死亡远比身体上的痛苦更刻骨铭心。
三、精神的恐惧,灵魂的折磨
《生死场》不仅演绎着身体层面与感情层面的悲剧,更深层的,也表现着精神的折磨。这种苦楚,首先来自最原始的家庭,来自自己的母亲。作为人,母亲自然爱着自己的孩子。可作为农人,在萧红的笔下,金枝的母亲却觉得金枝没有田里的庄稼来得重要:“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
一棵庄稼重于一个骨肉,这是《生死场》世界里悲惨的价值观,是不该被遗传的乡土基因,更是无法被人接受的轻视。
可是在金枝的悲剧的一生里,不仅是家人的不重视,爱人的折磨也给她带来了不小的痛苦。后来当她离开成业,告别了曾经天真的自我,回到了妈妈身边,动荡的社会和纷杂的战火却又丝毫不施舍喘息的机会。与母亲短暂重逢几天后,金枝便踏上了前往城市的路途。然而到了城市里,她却依然找不到出路和尊严。为了生计,她献出了自己的精神、剖除了自己的灵魂。终于,她实在无法承受这种精神上的折磨。她想到了逃避,去做尼姑。可是尼姑庵败坏了,她这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至此,这位萧红着墨最多的角色彻底陷入了生命的绝境,连同她的精神一起被扔到了不知名的地方。
可以说,在萧红的笔下,金枝的一生就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悲剧,是那个时代里一步步走向无助、绝望的女性的典型代表。悲剧就这样在萧红的笔端一个个诞生,一个个被摧毁的人格牵动了每一位读者的心。尤其是精神意志的摧毁,其悲剧感远甚于身体的摧残与感情的覆灭。
当我们回过头来思考萧红为何可以如此深刻地书写女性的悲剧,其中的原因显然与其颠沛流离的人生紧密相关。然而相比于其他同时代的刻画女性命运的作品,如曹禺的《雷雨》、冰心的《两个家庭》,或许因为亲身经历的共鸣感,萧红对女性的书写没有停留在纯粹的家长里短,而是在生与死的层次上,由浅入深地展示了女性在特殊时代的种种悲惨。这些悲剧写在笔下,印在书上,悲痛在人们心中,并从中得到启发。鲁迅之言“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是对她和她笔下角色的最到位的评述。为了生存,接受悲剧者不在少数。然而只有真正有脊梁的女性,才能站得笔挺,才能走出悲剧的囹圄,创造新的生活。
参考文献:
[1]萧红:《生死场:萧红小说精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
[2]陈千里:《<生死场>:女性对“家庭”的恐惧与颠覆》,《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一本能够让你对人生有另一种认知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