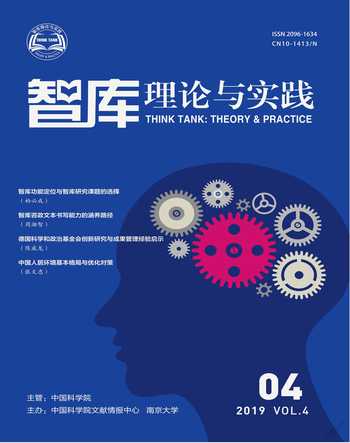学者的智库作用与角色
摘要:[目的/意义]现代智库定位于“公共政策研究分析与参与”,在国家立法和政策制定中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方法/过程]本文从高校学者被时代赋予智库使命出发,结合近几年来参与国家立法和政策制定的实践与体会,以国家公共图书馆立法为例,阐述学者的智库作用,分析立法服务中的学者角色问题,为高校学者参与智库与社会服务提供参考借鉴。[结果/结论]学者要发挥学理保障作用,以客观公正为前提,善于理性思考和理智地分析存在的问题,发挥第三方的作用,承担批评者的角色。
关键词:智库 高校学者 立法 公共图书馆法
分类号:D920.1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19.04.03
关于智库的术语研究很多,有“思想库”“智慧库”“智囊团”“脑库”等称谓。但在《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中,“think tank”指“有组织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机构、公司或团体,通常接受政府或商业客户的委托。政府客户的委托案,大多是有关社会方针计划和国防的议题;商业客户的委托案,主要是为新科技和新产品的开发及测试。思想库的经费来源包括资助、合约、私人捐赠、研究报告出售等”[1]。而“brain trust”(智囊团)特指F.D.罗斯福在1932首次竞选总统时的顾问团[1]。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将智库界定为“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專业研究机构”[2],实际上已将智库狭义化了。由于现代智库已定位于“公共政策研究分析与参与”(public-policy research analysis and engagement),在学术和决策者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发挥桥梁作用[3]。高校学者特别是社会科学学者被时代赋予了智库使命,一方面,政府决策部门和各类智库机构应当开发高校丰富的智库资源,激发学者参与智库工作的积极性,充分发挥高校学者的作用;另一方面,高校学者除做好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工作外,还应当胸怀天下,服务社会,主动承接社会重大项目,在公共政策等领域承担智库角色,为经济与社会发展乃至人类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近几年来,本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南开精神,笔者参与了国家公共文化立法、国家公共文化示范区建设、全国公共图书馆评估等重要工作,发挥了立法服务与政策支撑功能,实现了学者的社会服务价值。这里,仅以国家公共图书馆立法为例,阐述学者的智库作用,分析立法服务中的学者角色问题,为高校学者参与智库与社会服务提供参考借鉴。
1 文化部“公共图书馆法”起草修订与法律解读工作
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图书馆界不断呼吁图书馆立法,但立法工作的真正启动始于2001年4月文化部在天津召开的《图书馆法》专家座谈会。由于图书馆界关于立法的分歧较大,导致2004年立法陷入停顿状态。随后,由于《图书馆法》被列入全国人大重点立法项目,立法工作得以继续,2008年11月文化部召开的《公共图书馆法》立法工作会议,将原来的制定《图书馆法》的目标改为制定《公共图书馆法》。
作为文化部“公共图书馆法”起草修订组成员,笔者在2014—2015年参加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如2014年4月4日召开的“公共图书馆法专题研讨会”,2014年6月10日召开的“公共图书馆法工作会”,2014年12月4日召开的“公共图书馆法立法工作研讨会”,2015年2月6日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召开的“公共图书馆法”修订会等。
笔者作为专家学者参与《公共图书馆法》起草修订工作,除参与政府部门如文化部公共文化司主持的文本起草修订以及多次参与学术界和业界组织的公共图书馆法律问题研讨,还参加国务院法制办和全国人大法工委等立法部门主持的公共图书馆法专家座谈会,如2016年3月1日参加国务院法制办教科文卫法制司召开的《公共图书馆法》专家论证会等。这是一项光荣的使命,代表了广大图书馆学理论工作者发声。这一工作持续时间长,需要时间的投入,需要科学的理论研究,更需要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和科学的立法精神。
按照我国“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4],为配合《公共图书馆法》的出台,文化部公共文化司迅速组织关于《公共图书馆法》“解读”与“问答”工作,成立了由文化部公共文化司领导的编写组,按照分工,“解读”一书对于《公共图书馆法》第一章总则部分的解读由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负责,笔者和国家图书馆的汪东波、申晓娟参与撰写;“问答”一书对于第一章总则部分的问答由笔者负责。两书于2019年1月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在组织编写“解读”与“问答”的同时,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和中国图书馆学会及时开展了《公共图书馆法》的大规模宣讲工作,笔者作为宣讲团成员,赴全国各地进行宣讲。
2 知识背景与信息不对称
立法决策者对立法程序和立法的总体情况比较熟悉,拥有较多的信息。相比之下,决策支撑一方智库对立法的具体要求和相关知识知之甚少,不掌握相关信息。
由于知识背景的不同和信息不对称,图书馆学者在立法中习惯于从专业的角度使用专业术语,由图书馆学专家学者起草的公共图书馆法律文本显示出较强的专业色彩,而政府公务员、立法决策者以及法学专家学者则从法律和社会的角度提出对《公共图书馆法》的文本要求。西方法学理论的奠基人孟德斯鸠(C.L.Montesquieu)在《The Spirit of the Laws》一书中论制定法律时应注意的问题时强调:法律条文的文风应当简洁;法律条文的文风应当平实,直截了当比拐弯抹角更好理解;法律用语必须让所有人都理论为同一概念,这是最基本的要求;法律条文在明确事物概念后,就不应再使用模糊不清的词语;法律不应深奥难懂,而应通俗易懂;倘若没有充足理由,就不要随意修改法律[5]。美国安德瑞·马默(Andrei Marmor)的《Philosophy of Law》强调“法律是用自然语言来表达的”[6]。按照这一原理,早年图书馆学者起草的法律文本不符合法律文本要求,后来,笔者在《公共图书馆法》文本修订中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例如,关于图书馆资源建设中的出版物缴送制度,在理论界中有称“缴送制度”,也有称“呈缴制度”,说法不一。《公共图书馆法》的“送审稿(2012)”和“征求意见稿(2015)”都使用的专业术语“呈缴”。《公共图书馆法》“草案(2017)”第二十二条“中国境内出版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国家图书馆送交正式出版物”,这里使用了“送交”一词,到2017年正式颁布时将“送交”改为“交存”,而且还将交存的对象从国家图书馆扩大到所在地省级公共图书馆,这一用语的改变更适合法律文本的社会理解。
3 立场上的差异
立法决策者、政府公务员和法学家们基于立法的整体环境和整个法律体系,更多地站在公民和社会立场上来考虑公共图书馆立法的问题。而图书馆学者在立法中基于图书馆发展的认知,特别是我国图书馆立法与发达国家相比落后的现实,更加急迫地希望早日立法,并不理解立法决策者所讲的法律资源有限的问题,在讨论具体法律条文时,更多地站在图书馆立场上考虑问题,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
例如,在立法原则上,2014年以前,公共图书馆立法主要考虑的是行业利益保障,图书馆专家学者基于图书馆的发展现状,呼吁一切从图书馆出发,如何保障图书馆的利益、馆员权利,希望通过立法保护图书馆的人财物,实现图书馆的快速增长。2014年以后,经过与立法工作者的交流,立法原则有了重要转变,以保障图书馆行业利益作为立法的出发点转到以保障公民权益作为立法的出发点。这样一来,公共图书馆立法不仅仅有了行业基础,也有了社会基础,有了更大的目标,解决了部门立法难以突破行业局限性的问题。公共图书馆为什么要立法,就是为了实现两大目标,一是促进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公共图书馆法》“征求意见稿(2015)”和“草案(2017)”以及最终法律文本增加了“发挥公共图书馆功能”的内容;二是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提高公民素质,传承人类文明等。只有实现了前者事业发展保障,才能很好地实现后者的公民权益保障,也只有以后者的公民权益保障作为出发点和基本保障,才会有理由有依据从根本上保障事业发展,两者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
又如,在讨论图书馆经费问题时,图书馆学者要求明确图书馆经费的比例,像国外图书馆法那样,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公共图书馆的经费保障问题。这一诉求虽然代表了广大图书馆工作者的心声,但在立法工作者那里难以通过,因为从我国实际出发,除了教育法(教育经费占GDP的4%)等少数法律,一般都不得将经费具体化。最后,只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大对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的投入,将所需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并及时、足额拨付”这一总体性和原则性的规定。针对现实中很多地方挪用公共图书馆经费的现象,图书馆学者要求在法律中纠正这些不正当的行为,在《公共图书馆法》的“送审稿(2012)”和“征求意见稿(2015)”中都使用了公共图书馆经费“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这样较强烈的用词,而后来的“草案”(2017)和最终文本删掉了这一表述,改为从正面提出“及时、足额拨付”的要求。这样做,是因为“法律的语言决不可能等同于报纸的语言、书本的语言和交际的语言。它是一种简洁的语言,从不说过多的废话;它是一种刚硬的语言,只发命令而不作证立;它是一种冷静的语言,从不动用情绪。法的所有这些语言特点,就像其他任何风格形式一样有其存在的道理”[7]。“法律职业人的工作是一种理智的工作,它通过概念的条分缕析来调整混乱模糊的人际关系”[7]。
当学者与立法决策者、政府公务员、法学家在立法立场上有较大的分歧甚至产生冲突时,仅仅换位思考是不够的,后者要能够理解并宽容学者的行业情怀,而前者必须理解法律的本质,必须超越已有的立场,更加冷静地思考,理智地解决问题,促进学理与法理的结合。
4 地位和话语权的不平等
在公共图书馆立法过程中,政府公务员、立法决策者以及法学专家学者处于主导和优势地位,拥有较多的话语权;相比之下,图书馆学者处于从属和弱势地位,没有或缺乏必要的话语权。
全国人大代表有权向全国人民代表大會提出法律案[8]。自1996年以来,许多人大代表为此做出了努力,联名推进图书馆立法。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和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馆长卢云辉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为公共图书馆立法鼓与呼。这些图书馆专家运用自己的话语权,为图书馆事业法制化做出了巨大贡献。2013年10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发布,《公共图书馆法》被列为第一类项目即“条件比较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立法项目”,公共图书馆立法终于进入关键阶段。此时,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作为重要任务,全国人大、国务院法制办和文化部都将文化立法的重点从原来的公共图书馆立法转到了公共文化服务保障立法。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立法工作是2014年4月正式启动的,与公共图书馆法的立法工作由文化部牵头不一样,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立法工作直接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牵头,成立了由中宣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务院法制办等十多个部门参加的立法领导小组,同时成立了起草小组和专家小组。这部立法虽然起步晚,但规格高,立法进程快速。
在全国人大高度重视并抓紧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时,有一种声音渐成优势,认为有了《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就没有必要再为公共图书馆立法了,理由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包括了公共图书馆,公共图书馆法的内容完全可以被《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替代,没有必要重复立法。当听到这种声音时,许多图书馆人感到期盼已久的公共图书馆法又一次要遭受“灭顶”之灾。
《公共图书馆法》会不会难产?笔者和许多图书馆学者一样,十分焦急。在2014年底的一次研讨会上,有政府代表提出来,鉴于目前的情形,公共图书馆法在全国人大立法难度太大了,同时通过公共文化的两部法律几乎不可能,建议考虑改为制定《公共图书馆条例》,与《博物馆条例》相对应,在国务院层面通过较为容易。这是公共图书馆立法生死存亡的时刻,如果不据理力争,图书馆立法就真的希望渺茫了。于是笔者多次向法学界人士、向全国人大立法工作者陈述为什么公共图书馆必须立法,而且在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制定的同时,仍然需要加强图书馆立法的理由。经过我们一批图书馆学专家学者的努力,最终获得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建立在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十易其稿,于2016年12月2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高票通过,整个立法工作仅用时两年多,“在整个立法中算是比较快的,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文化领域立法的范例”[4]。
遗憾的是,在一些地方立法过程中,立法工作和政府决策者常常把专家学者放在一个非常不重要的地位,认为专家机制只不过是开会时请专家代表发个言,或者请请专家学者摆个姿态和样子,并不真正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也不是出于对于专家学者的尊重和对于知识的崇拜。
5 学者的学理保障作用与科学家的角色
学者的责任是要坚持立法的学理性。“要证明一部法律合理,就要讲得有道理”,为此,孟德斯鸠举例说,“罗马有一部法律规定,盲人不得进行辩论,因为他看不见法官的服饰,其实,站得住脚的理由有很多,却有意提出这么一个不成理由的理由。法学家保罗说,腹中婴儿七个月大时已经发育成熟,毕达哥拉斯的数率理论似乎可以证明这一点,这很奇怪,怎么要靠毕达哥拉斯的数率理论断案呢?”[5]。这说明,任何一部法律的成立,首先要建立在学理成立的基础上。而学理成立,必须要依靠专家学者进行科学的研究,而不能靠立法者的认知、简单推理或个人想象。
这里,举几个例子,说明在公共图书馆立法过程中学理的重要性。
立法必须考虑权利问题,图书馆人捍卫谁的权利,这是十分重要的。早期呼吁图书馆立法的学者主要考虑的是图书馆员的权利,而没有考虑公民权利。通过与法学工作者交流,我国立法必须从公民权利保障出发,这与多年来图书馆界的读者第一原则和为公民服务思想相统一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中论述了“公民权”(citizenship),他在1763年2月7日的讲座中将个人权利分为3个层次:作为个人的权利;作为家庭成员的权利;作为社会成员的权利[9]。在1766年的讲座中,他谈到“法律的目的在于防止损害。一个人可以在几个方面受到损害:首先,作为一个人;其次,作为家庭成员;再次,作为国家成员”[9]。他还讨论了政府的3种权力:“立法权,即为着公共利益而制定法律的权力;司法权,即使各个人不得不遵从这些法律并处罚那些不遵从的人的权力;行政权,或像有些人所称为的那种中枢权力,包括宣战权力和媾和权力”[9]。公共图书馆立法,不仅仅要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也包括公民的受教育权利和信息权利。
立法不能回避公共图书馆的主体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公共图书馆宣言》和《公共图书馆服务指南》两份文件中对于这一问题的表述并不一致,前者只是强调“建立公共图书馆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责任”[10],后者则将公共图书馆确定为由社区,如地方、地区或国家政府,或者一些其他社区组织支持和资助的机构。“送审稿(2012)”将公共图书馆的设立主体确定为政府,既与当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强调政府责任有关,也与《公共图书馆宣言》的导向有关。
之后,民办图书馆成为公共图书馆立法理论研究的热点。一是因为国家陆续出台了有关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事业、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等系列政策;二是因为民办图书馆在我国处于刚刚兴起之际,总体规模较少,发展很不平衡,亟待政策支持。
2014年在笔者参加的一系列立法工作研讨中,文化主管部门领导反复强调立法过程中要贯彻中央文件精神,充分考虑民办和外资进入公共文化领域的现实。讨论中基本形成支持民辦图书馆入法和反对民办图书馆入法两派意见。
图书馆学界对这一问题展开理论研究。《国家图书馆学刊》2015年7月第3期围绕民办图书馆应不应当纳入公共图书馆立法范畴组织了专题讨论,主要有3种意见,第1种意见支持民办图书馆入法,理由是要与国际接轨、与国家政策相吻合、与地方法规相匹配、合理继承历史传统以及解决现实发展问题[11];第2种意见反对民办图书馆入法,认为民办图书馆并不属于《公共图书馆法》的调整范围[12];笔者则提出了第3种折衷的意见,既不能简单地将民办图书馆算作公共图书馆,也不能将民办图书馆排除在公共图书馆体系之外,而是有条件地将民办图书馆纳入图书馆公共服务体系[13]。
《公共图书馆法》“征求意见稿(2015)”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既不直接使用“民办图书馆”的概念,又贯彻了支持社会力量依法设立公共图书馆的精神,在第二条公共图书馆界定中除了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还包括“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设立的公共图书馆”,且在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设立公共图书馆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保障公共图书馆正常运行经费”,第六条规定“国家鼓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设立公共图书馆”。这一立法思想与笔者针对民办图书馆是否入法的意见基本一致,是一种折衷处理、回避矛盾、比较稳妥的方法。
后来的文本中继续体现国家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与服务的制度设计,一方面,突出强调政府责任,对“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提出明确要求;另一方面,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公共图书馆,照顾到了民办图书馆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与服务的积极性。“草案(2017)在第五条第二款”做了这样的修改“公民、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设立的公共图书馆由其提供所需经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政策扶持”。而最终法律文本对于社会力量的表述不再突出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回到“征求意见稿(2015)”的表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分两条规定,第四条第二款“国家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筹资金设立公共图书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政策扶持”;第四十五条“国家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措施,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设立的公共图书馆提供服务给予扶持”。通过解决社会力量参与和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很好地回答了民办图书馆是否可以入法的根本问题。
公共图书馆基本概念是立法过程中遇到的重要学理问题,公共图书馆法起草的各个文本每一版涉及的概念界定都会引发争论。
《公共图书馆法》的“送审稿(2012)”关于公共图书馆定义的条款是“第二条第一款:本法所称公共图书馆是指由政府设立,开展文献信息资源的收集、整理、保存、保护,面向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信息与知识服务,开展社会教育活动的公益性机构”。“征求意见稿(2015)”将这一条修改为“第二条:本法所称的公共图书馆,是指以提供阅读服务为主要目的,收集、整理、保存、研究和传播文献信息,向公众开放,并依法登记的非营利组织,包括由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和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设立的公共图书馆”。
对这一定义,反映最强烈的是公共图书馆的性质问题,一些图书馆专家学者反对使用“非营利机构”作为公共图书馆的性质,这违背了公共图书馆的原有性质定位。如果定性为“非营利机构”,那等于允许公共图书馆收费或不以营利为目的开展经营活动。在图书馆学教科书中,一再强调图书馆是文化、科学、教育机构,从来没有人也没有文献将图书馆纳入非营利概念范畴。在笔者参与的由公共文化司起草的文本中,也没有这样的表述,为何公布的“征求意见稿(2015)”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呢?后来才知道,“征求意见稿(2015)是对国家图书馆、中国政法大学、国家行政学院3个课题组提供的文本进行集成的结果,这一条是采纳了非图书馆学专家的意见。
国务院法制办2016年3月1日召开的那次专家论证会,除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和中国图书馆学会、国家图书馆的领导外,还邀请了图书馆学、行政管理和法学专家。论证会的首要议题就是“公共图书馆应当定位为非营利组织还是公益性机构?为什么?应否在公共图书馆的定义中加以描述?”。笔者从学理上发表了观点。经过与立法专家交流,否定了将“非营利”作为公共图书馆性质的做法。
当公共图书馆立法进入到全国人大对草案审议的过程中,笔者参加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2017年9月14日召开的专题座谈会,这次会议专门讨论公共图书馆和文献信息两个概念。经过反复研究,最终法律文本第二条第一款将公共图书馆定义为“本法所称公共图书馆,是指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收集、整理、保存文献信息并提供查询、借阅及相关服务,开展社会教育的公共文化设施”;第二款解释了文献信息“前款规定的文献信息包括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缩微制品、数字资源等”。
由此可见,公共图书馆立法是建立在学理基础上,充分吸收了专家知识和意见,整个过程较好地体现了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的精神。
6 學者的第三方作用与批评者的角色
在立法和公共政策领域,作为政府内部咨询的智库和作为政府外部咨询的智库有一个重要的差别,就是后者更强调独立性。学者要发挥智库功能,必须以客观公正为前提,保持中立态度,发挥第三方的作用,承担批评者的角色。这是智库机制中的一个难点。
2017年6月,公共图书馆立法进入最后的关键阶段,即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决定最终能否通过并颁布。这一阶段要经过四步走:第一步是人大常委会听取汇报。第二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进行常委会讨论前的工作,包括向公众征求意见、向相关委员会征求意见、向人大代表和业界专家征求意见。第三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分组审议。第四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
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于2017年10月11日召开了公共图书馆法草案通过前评估会,笔者作为专家应邀参加会议。这次会议是一个高规格的小型会议,会议只有两个议题。第一个议题是公共图书馆法草案中的主要制度规范的可行性以及草案是否已达到成熟状态。针对这一议题,笔者在会上说,公共图书馆法建立在多年来图书馆界理论研究基础上,草案经过充分的论证和广泛征求意见,既符合法理,又符合学理,已达到了成熟状态;草案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时代性,二是专业性。第二个议题是公共图书馆法的出台时机和实施后可能达到的效果以及出现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和其他专家一致认为,公共图书馆法是图书馆界期望已久的法律,从当前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社会形势来说,法律出台更加迫切,党的十九大召开后立即出台是最佳时机。与会代表也都认为,公共图书馆法的主要制度规范符合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实际,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已经比较成熟,建立尽快审议通过。
这次会议结束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快了立法步伐,十九大会议一结束,公共图书馆立法就进入到最后阶段的第四步,2017年10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法律委员会认为该法律草案已比较成熟,建议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当笔者看到“公共图书馆法草案二审稿充分吸收各方面意见,进一步增强了时代性和专业性,主要制度规范符合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实际,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14]这样的报道时,感到欣慰,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采纳了笔者在2017年10月11日会议上对于公共图书馆法的基本评价,后来笔者还以《<公共图书馆法>的时代性和专业性》[15]为题发表了文章。
2017年11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十次会议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草案二次审议稿)》进行分组审议,建议进一步修改后,提请本次会议通过。2017年11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公共图书馆法颁布成为2017年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世界图书馆事业发展也有着特别的价值与贡献。
笔者作为一名图书馆学者,作为直接参与公共图书馆立法的成员,为公共图书馆法的出台感到兴奋,多年来包括笔者在内的几代图书馆人的梦想得以实现,笔者在许许多多图书馆学前辈为立法孜孜以求、百折不挠的精神激励下,参与到立法的研究和推动之中,做了一些工作,为公共图书馆法做出了一名图书馆学专家应有的贡献。笔者和其他专家提出的策略建议被政府官员和立法工作者采纳,这说明了我国的立法工作充分发挥了专家智库的作用,越来越具有科学性。
学者善于理性思考和理智地分析存在的问题。虽然公共图书馆法在政府和业界的共同努力下得以颁布,但并不代表它已经尽善尽美了。一部法律的出台必然留下许多遗憾,公共图书馆法也不例外,有许多问题在短时间内很难以解决,而且,既不要轻视法律的效用,也不能对一部法律有过高地期望和超出实际的估计,法律不是万能的,一部公共图书馆法,也不可能解决现实中公共图书馆存在的所有问题。
几个遗留的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与推动。如关于图书馆员职业资格制度,200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首次将“我国图书馆员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的建立与实施”作为重点课题。2004年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国家文化部正式发布试行3个与图书馆行业有关的“国家职业标准”(图书资料馆员、古籍馆员和文献修复师)。
我们应当看到,虽然专家学者已经很好地发挥着咨询和决策参考的作用,向第三方的机制迈进。但是,专家学者的批评者的角色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由于通常情况下,决策者并不愿意听到批评的声音,往往不请那些喜欢批评的人参加座谈会,这样的结局必然是让专家学者为决策者唱赞歌、当解说员,不能从批评者那里获得宝贵的借鉴,地方上这种现象的普遍更影响和遏制了决策过程中的专家批评机制实施。
实际上,现实中的许多政府公务员和决策者并没有很好地理解“批评”二字的含义,学者的指评并不是简单否定、责备、呵斥甚至谩骂,批评是一种客观的分析态度,是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批评是一种有益的科学行为。在专家智库作用发挥过程中,不能没有批评。当然,这种批评还依赖于有利于批评的决策环境,也依赖于专家学者的批评水平以及对批评艺术的把握。
参考文献:
[1] 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 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修订版)[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1: 1545.
[2]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 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 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EB/OL]. [2019-06-04]. https://www.docin.com/p-1598719323.html.
[3] MCGANN J G. 2017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EB/OL]. [2019-06-04]. https://doc.mbalib.com/view/77bb72102b8d12ac1751c40a3c9b27f3.html.
[4] 柳斌杰, 雏树刚, 袁曙宏.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解读[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7: 3-4, 7.
[5] (法)查理·路易·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M]. 钟书峰, 译.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 297-300.
[6] (美)安德瑞·马默著, 孙海波, 王进译. 法哲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154.
[7] (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 法律智慧警句集[M]. 舒国滢, 译.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 12, 132.
[8] 朱力宇, 张曙光. 立法学(第二版)[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6: 156-157.
[9] (英)亚当·斯密. 法理学讲义[M]. 冯玉军, 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160, 381, 388.
[10] IFLA. IFLA/UNESCO public library manifesto 1994[EB/OL]. [2017-11-01]. https://www.ifla.org/publications/iflaunesco-public-library-manifesto-1994.
[11] 王子舟. 民间图书馆应该纳入公共图书馆法的理由[J]. 国家图书馆学刊, 2015(3): 10-13.
[12] 翟建雄. 关于民办图书馆暂不入法的几点思考[J]. 国家图书馆学刊, 2015(3): 13-15.
[13] 柯平. 应将民办图书馆的公共服务纳入“公共图书馆法”范畴[J]. 国家图书馆学刊, 2015(3): 7-9.
[14] 中经文化产业. 与你有关! 公共图书馆法草案有这些新变化[EB/OL]. [2017-11-07]. http://www.37txt.cn/a/21144/460226.html.
[15] 柯平. 《公共图书馆法》的时代性和专业性[J]. 图书馆杂志, 2017(11): 7-11.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Think Tank of Scholars
——Taking Public Library Legislation as an Example
Ke Ping
Business School,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Modern think tank is positioned as "public-policy research analysis and engagement", which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national legislation and policy making. [Method/process] This article embarks from the university scholars, who have entrusted to think-tank mission by the era, combines with the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of national legislation and policy formulation in recent years, takes the national public library legislation as an example, expounds the function of scholars' think tanks, and analyzes the role of scholars in legislative services. It provides reference for college scholars to participate in think tanks and social services. [Result/conclusion] Scholars should play the role of academic support, presuppose objective and fairness, be good at rational thinking and rational analysis of existing problems, play a third-party role, and assume the role of critics.
Keywords: think tank college scholars legislation public library 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