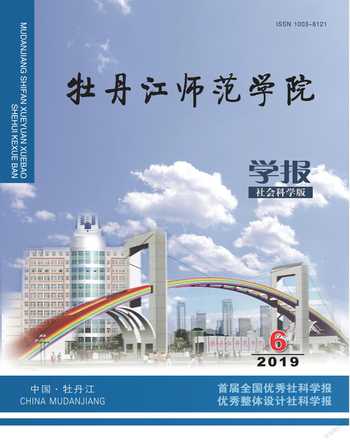失独父母的丧痛与生命意义回归
白福宝 钟年
[摘要]失独给失独父母带来了巨大的丧痛,也使得他们丧失了把繁衍后代作为生命延续和追求生物学意义上的永生的可能。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看,失独还意味着无法承续“香火”和传宗接代,甚至还有“无能”“无德”的文化隐喻,这对失独父母的世界观和生命意义提出了重要挑战。目前追求肉体生命的真正永生还无法实现,但我们不仅可以通过繁衍后代,还可以通过“立德、立功、立言”等多种创造个人成就和社会价值的方式来实现象征意义上的永生。人生有意义不完全依赖于人能否繁衍和生命的长度,当我们充分发展自己的潜能和创造力、投身于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时,便在实现意义的过程中超越了自己。死亡的必然性提醒我们要规划有限的生命时间去追求那些值得做的事情,并让我们存有敬畏之心和过一种有道德规约的生活。
[关键词]失独;失独父母;死亡;永生;生命的意义
[中图分类号]B849 [文献标志码]A
我国在1979年至2013年问实行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大部分城镇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而据卫生部发布的《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显示,我国现有失独家庭已超100万,同时以每年7.6万的速度增长。这些独生子女或死于病患、车祸、凶杀,或死于天灾,还有的死于自杀、过劳等。受年龄、地域、是否(可)再生育和收养等因素的影响,失独父母所遭受的心理打击和面临的现实困难各有不同。因此,结合父母的生命历程,我们区分了“暂时性失独”和“永久性失独”两种情况来理解失独父母的悲痛。如果失独发生在父母都尚有再生育能力之前,失独父母还有再生育的可能,这种情况称为“暂时性失独”;如果在独生子女死亡后,由于生理、经济等各种因素,失独父母客观上不能或不再生育也未收养子女,且离世的独生子女也未留下任何子嗣后代,这种情况即为“永久性失独”,也是本文主要探讨和分析的情况。
丧亲之痛并没有完全相同的体验,它是因人而异的,也并不存在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特定阶段。但是,无论独生子女是哪一种情形的离逝,失独都给失独父母带来了难以弥补的哀痛和遗憾。如果独生子女的死亡是突发的,失独父母的痛苦程度会更进一步加深。甚至,对一些人来说,失独简直就是毁灭性的打击。“白发人送黑发人”违背了自然的先后秩序,失独父母身上所承受的不幸和苦痛不是一个简单的“哀”字所能涵盖。这种哀痛常常造成失独父母内心的空虚和失落,投射在子女身上的期待与盼望也随之破灭,以及由此带来的医疗和养老等现实问题。失独父母被迫需要重新调整目前的生活和对未来的规划。有一位失独母亲在接受访谈时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我感觉天塌下来了,万箭扎心,破碎的心无处安放,失去了精神支柱,孤立无助,害怕晚年凄凉绝望,这几年来无所适从,随时间煎熬度日”。失独甚至让一些失独父母陷人某种与外界隔离的沮丧状态,对他们来说,无论生活有什么意义似乎都已不再重要。简而言之,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生活的重心,一蹶不振,像一团漂浮在空中的雾气,有的甚至发疯或因绝望而自杀身亡。
一、失独父母的丧痛:从“无后”说起
失独父母面临生病送医、生活照料、养老赡养、精神慰藉、丧葬善后等各种现实问题。对于永久性失独父母而言,留给他们的还有“后继无人”的悲痛。道金斯在其《自私的基因》一书中认为,我们以及其他一切动物都是各自的基因所创造的机器,我们与生俱来的任务就是把我们的基因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早些年美国一些学者通过实证调查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死亡恐惧和生育意愿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其原因在于人们把生育后代当作自我延续的手段之一。人如果能在死前留下自己的子孙后代,生命就得到了延续。周欣悦等也以中国人为被试,通过实验研究发现与死亡相关的观念提示可以增加被试的生育意愿,生育子女可以作为缓解死亡焦虑的一种方式。通过生育子女,把自己的基因遗传给下一代,通过无穷无尽的血缘传递,我们获得了生物学意义上的永生。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失独父母失去了把繁衍后代作为延续生命和追求“永生”的途径。对于他们而言,失独的严重性在某种意义上更甚于自己的死亡。
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父母对孩子生命的在乎程度是随着孩子的成长而发生改变的。具体来说,直到子女的生殖潜力到达顶峰之前,父母对子女的投人会一直增加,而在那之后,父母的投入就会开始减少,所以对于父母来说,失去一个到了青春期的孩子要比失去一个婴儿更令他们悲痛。也就是说,比起孩子刚出生或出生几个月内夭折,父母对青春期孩子的离世更为悲痛。一方面是因为父母和已经到了青春期的孩子相处时间更长,彼此间的情感联结较为深刻,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养育他们,对其生命有较多的期待。但另一方面的原因是,青春期的孩子已经具备生育能力,能够将自己的基因遗传给下一代,即将为父母带来繁衍后代上的回报。
受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中国人通常认为子孙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和延续,因而繁衍后代实则是在追求自己生命的不朽。一个人虽然死了,但只要其还有子孙,生命就仍在延续中。父母和子女存在某种意义上的共命关系,很多父母在子女身上投射了自身的价值感与成就感,甚至为了子女可以牺牲自己的欲望和生命。因而,独生子女的早逝虽然不是纯粹的“我”之死,但对于其父母而言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他人或普通亲人之死。尽管他人的死亡也会提醒我们死亡的存在,但我们一般不会因为他人之死而有很深的死亡体验。而失独不仅让失独父母体验到自身的死亡,而且是追求生物学永生意义上的“我”之死。所以,没有子嗣是追求永生的真正破灭,是一种彻底的死亡,这在中国人的观念意识里是根深蒂固的。
在西方,生命的延续基本上只有指个体层面的生命延续,而对中国文化传统而言,生命的延续除了指个体自身生命的延续之外,还带有很重的家庭生命延續的意味,这也是“传宗接代”的本意。血亲关系是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核心基础。一个家庭如果没有子嗣,血脉就得不到传承,就没有人会继续施行对祖先的敬礼,而“香火中断”在中国被视为最大的不幸。传宗接代是为了“香火”不灭,而要承续“香火”,就必须有祭祀祖先的后代,子孙越多说明家族“香火”越旺。
家庭本位的思想成为中国生育文化的一大特点。孟子更是把是否生育子嗣提升到了孝的高度,提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点。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传宗接代成为人生的第一要务和主要使命,这个观念已经内化到心灵深处,一些人甚至把生育上的成就看作是自己人生最大的成功。而“永久性失独”则意味着子嗣传承彻底结束了,这对于生活在“传宗接代”这一传统文化氛围里的失独父母而言,其哀痛和丧失是任何东西都弥补不了的。
一般意义上,传宗接代即是要求子女将父祖传承下来的血脉和家业续接下去,而且只承认儿子在传宗接代中的作用。按照这种文化传统,有儿有女者,只赋予儿子继承权;有女无儿或无子嗣者,则要过继嗣子,以承继家业,延续香火,称为“立后”。如果某人没有儿子,他就会从子嗣较多的兄弟那里过继一个儿子奉养香火,以继续自己这一支血脉的传承。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中国人会历经千辛万苦要生一个儿子。父母除了指望儿子将来为自己养老之外,还指望他传宗接代、继承家业。这种观念同时也造就了“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文化。子孙多,“香火”自然兴旺,同时还可避免因有子女早逝而导致“无后”。
生育子嗣是中国人追求不朽、实现生命永恒的基本途径之一,也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所在,这种生命观甚至被直接表述为“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无儿无女或有女无儿便意味着“无后”或“绝户”,这是人生最大的不幸。中国的一些地方甚至把女性能否生育以及能否生男孩作为衡量她们一生功绩的标准。从这个方面来看,失独父母丧失的不仅有自己生命的延续,还有家族“香火”的传承,甚至还有生命的意义。受这种传统观念影响越大的失独父母,所体验到的痛苦和打击也就越大。
另外,在中国很多农村地区,“无后”不光有家族“香火”断灭的文化象征,还有其他方面的文化隐喻。一个女人如果连续生了几个女儿而没有生儿子,可能会被认为无能——没有能力生儿子;或者无德——前世没有积下生儿子的阴德。同样的,独生子女(唯一也是所有的孩子)早逝了,其父母或家庭也会被认为福薄、家宅风水出问题或是祖上积德不够。这种因果报应下的“指指点点”和“冷言冷语”无疑给失独父母又扣上了一顶沉重的、难以摘掉的“帽子”。有时给失独父母带来更多伤害和痛苦的不是孩子的死亡,而是周围人的态度、评价与反应。
“无后”使得失独父母在生物学意义上的永生遭到了破灭,其生命的意义遭遇了整体性的威胁和挑战。“后”对于个体而言,不仅保证了血脉的不断传递,也具有重要的精神意义。因此,“无后”不仅指没有后代这一生物学事实,还包括由此延伸出的一系列社会学意义上和精神方面的问题。简言之,失独对失独父母的世界观和生命意义提出了重要挑战。
二、失独父母的生命意义回归:永生和死亡的意义
对一些失独父母来说,独生子女的死亡简直就是毁灭性打击。在这种时候,失独父母内心深处对于死亡的恐惧也很容易被引发出来。有些失独父母被悲伤压倒,从现实世界中退出,进而迷失了自己,陷入了悲痛的无底深渊中,可以说这是一种对“虚无”的整体性恐惧。失独之后,失独父母不得不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
(一)重新思考追求“永生”的多样性
如果我们的肉体能够一直活下去,那我们就在生物学意义上获得了真正的永生。但就目前的医疗技术水平来说,我们还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肉体永生,所以每一个想超越死亡的人还应该思考追求“永生”的多样性问题。即使肉体死了,“我”也未必彻底终结。我们还可以通过子孙后代活在世上或者通过自己创造的作品或事业获得某种意义上的永生。虽然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永生,但都是象征意义上的永生。
每个人的存在都是独特而唯一的,一个普遍有效且能够被所有人履行的人生任务是不存在的。每个人应对死亡、追求永生的模式也各不相同。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现实本身也是多元变化的。当我们投身于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时就超越了自我。因而通过繁衍后代并将自己的基因、财产、价值观等传递下去只是其中一种,并不是生命唯一的意义,虽然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种。
我们还可以通过宗教信仰建构的超越死亡的美好蓝图如灵魂不死、死后复活、得道成仙、进入天堂享福或轮回转世,或者相信死后精神上会与某个“永恒的生命”存在联系,或者把自己的生命与其他所有生命、大自然乃至整个宇宙看作一体来实现永生。当然,当自己原先认同的“永生”模式遭到永久性毁灭,或者说我们寻求意义的过程遭遇挫败时,要从一种模式转换到另一种模式并不容易,这中间可能会经历严重的失落。但是,我们仍可以从痛苦中找出意义。总而言之,对意义的追寻和创造是人的存在方式,意义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根本特征和最终依据。我们可以也需要在精神层面和象征意义上实现对死亡的超越。
作为社会性动物,人的“活着”涉及生物性之活和社会性之活,这意味着我们的存在还有社会学方面的意义。个人的独特性也是相对于人类社会这个整体而言才具有重要意义。在我们所属群体中寻找生命力的源泉,也是通过文化达到象征性不朽的方法。《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通过“立德、立功、立言”在死后留下有价值的、能够发挥作用的“成就”而实现人生的意义,进而实现不朽,是一种较为人世的方法。虽然你死后肉体生命没有继续活着,但是你的一部分比如你创造的“作品”还继续“活着”。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是“变得不朽”,而是“值得不朽”。
胡适在《不朽——我的宗教》一文中指出,此“三不朽论”有三层缺点:只限于极少数人、没有消极的制裁以及“功、德、言”的范围太模糊等,并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不朽论。他认为,“小我”虽然是有死的,但是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大小,无论是非,无论善恶,一一都永远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而这个“大我”,即整體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将给有限的生命个体赋予永恒的意义。因而,人类还可以通过交往、学习和传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尤其是对社会和他人的影响力,而使自己获得某种意义上的永生,即将我们的思想和情操通过我们的言行在文化共同体中保存下来,以或隐或显的方式继续存活。这样,“小我”和“大我”就融合在了一起。
所以,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举动将生命置于一个更大的更有意义的视域内。如果我们不能将“小我”放在一个更大的整体中,那么它就变成一个无头无尾的时间片断,没有不朽的意义。一旦我们超越有限的自我,就会发现一个更伟大的“我”,一个无所不在、永恒不变的“我”。因而,走出哀痛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去创造价值和帮助他人。也许我们真正害怕的不是肉体的死亡,而是自己完全消失,没有人再记得、关注我们,人们也常说死者只有在生者最后一次提起他的名字时才真正死去。死亡终结了生命,但它并没有终结一段关系。其实,所有的生命是都相互关联在一起的,共同给出宇宙的面貌。生离和死别可以切掉形体上的联系,但是精神上的联系却不会被断除。反之,我们越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孤立的实体,就会越害怕死亡。
(二)重视生命的意义而非生命的长度
未能看到子女繁衍后代,延续“香火”,继承家业,确实是人生的一大遗憾。但是,如果我们活着的意义只在于繁衍、抚育下一代,只是为了孩子而活着,那么我们自身短暂的生命的意义何在?一代又一代无穷无尽的繁衍,其目的又何在?假如短暂的生命本身没有意义,那么无论繁殖多少代也不会使它变得有意义,而只是在延续一件无意义的事情,“延续”在什么时候结束也就不重要了。只有当生命自身有意义的时候,生命的繁衍才会有意义,因而人生有意义不完全依赖于人能否繁衍和生命的长短。性、爱和婚姻不是只有为了生殖繁衍的目的才具有意义。依靠生殖繁衍带来的“永生”也意味着死亡是必然的,因为生命周期不可避免地把所有人都带向毁灭。
当我们活着是为了维持家业、家族生命以求某种“永生”时,我们就像是活在一个非自身(otherwise than being)的世界之中,我们和自己的生命存在疏离了。当我们把孩子看作自己生命的延伸和延续时,即使孩子还在世,我们也会一直焦虑和担心着他们。没有后代不能也不会使人的存在失去意义,例如我们都会铭记周恩来总理对我们国家的卓越贡献。如果我们把繁衍后代当作人生獨特的、最终的意义,实际上就诋毁了没有后代的人的生命意义。而且,当我们过于强调活着的意义和价值,尤其是生命的生物学意义时,实际上也是在加剧生与死的对立。当然,这并不是要求失独父母要在最终的意义上忘掉失独的悲痛,而是要能从失独的丧痛中走出来,继续寻找生命的意义,如此生命便有了新的意义。
既然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终有一死,我们也就应该反思自己是否真正活过,是否充分发展自己的潜能和创造力,有无虚度人生。我们越不曾真正活过,我们对于生命终结和虚无的恐惧也就越强烈。生活的经验不仅有“生”,而且还有“活”。人如果没有可以填充精神的东西,就不能充分地活。生命的短暂性反而对我们提出了更大的责任感。通过活出丰盛的生命来达成永生的意义,这是就连死亡也抹杀不了的。当我们觉得自己在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对于死亡的恐惧可能会淡化,对于永生的渴求也就不会那么强烈。有时候我们害怕的不是无法“永生”的问题,而是生命已经丧失了意义和希望。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不再通过延续后代来让自己“得到幸福”,而是通过实现意义让自身“值得幸福”。生命的意义不是在时间长度上通过繁衍后代来超越自己,而是在生命高度上通过实现意义超越了自己。
人不仅是自然的、肉体的存在,社会和文化的存在,而且也是精神的存在。我们越是有意识地建立身心的连接以及自身和世界的连接,就越有利于我们作为一个整体获得更高水平的平衡和稳态。这种连接带来的体验可以发生于男人和女人之间、人和宇宙之间、人和艺术创作之间,抑或是人与上帝之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由担心子女的生死、前途,转而对整个生命充满敬畏之心。有多种途径可以带我们超越自我的界限而达到这种和谐同一的状态。一旦我们转化了自我的欲望、烦恼与局限,就能发现一个更大的“我”,这个真正的“大我”融于整个宇宙之中。
(三)反思死亡存在的意义
所有的生命都有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每个人都会衰老死去。当我们越想在世界追求“永生”的价值,我们对死亡、对虚无的恐惧就会越大。死亡真的会毁灭所有的意义吗?如果我们的生命在时间上不是有限的而是无限的,即假如我们的肉体生命是永生的,那么究竟会怎样?我们会不会得过且过,无限期地拖延值得或想要做的事情?如果真的可以活到永远,我们就总是可以重新开始,好像一切都来得及。但即使我们可以永远活着,也不意味着我们会一直充满活力。如果我们丧失活力,衰老地活着,那么永生就远非一件美好的事,反而可能是一件可怕的事,让生命变得乏味、糟糕甚至痛苦。在这种情况下,死亡反而能够帮助我们结束煎熬。永生并不意味青春永驻,还可能被年老体弱困住,比如不得不更长久地忍耐失能和失智。也就是说,健康、快乐地活着要比永生更有意义。
死亡是必然的,我们无法摆脱它,而且死亡具有不确定性,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特别小心谨慎地对待生命,不放任自己去死,以及思考怎样在有限的时间里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谢利·卡根进一步说,不是因为我们终有一死,也不是因为从绝对量上来说我们只能存活很短的一段时间,我们才要小心谨慎;而是相对于有那么多值得追求的目标,以及达成这些目标又那么复杂困难而言,我们的时间太有限了。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把值得做或想做的事情都做一遍,所以,死亡的意义就在于它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人生任务:决定哪些事情是值得追求的并努力达成它们。而所谓“赋予生命意义”也可以解读为将我们生命剩余的有限时间用于此或用于彼的规划。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程度上获得了面对死亡的自由,这种规划和选择也体现了人生的意义所在。如果我们一味地排斥死亡、恐惧死亡,反而无法全然地活着。死亡的存在提醒了我们要赋予人生以意义,防止我们过一种无意义的生活。因此,失独父母需要重构认知,重写人生故事,学会和过去告别,合理规划未来,重新寻找生命的价值所在。
对于一些文化传统来说,死亡并不是最终的消灭,死亡恐惧也不是最深的恐惧,死亡是一个过渡,人们从这里“借道”走向真正期待或害怕的地方:接受“法官”的审判。死亡让我们思考安身立命之道和灵魂是否不朽的问题,并将其与人活着的善恶行为结合起来。如果你一辈子没有考虑过别人,你会被判罚永远“吃苦”;相反,如果你一直听从律法和善心的指引,你便会永生或永远幸福。也就是说,死亡的存在或者说是对死后的恐惧让人们在俗世生活里能够遵从律法、自我约束,维护共同的文化世界观。而文化世界观为人提供了秩序、意义和价值体系,让人感觉自己是一个比自身更强大、更持久的集团或文化整体的一部分,给人带来不朽的使命感。当我们感觉自己属于一个宏大的“整体”,我们更愿意通力合作、分享资源、同心同力来一起解决现实的各种问题。也许,这就是死亡的存在所带来的意义:引导人们生出包含但不限于对来世的敬畏之心,以及过一种有道德规约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