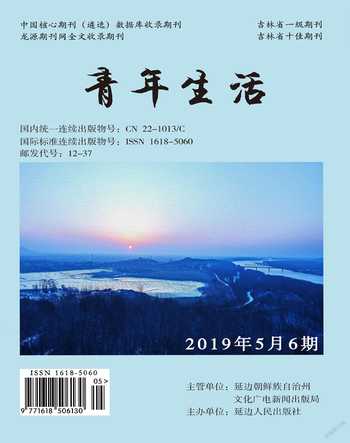从“小大之辩”看庄子“逍遥游”精神境界
刘倩
摘 要:《庄子》一书中所描述的逍遥游境界令人神往。然而,究竟什么是逍遥游?到底该如何理解逍遥游的境界?本文力图通过对《逍遥游》文本的梳理,从“小大之辩”这一角度入手,来把握逍遥游之奥义,并最终得出结论,“逍遥游”实际上是一种精神境界。
关键词:庄子;《逍遥游》;“小大之辩”;精神境界
一、鹏鸟与学鸠的小大之辩
在“逍遥游”的第一、二段,庄子极力渲染鲲鹏之大,蜩与学鸠之小。首先,庄子用诗性的语言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气势磅礴,浩渺无涯的迷人画卷:“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在这里,无穷的变化与浩瀚的境域相结合,共同为大鹏的出场营造出一个华丽的背景,以烘托鲲鹏之大。此外,还有直接的正面刻画:“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其翼若垂天之云”。鹏鸟的后背大概有几千里的长度,而它雄健的双翅则像天边的云彩一样无限舒展开来。这里写了大鹏鸟的体型之庞大。“怒而飞”“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怒”即攒足了力气,奋起而飞。“水击”即击水“抟”,指环绕着飞向上空“扶摇”指旋风。鹏鸟振翅拍水,水浪远达三千里,便乘着旋风环绕飞上九万里的高空。这体现了鹏鸟运动之力度之大,幅度之广阔。
学鸠之“小”也是庄子着力刻画的:“我决起而飞,枪榆枋,时则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决”,迅速的样子;“抢”,突过;“控”,落下。学鸠的运动状态是一下子就起飞,碰到榆树、枋树树枝的高度便停止飞翔。有时到达不了,就仅仅停留在地面上。很明显,学鸠飞行所耗时间短,范围也十分狭小。“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相对于大鹏鸟的九万里高飞,学鸠鸟是持一种嘲笑和不屑的态度的。对于学鸠鸟的无知,庄子是加以讽刺的:“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到近郊去,带三餐,就足够了。但是如果要到百里之地去,就得花费一整天的时间准备干粮。若作千里之行的打算,那就得备好三个月的干粮了。在这里,庄子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要想到达高远的境界,就得具有相当厚实的积累,大境界有大积累。鹏鸟的“九万里而南为”正是其大境界的体现。而境界狭小的蜩与学鸠鸟又怎么会知道?这正如庄子所写“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那么,大鹏鸟就是庄子心目中的理想形象吗?鉴于庄子对于大鹏鸟如此耗费心力的渲染与刻画,很多解庄者便认为大鹏即是庄子所赞頌高歌的对象,是他心中“逍遥游”理想的完美体现。然而这个理解是有所偏差的。因为,显然大鹏鸟是不完美的,在这里,庄子列举了水与舟,杯水与草芥,杯与水这三个例子来类比说明了大鹏鸟的局限性。“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对于细微的小草来说,一杯水就能够让它漂浮起来。对于杯子而言,要让它浮起来,则需要更多的水。至于大船,那就更不用说了。依次类推到大鹏,“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只有积攒了九万里的高风,才能承载起大鹏巨大的翅膀,使之遨翔天际。在这里,大鹏鸟和舟、草芥、杯子一样,都需要依靠外在条件才能达致某种的境界,它们都是有所待的,是不逍遥的。所以大鹏鸟并不是庄子“逍遥游”理想的寄托。鹏鸟之“大”实际上是在为“心之游”所达至的大境界作铺垫。
二、人间的小大之辩
在学鸠与鹏鸟之间有“小大之辩”,同样,在人世间也存在着“小大之辩”。“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徵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这里的“其自视也亦若此矣”中“若此”指代上文中的斥晏鸟。在庄子看来,那些才智可胜任一官之职,或行为能聚拢一乡之众,或德行合乎一国之君的人,甚至是能够得到一国人民信赖的人,也往往如学鸠、斥晏鸟一样,是“小知”。他们整日被各种世俗名利所纠缠,困扰,而宋荣子和列子则不是这样:“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宋荣子已经不受人世间社会评价和舆论的影响,能够正确地区分内外、荣辱,对人世间荣华富贵也都不屑于追求。而列子则能够“御风而行”,对人世间的功名利禄也不汲汲追求。然而,庄子却说他们是“犹有所待者也”。在庄子心中,超越了世俗的宋荣子和列子仍然没有到达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三、无所待的精神境界
接下来的“若夫”一句则道出了庄子心中的理想境界和理想人格。“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天地之正”郭象注曰:“天地者,方物之总名也”,“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顺万物之性也”天地,即是自然万物。“天地之正”指的是自然之性,万物本然的状态。“而御六气之辩”,“六气”,指的是构成宇宙的六种基本成分。“辩”,即变,变化。“御六气之辩”意思是游于变化之中。而“无穷”,就是指辽阔自由的境界。这一部分的意思是:能够顺着自然万物的本性,随着它一并发展,与万物相和谐,就能够达致于自由自在的境界。从“若夫”到“者”,是一个“者”字结构,指代能够按上述说法那样做的人。“彼且恶乎待哉”中的“彼”字衔接上一句,指那一类人,句意为:他们还有什么依待的吗?这一句话说明了到达无待境界的途径,即“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因此,达到无待的途径是顺自然万物之性,与外部世界融为一体。然而,外部环境与自我本身是互相冲突的一对。要化解物我之间的矛盾,唯有消解自我,即无己,才能够真正与自然万物相和谐,达到无待境界,“在内心中消融物我之间的对立,让思绪在广阔无垠的至大之域自由漫游”。所以,达到无待境界的途径是无己。
“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中“故曰”二字承接上文的无待境界。“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指的就是能够达到无待境界的人格形象。“无名”指有名而自不以为有名;“无功”指有功而不自以为有功;“无己”指有己而不自以为有己,这里的不自以为有己,指的是忘己。正是由于忘却了自己,消解了对外部环境的成见,才能秉持一种“不自有”的心态来对待“功”和“名”,做到“无功”和“无名”。在这里,“至人、神人、圣人应是有区别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至人高于神人,神人高于圣人。”至人无己”是“神人无功”与“圣人无名”的关键,三者共同指向无所待的大自由、大逍遥境界。所以,我们可以说,逍遥游的实质“即思想在心灵的无穷环宇中遨游飞翔”,是一种无所待的精神境界。
参考文献:
[1]庄周,《庄子》,方勇译注,中华书局2010:2.
[2]夏当英《从“逍遥游”到“知北游”,《安徽大学学报》,1997(1).
[3]林容杰.“小大之辩”与“有无之辩”[J].厦门大学学报,2010(6):63.
[4]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M].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