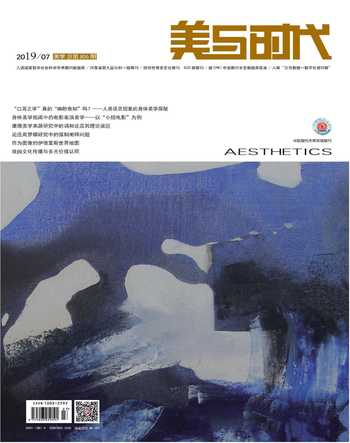论庄周梦蝶研究中的强制阐释问题
摘 要:庄周梦蝶的故事是《庄子·齐物论》的压篇之作,历来被视为是《庄子·齐物论》,乃至整部《庄子》的总结,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和艺术魅力。自张江教授提出“强制阐释”的观点后,学术界开始反思和审视当代中国的文学研究。在借鉴西方文论成果研究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时候,一部分学者往往忽视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错位现象,盲目照搬西方文学理论,落入“强制阐释”的误区。借探究庄周梦蝶研究中的强制阐释问题,从新的切入点认识庄周梦蝶,或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正确阐释路径。
关键词:庄周梦蝶;强制阐释;阐释路径
《庄子·齐物论》的篇末记载了一个短小却美丽的寓言: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而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1]92
为方便叙述,本文以“庄周梦蝶”概括这则寓言。“庄周梦蝶”的寓言是《庄子·齐物论》的压篇之作,庄子在此篇末尾提出“物化”一词,可谓是对《齐物论》,乃至于整部《庄子》的总结与升华。它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奇妙的艺术魅力,使这则小小的寓言不仅成为了历代文人争相引用的经典,还引起后世学者的关注和研究。随着西方文论思想的传入,不少学者开始借鉴西方文学理论成果研究中国文学问题,大大扩展了中国文学作品的解读空间。在西方文论的启示下,部分学者尝试从全新的角度去阐释“庄周梦蝶”,“庄周梦蝶”的研究有了创新和突破,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些研究者盲目照搬西方理论,甚至削足适履,没有考虑到“西方语境中产生的这些批评理论与我们的文学现实之间的错位现象”[2]8,落入了“强制阐释”的窠臼。
一、庄周梦蝶研究中“强制阐释”的表现
2014年,张江教授提出了“强制阐释”这一重要概念,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张江教授在《强制阐释论》一文中明确指出,“强制阐释是指,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3]5。张江教授提出“强制阐释”,本意是概括当代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但许多学者认识到,“强制阐释”也可概括在借鉴西方文学理论成果解读中国文学作品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不可否认,在当代全球化话语体系下,西方文论传入中国,并且深刻影响文学研究是不可避免的。思考在吸收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中的“强制阐释”问题,并不是要我们固步自封,抵制西方外来思潮,而是要找到在吸收西方文论成果的同时,而不陷入“强制阐释”的正确研究路径。本文拟选取“庄周梦蝶”这一寓言的研究,试图对此探讨一二。
庄周梦蝶的寓言虽短小,但意义深远。它在《庄子·齐物论》的篇末,且提出了“物化”这一重要概念,历来学者对这则寓言的阐释纷繁复杂,没有一个定论,其原因在于文本不明确的意义和耐人寻味的表达。在“以西评中”的浪潮中,不少学者开始借鉴西方文论阐释“庄周梦蝶”,出现了很多新颖的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其一,运用现代心理学或弗洛伊德精神分析阐释“庄周梦蝶”;其二,在生态美学视域下的“庄周梦蝶”研究;其三,运用逻辑学阐释“庄周梦蝶”;其四,借鉴西方悲剧主义、存在主义、相对主义等阐释“庄周梦蝶”。这些研究中不乏优秀的成果,但也有一些学者盲目照搬或简单挪用西方文学理论,导致研究成果偏离文本内涵,有“强制阐释”的嫌疑。如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观点阐释“庄周梦蝶”的观点就认为,人之所以变成蝴蝶的原因,归根结底是一个心理现象。根据弗洛伊德关于梦的解释,梦不是偶然形成的联想,而是被压抑的欲望(或潜意识的情欲)伪装的满足。由此得出蝴蝶梦可以被看作是庄子在潜意识中的一个愿望的变相的实现。而根据弗洛伊德的“人格三部结构”,即人格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所构成,得出“庄周梦蝶”这个故事并不是在讲述“庄子”和“蝴蝶”作为两个不同个体的意象,而是关于一个人的被分裂的“本我”和“自我”的意识活动的结论[4]。这种观点犯了两个错误:
首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属于心理学范畴,本不属于文学理论。但我们不是反对跨学科、跨领域的交叉融合,张江教授指出我们承认文学征用场外理论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不能背离文学的特质,一定要深刻把握文学实践[3]7。在《梦的解析》中,弗洛伊德把梦定义为人的受压抑的“愿望的达成”[5]。弗洛伊德所說的梦与“庄周梦蝶”中的梦并不属于同一范畴。最新的心理生理学研究结果表明,梦活动本质上是生理的,但包含人的心理因素。弗洛伊德所说的梦也就是人的一种生理、心理活动,属于理性和科学的范畴。“庄周梦蝶”中的梦,与现代意义上的“梦”有本质上的区别,它有哲学范畴上的意义,并不能等同于人的梦活动。庄子是否真的做过一个关于蝴蝶的梦是无法考证的,但庄子好为寓言,我们倾向于认为庄周梦蝶是庄子所构思的一个寓言故事。关于梦,庄子在《齐物论》中还讨论过,“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1]85。庄子在这里告诉我们,人做梦的时候是不知道自己在做梦,梦中还做着梦,只有醒来才知道自己在做梦,愚人往往以为自己已经清醒,但其实还在梦中。庄子所说的“梦”是与“觉”相对的,在梦中的人往往不知道自己在梦中,自以为清醒的人,其实也是在梦中。在这个意义上,“梦”并不是单纯的心理活动,而是具有丰富的内涵。“觉”是觉醒、清醒的状态,而“梦”是不清醒的状态。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出发,梦中的蝴蝶被看作是现实中被压抑的潜意识。庄子在现实中得不到自由,因此在梦中化成蝴蝶,获得精神的愉悦与自由。蝴蝶这个意象也许是真的代表了庄子所渴望的自由,但是蝴蝶梦并不是庄子之梦,而是他构思出来一个寓言故事。与其说蝴蝶是庄子的潜意识,还不如说蝴蝶是庄子的艺术构思,研究者把庄周之梦当作是真正的梦的活动来解析,是无法把握文本真实的内涵。
其次,犯了“主观预设”的错误。张江指出,“主观预设的批评,是从现成理论出发的批评,前定模式,前定结论,文本以至文学的实践沦为证明理论的材料,批评变成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理论目的的注脚”[3]8。作者在展开批评之前,已经选定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作为立场,前置结论,批评的全过程都是围绕立场的需要展开的,因此批评离开了具体文本,丧失了客观性。批评并不是为了分析文本,而是为了证明理论和结论的正确性。
从弗洛伊德的“人格三分结构”出发,认为庄周梦蝶的寓言是关于一个人的被分裂的“本我”和“自我”的意识活动。按照弗洛伊德这一理论解读“庄周梦蝶”,可以这样理解文本:一天夜里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怡然自得而忘记自己是莊周。醒来发现还是庄周自己,此时庄周恍恍惚惚地分不清究竟是自己梦见蝴蝶,还是蝴蝶梦见自己。批评者是站在主体意识到自己是庄周的立场上说话,认为整一则寓言是作为主体的庄周的自我体验。蝴蝶因此沦为客体,蝴蝶的立场也就被取消了。这是精神分析下“庄周梦蝶”研究的一个共同特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精神分析理论可以解释庄周为何可以梦为蝴蝶,但是无法解释蝴蝶为何可以梦为庄周。在用精神分析阐释作品时,为了切合理论,批评者需要在解读过程中取消蝴蝶这一视角,强调庄周的主体地位,让蝴蝶这一意象变成庄周梦见的客体。
细读文本,庄子说“周与蝴蝶必有分也”,分是分别、界限,庄周与蝴蝶一定是有所分别的。庄周与蝴蝶的分别之处是什么呢?林希逸认为,“在庄周则夜来之为胡蝶梦也,恐胡蝶在彼,又以我今者之觉为梦,故曰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这个梦觉须有个分别处,故曰周与蝴蝶与?这个梦觉须有个分别处,故曰周与蝴蝶必有分矣”[6]。在林希逸看来,庄周夜晚梦见蝴蝶,蝴蝶在另外一个地方,又梦见变成庄周。庄子所说的“必有分”,也就是梦与觉之分。刘涛还认为,“必有分”不仅是形体之分和梦觉之分,还有真与幻之分[7]。总结一下,“庄周梦蝶”这个故事有两重叙事,第一重叙事是显而易见的,即“庄周梦蝶”,庄周梦中变成蝴蝶,全然忘记自己是庄周,醒来发现自己是庄周。另外一重叙事省略了蝴蝶的视角,即“蝶梦庄周”,蝴蝶梦见自己是庄周。也就是说,此时自认为醒过来的庄周,也许是蝴蝶梦中之物。刚刚所做的蝴蝶梦,是现实中的蝴蝶。这时候梦与觉、幻与真一下子交融在一起,庄周无法分辨此时的自己是刚刚从蝴蝶之梦中醒过来的庄周,还是刚刚的梦是真实的,自己原本是只蝴蝶,此时做梦成为了庄周。究竟哪里是梦、哪里是现实,庄周自己陷入了迷茫。
在“庄周梦蝶”这个故事中,庄周与蝴蝶是两个自然个体,他们通过“梦”这种机制互相转化。庄周无法分清的绝不是做梦的人是谁,而是分不清梦与觉、真与幻的界限在哪里。正如庄子所说“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当人在梦中时不知道自己在做梦,而愚蠢的人往往自以为自己是清醒的。醒过来的庄周,究竟是真实的庄周,还是一只梦见自己变成庄周而忘记自己是蝴蝶的蝴蝶呢?正是这种扑朔迷离、梦觉难分、真幻难辨的艺术魅力,才让“庄周梦蝶”这个故事成为后世文人争相引用的典故。因此把“庄周梦蝶”这个故事当成是一个人分裂成“本我”与“自我”的意识活动削弱了文本的艺术魅力。
美国学者爱莲心是研究《庄子》的最高产的学者之一。他在《向往心灵转化的庄子:内篇分析》一书中大胆地用相对主义、逻辑学等方法来研究庄学,一反传统,启发我们的思考。爱莲心大胆地质疑“庄周梦蝶”这个寓言的编排顺序,他站在西方逻辑学的角度,认为庄周梦蝶这个寓言是一个不成熟的版本,有着逻辑上的模糊性。首先,庄子一开始明确地说“昔者庄周梦为蝴蝶”,那么为什么又说“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这在逻辑上无法说通。其次,如果庄子连自己是庄周还是蝴蝶都不知道的话,为什么还说“周与胡蝶必有分矣”。基于“庄周梦蝶”的逻辑问题,爱莲心认为有必要调整“庄周梦蝶”的文本顺序,即“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俄而觉,则蘧蘧然周也。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为物化”[8]91。原文与调整后的文本的区别在于,原文“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的发问是在庄周醒来后,后者的发问是在梦中。爱莲心可以说是第一个对蝴蝶梦文本顺序提出质疑的学者。但是因为文本逻辑而调整后的文本又产生了新的逻辑问题,既然庄周在梦中化成蝴蝶,“不知周也”,此时在梦中的他又怎么会发出“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的疑惑呢?在笔者看来,爱莲心从逻辑性原则的角度重新编排“庄周梦蝶”这个故事确实是破天荒的尝试,但是这种尝试却破坏了文本。爱莲心为了让“庄周梦蝶”这个寓言符合他自己的观点,判定“庄周梦蝶”是“大圣梦的一个不清楚的版本,它试图说大圣梦要说的东西,但说得更不完整、更不完美”[8]109,并且对原文加以修改,试图说服读者,同样犯了“强制阐释”的错误。
二、庄周梦蝶的阐释路径及思考
张江教授提出“强制阐释”的概念引导我们审视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不难发现“强制阐释”也表现在我们借鉴西方文学理论研究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勘探在西方文论的影响下,庄周梦蝶研究的“强制阐释”问题,是为了思考“庄周梦蝶”,乃至于中国古代文学的阐释路径。
“庄周梦蝶”研究中的“强制阐释”问题给我们深刻的思考——在西方文论盛行、各学科交叉融合的今天,我们应该怎样阐释中国古代文学。不加筛选、盲目照搬西方文学理论,会忽视中国文学传统,使阐释远离中国文学精神。余英时教授在《怎样读中国书》一文中说:“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国史者先有外国框框,则势必不能细心体会中国史籍‘本意’,而是把它当报纸一样地翻检,从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9]在张江教授还没有提出“强制阐释”的概念之前,余英时教授已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学术界“以西释中”的误区,学者在展开批评之前,先设定好理论前提,然后再从文本中勘探与理论相一致的东西,这样的阐释是不得中国古代文学的深意,往往是牵强附会、生拉硬套的。作中国古代文学的学问,最重要的是回归中国文学传统。中国文学传统与西方文学传统迥乎不同,如果漠视中国中国文学传统,容易歪曲文本的内涵。如上文提到的庄子的梦与弗洛伊德的梦不在同一个认知范畴。再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以叔本华哲学为依据,认为《红楼梦》中的“玉”象征着“生活之欲”[10]。这样的解释就是理论先行,完全没有理会中国的文学传统,因此受到后来者的质疑。
强调回归中国文学传统,并不是要抵制西方文学理论的引入。西方文论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是积极的,而且是无法避免和不可逆转的。在研究中,发挥西方文论作用的同时,避免走入“强制阐释”的误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著名的学者胡适、王国维等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时也曾犯过“强制阐释”的错误。李春青教授指出,西方文学理论有其“有限合理性”[2]6。“有限合理性”有两层内涵,一是西方文学理论有合理性,不应该把它看做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毒药;二是这种合理性是在有限范围之内,一旦超过这个范围就容易有“强制阐释”的倾向。因此,如何在这个“有限合理性”的范围内取得平衡值得思考。我们在借鉴西方文学理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问题时,更多地应该借鉴其“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视角与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路径”,而不是把理论视为公式去机械地分析文本。
三、结语
李小贝指出,强制阐释的提出打破了西方文论的神话[11]。西方文论神话的打破,也就意味着新的文论的建构。在借鉴西方文论研究成果研究中国文学问题,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上,“强制阐释”问题积弊已深。研究回歸中国文学传统,应注重回归作品的审美上,而不是把文学作品变成西方文论的印证,这样才能使中国文学研究走得更远。
参考文献:
[1]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李春青.“强制阐释”与理论的“有限合理性”[J].文学评论,2015(3):5-8.
[3]张江.强制阐释论[J].文学评论,2014(6):5-18.
[4]马荟玲,王爱敏.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解读庄周梦蝶[J].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5(5):121-125.
[5]弗洛伊德.梦的解析[M].赖其万,符传孝,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37.
[6]林希逸.周启程,校注.庄子鬳斋口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7:44-45.
[7]刘涛.分与物化:庄周梦蝶的主旨[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20-22.
[8]爱莲心.向往心灵转化的庄子:内篇分析[M].周炽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9]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J].刊授党校(学习特刊),2006(7):11.
[10]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一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1-23.
[11]李小贝.当代西方文论神话的终结——强制阐释论的意义、理论逻辑及引发的思考[J].学术研究,2016(6):6-10.
作者简介:陈咏丰,华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