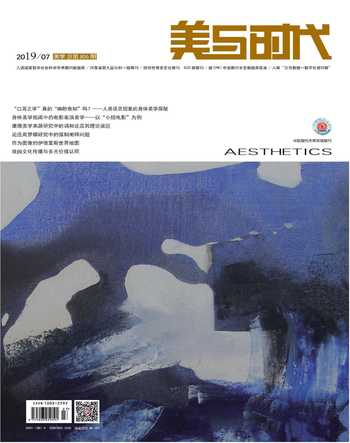几个版本的《牡丹亭》舞台美学赏析






摘 要:昆曲又称“昆剧”“昆山腔”,被誉为“百戏之祖”。抒情性强、肢体动作细腻、唱腔柔美、音律舒缓等特点使得它在中国戏曲的舞台上历久弥新。昆曲尤以汤显祖剧作最为经典,其中《牡丹亭》更是戏曲舞台上被演绎最多的剧本,它讲述了一则瑰丽奇绝的人间情事。
关键词:昆曲;汤显祖;《牡丹亭》;实验戏曲;舞台美学
一、实验戏曲《梦》
(一)梦为肢体,情为诗心
昆曲又称“昆剧”“昆山腔”,是中国戏曲几大剧种的始祖之一,被誉为“百戏之祖”。昆曲的突出特征有抒情性强、肢体动作细腻、唱腔柔美、音律舒缓等。昆剧尤以汤显祖剧作最为经典,其中《牡丹亭》使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描绘了一个奇绝瑰丽的爱情故事。在汤显祖所生活的明中叶,社会已经具有了资本主义的初级经济形态,而当时统治阶级昏庸,民众生活苦难,市民阶层渴望冲破统治者的高压。“现实生活中并没有春天”[1]341,于是“因情成梦”(《玉茗堂尺牍之四·复甘义麓》),“在‘梦’中,有法之天下变为有情之天下,从而有了‘春天’”[1]341,进而“因梦成戏”(《玉茗堂尺牍之四·复甘义麓》)。“临川四梦”正是汤显祖寄托理想的载体,正如他自己所说:“弟传奇多梦语。”(《玉茗堂尺牍之四·复甘义麓》)也正是因为其“牡丹”为“梦”,于是梦中人“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生生死死总关情,花开花谢又一春。杜丽娘一“死”又一“生”皆因对现实状况的不满,因而跨越阴阳两界寻求方法,寻求解脱。
《牡丹亭》与《紫钗记》《邯郸记》《南柯一记》四部并称“临川四梦”,四剧情节皆有梦境。《牡丹亭》和《紫钗记》剧中含有“梦境”之情节;《邯郸记》及《南柯记》本就是主人公的一场大梦。“梦”与“现实”构成对应关系,促成了故事的行进,亦传达了作者“人生之梦”的情思。汤显祖剧作以“梦”为戏曲的肉身化载体,以“情”为神灵之寄。
(二)小剧场中的实验剧
“由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北京戏剧家协会、北京天艺同歌国际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共同主办,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交流推广项目,2018第五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于10月23日在繁星戏剧村正式开幕。”[2]该活动以“实验戏曲”为范式将传统戏曲与当代舞台表演样式进行融合,是一次古典与现代的碰撞,旨在创新和探索。该艺术节上演剧目共18部,其中与汤显祖经典作品相关的共有两场:《梦》及全男班《牡丹亭》。
实验戏曲《梦》是一场“极简”的表演,通过一说书者——“梦人”之口述,“四梦”以四个唱段的形式被串联在一场演出之中。整场演出使用了粤剧、越剧和昆曲三种不同唱腔,每个段落选取相应曲本中最具代表性的章回,使觀众一下子便被精典唱段所吸引,进入熟悉的共情之境而陶然自醉。可以说,这是一场专为熟读汤显祖文本的观众打造的试听享受。
幕启,筝、琵琶、鼓、萧四名乐手分立舞台四周,“梦人”居于舞台中央,灯光追之。“梦人”着素色布衣,以一段科白开启了“四梦”的讲述。此实验戏曲之所以为“极简”,除了曲本的精简、布景造型的简练之外,它的叙事层级也是极简的。四个唱段共两名演员,男女各一,讲述者“梦人”在两个唱段间隙是汤显祖、是戏评人,在唱段开启后又是剧中的主人公。舞台侧面有一桌子,悬挂四套长衫、四幅髯口,“梦人”着素衫念完科白便取一套装扮,进入唱段成为角色,“通过‘黑三’、‘惨三’、‘白三’三种髯口(胡须)的变化,依次表现主人翁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人生追求。”[3]《梦》的两位演员唱念做打舞的基本功是极佳的。可以说这场表演把旁枝的舞台元素化到极低,将表演本身突出到最高。这样的形式相较于老派的中国戏曲更易于被年轻人以及其他文化背景的观众接受,使人观之不易产生戏曲的程式化所带来的区隔感。
在音乐编配方面这台戏也体现出了高超的制作水准。四个唱段以不同的戏曲唱腔演绎,“为避免南腔北调音律不协,在音乐声腔上作了新的尝试,融以昆腔、京韵、粤调、古曲等元素,并以此为基础予以新的音乐旋律”。乐部在乐器构成方面更像是小型室内鼓吹乐队,而非以往的胡、板模式。在乐段的编配中器乐的功能更突出,筝与琵琶时常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创”入段落,在故事间隙时而有乐器的“讲述”。器乐以音乐塑造意象的特殊方式,以故事性的口吻调拨观众的情绪,而非寻常那般只是个背景。这一模式更像是舞台话剧,使整个表演更活泼生动。
二、素颜版全男班《牡丹亭》
此次登上小剧场戏曲艺术节的全男班《牡丹亭》是对经典的另一种别样呈现。当观众首次接触演出资讯时必然被“全男”“素颜”等字眼吸引。男旦在戏曲的舞台上并不稀奇——为人们所熟悉的“四大名旦”皆是乾旦,但全剧组男性演员以不着脸谱的方式演绎《牡丹亭》,难免让人产生怀疑:这样还能让人想起《牡丹亭》的故事,还能让人想到杜丽娘吗?
这场演出共演绎《游园》《惊梦》二折,表演采取讲演交替的方式。杜丽娘的扮演者兼导演金谷在每一唱段之前先为观众解说一番台词剧情及所使用的手眼身法步,随后演员登台演绎相应的内容。这种形式便于初级受众看懂每一段落的故事情节和戏曲程式技法。
表演开始,几位乾旦依次登场,观众们猛一下子是不适应的。当看到几个大男孩饰演的春香伴着小姐梳妆,一个俏皮活泼,一个娇羞欲滴的样子时难免有一些想笑。随着剧情的推进,金谷扮演的杜丽娘之如花美眷感渐渐出来了,虽不着头面、不饰颜彩,干干净净的素颜下依旧升腾起娇滴滴的女儿感——只见“她”眼波流转,媚眼如丝。笔者同行友人道:“不敢看他的眼睛,太勾人!”可见,乾旦加上素颜依旧能够完满地传递出古时深闺娇女的一颦一笑。金谷就乾旦这一问题道:“乾旦艺术是用男人的身体在舞台上画出女性的线条,传达的审美是似与不似之间的意味,这与整个中国戏曲美学是统一的。在今天乾旦已经不只是一个行当的意义了,而是中国戏剧表演之大写意美学的一个重要支流。”[4]
全男班这一版本的演绎同样是勇敢、创新、极简的。他们删繁就简抛掉华丽的服饰脸谱,仅仅依靠唱腔和身段技巧表现以往舞台戏曲多个部门所承载的内容;同时又是“归一”的,全体男性演员分饰少女、青年、老妇等多个性别、年龄区间的角色,其差异的表征仅仅依靠演员的舞台技巧。这种去表象符号的表演方式更贴近本质:在几乎抹掉了所有用以种属性质区隔的元素后,仅仅以最贴近原生的纯白状态展演故事,这似乎是一种使文本初具生命体征的式样。此次全男班的素颜表演正是表演理论研究者所关心的——戏剧表演中删除哪些元素后仍可称之为戏剧?这种“删除”的最大极限在哪里?
导演金谷就这场戏的表演风格谈道:“我们的艺术指导是北方昆曲剧院的昆曲名家张卫东先生,这个版本的演出路子是沿袭老的京朝派唱念和表演调度。陈德霖先生传给尚小云先生,尚小云先生在荣春社传给杨荣斌先生,杨荣斌先生又传给张卫东先生,张卫东先生又传给我,大概是这样一个传承脉络。所以跟所有昆剧团的路子都不同。我们除了有导赏和讲解,演出部分是遵照经典完全没有改动的。”全男班的表演在唱念的技巧上是令人满意的,在身段做打上则更突出一些。许是整班年轻小伙的缘故,演员们在舞台上很有活力,生角旦角都元气满满,杜、柳二人的互动常使观众忍俊不禁,确实是一出带给人新鲜试听的实验戏曲。
三、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
(一)“青春”版本的独特视听
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是近些年流传度较高、资源保存最完整的一个版本。青春版《牡丹亭》自2004年4月起首次登上台北国家剧院的舞台,至今已在全世界巡演二百三十余场,规模空前浩大,为中国昆剧的传播和发扬起到了突出作用。白先勇将原先的剧本做了删减,该剧目分为上中下三本,每本九折共二十七折,三天演完,每天一本,可让观众一下看个痛快。既为“青春版”,可想而知这部《牡丹亭》的新编是与以往不同的。演员都是年轻的,台词也是重新加工过的,除原本唱段保留昆腔外,念白上更接近普通话的发音,此外还加入了一些解释性对话更易于不同层次的观众接受。
青春版《牡丹亭》的台词念白较之原本有了一些增设,人物对话被丰富了,剧组在原本文绉绉、半古汉语的台词上增添了一些口语化、符合当下流行语境的段落;在方言口音问题上,昆山话的痕迹被弱化了,让观众能听得出来方言的腔调但大部分发音是普通话的;舞台道具方面也有不同,剧中人物在演杀头的戏码时是由实体道具充当“首级”的,观众的观看更具肉身感。这在以往戏曲的程式化表演中很有可能被处理成虚拟的方式,演员做个动作示意一下,这样就是杀人头滚地了,那样就是洗脸梳妆了,而不必拿各种脸盆茶盏的物件出来。这种具象化的表演借鉴了歌剧、话剧等戏剧表演的舞台风格,这样表演更为年轻观众、外国观众受用。此举也正应了“青春版”的称谓——“青春”的不仅仅是演员,青春的亦是受众,更是剧种的传承方式。青春版《牡丹亭》这部剧做得不是那么严肃刻板,它在许多方面都有着革新。舞台导演翁国生在访谈中讲道:“他们(白先勇、汪世瑜)有一个新的创作理念,他们不想这个戏仅仅是个传承,他们更希望这个戏在传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我和白老师、汪老师碰撞的最有共鸣的一点就是我们都想运用一种新的导演方法来重新制作这部青春版《牡丹亭》,也就是昆曲最根本的、最经典的、最本体的东西,咱们一点一滴都不变,保持昆曲原汁原味的传统经典,但是在21世纪的舞台上,在面对着海内外这么多年轻的戏曲观众的环境下,如果你还是按以往的昆曲舞台上的传统演法,就是挂个悬挂式的戏曲灯笼,搞两道装饰性的蝴蝶帷幕,大白光,一桌二椅。肯定不可能有现在青春版《牡丹亭》演遍海外各国、全国各地的靓丽效果。”[5]
(二)下本《折寇》中的相关问题
在下本《折寇》一出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原本《围释》中金朝使者是由老旦扮演,负责向娘娘翻译的侍从是一个贴旦,而在青春版中金朝天使和翻译官都成了丑角。
汤显祖为何把调戏杨婆的番人使者设定为女性?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尚未查证到可靠资料,既然没有可靠的材料来专门解释这一问题,不妨就把它直接理解为汤显祖在这里写了一个少数民族女性官兵调戏杨妙真的桥段。在原本第二十三出《冥判》中有这样一个桥段——杜丽娘在地府中排队等候判官发落,前面排着四个男犯。判官审到一个喜好南风的名叫李猴儿:“(净)叫李猴儿。(外)鬼犯是有些罪,好男风。(丑)是真。便在地狱里,还勾上这小孙儿。”因他喜男色,判官罚他下辈子做蜜蜂:“(净)你是那好男风的李猴,着你做蜜蜂儿去,屁窟里长拖一个针。(外)哎哟,叫俺叮谁去?”李猴儿不服也没得办法,气哼哼地飞走了:“(外)俺做蜂儿的不来,再来叮肿你个判官脑。(净)讨打。(外)可怜见小性命。(净)罢了。顺风儿放去,快走快走。(净噀气介)(四人做各色飞下)”此处是一个招笑的、带有亵语性质的哏,汤显祖拿男同性恋者开了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可见,《牡丹亭》剧本中出现同性恋者的桥段不止一处,可以认为汤显祖对同性恋这一通常被大家所避讳的现象注入了一定程度的关注,而这一问题恰恰与“情”有关。
青春版《牡丹亭》为什么把金朝特使处理为男性丑角?我们知道白先勇先生本人是同性恋者,他本人并不避讳这个事实,他创作的小说《孽子》两次被搬上电影的银幕,人们为他笔下流离失所的“青鸟儿”叹惋。白先生在访谈中提到青春版《牡丹亭》的编剧小组包括他本人共有四人。按理说白先生必然注意到了戏中这一问题。青春版不仅把调戏杨妙真的金朝天使处理成了男性丑角,《冥判》中的男犯也被删掉了。如前所述,青春版《牡丹亭》的目标受众是广泛的,是全世界各种文化背景的人,因此这种相对保守的处理也是稳妥的。
汤显祖作牡丹亭言“情”既然能够开创震撼后世的“唯情说”,这剧中人物的“情”的样式便不应该局限于男女主角。杜丽娘、柳梦梅之情冲破生死阴阳;李全、杨妙真之情浪迹天涯、血雨腥风;另几位走过场的角色也有着冲击封建人伦的“情”。
众所周知,“同性恋”是一种符合生物自然特性、普遍存在的现象。不仅仅人类群体,科学家在多种不同的动物种群中也发现了喜好同性的现象。汤显祖作为一位情思细腻洞察锐利的文学家,必然洞悉了这些与人性、与“情”相关的自然现象,因而他在剧中看似一笔带过的几则对同性恋者的刻画都是无伤的、诙谐的,使观众阅后捧腹大笑而不会产生厌恶情绪。
同性恋问题是一个从古至今长存的议题,但直至二十一世纪的今日,许多人在聽到这些字眼的时候仍然会条件反射地眉头紧皱道:变态、恶心。事实上同性恋也好,异性恋也罢,它们都是人与人之间自发自愿的情感力量,它们仅存在于参与者内部而对外部群体无伤,是力比多带来的原动力。在言及“情”的冲破时,汤显祖用简单几笔提到了这一现象,在其身处的时代具有强烈的先锋性。
参考文献:
[1]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341.
[2]第五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正式开幕[EB/OL].[2018-10-24].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5201490389754074&wfr=spider&for=pc&isFailFlag=1&from=415a.
[3]《梦》:一场四百年前的“网红剧”[EB/OL].[2018-10-25].https://mp.weixin.qq.com/s/dygQNNpoMJBXiY2dNWnI9Q.
[4]“男”得一见,“最高”海拔《牡丹亭》[EB/OL].[2018-11-16].https://mp.weixin.qq.com/s/61N7hjPbNg91KnI9zV5U-g.
[5]《白先勇与青春版〈牡丹亭〉》访谈录/导演翁国生访谈.[EB/OL].[2015-01-16].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ee40a30102vb29.html.
作者简介:陈秋旻,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