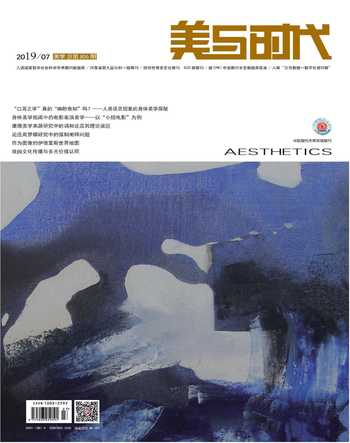身体概念何以能够成为重建诗学的起点?
摘 要:王晓华教授关于身体诗学与美学的研究形成身体话语的“当代史”。“身体”概念的复杂意指,决定了《身体诗学》运思的艰险。等身性提示出身体诗学对待物与世界的平等观念,而超越维度则显示出身体诗学具有的谦卑态度和神圣感。与现象学还原的路径相反,身体诗学的论证包括两个次序相连的操作:理念的还原与思想的还原,不妨称之为“身体诗学的存在还原”。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心”是“身体”能动性的意谓。交心的实质在于互身。有别于认知学所遵循的主体理性原则,身体诗学依循关系理性展开生活世界。与人之存在的言说相伴始终的是身体观的演化、身体活动形态与身体对象化的呈现。存在关切下的身体观与身体化,分别相关于人类文明与文化。
关键词:《身体诗学》;王晓华;身体;诗学;重构
相较于神学话语中的罪恶之身、理性话语中的卑伏之身和实用话语中的工具之身,“后学”话语中的“身体”已然洗去污垢,登上主场。登台后的“身体”不无夸张地讲述其被规训、被象征和偶尔任性之乐的故事。关于身体的言说形成身体的话语传统,新的言说一方面接续上最早的话语,维持了传统的生存;另一方面被引渡到新的文化语境中,同时嫁接上新的身体经验,形成身体话语的“当代史”。王晓华教授执著于身体话语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关注身体话语,先后发表与出版相关主题的论著近三十种。他主张身体而非灵魂是文学活动的主体,身体诗学(美学)“研究的重点不是身体如何在诗中获得表现,而是身体怎样通过诗来表现自己”,提倡“诗学的身体转向”,致力于构建以身体为基础的诗学体系,其身体美学研究蜚声学界。其新著《身体诗学》(人民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以深思缜密见长,评述已多,笔者拟从阅读启示的角度凝视作者的“身体”之思。
一
“身体—主体”说贯穿于王晓华教授的学术研究历程。他主张美学与诗学研究应当由对“意识—主体”的研究回归到身体诗学(美学)。可以这么说,其学术目标在于建立以文化人类学为参照系的诗学(美学)身体学。循其思路,作为具体存在之身,首先是个体之身。个体之身既是个体世界的主体,又是个体经验的策源地。身外世界原本无关于个体主体的,因个体之身的感知感受而成为身体经验的对象。就身体经验而言,个体之身既是经验的主体,又积存沉淀了经其亲验的内容。上述理解中的“身体—主体”说中的“主体”,一方面作为经验的主体,类似于霍布斯所谓的“感觉者主体”;另一方面作为经验的内容,近似于笛卡尔所谓的“呈现于思想中的客体”,可谓之为“呈现于身体中的客体”。作为主体的个体之身,在进一步的还原操作中离析出“主体-客体”二分的结构。这种结构可能就是《身体诗学》中的“自反性关系”概念所描述的主项。
主体地位所承诺的自主性,并不足以担保身体经验的自足性。概念分析上的自足性,无法掩饰身体经验的贫乏苍白。身体经验的生成有待于身外之物。在有关“身体意识与生态诗学”的讨论中,身体被归约为有机物。有机物的生物属性是众有之身的生理基础,即共同之身的同一性所在。有机物对于世界的“刺激-反应”模式,如果视为对生态环境的尊重,那么,从另一角度而言,则可视为对主体的自觉能动性的取消。当然,将身体还原为有机物的本质化过程,也体现了对于身体本体的努力探求。《身体诗学》封面的提要文字“让身体在本体论(尤其是社会本体论层面)显身”,清楚标识了著者的追求。从本体论的层面而言,身体的存在本意,较身体因何而在更为根本。基于因何而在的思考,身体被归约为有机物。由于存在的本意不可究诘,常常从存在的目的把握身体存在的意义。目的设定不同,身体的本意理解迥异,既不可亦无法简单划一。如果将存在分为无机、有机与社会三个层次的话,身体在社会本体论的显身,意味着与“身体-有机物”的本质推导路径相异。以上所言,事实上涉及对身为何“体”的理解问题。
作为诗学体系基础的身体概念,具有本体意味,一切由“此”出发,循“此”而展开,最终回归于“此”;作为诗学(美学)活动主体的身体,是统觉的中心,类似于意识活动中的自我;作为诗作主体的身体,是诗学的身体主题。至于赋予世界以意义,成为万物尺度的身体,则属于超越的实体,是思考身体与世界关系的浪漫想象而非结构模式。身体-实体概念虽为“体系创造”所必要,然而作为绝对超越之存在,又无法容留于体系之内。身“体”概念的复杂意指,决定了《身体诗学》运思的艰险。
二
作为复数的体系,诗学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之分。前者由理念出发,谓之为意识诗学;而后者则由经验出发,王晓华名之为身体诗学。不同于凯瑟琳·库奇内拉Poetics of the Body所谓的“诗中的身体”,新著旨在建构植根于身体的诗学而非诗学中的身体。身体诗学概念意味着身体的诗学主体性,其前提在于身体内蕴的诗性。诗学意味着创造,创造基于身体的活动;而诗性源于盈余,盈余意味着丰富多样。想象的丰富多样指向未来的可能性,而时空绵延的可能性恰是创造的内在属性。可能而非确定,创造而非现成。惟其如此,才值得期待,充满魅惑。所谓的不确定并非结构的空白而是对创造的期待。创造的身体不是观念性的存在,而是时空中展开的存在,是在绵延中的创化变易;就存在性而言,不是to be,而是becoming。在未来的开放性上,诗学与诗性邂逅而交汇。身体的诗性在于创造,指向身体的开放可能性,此应是身体诗学的命义与蕴涵所在。
身体的诗性源于身体的创造性活动。还原为有机物的身体的活动,是否都具有诗性?若其有则其自有。在有机物的层面而言,视身如物,等身同万物。不仅身体具有诗性,而且万物也具有诗性,且诗性自有而非他者所赋予。众物居于世界之中,物的诗性照亮世界,世界因万物的创化活动而在,而非赋予万物以诗性。此处所谓身体诗性表现为万物的生机及形态。万物自有诗性,而世界的诗性则体现为万物的联结与互动。以上关系不妨理解为身体诗学与生态诗学的理论纽带。若其无则如何理解身体的诗性?则只能是:作为有机物的身体,因分有了他者的诗性,而被赋予诗性。世界只是万物存在的形式,不具有主體资格,不可能拥有可分享给他者的诗性。具有诗性的他者只能来自于世界之外的超越者。超越者即在世界之外又作用于世界之中,不然,诗性无法分有。超越者不能感知和理“知”,却能够通过直觉来体验,通过象征去存想。因超越者不可描述,而作为存想超越者方式的直觉和象征则成为描述超越者诗性的谓词。直觉和象征,超越感知与理知,相关于身体经验,姑且谓之为“亲知”。此处所谓身体诗性,既不在于可感知对象的共同性,也不在于身体主体的共通性,而表现为经验方式的个体性——亲知亲证。
由身体诗性两种类型不难引绎出身体诗学两方面性质:等身性及切身性。等身性即视物等身,物我同身。身体已经内化为观物与经验世界的方式,经验世界万物的同时也在经验自身。以身观世界,世界成为一拟身性的存在。切身性指涉身体诗学语言的构造与意指。身体诗学语言既包括身体活动与其具体化之物,也包括身体诗学的术语与概念。术语与概念是用来描述和解释身体诗学的蕴涵及对象的。构词机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拟身化:语言模仿身体,以身体的形态、活动及空间关系作为造词的基本参照。造词机制表明了语言与身体的同构性,或者说语言为身体代言。关于超越对象的亲知表达,类同于指月。现象界的语言不足以直接把握世界之外的超越者,但可以用对亲知体验的描述去象征亲知的对象。象征之所以可行,固然是不得已,但也有赖于对象征与象征之物之间平行关系的信念。基于此平行关系,通过比附和想象,身体诗学别具超越维度。如果说等身性提示出身体诗学对待物与世界的平等观念,那么,因超越维度的照临呈现出身体诗学具有的谦卑态度和神圣感。
三
诗学毕竟相关于人的制作,如何在“人”与“身体”之间建立切实关联,是身体诗学面对的首要问题。王晓华教授在其论著中反复阐述“人就是身体”的观点。许多评论文章都视其为“身体诗学(美学)”的核心主张,若视其为“身体诗学(美学)”理论体系的基石亦不为过。就观点本身而言,若视为事实的归纳——个体之人的存在表现为具体的生理之身,虽然符合常识却无当其要;若视为概念的演绎——人性包含身体属性,亦毫无新意。在此命题中,“人”与“身体”两个概念,通过“是”建立关系。从语法而言,“身体”是对“人”的说明与阐述;从逻辑而言,“人”概念处于“身体”概念之下——在“身体”的意涵表达式中,“人”仅是一个可替换的变量。根据新著的论述,“是”,作为系词,用于此处标示“人”与“身体”间的属于关系——人属于身体,而身体是人的存在基础;而“就是”一方面强化了对于命题的确信态度,同时也表达了论者的知识信念——对人的理解只能发生在身体概念的框架下。作为对“人就是身体”观点的补充解释,“人是会思想的身体”的断言,一方面收拢了身体论域,另一方面丰富了原有论题的内涵。“会思想”是身体的伴生状态,属于身体的机能;同时,“会思想”也是“人”的特征,成为“人”与其他身体变量的唯一区别。换句话说,思想能力是人与其他身体的根本区别,即人的基本特征是思想能力,而思想能力属于身体感官和神经系统的机能。综合两个命题的要点,一个结论呼之欲出:人在存在与精神两个方面都属于身体,从而为身体诗学奠定了理论基石。
在具体论述中,新著援引了大量现象学理论作为理据。不过,在论述的过程中,却走了一条与现象学还原相反的路径。按照现象学原理,从意识内容的基础地位而言,本质还原悬置了存在对象,保留意识能力;先验还原搁置了意识功能即作为生物性存在的自然人,仅余下苍白的先验自我与意识内容静静向视。不同于上述现象学的还原,身体诗学的论证包括两个次序相连的操作:理念的还原与思想的还原。理念的还原意即搁置人的理念,保留人的思想能力;思想的还原意味着搁置思想能力即身体器官的机能,保留存在对象即身体与人对面。经过两次还原最后请出晦藏的身体,恢复其应有的身份。上述理路不妨谓之为“身体诗学的存在还原”。不管身体诗学的具体理论成果的意义如何,其存在还原的思路不失启示价值。
如果“人”与“身体”的还原关系成立的话,“人”岂非成为“身体”的象征符合,而“身体”则是“人”的指称和意谓。“身体”作为存在者的具象性,被称为抽象的“人”概念所取代。“人”僭据本应属于“身体”的宝位,冒享尊荣。按照以上逻辑,一切人文学说,应该返璞归真,还其本来面目:身体学。文化人类学,应即文化身体学。反过来说,身体诗学,应该就是诗学人类学。诗学人类学更有助于揭示身体诗学的人本属性,但一般人类学所谓的“身体”与身体诗学中“人”所僭称的“身体”关系如何?对此问题的解释,难免要求助概念辨析来寻找避难所,承认二者同词而异指。作为“人”之意谓的身体与因“文”而“化”的身体,若不能建立内在关联,势必简化身体诗学的内涵。一个本质化的身体又能解释什么问题?
四
就身体诗学(美学)最应该且较适合承担的理论使命而言,与其说在于存在意义和认识方式方面提供的新知,不如说面对现实问题时,其在理解问题、开启思路方面贡献的智慧。以“心-主体”为基础的人文学,虽然以构建普遍价值和共通理念为目标追求,但学理上的、认知理解方面的普遍性,一旦落实为现实世界的普遍化,就会遭遇到价值理念上的冲突和对抗。先验的价值理念,落实为普遍化的价值推广,就会发现,要么扞格不入,要么极其容易。一般而言,价值推广的普遍化以文化圈为限。同一文化圈的人,具有相同的文化心灵,拥有相近的价值观。同心同理以同文为前提和界限。因价值理念的越界而导致的文化冲突和战争成为本世纪初最大的政治问题,这还不包括此前延续半个世纪的意识形态对抗。以价值理念和意识观念为主体的旧秩序已经“礼崩乐坏”、狼藉不堪。当然,也不排除价值共鸣现象的存在。不过,此现象一般发生在同样的存在境遇与需求的条件下,即“身临其境,心同其感”。以存在者的基本存在为理论对象的“身体—主体”人文学,处理的是人所共同的存在需求、存在形态和存在环境等问题。身同则志通。基于“身同”的经验前提,从普遍性的志到普遍化的身体实践,在逻辑上较为融洽。因此,身体诗学的意义应在于——面对当世的文化冲突和战争问题,以身体的统一性收拾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为界限的旧秩序,重新确立共同认可的基础和问题解决的出发点。
新著力倡“身体-主体”说。摧毁“心—主体”观的千年堡垒自是其题中之义。炮火连天,而“身心二元论”无辜中弹。就学理而言,本体的一元性与认知二分法及实践的辩证创化,并行而不悖。“身体-主体”与“心—主体”在本体论上针锋相对,不可同时为真。自然要立此必破彼。不过,二者本体论上的对立,并不影响认识论上的身、心共在。身心二分是理解和解释人性的认知框架,是把握概念的手段,符合逻辑分析的要求。即使主张“身体-主体”说,也不妨碍在具体论证中使用身心二分的手段推进对问题的分析和解答。引申而言,二分是逻辑理性的体现。逻辑理性在形式上的二值性要求,展开为具体思维中的二分法操作,进一步沉淀为二元论的理论体系。消除身心二元,固然有助于确立“身体-主體”说,但无对的身体成为绝对的存在,既取消了身体的多样性内涵和丰富形态,又拒绝运动、变化和创造,从而走向超越存在。不仅不能够借助身体进行思想,就连如何把握身体都成问题。另外,二元性内在于身体经验中——经验主体与经验内容,无法消除。事实上,一旦涉及具体时空、纳入价值论域或进入实践领域,身体经验的二元性则呈现为演进与相互转化的辩证形态,促进经验的形成和身体诗性的滋养。如果消除“主体”概念的人化色彩、恢复其述谓功能的话,不妨认为“身体-主体”说补足了身体的意义,强调了身体作为心灵基础的功能。
作为论述的支撑,身体诗学(美学)征用了三方面的理论资源:唯物论、实践哲学与中国传统重身观念。相对于物质的本体意味和实践的目的指向,重身观念体现了对具体存在的现实关切。不过,这种重身观念不仅体现在关于“身”或“体”的描述和论说中,还体现在关于“心”的言说中。除了与佛禅相关的意识功能和先验精神及受佛禅影响的“心学”所谓性体外,传统文化中的“心”,多为“肉”心,与身体息息相关之心、感受感动之心,即heart;而非理性认知之心,抽象观念之心,受先验本体统摄的“虚”心,即mind。与“mind”仰赖先验预设作为认知共通性的外在担保不同,“heart”不追求普遍、绝对与永恒,而强调具体情境的感受性、体验性以及经验的传递性,而这种传递性类似于传统所谓“推己及人”。传递的边界,有层次之分且有前拓与后缩之变化。变化的依据在于文化的接近度与价值观念的共识度。此“心”的“感”与“动”来自于肉“身”的体验并存储于“肉”身,且經验的传递依赖个体之“身”的交际。“心”成为“身”的能动性的意谓。交心的实质在于互身。与此心相关的则是身体经验的分享与互通,即身体间性。有别于认知学所遵循的主体理性原则,身体诗学(美学)依循关系理性展开生活世界。
五
相对于科学世界而言,生活世界属于前科学的世界,充满着灵动的身体,沉淀着存在的意义。人生在世,身隶界中。当人在对世界之外的想象及对世界之物的观照之余,当人发出世界竟然存在和世界如何存在的惊叹之后,当人把目光由外在世界转向自身时发现,自身竟然而在及如何而在的问题,居然同样令人不解与着迷。被超越者、真理所吸引的智慧之光第一次投注到自身,作为人之内在而自在的身体第一次成为人的对象,对人的存在意义及存在方式的思考,就渐次明朗而具体起来。与人之存在的言说相伴始终的是身体观的演化、身体活动形态与身体对象化的历史呈现。虽然意义之光掠过身体投向远方,但意义之光下面的身体影像反向意指存在目的;人之存在方式显现为身体之文和身体之物化创造。存在关切下的身体观与身体化,分别相关于人类文明与文化。笛卡尔谓“我思故我在”,以怀疑的精神功能作为人之意义所在。仿此造句,身体诗学(美学)的主张要略为繁琐一些,“我身故我在,我感故共在”。
参考文献:
[1]王晓华.身体主体性的起源与审美发生论:主体论身体美学论纲之一[J].河北学刊,2009(3):59-63.
[2]王晓华.身体,生活世界与文学理论的重建[J].文艺理论研究,2016(4):6-14.
[3]殷国明.“身体”的文化战争[J].社会观察,2004(5):24-25.
[4]王柯平.柏拉图的身体诗学观[J].哲学研究,2005(7):80-86.
[5]颜青山.“存在”作为二阶谓词的现象学意义[J].社会科学,2014(11):115-126.
[6]方英敏.关于身体美学的三种定位[J].学术研究,2018(4):152-161.
[7]王晓华.个体哲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8]王晓华.身体美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9]王晓华.身体诗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10]利科.哲学主要趋向[M].李幼蒸,徐奕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作者简介:殷学国,博士,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诗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