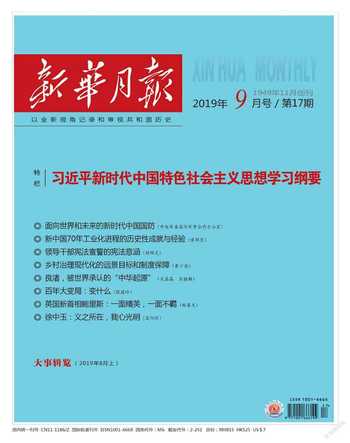教师的新挑战:孩子到底该怎么管?
王煜
教育惩戒权、家长作业、师德建设……不回避这些现实中的热点问题,而是直接点出,并给出了明确的解决方向,这使得2019年6月底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成为近年来最受公众关注的教育发展纲领性文件。
细细研究可以发现,这份《意见》对教师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力图为国家打造一支好品德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教育惩戒权”这个词,乍听起来有些生涩,究其原因,是因为在较早以前,人们认为这项权利过于自然,无需讨论;而到了近年,教师很少在实践中运用这项权利,人们又开始对它感到陌生了。然而称谓的距离感并不能改变它对教育现实的影响,从教师频频遇到“该怎么管教孩子”这样的日常问题,到河南省栾川县“一男子因为求学时被老师体罚过,20年后拦路掌掴老师”这样特殊的案例,都指向一点:教育惩戒权到了必须该讨论的时候了。
在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初等教育学系主任王健看来,惩戒是教育天然就具有的功能。他说,汉字甲骨文的“教”字右半边就是一个手持教鞭的形象,左半边下面是表示小孩子的“子”。从“教”字的起源就能看出,对学生进行规约、训导,提出刚性的要求,从来就是教育的应有之义。
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这样天然的权利,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少数教师的滥用造成的不良影响,逐渐被广大教师群体束之高阁。到现在,不要说体罚学生,就是教师批评学生几句,也会被某些家长认为是“心罚”,产生很强的抵触情绪。《意见》提出“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是要促成这项权利的回归。

王健认为,讨论教育惩戒权,更重要的是讨论如何让教师用好这个权利。他告诉记者,最关键的就是制定细则,把惩戒在什么情况下实施、如何实施规定得非常清楚,让教师和学生都理解。不然,如果规则模糊、弹性太大,有些学生会一次次故意犯错来试探教师的底线在哪里,有的教师可能会因为个人情绪失控而对学生施加过度惩罚,这都会造成许多矛盾,最终让教育惩戒无法真正实施。
他说,在受中华文明影响的一些亚洲国家,例如韩国,对教育惩戒权就有非常细致的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允许教师打学生手心,用多宽的尺子、打什么部位、打多重的力度、打多少次数等,都有明文规定。这就对师生双方都形成了有效的约束和监督,家长也能据此评判教师的惩戒是否合理。
这次中央的《意见》里,也明确指出要出台教育惩戒权的实施细则。教育部2019年8月2日召开的关于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的新闻通气会上,该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将尽力加快教师惩戒权实施细则的研制和出台。他介绍,实施细则的内容主要包括惩戒实施范围、程度、形式等。
他说,细则主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当前一些学校一些老师对学生不敢管、不愿管的问题。这实际上是没有完全履行教书育人的职责,因为按照《教育法》《教师法》有关规定,学校和教师都有责任去对学生实施管理教育。第二个就是解决不善管、不当管的问题。
王健说,教育惩戒可能包括一些轻微的体罚,但并不完全等同于体罚,教师的“工具箱”里完全可以有更丰富的工具来实施惩戒,起到震慑式教育的作用。例如,可以让学生来承担额外的班级值日任务,或者限制他参与某些班级活动,作为对他的一种惩戒手段。
他还提出,与其说现在《意见》的精神是要把教育惩戒权还给教师,不如说是让公众明白:其实最需要规范的教育惩戒的是青少年学生自身,他们需要这样的手段来帮助他们健康成长。国家推行这样的政策以及学校、教师、家长等各个群体为此付出的努力,都是出于对学生成长的关爱。
“好的教育惩戒制度,可能最后几乎没有使用的机会,但这并不代表它没有用。”王健说。
作业究竟是布置给学生做的还是给家长做的?当面对教师布置的明显超出孩子解决和承受能力的作业,以及教师要求家长来批改孩子的作业时,人们常常产生这样的困惑。对此,《意见》鲜明指出:“杜绝将学生作业变成家长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
王健表示,要解决“家长作业”的问题,关键是要划分好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边界,“在对学生的教育上,家校协同不能变成家校趋同”。他说,如果教师模糊了两者的边界,容易造成两种情况:一种是《意见》里专门指出的,教师布置的作业难度和数量明显超出学生的承受能力,把本该让学生完成的作业变相地变成了布置给家长;另一种是教师随意布置作业了事,一些家长觉得学生通过这样的作业得不到课业的巩固,又从其他途径去给学生增加额外的作业,或者让他们去上补习班。这显然都是不合适的。
值得注意的是,《意见》在严格禁止教师布置“家长作业”的同时,还在“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这一部分中专门提出:要提高教师的家庭教育指导能力。这是从另一个方面对家校协同教育提出了要求。
上海市奉贤区教育学院副院长张竹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提高教师家庭教育指导能力”这样的表述,是首次见诸中央文件,具有风向标作用。他提出,“家庭教育指导能力”也并非新鲜概念,而是在之前已存在于对教师的素质能力要求中,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从原来的“选修课”逐渐变为每个教师应知应会的“必修课”,成为对教师新的要求。
张竹林说,家庭教育指導要求教师具备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等基本的通识理论知识。具体的实现方式既包括传统的家访、家长会、家长学校等,也包括当前的网络技术手段。如何做好家访、如何开好家长会、如何处理家校矛盾等,都是教师必须面对的实际问题。
王健认为,每个家庭的需求和对孩子的期望都不一样,“老师说的相同的一句话,有的家长听了笑起来,有的家长听了却要跳起来”。这就要求教师针对每个学生的不同特点,“一家一策”地开展家庭教育指导,这对教师提出了较高的灵活变通的要求。
他说,例如,教师指导家庭教育的场合也并不局限于学生的家庭,可以把教育的场景挪到学校来:教师如果发现班上的学生在过生日时都请同学到自己家,然后互相攀比谁收到来自同学的礼物更多更好,那他就可以主动发出倡议,让生日临近的学生在班上过集体生日,让同学们一起为他们庆祝,而不要再单独请客。
在张竹林看来,家校协同做好家庭教育,要关注和用好“四个力”,即家长的家庭教育胜任力、教师的家庭教育指导力、政府部门的政策推动力、全社会的教育合力。他提出,尤其是要提高“四力”中家长和教师的能力建设,他建议以《意见》为指南,将教师家庭教育指导能力列入教师入职基本能力的培训培养和评价考核体系中,在有条件的大学开设家庭教育专业,开展家庭教育学科研究和建设。
他说,上海在加强家庭教育、推动家校共育上开展了不少探索,积累了许多经验。上海在这方面起步较早,从1979年起,就有一些学校开展了家长学校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各学校重视和完善了家委会建设,重视家长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建设。目前,上海市中小幼学校基本实现家长学校和家委会全覆盖。上海在线下推进从市级、区级到街道、社区的家庭教育指导“网格化”建设,在线上推进“互联网+”家庭教育指导,开设家庭教育指导慕课、“空中父母课堂”。此外,上海市教委牵头开展了家庭教育示范校的评选,以评促建。
2018年起,上海市教委建立了“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教师”常态化培训制度,组织各方专业力量,研制了分学段《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实务》,首次明确提出了教师作为家庭教育指导者应该完成的四大任务和必须具备的四大能力。这为提升教师的家庭教育指导能力,提供了专业保障。
被誉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千百年来都是令人尊敬的职业。我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教育部门,也从来都把师德放在教师队伍建设的首要位置予以重视。不过,当前人们越来越多地发现,有些年轻的中小学教师,就读的并非师范专业,毕业后从事教师职业也不是因为他有当教师的意愿,而是为了就业、落户等“现实”的原因,这样的老师,他们的职业信念能得到保证吗?也有人表示,当下只要大学毕业,再考取教师资格证就可以走上教师岗位,这样的门槛是否太低?
张竹林说,在过去的一段时期,我国的中小学教师基本全部来自师范专业的毕业生,无论是中等师范学校还是高等师范院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大都基本符合教师的职业要求,从职业信念到专业水准,含金量都比较高。后来由于现实情况的变化,教师来源变得多元化。
他说,持续的在职师德培训;开展“卓越教师”培养工程,让名校长、名教师以工作室的形式辐射传承优秀师德;以及举办“教书育人楷模”“我心目中的好老师”评选,教育部门这些正在实行的举措,都能有效地提升教师的师德师风。
王健表示,目前我国的教师队伍仍然处于缺人的状态,因此多元化来源还将继续。同时,国家已经注意到了人们担忧的教师职业信念和从业门槛的现实问题,开始从教师的源头采取行动,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他介绍说,2018年1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以及随后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的《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中都提出:要建立以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非师范院校参与的中国特色师范教育体系。也就是说,教育部门要推动一批有基础的高水平综合大学成立教師教育学院,设立师范专业,参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培训工作。王健说,北大、清华、复旦等高校都正在筹备这项工作。
同时,已有的师范院校不能“去师范化”,不能丢失师范专业的特色。国家还将启动对师范专业的认证制度,对每个院校的师范专业评定等级,等级的高低反映在毕业生从事教师职业的考核程序上就是:最高等级专业的毕业生可以免试入职,次级需要参加笔试,最低级需要通过笔试与面试。王健说,等级评定将把该师范专业从事教师职业的毕业生在岗十年的情况都纳入考察范围,尤其注重师德师风领域。这套评估体系中,也包含师范专业的退出机制。
他透露,教育部门也在研究提升教师的入职门槛,将来非师范专业的毕业生,可能需要再获得师范专业的相关学位才能成为教师。
王健说,教师与律师、医师一样,本应是专业性较强的职位。依靠新的制度,将来我们整体解决了教师“有没有”的问题后,相信可以进一步解决“优不优”的问题。到那时,教师队伍的专业化,将踏上新台阶。
(摘自《新民周刊》2019年第3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