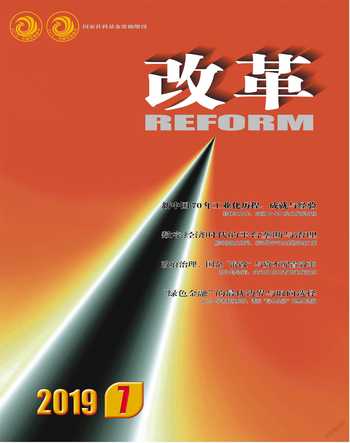新中国70年企业扶贫历程回顾及其启示
李先军 黄速建

内容提要: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在促进我国经济恢复的进程中自然地改善了民众的贫困状态,表现为一种间接的扶贫方式,且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积蓄了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以社队企业和乡镇企业为开端,以当前日益活跃的农村农民创业为趋势,在企业主动性行为和政策引导下,企业以多元化的方式有力地促进了农民收入的提高和农业农村的发展,成为推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重要力量。要客观地认识企业在扶贫工作中的作用;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为企业扶贫提供支持;强化企业扶贫工作重点,突出产业扶贫和教育扶贫。
关键词:企业扶贫;精准扶贫;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F1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19)07-0016-11
在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框架下,与城市相比较,农村在基础设施、资金、人才、技术、知识、市场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比较劣势,企业与农村的发展是一种割裂的关系,企业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长期以来不为学者们所重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袤的中国大地孕育了极具适应性和创新性的企业,它们在提供就业、促进增长、贡献税收、推动创新、缓解社会矛盾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为驱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全面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企业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国独特的制度背景使得“中国的工业化显著有别于世界各国的特点之一就是农村工业化”[1]。企业在我国农村发展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促进了贫困地区经济增长,为贫困民众增加收入、供给资金、转变观念和获取市场优势等发挥了巨大作用[2]。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村集体经济,到改革开放初期具有集体性质的社队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兴起,再到农民工进城获取传统农村所无法提供的“工资性收入”,农业产业化背景下龙头企业发展对农村发展的整体带动作用,以及进入新时代后的农村农民创业,都体现了我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变化[3],反映了农村特殊土壤环境下企业发展与演化的历史现实。
回溯新中国70年企业扶贫的历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企业在我国农村发展中的独特贡献及其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作用。同时,对新中国70年企业扶贫取得的成果和经验进行总结,可为下一步推进企业扶贫工作提供参考。
一、新中国70年企业扶贫历程回顾
从时间和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1949年以来企业参与扶贫可分为五个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类型的企业,以适应性的方式参与到扶贫工作中,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贫困民众收入的改善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企业的间接减贫功能发挥阶段(1949~1977年)
新中国成立后,为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党和政府积极组织生产,国民经济得以快速恢复,农村和城市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发展。在城市,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重工业化成为必然,大量的工业企业建立起来,工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140亿元增长到1959年的1483亿元,再到1977年的3725亿元;工业企业数也从1957年的16.95万户增加到1977年的32.27万户,城市工业企业的发展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城市主导下的发展模式和重工业化的产业发展方式,使企业在改善民生方面的作用难以发挥。尽管城镇居民收入有所提升,但远远落后于整体经济的增长速度。在农村,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成为农村发展的主导思想,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成为这一时期农村建设的重点。基础设施的改善为农村提高生产率和农民增加收入创造了条件,农村发展的整体物质基础不断改善。
新中国成立前夕,整个国家基本上处于全面贫困的状态。党和政府通过发展生产,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尽管未能实现大部分民众的脱贫①,但为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环境,解决了机会不均等问题,为改革开放后的较长时期的快速发展积蓄了力量。企业作为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主体,尽管未能直接开展大规模的对口帮扶工作,但正是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间接地促进了民众温饱问题的缓解。企业主要通过间接的方式推动贫困和欠发达地区的脱贫,即企业创造的价值服务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为增加居民收入进而推动脱贫提供物质基础。
(二)乡镇企业为主参与下的“开发式扶贫”探索阶段(1978~1993年)
发源于农村的改革开启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征程,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得以迅速释放,民众生活水平得以大幅度提升。但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后城市尤其是东部城市的快速发展,使城乡发展差距扩大,贫困人口进一步在农村集中,这一现实情境也决定了我国扶贫工作以农村和西部为重点的基本思路。1986年我国成立了专门的扶贫机构——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1993年改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作,确立了贫困地区经济开发方针,制定了专门针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政策措施,对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实施重點扶贫开发,确定了对贫困县的扶持标准,将70%的扶贫资金用于贫困县,并核定了贫困县,分中央政府和省(自治区)两级重点扶持。在此背景下,乡镇企业发挥了创造价值、提供就业、贡献税收等方面的作用,形成了巨大的辐射效应,成为我国“开发式扶贫”的重要力量。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农民收入显著改善,农村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农村劳动力出现了富余。在集体经济的影响下,社队企业应运而生。它有效地适应了城市重工业化灵活性不足以及无法满足居民生活消费多样化需求的现实,在改革开放后快速发展。198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明确提出发展乡镇企业,但直到1997年《乡镇企业法》的颁布施行才以法律的形式明晰和理顺乡镇企业的产权关系。1978年乡镇企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不到25%,到1987年比重达52.4%;1993年乡镇企业个数发展到2452.93万个,企业职工数达到12 345.31万人,企业总产值达到32 132.32亿元[4]。乡镇企业通过解决农村就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进农民收入直接促进了农村的脱贫。1993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达到921.6元,较1978年增加了5.90倍,增速略低于同期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6.51倍),农民生活水平得以显著改善。此外,乡镇企业的发展,也为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成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先决条件。
在乡镇企业发展带来的自然扶贫功能之外,改革开放后的城市企业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对口扶贫工作,例如邯郸市对邯郸县和武安县两个贫困县开展了一些对口帮扶工作,总结了八种对口扶贫活动,分别是:城市企业与贫困乡村联合兴办生产摊点;向贫苦乡村扩散产品;组织产销联营;招收临时工、合同工和轮换工;派出技术人员到贫困乡村进行技术服务;进行技术教育和培训;提供经济、技术信息;帮助解决特殊困难[5]。为解决农村脱贫中的资金问题,金融机构也开展了对口的贷款扶贫工作,例如农业银行万县地区中心支行通过对万县烟草公司承贷扶贫贴息贷款,促进了当地烟农收入的显著提升[6]。这一阶段城市企业主要针对邻近的农村或者贫困地区,利用自身的技术、人才和资本优势开展相关的帮扶工作,属于从城市中心向外围的辐射。
这一阶段,我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突出成效。截至1993年底,尚未完全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①由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8000万人。这部分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国家重点扶持的592个贫困县,分布在中西部的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区、地方病高发区以及水库区,而且多为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地区的共同特征是:地域偏远,交通不便,生态失调,经济发展缓慢,文化教育落后,人畜饮水困难,生产生活条件极为恶劣。
(三)企业的有效支持与参与下的开发式扶贫阶段(1994~2010年)
针对上一阶段扶贫工作遗留下来的现实难题,1994年3月,国务院发布“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它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目标、明确对象、明确措施和明确期限的扶贫开发行动纲领,标志着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进入了攻坚阶段。扶贫工作转向以贫困县为重点对象,以开发式扶贫为重点,辅之以劳务输出和易地搬迁扶贫的整体扶贫思路。进入21世纪,“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目标基本实现。为进一步巩固扶贫成果,2001年国家制定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扶贫工作进入巩固扶贫成果、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综合开发阶段,贫困人口集中的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和特困地区成为扶贫开发的重点。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后,东西部对口帮扶不断深化,东部企业的对口帮扶成为支持西部贫困地区发展的重要抓手。在此阶段,企业以其灵活性和适应性在政府主导的开发式扶贫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和发达城市吸附了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不仅改变了农民的收入结构,而且为推动农村从封闭状态向开放状态转型创造了条件。
在“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一严格的户籍管制背景下,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农业富余劳动力在农村内部产业转化的结果[7],这是一种封闭式的内生发展方式。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国家逐步放开了对农民进城的限制②,沿海发达企业和大城市极具优势的收入溢价吸引了大量农民进城,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得以形成[8]。农民工的进城,是农村劳动力再调整和优化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促进了农民从“土地依赖”向“能力依赖”的转型。与之相对应的是,企业在城市和东部地区的集聚,吸引了农民涌入城市,在获得收入溢价的同时推动了城镇化的加速。就从事农业的人口和农民的收入构成而言,1996年末从事农业的人口数为42 441.19万人,到2016年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减少至31 422万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截至2006年末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达13 181万人③,大量涌向城市的农民工就业群体改变了我国传统的城乡分割的“稳态”。从收入构成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资性收入开始成为农户收入特别是现金收入的主体部分,1990年工资性收入占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重仅为20.22%,到2003年已增长到35.02%,并保持持续的增长态势①。尽管受制于封闭式的内生发展方式以及产权不明晰、经营管理粗放等一系列问题的限制,乡镇企业趋于衰落,但产权更清晰、更具活力与效率的民营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快速发展。农民工进城大潮热情不减,这本质上是我国农村与现代市场经济更紧密交汇的新方式,是我国农民嵌于城市企业发展的一条路径,是我国市场化、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利用自身的资本优势,不仅实现了自身的成长和利润目标,而且为解决就业、增加收入、缴纳税收创造了途径,进而促进了我国社会整体贫困问题的解决。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形成了有效的知识积累效应,且农民的进城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尤其是中小城镇的发展。
与此同时,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需要也催生了以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代表的农业产业化发展[9],它是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有效补充和完善。一方面,龙头企业以其规模、资本、市场、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成为联系农民、合作社与市场的重要纽带,为农民增加收入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尽管对于龙头企业与合作社在农民进入市场过程中是否是一种公平的合作关系存在争论[10],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对我国“三农”问题现代化的一种探讨,新型农村组织的发展带动了一大批农民先富起来,有效地解决了大批农民工进城后的土地耕种问题,也为农民进入市场积累了经验和知识,为农民更加广泛地参与市场创造了条件。农业产业化开发扶贫有助于贫困地区的农业与市场对接,改善基础设施,促进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有效改善[11],有利于农村地区的脱贫。
在“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这一系统扶贫框架下,区域对口帮扶作为推动西部贫困地区脱贫的重要工具,在西部大开放战略提出后得到进一步深化,这既是对“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进一步延续,又是21世纪重点做好西部贫困地区脱贫的重要战略部署。企业的发展对于帮助西部贫困地区打破贫困恶性循环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12],到2010年,按低收入贫困线衡量的农村贫困人口为 2688 万人,貧困发生率为2.8%,我国基本上解决了困扰农村几千年的温饱问题,“底线”脱贫目标基本实现。
(四)政策激励下企业参与的大规模精准扶贫阶段(2011~2016年)
解决基本温饱问题这一“底线”目标与共同富裕的目标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为此,201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通过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国际合作等多种方式,推动我国农村贫困地区脱贫。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这一概念。2014年5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由此在全国范围内拉开了精准扶贫工作的序幕。在此指导下,我国开展了“精准扶贫行动”,对贫困地区加大了基础设施投资、资金支持、人才支持等。进入这一阶段,扶贫开发已经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截至2018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1660万人,累计减少8239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10.2%下降到2018年的1.7%①。在精准扶贫工作开展过程中,我国立足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现实,从政府主导的精准扶贫工作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模式转变。企业作为对口帮扶的重要实施载体,在推动精准扶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承担重要社会使命的国有企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指引下,积极参与扶贫工作并取得了卓越的成效。《中国企业扶贫研究报告(2018)》显示,在参与定点扶贫的300多家中央单位中,中央企业占了近1/3。中央企业结对帮扶的246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占全国592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41.6%,分布于全国21个省(区、市)。此外,中央企业还对口支援西藏自治区21个县和青海省藏区16个县。据不完全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企业投入定点扶贫资金超过了75亿元。国资委聚合中央企业扶贫力量,设立了“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东达到104家,两期募集资金规模达到154亿元。财政部、国家开發投资公司和中国烟草总公司共同发起“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基金”,基金总规模达到182亿元,吸引社会资本超过1000亿元[13]。
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也在精准扶贫战略的指导下积极投入资金、人才、技术等参与扶贫工作。1995年开始的“光彩事业”是联系民营企业参与中西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平台,成为PPP模式促进贫困地区发展的典范[14]。仅2010~2014年,全国共实施光彩项目39 559个,公益捐赠427亿元,培训463万人,安排就业654万人,带动脱贫826万人[15]。2015年10月,全国工商联、国务院扶贫办、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等联合启动了“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至今已有6万多家民营企业参与其中。截至2018年6月底,进入“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台账管理的民营企业达5.54万家,精准帮扶6.28万个村(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村3.99万个),帮助755.98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产业投入597.52亿元,公益投入115.65亿元,安置就业54.92万人,技能培训58.31万人[16]。
这一阶段,企业从间接提供就业、增加收入、促进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发展到直接参与到扶贫工作中,甚至是主导部分地区和贫困民众的脱贫工作。这既是对中央相关战略的回应,又是企业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履行社会责任和创造社会价值的主动选择。但是,企业依然是外生于农村发展系统的,企业与贫困农村发展之间仍存在不可避免的价值和目标冲突。
(五)新时代农村企业内生发展参与乡村振兴阶段(2017年至今)
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出“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2018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激励各类企业、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战。2019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大力扶持贫困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这是新时代对扶贫工作的新要求,也凸显了当前企业在参与扶贫工作中的新变化。这一阶段,企业扶贫凸显了企业价值与扶贫工作的有机融合,企业扶贫项目和农村创业成为促进农村脱贫的内生驱动力量。
经过改革开放后较长时期的高速发展,我国的市场结构已发生较大的变化,农村市场尚存在较大的成长潜力,这为企业市场转移、开辟蓝海市场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外部资本的进入开辟了企业支持农村发展的新局面。大量企业在农村布局,利用农村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缺口以及有待开发的市场优势和资源优势,形成了对农村发展的有效渗透,这不仅有利于农村整体基础设施的改善,而且有利于农民收入的提升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在这一阶段,企业在扶贫时往往倾向于与企业本身的战略和发展目标相匹配的投资,在履行相关社会责任的同时实现企业自身价值的提升。
大企业所具有的规模优势有效地解决了农村发展的效率问题,但在解决农村发展的异质性和精细化方面还有待提升。随着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农村市场的交易成本有所下降,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则为农村孕育的创业机会提供了“破土萌发”的机会,在“双创”政策的支持下,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商业模式成为“双创”背景下农民创业的重要选择[17]。在此背景下,农村市场从大企业主导、农民参与的模式朝着农民内生驱动的主导模式转型,企业真正成为农村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截至2018年,各类返乡下乡创新创业人员累计达780万人,“田秀才”“土专家”“乡创客”等本乡创新创业人员达3100多万人。农民创业领域不断拓宽,由种养向纵向延伸、横向拓展,创办的实体87%在乡镇以下,80%以上发展产业融合项目。农村创业载体不断增多,认定农村创新创业园区和实训孵化基地1096个,益农信息社覆盖1/3以上的行政村。农民自主创业改变了农村发展中企业外生和封闭式内生发展的状况,企业真正成为农村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这为从根本上推动我国农村的市场化、改变农村经济社会相对落后的面貌提供了新的路径,也为未来乡村振兴的推进提供了新的路径。
二、新中国70年企业扶贫的主要成就与经验
70年来,我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一成绩的取得,源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政府的强力推动和社会的积极参与。企业在扶贫工作中扮演着联结者、促发者和行动者的角色,有力地推动了贫困地区的脱贫和持续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延续的发展路径。
(一)企业扶贫是我国扶贫系统的重要方式
从扶贫的方式来看,西方的扶贫主要依靠二次分配来实现,并重视工会、社团以及各种慈善基金会的力量,企业更多地被视为纯粹的经济主体和纳税主体,企业扶贫主要体现在近年来兴盛起来的社会企业,这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理念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与西方不同,我国的扶贫表现出政府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模式,企业在扶贫工作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西方企业一般靠贸易发展壮大,且在城市集聚,我国的企业发展则与之不同。一方面,改革开放前集中在城市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企业被纳入国民经济计划体系,一部分在改革开放后得以快速发展成长为当前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大型企业,另一部分则衰落消失在历史进程中,同时城市优势的发挥导致改革开放后孕育出一大批个体和私营企业;另一方面,我国农民的创新和冒险精神在改革开放后得以释放,乡镇企业和个体户成为农民摆脱贫困桎梏的自然选择,早期是为了改善自身的生活状况,先天具有扶贫的自然属性,在改制和成长过程中向城市迈进并融入其中,成为民营经济的重要力量。城市企业和农村企业“双轨道”的发展模式,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来源,在此过程中也间接地促进了农村的发展,对于贫困地区和国家脱贫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对于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不同属性企业在参与扶贫过程中的角色来看,它们也表现出鲜明的差异。我国的国有企业不仅需要实现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目标,而且具有重要的社会使命,参与扶贫工作、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国有企业的重要责任,也是其维护品牌形象、促进企业价值提升的重要方式。民营企业作为私营部门的核心力量参与社会扶贫工作中,是企业发挥其信息优势、效益优势和效率优势的结果[18]。我国企业参与扶贫工作,不仅是对企业使命、价值的再定义,而且是对减贫、扶贫工作的重要创新,是我国扶贫系统的重要内容,也具有重要的推广和借鉴意义。
(二)企业扶贫是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企业在扶贫工作中的有效参与,不仅增加了贫困地区民众的收入,而且以经济手段改变着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乡村面貌,推动了农村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变迁,促进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具体来看,企业扶贫中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为农民增收创造了新的机会,改善了农村经济落后的面貌,不断形塑农民对市场的认知,促进了贫困状态的“跃迁”,企业在农村的发展从另一条路径上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并加速了农村的市场经济进程。从新中国成立以来GDP中工业增加值和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变化情况来看(见图1,下页),前者从1952年的119.6亿元(占GDP的17.61%)增加到2018年的3.05万亿元(占GDP的33.90%);而后者则在GDP中的比重从50.94%下降到7.50%①,工业和农业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发生了逆转。与此同时,企业在扶贫的过程中改变了城乡分离的发展路径,促进了城乡的融合,加速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进程。1978年之前,城镇年均增加人口保持在500万人以内,1979~1995年,城镇年均增加人口保持在1000万人左右,1996年之后则保持年均增加人口超过2000万人的规模,这一数据与实施开发式扶贫后年均脱贫人口数据较为接近。
(三)企业扶贫是价值驱动和政策推动双重力量的结果
无论是在改革开放前的间接式扶贫,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的社队和乡镇企业阶段,还是农民进城的城市企业发展阶段,抑或当前的“大众创业”阶段,企业的核心目标都是创造收入和获取利润,这是企业本质属性所决定的。这一目标与扶贫的核心功能目标是一致的,正是因为核心目标的一致性,企业才具有了与贫困民众一道发展的可能性。企业扶贫表现出强烈的自主性特征,且从实证检验来看,融入国家扶贫開发政策有利于提升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尤其对于规模小、年限长的企业和国有企业更为有利[19]。发源于我国农村的乡镇企业,其本身是农民为摆脱自身贫困状态融入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缝隙”的一种短期之举,其直接目的是增加收入,但由于其能够直接有效地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以及快速获取收益,因而实现了自身的富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进入农村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提升在农产品和农资产品市场中的控制力,但在此过程中带动了当地农业的发展,直接改善了农村的生产方式和农民的生活水平;以乡村旅游为主的文化企业进入农村,本身是为了利用农村特有的自然风光和资源,但乡村旅游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农民的参与[20],增进了农民的收入,成为促进农村发展的重要方式;以大量房地产公司为代表的企业参与易地搬迁扶贫,这不仅与其自身的产业布局和核心优势高度协同,而且有效地解决了自然条件恶劣的贫困地区的脱贫问题;“双创”背景下的农民创业和农村创业,本质上是农民利用本地资源优势的过程,但这个过程中形成强大的辐射和带动效应,使其成为脱贫的重要工具。总体来看,企业参与扶贫首先是价值驱动,其有效地驱动了企业自主参与到扶贫工作中。
企业扶贫除了直接的经济动机之外,还体现出强烈的责任动机和情感动机。一大批企业主和其背后的企业从农村地区走出去并快速成长起来,这些企业会将资本从城市向农村地区转移,表现出本地化投资的倾向。尽管从动机来看,本地化的投资更有利于维护其与当地政府的良好关系,获取信贷支持、税收优惠、政府救助等,但其中也蕴含着这些企业主对“生于斯长于斯”故土的眷念[21],且表现出对农村地区市场发育滞后的巨大促动,积极发挥关键作用、示范作用和带动作用[22],在形式上表现出强烈的“关系化”倾向。他们很多成为农村贫困地区获取经济起飞的“带头人”,为农村发展提供有效的资本支持以及商业知识支持,促进农村落后地区观念脱贫、经济脱贫、能力脱贫和全面脱贫,并为乡村振兴创造条件。
与此同时,企业扶贫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政策激励特征。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就意识到农村企业家精神对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注重给予农村充分的自由度,从“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到西部大开发战略,再到《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都有对口帮扶、企业帮扶、产业扶贫、多方参与、企业承担等方面的倡议和要求,并对于参与扶贫的企业提供了相关的优惠政策和支持,成为推动企业参与扶贫工作的重要驱动力量。
(四)企业扶贫表现出多元的方式与路径
有观点认为,企业扶贫主要应当通过慈善捐助的行为来实现[23],这更多是出于对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和防范企业权利扩散的考虑。从我国的现实来看,企业扶贫表现出多元化的模式,从慈善捐助到产业投资再到价值投资,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扶贫方式。
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民众和企业主主要采用直接捐助的方式履行企业和个人的社会责任[24],且主要集中在灾难捐款、对贫困落后地区的教育援助、医疗和生活资助等。根据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2016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2016年全年接收国内外款物捐赠共计1392.94亿元,其中教育、医疗健康、扶贫与发展分别占捐赠总量的30.44%、26.05%和21.01%,企业捐赠总额达到908.20亿元,占捐赠总额的65.20%,其中民营企业贡献近50%。与此同时,企业直接参与农村贫困地区脱贫也表现出多元化的方式:一是产业投资,例如农业企业、乡村旅游企业等,利用农村的资源禀赋直接进行产业投资,既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又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农村的发展;二是价值投资,例如随着农村基础设施条件的不断改善,农村出现了新的发展机会,投资农村可获取收益;三是责任投资,这类企业往往是一些从农村地区走出去并快速成长起来的企业,企业主对故土有“生于斯长于斯”的眷念,通常表现出关系投资的倾向。
三、我国企业扶贫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一)对企业扶贫合理性的认知有待进一步深化
从我国企业开展扶贫的实践来看,企业一方面是自发地利用已有的资源和能力支持贫困地区和民众的发展,表现出一种自觉性的行为,另一方面是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参与一些扶贫工作,表现出一种外推式的行为。无论是自觉性的行为还是外推式的行为,企业在扶贫过程中都面临合理性的问题[25]:企业扶贫的价值何在?企业扶贫是否是一种道德的行为?是否能够实现帕累托改进?扶贫是否是企业的本职工作和应尽的义务?企业扶贫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企业扶贫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这一系列问题是困扰企业扶贫工作进一步开展的重要问题。现实中,企业扶贫的价值得到了普遍认可,其在扶贫的有效性尤其是可持续性方面得到广泛的认可,但对于企业是应该去扶贫及其是否偏离企业本质目标方面亦存在较大的争论。广泛接受的一个观点是,企业扶贫应该更多是一个参与者而非主导者的角色,扶贫工作應该与企业的经营工作有机协同,在实现自身经济目标的同时实现其社会目标,且社会目标的实现应该进一步强化其经济目标,例如有利于品牌建设、营造良好的社区关系和公共关系,甚至是获取供应商等合作伙伴的价值认同。这一观点实际上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即企业在实现经济目标的同时实现与利益相关方目标的协同。
此外,企业扶贫在现实中出现一些失当的行为,引发各界对企业扶贫合理性的质疑。闫东东、付华的研究发现,龙头企业的行为偏离了政府扶贫的初衷,它们存在“利用政府的扶贫资金、低利率贷款政策或是税收优惠等政策,为其进行扶贫之外的经营活动”的问题[26]。现实中企业扶贫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对企业扶贫合理性和有效性的担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未来参与扶贫和乡村振兴的积极性。
(二)需要稳妥处理好企业“给”和农民“参与”的问题
扶贫的可持续性根本在于能否激发贫困民众脱贫的内在意愿。在企业扶贫过程中,企业在资本、人才、技术、市场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这种优势是企业开展扶贫工作的基本条件,但也容易形成企业在扶贫过程中的主导性思维和支配性地位,导致贫困民众在企业的扶贫过程中丧失主体地位,进而导致企业扶贫效果大打折扣。从当前企业扶贫的实践来看,为保证短期内扶贫工作的效率,往往高规格地配备驻村干部、扶贫专职负责人,这对于充分调动企业内部资源和获取政府的相关投入十分重要。但是,扶贫工作的发起者和主导者依然是企业,企业往往从自身诉求出发,满足当地政府和上级政府的脱贫目标,但这往往是眼前和短期的脱贫,或者说是从平均水平上实现了脱贫,贫困民众的真实诉求往往难以得到满足甚至被“粉饰”,精准扶贫的真正目的难以实现,脱贫后返贫的风险较高。
(三)企业扶贫的拓展性和可复制性较差
尽管政府对于企业扶贫的倡议和号召力度较大,但企业扶贫更多地是作为一种“自然涌现”的现象,其可复制性较差,且现有企业在扶贫工作的进一步拓展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困难。一方面,扶贫从本质上应该属于政府的责任,以企业为代表的社会主体参与扶贫工作的合理性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对于未参与扶贫的企业来说,不可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迫”其参与。采用激励性和诱导性的方式鼓励和引导企业参与扶贫,又可能面临监管难度大、评价成本高、绩效风险高等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受制于当前整体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企业普遍面临较为严峻的生存压力,企业用于扶贫的资源投入受到较大的限制,企业进一步加大扶贫投入的积极性不高。
四、企业参与扶贫的推进策略
针对企业扶贫存在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对贫穷和企业本质的认识,明确政府在支持企业扶贫中的服务地位并提升服务质量,引导企业更好地参与扶贫工作。
(一)深化对贫穷和企业本质的认识,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促进企业参与扶贫
贫困本质上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匮乏,而且表现为机会的不均等、能力的劣势等,扶贫不仅仅是经济扶贫,更重要的是创造公平的环境和对贫困民众能力提高的支持,激发贫困民众的内生动力。作为市场竞争的产物,企业的本质是高效率地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企业是能力集合和成长的重要主体,对于扶贫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这是企业扶贫合理性的核心之所在。但与此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扶贫工作仅仅是企业的一项附属工作,不能对企业的核心经营业务造成冲击,这是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需要充分认识到的问题。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不仅要做好扶贫工作,而且要服务好企业,杜绝为实现扶贫目标而向企业“摊派”扶贫任务的行为。
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认识和支持企业参与到扶贫工作中。同时,对于企业在扶贫工作中的一些探索性行为予以包容,例如给予介于交易型投资和慈善捐助之间的“关系投资”以成长的空间,支持企业通过“关系投资”来帮助农村贫困地区实现理念脱贫、经济脱贫、能力脱贫和全面脱贫,既要认识到其合理性,又要接纳其局限性,为这类行为的涌现培育良好的发育和成长土壤,尤其是为企业成长和企业家成长提供良好的土壤。
(二)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为企业扶贫提供相关支持
政府需要增强服务意识,为企业参与扶贫提供相关支持,这既有利于激发企业参与扶贫的积极性,又有利于企业发挥其专长高效率地开展扶贫工作。
第一,着力创新农村资本供给,解决贫困地区农村发展的“资本门槛”。优化农村金融供给,进一步壮大农村发展基金,既要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又要加大对农村产业发展的投资;创新农村发展融资方式,鼓励属地大企业牵头中小微企业、外部投资方等组建农村投资主体,以不断壮大的民间资本供给补充农村发展资金的限制;设立农村投资的“缓冲机制”和“缓冲域”,对农村投资计提较高的坏账准备金,更加注重农村投资的社会效益,防范农村投资的短期化倾向。
第二,优化精准扶贫人才队伍,解决贫困地区农村发展的“知识门槛”。优化农村对口扶贫的人员结构,重点是增加懂产业、懂经营、懂资本、懂市场、懂技术的专业人员,并鼓励其与属地企业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合作,共同指导和帮助贫困民众;创新扶贫人员考核和晋升机制,鼓励扶贫人员在基层工作,并给予更多、更优的晋升机会,允许其参股农村企业;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鼓励其带动身边民众共同创业,在农村形成良好的创业氛围;加强农村创业和知识培训,鼓励大企业为配套企业提供管理及技术培训,由政府提供相关的资源支持。
第三,完善农村企业服务体系,降低农村创业和经营的“制度门槛”。在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进一步完善企业服务体系,简化农村企业注册、变更等相关手续,设立“巡回”服务机制,定期为农村企业提供相关的服务;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农村企业服务体系,由政府采购并支付相关费用;探索农村企业服务体系的远程操作和移动互联网模式,以适应互联网时代下的技术经济环境。
(三)强化企业扶贫工作重点,突出产业扶贫和教育扶贫
企业在扶贫工作中,应该将重点集中在产业扶贫上,利用产业扶贫,帮助贫困地区挖掘资源优势,实现资源向产品进而向资本的转化,促进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这是世界各国扶贫工作中总结的重要经验之一。企业既要发挥在经济活动中带头人的角色,为贫困民众树立脱贫致富的信心,又要考虑扶贫工作的可持续性和长远性,补足政府在基础教育投入之外的教育投入不足和精准性不足,支持职业教育发展,将企业作为知识管理和创造的平台,创造和扩散市场知识,真正帮助贫困民众融入现代市场经济体系。
参考文献
[1]李风华.中国农村工业的起源:基于制度的视角[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4):25-33.
[2]赵昌文,郭晓鸣.贫困地区扶贫模式:比较与选择[J].中国农村观察,2000(6):65-71.
[3]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课题组.改革开放40年中国工农关系演变:从缓和走向融合[J].改革, 2018(10):41-53.
[4]农业部乡镇企业局组.中国乡镇企业统计资料:1978~2002年[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3:3-11.
[5]佚名.邯郸发挥城市企业优势开展城乡对口扶贫[J].江西老区建设,1987(10):23.
[6]吴甫.企业承贷扶贫效果显著[J].四川金融,1988(9):42.
[7]张晓山,韩俊,魏后凯,等.改革开放40年与农业农村经济发展[J].经济学动态,2018(12):4-16.
[8]魏后凯,刘长全.中国农村改革的基本脉络、经验与展望[J].中国农村经济,2019(2):1-17.
[9]孔祥智,刘同山.论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历史、挑战与选择[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4):78-133.
[10]张晓山.理想与现实的碰撞:《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修订引发的思考[J].求索,2017(8):16-24.
[11]王兴国,王新志.农业龙头企业扶贫的理论阐释与案例剖析[J].东岳论丛,2017(1):82-88.
[12]和丕禪,郭红东,许莹,等.企业对口扶贫模式比较与政策建议[J].浙江学刊,2001(2):84-86.
[13]王翔.央企精准扶贫备忘录[J].中国报道,2018(10):30-31.
[14]郭沛源,于永达.公私合作实践企业社会责任——以中国光彩事业扶贫项目为案例[J].管理世界,2006(4):41-47.
[15]苏琳.中国光彩事业五年发展纪实:以义行善以利惠民[N].经济日报,2015-10-19.
[16]钟宏武,汪杰,黄晓娟,等.中国企业扶贫研究报告(2018)[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8:3-5.
[17]張亮,李亚军.就近就业、带动脱贫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环境[J].改革,2017(6):68-76.
[18]田雄,刘丹.泥淖之上科层之下:产业扶贫中乡土企业与基层政府的关系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68-78.
[19]王书斌.国家扶贫开发政策对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溢出效应吗?[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3):21-38.
[20]刘楝子.乡村振兴战略的全域旅游:一个分析框架[J].改革,2017(12):80-92.
[21]周大鸣.农民企业家的文化社会学分析[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2):32-37.
[22]张红宇.乡村振兴战略与企业家责任[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13-17.
[23]宋征,贾燕.我国可持续发展进程中企业扶贫状况及对策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1):212-214.
[24]张强,韩莹莹.中国慈善捐赠的现状与发展路径——基于中国慈善捐助报告的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5(5):82-86.
[25]SUCHMAN M C. Managing legitimacy: 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5, 20(3): 571-610.
[26]闫东东,付华.龙头企业参与产业扶贫的进化博弈分析[J].农村经济,2015(2):82-85.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planned economy, enterprises naturally improved the poverty situation of the people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China’s economic recovery, manifested as an indirect wa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accumulated strength for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With the deepe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starting with the social team enterprises and township enterprises, taking the increasingly active rural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as the tre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enterprise initiative and policies, enterprises have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increase of farmers’ incom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agriculture in a diversified way, which has become a driving force for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We should objectively understand the role of enterprise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strengthen the government’s public service capacity to provide support for enterprises’ poverty alleviation; strengthen the focus of enterprises’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and highlight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edu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Key words: poverty alleviation by enterprise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