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回家之前
帕姆·穆尼奥兹·瑞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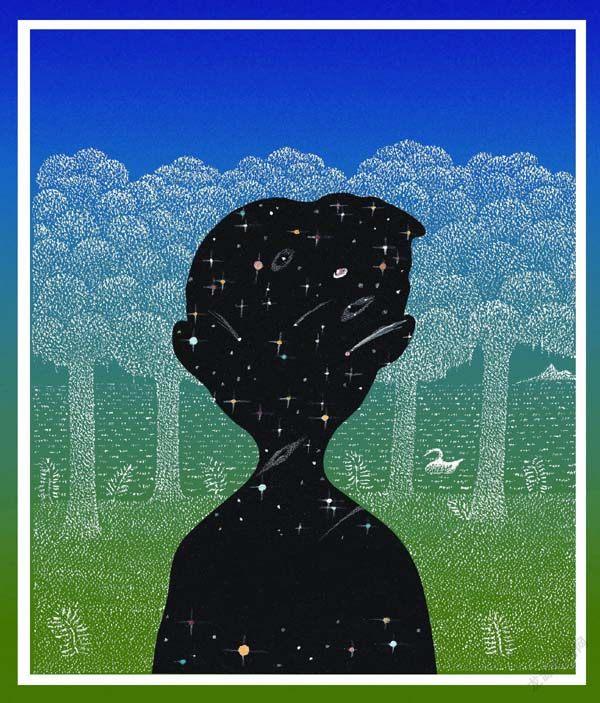
数日的大雨演变成了数周的大雨,无间歇的降雨让所有人都被困在家中,泥泞的路面也令所有货车对街道望而却步。
结果,因为大雨,舅舅奥兰多无法去自己的办公室,只好来到内夫塔利家,在他们的餐桌上忙着写新闻稿件。
舅舅奥兰多是母亲的弟弟,除了比母亲高一些,他简直与母亲长得一模一样,他们有着同样宽阔的面庞和幼犬般惹人怜爱的眼睛。内夫塔利很喜欢看舅舅工作,于是他在舅舅身旁也摆好工作的架势,模仿着舅舅的一举一动。
当舅舅奥兰多写东西时,内夫塔利就抄写书上的词。当舅舅奥兰多用字典查找一个词语时,内夫塔利也跟着做。当舅舅奥兰多把铅笔别在耳后,站起身来回踱步时,内夫塔利也尾随着他的步调前前后后地走。如同不懂放弃的滂沱大雨那样,内夫塔利也丝毫不放弃。
在舅舅奥兰多来家里的第四个午后,劳丽塔在厨房的地板上玩自己的娃娃,鲁道夫一边写作业一边哼着歌,母亲则在为晚餐准备土豆卷饼。坐在餐桌一端的舅舅奥兰多在书堆和报纸堆间埋头写东西。内夫塔利站在舅舅身旁,身体倾斜着越来越靠近舅舅。
“外甥,我不确定这张椅子够我们两个人一起坐,除非你坐在我的腿上。你真的打算看着我写完每个句子吗?”舅舅奥兰多问道。
内夫塔利将手指放在舅舅奥兰多的纸稿上:“那个词是什么?”
“是马普切人。他们是阿劳卡尼亚的原住民,是我们的邻居。”
内夫塔利飞快地拿起了自己的那张纸,抄写上“马普切人”这个词。
“如果你繼续这样模仿下去,恐怕有一天我得让你做我的工作搭档啊。”
内夫塔利微笑着,拼命地点头。
“好吧,既然你想要协助我的工作,那我需要你调整一下你那恼人的呼吸声!”舅舅奥兰多伸过手将内夫塔利一把抱起来,让他坐在自己的腿上,挠他的痒痒,和他嬉闹着扭斗。不一会儿,舅甥俩就在地板上滚成一团了。
鲁道夫也跳起来,向他们扑过去。
在他们三人危险地迫近自己的玩具娃娃时,劳丽塔尖叫起来。
他们三人立即大笑起来,翻滚着分开了。
母亲站着,将双手插在后裤兜里。“看来,在阴沉的雨天,我们都需要些消遣来转移一下注意力。”她说,“我们不要再待在这个房间里了,走,去大客厅,我给你们读故事听。”
“但——但——但是我们不——不——不被允许进入大客厅。”内夫塔利提醒她。
母亲微笑着,挑起了眉毛。“今天都允许。”
当母亲和舅舅奥兰多在做热可可时,内夫塔利、劳丽塔,甚至还有鲁道夫都回房间去拿薄毯子,兄妹三人咯咯笑起来。
这会儿,大家都盖着温暖的薄毯子,舒适惬意地依偎在一起,喝着热饮。母亲挑选了一本书,清了清嗓子,便读起来,这个故事把每个人都带进了一个住着精灵和公主的国度。
当故事结束时,劳丽塔掀开自己的毯子,蹦起来,跳着转圈圈,“我是公主!我是公主!”
“可你看起来不像是一位公主呀。”鲁道夫取笑道。
“的确,她看起来确实不像。我们能做点什么来改变一下吗?”舅舅奥兰多看着母亲说道。
母亲微笑着从椅子上起身,在那个由黄铜配制并有橡木装饰的巨大行李箱前跪了下来。
他们当中没有人见过箱子里都有什么。内夫塔利看着耸肩又微笑的鲁道夫。劳丽塔双手捂着嘴巴,屏息凝神期待着。
母亲抬起了笨重又弯曲的盖子。
衣服的霉味和雪松的味道吸引着内夫塔利凑上前去。
母亲拿出了一摞叠起来的裙子和一件羊毛外套,然后把一顶皮帽子递给了内夫塔利。在箱子的更底层,母亲找到了一件蕾丝衬裙和一条薄披肩。劳丽塔立刻拿来衬裙,套在自己身上。在劳丽塔旋转着绕圈时,母亲又拿出了一把吉他。舅舅奥兰多设法修复这把吉他,他拧紧琴弦,开始调音。
母亲又找到了一顶大礼帽,把它拿给了鲁道夫。
在母亲为劳丽塔系上披肩的空当,内夫塔利来到巨大的行李箱旁,仔细地打量着箱子。在箱底,他看见一捆用缎带绑起来的书信和明信片。这些书信和明信片里该保存着多少词语呢?
他探身向前,向下伸出手,抓住了那一捆……他居然头朝下摔进去了!
母亲转身喊道:“内夫塔利!”
“我在这里。”他那混合不清的声音从箱子底部传来。
等到舅舅奥兰多过来把他扶起来,安放在沙发上的,内夫塔利手里仍旧握着那捆书信。每一封信都从信封的顶部被打开过,所有的勒口处仍有蜡封,并且有一个心形的印记。最上面的一封信上,不知是谁在蜡封处写下了“爱”这个字。

母亲从他手上拿走这一捆书信,重新放回到箱子里,并小心翼翼地合上了箱子。“内夫塔利,行李箱盖很可能会砸到你的头或手。你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就为了一捆我们或许都不认识的亲戚寄来的破旧的书信和明信片?答应我,永远都不要再打开这个箱子!”
内夫塔利依依不舍地看着箱子说:“我发——发——发誓。”
舅舅奥兰多漫不经心地弹起了吉他。“内夫塔利,来,站到我身边。作为我的搭档,你认为我们接下来应该做些什么呢?”
内夫塔利抬起头,“唱一首歌——歌——歌?”
“这正是我的想法,”舅舅奥兰多说,他的一条腿倚靠在椅子上,吉他就放在他的膝盖上,“鲁道夫,不知道我们是否有这个荣幸听到你的歌声呢?这个家里没有人拥有你那样的歌喉。” 话音刚落,琴声就响起来了。
鲁道夫犹豫地看向母亲,又看向舅舅,似乎在寻求鼓励。
“你爸爸不在这里,鲁道夫。就当这是你帮我的一个忙。”
鲁道夫又看向母亲。
她点了点头。
内夫塔利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希望鲁道夫可以用他最高亢的声音来歌唱。他兴奋地拍着手叫道:“没——没——没错!”
鲁道夫笑了笑,戴上了那顶大礼帽。他唱了起来,先是轻柔地吟唱,“让我们用盛满喜悦与美好的酒杯畅饮……”
忽然,他停下来,望向每一个人,好像在确定什么。
舅舅奥兰多最先点头示意。“继续,我知道这首歌,它选自歌剧《茶花女》。唱得再大声些,节奏再快些。这是一首蕴含伟大精神的歌。”舅舅奥兰多再一次弹起了起始的和弦。
鲁道夫再一次展开歌喉。
母亲和劳丽塔跳起舞来。
内夫塔利也站了起来,一只脚轻踏着,双手打着节拍。
劳丽塔和母亲跳着华尔兹,她们越跳越快,两个人都笑了起来。
内夫塔利无法将自己的眼睛从鲁道夫脸上移开,因为鲁道夫的脸上已经找不到一丝生气和闷闷不乐的踪影。他的歌声是那么浑厚、丰盈,是实打实的歌剧腔。
鲁道夫展开雙臂高唱着,他的高音圆润纯厚,是那样动听,以至于内夫塔利的眼睛里盛满了感动的泪水。
舅舅奥兰多用了几组响亮的和弦来为鲁道夫的最后一个长音伴奏,也以此结束了整首歌。
鲁道夫摘下大礼帽致谢,随即又抛出礼帽,丢出一个完美的弧形。当鲁道夫在鞠躬谢幕时,母亲和妹妹劳丽塔都冲上前去,抱住了他。
“太——太——太精彩了!”内夫塔利呐喊道。
内夫塔利已回想不起是否他曾见过鲁道夫或者劳丽塔如此地开心,又或者上一次听到母亲开怀大笑是什么时候。他也跑到家人身旁,用双臂紧紧地环绕住他们,期望此刻盛大的欣喜能够持续到永远。
可惜这一切结束得太快,忽然母亲整个人僵住了,她举起一只手示意大家保持安静,然后把头倾向了一侧。
没有人发出一丁点声响,因为大家都想听出,母亲到底听到了什么。原来如此,是一阵微弱的火车汽笛声。尽管每天有数不清的火车从特木科小镇经过,但母亲总能知道哪一声汽笛来自父亲的火车。她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了。
内夫塔利无精打采地望着鲁道夫的脸。
“别担心,”母亲说道,“火车还没离我们那么近。现在,快……”
大家都仓促地行动起来。
鲁道夫和舅舅奥兰多重新摆好了行李箱里的一切。劳丽塔冲过去收拾所有的杯子和杯碟,但她的手抖得太厉害了,以至于一个杯子掉在地板上打碎了。劳丽塔开始哭起来。
内夫塔利跑到她身边。“没关系,劳丽塔。你拿——拿——拿着毯子先回卧室吧。让我来整理这些碎片。”
“可——可是……”劳丽塔睁大了泪眼,抽泣着说道。
“如果父亲发现了,我会说是我不小心碰掉的。”内夫塔利说。
劳丽塔用胳膊擦掉自己的眼泪,朝内夫塔利露出一个甜甜的笑容,便去收拾所有的毯子了。
与此同时,母亲在一项又一项的准备中忙碌着:从厨房拿回餐厅里的桌布,从橱柜里取回本应在餐桌上的烛台。她仔细谨慎又不失章法地叠好餐巾,摆放好玻璃杯和餐盘。这期间,她没有讲过一句话。
当内夫塔利清理好杯子和杯碟后,他跑过去帮助鲁道夫和舅舅奥兰多把多余的椅子挪回餐桌旁。他已经开始忧虑所有可能会跟他对视并问他问题的大人。
“有多——多——多——多少把椅子?”
母亲头也不抬地回答道:“至少有十二把。如果你父亲没有带回那么多客人,他也会把街上的陌生人请来填满每一个空位。梳一下你的头发,还有洗洗手。我得去热一下肉饼和牛排了。”
想到牛排配着洋葱还有土豆卷饼,内夫塔利已经止不住地流口水了。他希望这些美食可以填满那种空虚感——当他听到火车汽笛声时,将他淹没的空虚感。那是一种让内夫塔利觉得突然间失去了什么的感觉。
他看着母亲转身走进厨房,脸带愁容,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她的笑声、闪烁着光芒的眼睛,还有绯红的脸颊都去哪里了呢?母亲将它们都埋藏到哪里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