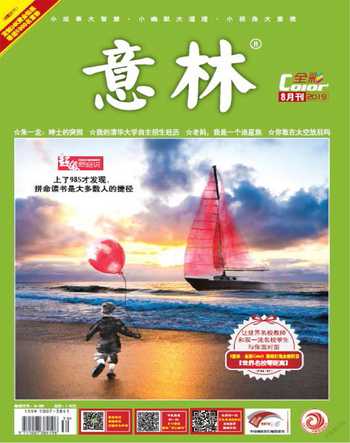落红有情
闫晗
87版电视剧《红楼梦》黛玉葬花那一段,黛玉用花帚扫起来的大部分是整朵的花,带着花蕊,花瓣齐整——落在地上的难道不应该是一瓣瓣琐细纤薄的花瓣吗?那些桃李海棠,总还要结果子的,怎么会整朵花都脱落枝头?纵使来了一阵风雨,让绿肥红瘦,也不该如此彻底。想必是节目组为了让葬的花更有辨识度,放入整朵的桃花,方便观众看个清楚。把花装到布袋子里再埋到土里,“质本洁来还洁去”,是行为艺术,林黛玉因为这场著名的行为艺术而拥有了诗意,袒露了心扉,给读者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花朵最好的归宿是什么呢?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大自然本身有合理的循环机制。凋谢也是有美感的,临水的樱花和海棠景观总是更有风味。落下的花瓣漂在水面上,徒留怅惘。难以保留的美才让人留恋和回味。榆叶梅的花不肯落,抱在枝上显得很颓,像皱巴巴的粉色卫生纸。生命短暂,芳华易逝,可花朵的志向不同,有的宁可枝头抱香死,有的零落成泥碾作尘。
我一直难以接受插花这种行为,买来或者折下鲜花放在瓶子里欣赏,的确会给房间增添雅致,短暂地美化心情,可过几天花瓣萎靡就要丢进垃圾桶里。感觉有些残忍,不得善终,像购买或租赁了妙龄女子的青春,又狠心抛弃一般。倒不如在枝头恣肆地美过,然后落在泥土里化作肥料,完成生命的轮回。
有的花可以食用,比如槐花,开花时节总是不得安生,常有人采摘槐花弄折了树枝。同为豆科植物的紫藤也可以吃,只是金贵又有诗意,大家舍不得去摘。老舍先生有诗云,“四座風香春几许,庭前十丈紫藤花”。不像槐花那么家常,生来要被吃似的。二月里在四川攀枝花,经过一棵高高的树,啪嗒落下一朵大红花,立即有人捡拾起来,放进袋子里。那是厚实的如巴掌大的花,当地人说这就是攀枝花,地名由花名而来。早上的街头有卖攀枝花花蕊的,十几块钱一斤,据说炖肉炖汤都好。张爱玲小说里提到的象牙红,也就是鸡冠刺桐,在葛薇龙的眼中成了碗口大,我每每觉得不可思议,象牙红细细的,大点儿的也就手指粗细,倒是攀枝花,才真的是碗口大。这是一种夸张的修辞,还是香港的象牙红格外大些?
在别处,这花也叫木棉,整朵拿来炖汤。在《老广的味道》里有位阿姨雨后捡拾落在马路上的木棉花,每捡到一朵都很开心。炖汤的配额是家中每人一朵,剩下的用棉线穿起来挂着晾干,留着其他季节慢慢吃。
林黛玉对花怜惜,也自怜。大观园里的其他姑娘,对花的态度则不同。另一位行为艺术家史湘云醉卧芍药茵,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还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这一幕写出了她大大咧咧的性格,对芍药花,她不会感慨身世,而是开发了别的用途拿来做枕头,亏得芍药花瓣丰厚。只是有些奇怪,换了地方便睡不着觉的湘云,怎么会大白天的睡倒在花园的石凳子上,安全感真是个捉摸不定的东西。探春是持实用主义态度,把花草当作经济作物来给大观园增加收入,“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宝钗和李纨也表示赞同,轰轰烈烈开展了大观园的承包责任制。有人看到美,有人看到吃,有人看到经济,性格和阅历决定了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