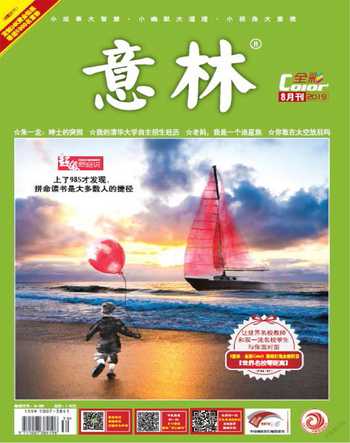囚鸟
秦羽墨
我在洞庭湖平原的某片产粮区监督收粮,住处安排在一个叫作白鹤山的粮站。闲来无事四处转悠,我喜欢秋后湖区的这种厚重感。
乌鸦、麻雀、八哥以及未来得及南飞的白鹤,不失时机地占领了大地所有的角落,天上到地上无所不在。有的稀稀拉拉在田里闹腾,有的整齐地排在电线杆上,它们唯一要警惕的,是随时可能出现的鹰。这是一幅各得其所、安然自得的景象,扑进眼眶的大地之物都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只是,作为旁观者的我,却是孤独的,不自由的,懒洋洋的。
我准备开门。先是钥匙转动的声音,紧接着是一阵翅膀发出的“扑扑”声。推开门一看,只见一只比麻雀大一点的灰褐色的鸟在卧室里挥舞着翅膀。这间卧室空旷无比,是由粮站活动室临时改造而成,腾出来给我住的。两边有十几扇玻璃窗子,其中一扇半开着。显然,这个不速之客是从那扇半开的窗子闯进来的。
它为我的突然出现所惊吓,不停地寻找出口,情急之下慌不择路,不断传来喙和爪子撞击玻璃的声音,频繁而急促,并发出“叽叽叽”的叫声。我机警地把门合上,并把那扇半开的窗子也关紧。
“今晚有鸟做伴”,这是我的第一个念头。一个多月来,我每天夜里只有孤灯相伴,着实有些寂寞。我尽力摆出一种和平相处、互不干扰的姿态,妄图消解它对我的恐惧。它的逃离行动持续了十几分钟,在屡屡碰壁毫无结果之后,终于安静下来。看起来它显然有些泄气,但并未绝望。它一会儿立在椅背上,一会儿又站到窗帘后面,躲躲闪闪的,不时试探着什么。
一只鸟飞进了卧室,飞进了一种紧张、恐惧,却要故作平静的等待之中。
失去了天空,空负翅膀,世界广阔,但没有一寸是自己的。地上的子弹和无形的绳索(墙壁),哪一样不致命?鸟之受困在于找不到出口,人呢,明知道路所在,却不敢迈出步子,人的悲哀实在远胜于鸟!
吃晚饭时这些想法一直在我心头萦绕,晚饭味同嚼蜡,毫无滋味。我边想着边推开门,灯亮的时候,看见那个小家伙立在离我最远的椅子上。显然,此时的它,对我的存在已经习惯,只是对突然亮起的灯感到不适,百无聊赖地飞了半圈,又回到原点。我想起小时候放学回来,常到田间地头帮大人做事,那时村里还没有通电,晚上做功课点的是煤油灯,母亲借着灯光给我和哥哥做鞋、补衣。在母亲看来,吃尽苦头,终于等到我和哥哥大学毕业,以为将有一个转机,彻底改变眼前的境况。没想到,意外接连发生。先是哥哥的腿受重伤,因为没钱耽误了手术;再是父亲离开了我们。工作的不如意,债务的烦身,我犹如卧室之鸟,越挣扎越是感到笼子的无处不在。世界宽广无边,天也无涯,出路何在?
一个卧室,一个人,一盏灯,加一只突如其来的鸟,这是一幅完美油画的构成。夜是静的,人是静的,鸟是静的,仿佛连灯光也显出静态来。但,静不是这幅油画的真实底色。画的背面,压抑着烦躁、恐惧、被束缚感,像是透过纸背面的颜料。
第二天我是被鸟叫醒的。其实每天都是如此,天一亮粮站就被鸟占据。我起床,看见那个小东西又在用喙不断地沖撞玻璃。窗台上到处站满了鸟,对面房子上的爬山虎里也有鸟在跳来跳去,其中不少是它的同类。几根曲折的炊烟将大地摇醒过来,不远的小山丘上,农民已经在摘橘子。
那只鸟肯定比我更早看到这些,我觉得自己有点残忍,在这个飞翔和饱食的季节,将它囚禁了整整一晚。我打开窗子,只听见“嗖”的一声,它就飞了出去。我在窗前愣了一会儿神,它没有划出一条我期待的弧线,我想它可能太急于离开了。
它需要它的天空。我,也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