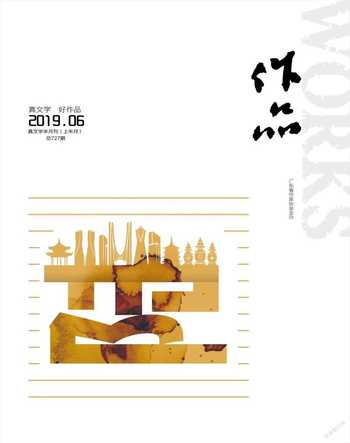哑琴(随笔)
詹谷丰
一
邓尔雅花巨资买下绿绮台琴的时候,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后世的俗人,会把“收藏”两个汉字与他的购琴联系起来。
在后人的想象中,绿绮台琴“唐武德二年”的制作时代和宫廷血统以及“岭南四大名琴”之一的声誉,一定可以囤积居奇,让它的身价插上升值的翅膀。在如今这个物欲横流,所有的精神和物质都可以用货币交换的时代,收藏,是人类最好的生财之道。
所有的文献,都没有绿绮台琴身价的记录,邓尔雅的巨资,始终是后人猜测的一个谜。《邓尔雅评传》(陈莉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在记录这个发生在1914年8月东莞可园的情节之时,也只有“邓尔雅毅然以千金购下,希望琴以传人,人以传琴”的简单描述。
没有价格的器物,才能潜藏巨大的价值,这些隐藏在交易深处的商业原理,是精明投机者的发财秘籍。后人的眼光落在绿绮台古琴身上的时候,许多人都忽略了邓尔雅一介书生的身份和传统文人的精神气节。
得到绿绮台琴之后,邓尔雅视如珍宝,他的欣喜和珍爱,多次通过他的诗文表露。我从《双琴歌题邝湛若遗像》《纪得绿绮台琴》《绿绮台记》《绿绮台琴史》《绿绮古琴拓本》等诗文以及为绿绮台所得篆刻的系列印章中,看到了邓尔雅内心的崇敬和笑容。邓尔雅的《绿绮台记》,拂去了岁月时光的尘埃,让后人看到了一介书生耗费巨资购琴的真相:
明季邝湛若先生蓄古琴二:曰南风,宋理宗物;曰绿绮台,唐制而明武宗物也。出入必与俱。庚寅广州再陷,先生抱琴殉国,王渔洋有《抱琴歌》及“海雪畸人死抱琴”之句,海雪先生所居堂名也。初武宗以绿绮台赐刘某,先生得之于刘家,至是骑兵取鬻于市,归善叶犹龙(佚其名,以祖荫锦官卫指挥同知)见而叹曰:“噫嘻,是御琴也!”解百金赎归。……继归马平杨氏,杨氏世善琴,随将军果氏来粤,寄籍番禺,其裔字子遂者,值咸丰戊午之夜,以琴托其友,友私质诸吾邑张氏可园。光绪壬寅,余识子遂于潘氏缉雅堂,子遂述此事,相与痛惜久之。又十余年,张氏益式微,琴亦残甚,室壁蠹蚀,每以为憾。余知张氏子孙不能守,谋得见之,首尾小毁,安弦试弹,已病痹。甲寅八月,始以廉值有之,摩挲再四,断纹致密,土花晕碧,深入质理,背镌分书“绿绮台”三字,真书“大唐武德二年制”七小字。……琴成距今一千三百多年,虽不复能御,然无弦见称于靖节,焦尾见赏于中郎,物以人重,固有然者,非经海雪之收藏,安知不泯然与尘劫而俱尽也。
购琴的真相,就是邓尔雅内心的真实想法。七十多年之后,我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推测,如果此琴不曾为邝湛若拥有,绿绮台琴的价值,在邓尔雅眼中,将会大打折扣。即使此琴年代悠久,尽管它出身高贵,它在珍藏意义上的光芒,将会黯然失色。邓尔雅没有任何掩饰,他旗帜鲜明地用“物以人重”作了购买绿绮台琴的理由。在他心中,绿绮台琴就是邝湛若的化身,就是“海雪畸人死抱琴”这句诗的最好诠释。
二
邝湛若在邓尔雅心中的重量,可以用泰山来比拟。
邝湛若,名邝露,号海雪。我对邝露的了解,来自陌生的粤剧舞台。《天上玉麒麟》和《蝴蝶公主》,是广东南海人邝露在粤剧舞台上的演绎。在粤剧舞台上,邝露用洒脱浪漫、传奇色彩和忠贞不屈塑造了一个诗人与英雄的光辉形象。由于邝露落拓不羁,情感丰富,通晓兵法、骑马、击剑、射箭等多般武艺,喜爱收藏和文物鉴赏,精于骈文,书法自成一格,又出任过南明唐王时期的中书舍人和出使广州,一生充满故事,所以最易成为舞台上的戏剧形象。
戏剧是艺术的演绎和塑造,现实生活中的邝露,除了诗人、书法家的身份之外,还是一个品格高尚的琴人。在邝露的平生珍爱中,有两张名琴,一张为今藏山东省博物馆的宋琴南风,另一张为1914年邓尔雅用巨资购买的唐琴绿绮台。
南风曾是宋理宗赵昀的内府珍品,绿绮台则为明武宗朱厚燳所有。帝王宫廷的高贵血统,让两张古琴价值连城,名扬天下。
天下所有的名琴,除了高贵的出身和皇家血统之外,无不经历曲折,命运坎坷。南风和绿绮台如何历经磨难艰险落到邝露手中,由于时光的久远已难以考证,但当邝露成为新的主人之后,它们的经历就逐渐清晰。传奇,是天下所有名琴的必然经历和命运。
古代的琴人,对古琴的珍爱,形同性命。在文献的记载中,出生于书香之家的邝露,琴不离身,“出游必携二琴”。在邝露那里,琴是生命的一部分,一个爱国者的生命中,可以没有金钱物质,却不能缺失寄托心志的七弦琴。因此,当敌人兵临城下,面对死神的时候,邝露用生命实践了他对琴的承诺,人在琴在,琴亡人亡。
永历四年(清顺治七年,1650年),邝露奉使还广州,遇清兵围城。他把妻兒送回家乡,只身还城,与守城将士死守达十个月之久。是年十一月,西门外城主将范承恩通敌,导致广州城陷。此时,邝露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恢复名士风度,身披幅巾,抱琴外出,适与敌骑相遇。敌军以刀刃相逼,他狂笑道:“此何物?可相戏耶?”敌军亦随之失笑。然后,他慢步折回住所海雪堂,端坐厅上,将自己生平收藏怀素真迹和宝剑等文物,尽数环列身边。抚摩着心爱的古琴,边奏边歌,将生死置之度外,绝食,最后抱琴而亡,死时年仅四十七岁。
“抱琴而亡”,是人类死亡最庄严的形式。它的悲壮和崇高,超过了战场上所有的血腥。“抱琴而亡”,虽然没有敌方的尸体,倒下的是正义,但却是人类气节的最直接体现。“抱琴而亡”四个汉字,升华了一种古老乐器的精神内涵,将人类的肉体生命与器物的灵魂融为一体。
邓尔雅不在邝露抱琴殉国的现场,但他穿越数百年的漫漫时光,看到了一个诗人的爱国气节,听到了七根丝弦在人的指上发出的镗鎝之声。在一个散文写作者七十多年之后的想象中,邓尔雅对邝露的崇敬,对古琴的理解和热爱,从此开始。
在邓尔雅的心里,世界上所有价值连城的器物,只有古琴没有铜臭的气味,那是一种不能亵渎的天地精灵,从七根丝弦上发出的声音,都是天籁之音。
三
邓尔雅从东莞张氏后人手中购得绿绮台琴的时候,他的心情一定错综复杂,百感交集。时光流逝了七十多年,如今的人,隔着一个时代,已经无法看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和听见一张琴的天籁之音。
我愿意将七弦琴看成是乐器的始祖。在我的臆想中,没有一种乐器比七弦古琴更久远,更没有任何一种乐器比古琴更能穿透人心,在人世间留下不朽的故事。
由于古琴的出现,人世间才会产生“知音”这样千古不朽的名词,才会出现伯牙、钟子期、聂政、公明仪、蔡文姬、嵇康、阮咸等流传后世的名字,才会让伯牙摔琴谢知音、聂政学琴报父仇、公明仪调弦对黄牛、蔡邕访友闻杀音、完颜璟雷氏琴殉葬、乐古春艳遇得古琴等故事从弦上走下来,与后世相遇。
古琴历史悠久,它出现的年代,有多种说法,但都与“古老”这个词关联。人世间没有一种乐器像古琴这样,用七根弦串联起伏羲、神农、黄帝、堯、舜、禹等这些远古时代的圣贤。
在没有音乐的混沌时代,第一个凝集乐音,再用材料和丝弦再现天籁之音的人,一定是人世间的天才,他是神派来人间传播福音的使者,所以,伏羲的出生,只能是圣灵感孕的结果。伏羲从风流动的声音中,感悟并制定了音律。
在古琴没有发明之前,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都是野性的,自然的,无法捕捉的,伟大的伏羲,第一个将风一般不可捉摸的美妙声音收进一个由桐木和丝弦组成的魔盒之中,然后在手指上跳跃展示。
清人徐祺认同伏羲发明古琴,用丝弦感通万物,在《五知斋琴谱·上古琴论》中,他用文字展示了一件乐器的来路:
琴这种乐器,创始于伏羲,成形于黄帝,取法天地之象,暗含天下妙道,内蕴天地间灵气,能发出九十多种声音。起初是五弦的形制,后来在周文王和周武王时,增加了两根弦,是用来暗合君臣之间恩德的。琴的含义远大,琴的声音纯正,琴的气象和缓,琴的形体微小,如果能够领会其中的意趣,就能感通万物。(殷伟《中国琴史演义》,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
古琴之后的乐器,钟磬簧笙,丝竹管弦,五花八门,没有人能够数清人世间能够称得上乐器的发声物,无论它们形体如何变化,形状如何创新,演奏方法如何花哨,制作材料如何高端,表演场所如何转移,它们都是古琴的子孙。单纯的音乐可以悦耳,但是无法通灵,更不可能将一个世界浓缩于匣中,储存于弦上。古人将七根弦上的声音,接通了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涵,接通了天地宇宙。
古琴发明于创世之神,它的诞生,一开始就注入了贵族的血统,所以,古代的帝王君臣都精通琴艺。世间的君臣,人类的道德,都包容在弦上。伏羲以“琴”命名的乐器,用“禁”的含义规范了人世间的伦理,即禁止淫邪放纵的感情,蓄养古雅纯正的志向,引导人们通晓仁义,修身养性,返璞归真,和自然融为一体。伏羲面对群臣,诠释了古琴与治世的要义:
寡人今削木为琴,上方浑圆取形于天,下方方正效法大地;长三尺六寸五分,模仿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宽六寸,和天地六合相比附;有上下,借指天地之间气息的往来。琴底的上面叫池,下面叫沼,池暗指水,是平的,沼借指水的暗流,上面平静,下面也跟随平静。前端广大,后端狭小,借喻尊卑之间有差异。龙池长八寸,会通八风;凤沼长四寸,和合四时。琴上的弦有五条,来配备五音,和五行相合。大弦是琴中的君主,缓而幽隐;小弦是臣子,清廉方正而不错乱。五音之中,宫是君、商是臣、角是民、徵是事、羽是物,五音纯正,就天下和平,百姓安宁,弹奏琴就会通神明的大德,与合天地的至和。
这段引自《中国琴史演义》中的文字,不可能是作者的现场耳闻和记录,后人的现代汉语翻译,遵从了真实准确的原则,再现了古琴发展史上最重要最生动的场景。
在后人的推测和想象中,群臣茅塞顿开,感受到了古琴无穷的奥妙,君臣对话,让一种乐器登上了哲学与人伦的最高峰。在伏羲的号令中,工匠们上山,砍伐桐木,精心制成样板,颁发天下。天下百姓,遂按图索骥,从此古琴繁衍,世代不息。人类最灵巧的手指,第一次在弦上纵跃翻飞,闪躲腾挪,曲尽世间奥妙。郑觐文先生的《中国音乐史》记录古琴指法四百多种,正是手的功能的最好展示和指法的发展与繁衍。古琴指法,“属于左手者有五十二种,属于右手者有五十种,更有古指法五十种,再加以轻重化法(如一挑有圈指弹出者,有竖指弹出者,有弯指轻弹者),细分之有四百多种,一法有一法之特点。自古音乐从未有若此之繁复者”。
古琴的漫长历史,从伏羲始祖开篇,从此蔓延不绝。后人通过文字看到的号钟、绕梁、绿绮、焦尾和齐桓公、楚庄王、司马相如、蔡邕等名词,都是琴的经典,都是不朽的故事。
邓尔雅不是琴家,但他是一个深谙琴理的文人,他知道,一张琴,就是一个世界,一张琴,从做成之后的首音到焦尾之时的弦绝,就是一个琴人的一生。所以,1914年8月,他从可园主人张敬修的后人手中购下绿绮台琴的时候,心中无以名状,他轻轻地抚摸绿绮台琴,立即感受到了邝露的体温。
四
邓尔雅心中山一般伟岸的邝露,远不是绿绮台琴最早的主人。对于千年历史来说,绿绮台琴之于邝露,也不过是短暂的寄托,是它漫长路途中的一处驿站。
世界上所有的名琴,都有非凡的出身。中国古代的帝王,都是古琴的知音,凡是世上最好的乐器,他们都要收入宫中。绿绮台琴作为世上的珍稀,必然有高贵的出身。我在所有文献中见到的绿绮台,都是一张髹黑漆仲尼式的皇家面孔,通体细密的牛毛纹,折射出一千三百多年的岁月沧桑,“绿绮台”三个汉字,用隶书体刻在琴底颈部,龙池右侧则是“大唐武德二年制”七个楷体字。
岁月沧桑,时光漫长,已经无人知道绿绮台琴出自何人之手。绿绮台琴问世的唐朝,正是制琴名家辈出的盛世,京城路氏、樊氏,江南张越、沈镣,蜀中雷俨、雷威、雷霄、雷迅、雷珏、雷文、雷会、雷迟,无不大名鼎鼎,出自他们手中的古琴,价值连城。所有的琴家,都以得到一张名琴而自豪得意。可以断定,绿绮台琴如不是出自制琴名家之手,明武宗断不会将它藏入宫中。
世上的每一张名琴,都有各自不同的命运。出身高贵,并非注定一生钟鸣鼎食,荣华富贵。绿绮台琴命运坎坷,是一千三百多年前制作它的工匠和拥有它的明武宗朱厚燳所没有想到的。九泉之下的主人,如果知道他的珍爱流落民间,一定心如刀绞,痛不欲生。
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记录了绿绮台琴和它的行踪。绿绮台与春雷、秋波、天蚃一起,被誉为岭南四大名琴。明武宋朱厚燳将琴赐与刘姓大臣。从刘姓大臣到邝露之间,是一段漫长的光阴,这段历史可惜被岁月堙埋了,我无法找到其中的关联脉络。现有的文献,只是记载了琴归邝露之后的踪迹,此前的经历遭遇,已经成了一个难以破译的谜。
世事难料。所有的研究者,都只能在刘姓大臣到邝露之间留下空白,文献也只能用“明末散出民间”来敷衍后世。
邝露殉国,绿绮台落入了清军之手。这个不知道姓名的清兵,不知道这张琴的来历和价值,只是谋划着如何将邝露的平生之爱兑换成银子。于是,一个爱财的士兵,抱着绿绮台琴,来到了街市。
对于一张价值连城的古琴来说,这个清兵仅仅是个爱财的小人,他无法看出“绿绮台”三个字的奥秘,更不可能知道“大唐武德二年制”的价值,他眼中只有银子。万幸的是,绿绮台古琴没有埋没,它无意中遇到了知音。
许多文献在叙述这个重要转折时,异口同声地描述:
琴被清兵所抢,售于市上,为归善(今惠阳)人叶文龙以百金所得。(百度词条)
湛若既殉难,绿绮台为马兵所得,以鬻于市。(屈大均)
初武宗以绿绮台赐刘某,先生(邝露)得之于刘家,至是骑兵取鬻于市。(邓尔雅)
这是一个没有争议的情节,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过程,可惜的是,后人在以可园绿绮楼为背景的写作中,屡屡忽略了绿绮台琴从清兵至叶文龙过渡的重要过程,即使曾与绿绮台琴密切相关的岭南四大名园之一的东莞可园,在编辑出版可园的图书中,也有意无意地隐匿了这个戏剧性的情节。后人的粗疏,总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所以,再近的历史,也常常面目模糊,云山雾罩。
一张名琴的波折,并没有在此终止,只要世道坎坷,绿绮台琴就免不了流离失所。归善人叶龙文,是一个慧眼识珠的人,他在热闹的街市上看到了那个摆卖名琴的清兵。历史常常忽略细节,在史无记载的地方,我能够想象得到叶龙文(亦有文献写为叶犹龙)见到绿绮台琴时的惊异和狂喜,此时的叶龙文,肯定心跳加速,他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当他定下心来,仔仔细细打量那张琴之后,才相信了这个意外和惊喜。我见到的所有文献,在记录一个人的欢欣时,仅仅用了“见而叹曰:‘噫嘻,是御琴也’”一笔带过。
慧眼识珠的叶龙文,肯定不是等闲之辈。邓尔雅在《绿绮台记》中注明为“佚其名,以祖荫锦官卫指挥同知”,只有具有书香官职背景之人,才有可能认识一张琴的真实面目。
历朝历代,都有造假之物。只不过我生活的这个时代由于世风日下铜臭熏天,造假尤烈,以至有伪钞、假饮料、假酒乃至假冒的官员等前所未有之事。
抗金名将岳飞的孙子岳珂,在其记载遗闻轶事的《桯史》一书中,就揭露过古琴造假。由于此事为岳珂亲历,所以为后世人信服。
南宋嘉定三年(1210年),有一士人携一张名为冰清的古琴,来到酷爱鉴藏古琴的北京官员李奉宁家,用传家宝的名义让主人当即心动,爱不释手。冰清古琴形制奇特,通体断纹鳞波,刻有晋陵子的铭文,又有“大历三年三月三日上底蜀郡雷氏斫”和“贞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士雄记”的落款。
李府家中上下宾客,都认为此琴为唐代古物,稀世之珍,不可多得。还有人引经据典,搬出《渑水燕谈》中有关冰清古琴的记载,证实此琴出自唐代制琴名师雷氏之手。
就在主人即将花巨资交易古琴之时,岳珂站了出来,他力排众议,以避讳和凤沼孔眼无法探笔写字的理由,让所有人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岳珂认为,本朝仁宗皇帝赵祯即位以来,当避讳“贞”字,古琴的凤沼中的“贞”字从卜从贝,而且贝字有意缺笔,少了旁点。四百多年前的唐人,如何知道为宋朝的皇帝避讳?
在古琴的历史上,岳珂火眼金睛识破伪琴的故事,至今为后世的琴家乐道,也记住了《桯史》中的警告:“今都人多售赝物,人或赞媺,随辄取赢焉。或徒取龙断者之称誉以为近厚,此与攫昼何异,盖其蔽风也。”
叶龙文的眼光没有辜负绿绮台名琴,他当得起“慧眼见真”这个出自佛教经典《无量寿经》中的词语的褒扬,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即“解百金赎归”。
从杀人的清兵手中来到有鉴赏能力的文人怀抱,对于灾难中的绿绮台琴来说,绝对是一件幸事。我在文献中看到了接下来的欢娱和悲伤场面:
暇日招诸名流泛舟西湖(叶遭国变,不复仕进,筑泌园于惠州之西湖),命客弹之,于是屈翁山、梁药亭、陈独漉、今释诸子皆流涕,为赋长歌。
时光流逝,后人已无法听到绿绮台琴在惠州西湖上的凄伤之音,也不可能考证出弹奏的曲调,但从座中诸子的声名影响来看,绿绮台琴遇到了最好的知音。
屈翁山,即番禺屈大均,岭南三大家之一。
梁药亭,为南海梁佩兰的号,岭南三大家和岭南七子之一。
陈独漉,即顺德陈恭伊,其父为南明抗清英雄,岭南三忠之首。与屈翁山、梁药亭齐名。
今释,广东丹霞别传寺名僧。
应叶龙文之邀游览西湖欣赏名琴的四个人,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诗人。这些力主抗清名气高洁的岭南名流,动情流泪之后,为绿绮台琴泼墨挥毫,作长歌赋。
五
可园,是一座让东莞人感到自豪的园林。作为与顺德清晖园、佛山梁园和番禺余荫山房并称的岭南名园,它让我无数次走进那片蜃楼悬阁,廊庑萦回,叠山曲水的清代建筑。每次进入可园,必到之处就是绿绮楼。每当天阴雨暗,游人寥落的时候,我总是在可园的每一块砖瓦上听到琴声。细心揣摩,既有《高山》《流水》的美妙,又有《胡笳十八拍》的幽愤,更有《广陵散》的壮烈。那些深入到了建筑内部的古琴声,总会在知音来临的时候,幽幽地复活。我总是认为,可园虽然楼阁众多,那片一楼五亭、六阁、十九廳、十五房的组合建筑,如果没有绿绮楼,将会黯然失色,将会失去精神。
我曾经认为,具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唐代古琴绿绮台,历经磨难之后,被叶龙文收藏,当是最好的结局。然而,没有眼睛能够看得见千里之外的山河,也没有预言家占卜到绿绮台琴未来的命运。
绿绮台琴与可园的缘分,其实是古琴的磨难与波折。绿绮台琴是如何从叶龙文处流落,最终被马平杨氏所得,后人的所有解释,都附会于邓尔雅的《绿绮台记》:
继归马平杨氏,杨氏世善琴,随将军果氏来粤,寄籍番禺,其裔字子遂者,值咸丰戊午之役,以琴托其友,友私质诸吾邑张氏可园。
邓尔雅及后来者的文章,均没有交代绿绮台为何归于马平杨氏,马平杨氏如何从叶龙文处得到名琴。历史的粗疏之处,常常有故事发生,可惜的是,所有的情节和细节,都被岁月埋葬了,无处掘墓,无人考古。
广东古琴研究会副会长莫尚德先生在《广东古琴史话》一文中用白话翻译了邓尔雅的《绿绮台记》,认为“以后琴归马平杨氏,他们世代都弹琴,随果将军来粤,寄籍番禺,值咸丰戊午(1858年)有兵灾,杨氏子孙名子遂的把琴托朋友保存,朋友却私自把琴典质给东莞张氏可园”。
《邓尔雅评传》在交代这一线索时,虽然简洁,却更为清晰:后来此琴由叶龙文后人保存了数代。太平天国时期,此琴落入平县杨氏家中,杨氏后裔将此琴交付东莞朋友陈氏保管,而朋友私自押在东莞张氏当铺。时当铺主人,乃明末抗清名将张家玉后人。深知此琴的重要性,于是张敬修当以重金,陈氏无力赎回。
张敬修与可园,是东莞的一个传奇。
东莞人张敬修为唐代宰相张九龄弟张九皋的后代。这个曾在广西、广东平息匪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抗击过英军的武将,一生中任过浔州知府、右江兵备道、广西按察使、江西按察使、署理布政使,由于在战场上负伤,便萌生了在家乡建园体憩养病的想法。张敬修虽是武将出身,却一身文人气质,琴、棋、书、画、均是他的喜好,所以,建成之后的可园,成了梅、兰、竹、菊的精舍,成了画家居巢、居廉创作授徒之所,成了岭南画派的滥觞之地。
从某种意义来说,可园主人张敬修,是绿绮台琴的知音。
那个违背杨氏信任与嘱托,私自将绿绮台抵押的人,是绿绮台的灾难,所幸的是,他遇到了张敬修。可园博物馆原馆长王红星先生认为:“张敬修收藏绿绮台琴,应凝聚了身为一员武将的张敬修追崇英雄忠贞不屈的思绪”。(《东莞可园》,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
我从王红星先生文章中“咸丰八年(1858年),张敬修辗转得到绿绮台琴。张敬修专门在可园中命名一楼为‘绿绮楼’,以宝藏之”的叙述中看到了张敬修的欣喜和珍惜。
在可园一楼五亭六阁十九厅十五房的古典格局中,绿绮楼并不是最高的建筑,也没有最气派的设计,有关资料中“此楼按照古制陕而修曲,修建而成,歇山顶,青砖砌筑墙体。内侧沿楼设廊道,廊道设风雨槛窗。人依廊栏,石山伫立,紫荆淡雅,石榴花开,龙眼苍翠,廊榭环绕,花木扶疏,竹影参差。随曲廊移步,景随步移”的世俗描述仅仅是一种外相,并没有让它鹤立鸡群,唯有绿绮台,用千古的琴声,使它奇峰峻拔,一览众山。
绿绮台琴,以贵宾的身份,隆重地置放于绿绮楼的中心位置。绿绮台琴到来的那天,绿绮楼里的红木桌椅、雕花门扇和丝绸布幔乃至桯几上的精致景德镇瓷器,都成了陪衬,不仅如此,可园中的所有楼阁亭榭和花草树木,都一齐向这张来自遥远唐朝的古琴致敬。我想,绿绮台琴辗转来到东莞,从此成了张敬修可园的镇园之宝。
由于绿绮台琴的到来,可园光彩焕发,可园曾经的光芒,都被一张稀世古琴掩盖了,张敬修的客人一时蜂拥而至,几乎踏破了坚硬的石质门槛。风骨之士邝露的遗物绿绮台古琴,成了可园的中心,成为岭南风流文士们口头不绝的谈资。
张敬修以当铺主人的身份,得到了无价之宝绿绮台琴,他在可园绿绮楼中一遍遍抚摸古琴的时候,只有欣喜涌上心头,他不会想到,坚硬的砖瓦,也有衰败的时光。
可园幽深,所有的建筑和花草树木,均掩藏了张敬修曾经的当铺主人身份和他用重金当琴,让陈氏无力赎回的手段和心机。
六
绿绮台琴在张敬修可园的绿绮楼上吸引文人骚客们击节赞叹的时候,邓尔雅,正是座上的一个客人。
文献只记载了“邓尔雅与可园张家素有交往,对于邝露高风亮节,邓尔雅一直深为钦佩”的事实,却没有人知道,在绿绮楼上欣赏名琴古声的时候,邓尔雅有没有过“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心境。与白居易诗里的琵琶相比,古琴显然更久远,更多经典故事。
邓尔雅在可园欣赏绿绮台琴的时候,总是想起抱琴殉国的英雄邝露,他从未想过,绿绮楼上的绿绮台琴,还会有易主的时候,他更没有想过的是,有朝一日,自己会成为这张名琴的新主人。那个时候,建园的张敬修已经不在人世,可园也随着张敬修的离去而逐渐暗淡。
绿绮台琴和可园,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它们的存在,如同车的两个轮子,形似鸟的一对翅膀。邓尔雅亲眼见证了可园的兴盛和式微,那座岭南著名的私家园林,和那张邝露曾经拥有过的古琴,构成了血缘般的荣辱关联。
在关于绿绮台古琴一节中,《邓尔雅评传》有“民国初年,张家逐渐中落,要靠变卖家藏度日”的描述。九泉之下的张敬修,已经不能为他始建的园林力挽狂澜了。
一座园林的衰落,同时也是一张古琴式微的开始。
1914年,是绿绮台琴命运的又一次转折。同年8月,邓尔雅听到了可园后人变卖家藏的消息。一丝忧虑,开始从夜深人静的时刻弥漫,逐渐占据了他的心。邓尔雅想到的是,当一个世家不能以他们擅长的书画谋生的时候,家财的散失,当是不可避免的结果,邓尔雅想到了绿绮台古琴……
邓尔雅用“探访”开启了他与绿绮台古琴的缘分。《邓尔雅评传》如此记载了一张名琴的易主:
1914年8月,当听说张氏子孙在变卖家藏度日,邓尔雅就预知此绿绮台琴必不能守,遂前往探访,只见绿绮台琴的尾巴已经损坏,琴身已被虫蚁所蚀,不禁悲从心生。邓尔雅毅然以千金购下,希望琴以传人,人以传琴。
绿绮台古琴,當它以珍稀宝贝的身份易主时,新的主人一定充满了喜悦,那个从邝露的尸体上夺得古琴的清兵如此,那个辜负杨氏重托,私自质押古琴的未名者更未能逃脱,可园主人张敬修得到古琴,以宝藏之,亦不免得意,只有邓尔雅,念英雄邝露,购殉国遗物,虽是残琴,已经绝响,却无丝毫遗憾。
邓尔雅得到绿绮台琴之后的心情,通过一个篆刻名家最擅长的方式体现。他用坚硬的石头,记录了这个瞬间。我在文献中看到了邓尔雅作于一百年前的印“绿绮台”,并留下了“摩挲再,断纹致密,土花晕碧,深入质理,背镌分书‘绿绮台’三字真书,‘大唐武德二年制’七小部,十四年八月得邝湛若藏唐琴绿台”的边款文字。在邓尔雅心目中,唐琴绿绮台只为英雄邝露留名,其他的拥有者都是过客与陪衬,可以忽略。
邓尔雅出身书香门第,幼承家学,善小学,精鉴赏,工诗文,篆刻书画俱精,门人弟子众多,被研究者称为“金石印人,文字学人,书画奇人”。因为邝露的缘故,绿绮台琴被邓尔雅赋予了传奇色彩和爱国气节,一张古琴,超越了器物的属性升华为人与精神的象征。
在一个金石印人眼里,文字可以说话,石头最有温度,邓尔雅一生中,用诗词、文章、印石、拓片等多种方式为绿绮台琴树碑立传,远远超过了对一件器物的热爱,只有从历史中逃难出来的琴家,才能看到古琴背后的人物,那是人的风骨和气节。
《邓尔雅诗稿》中,随处可见到绿绮台的影子,邓尔雅刻刀走过的石头上,多是与古琴关联的文字。后人在《双琴歌题邝湛若遗像》等诗中读到“双琴南风、绿绮,出亦琴,人亦琴,海雪之堂二雅文心,今我见琴如畸人,急弦亮节难为音,自然有奇气,自然有奇意,人间不能名,希声闻上帝”这样发自心灵深处的文字时,如何能够无动于衷?
我在黄脆的文献中,见到过邓尔雅分赠给章太炎、西神祠丈、高旭、张其淦、苏曼殊、容庚、容肇祖等人的绿绮台古琴拓本,当受赠者读到拓本上的附诗时,立即就看到了一张古琴和一个古琴收藏者的情怀。
名士名琴亡未亡,岿然若见鲁灵光。
畸人亦有凌云作,古调如闻海雪堂。
愿学谪仙怀犹抱,亲窥赤疋境难忘。
先生往矣流風水,余韵而今极绕梁。
容肇祖是邓尔雅的外甥,由于血缘亲情的关系,面对绿绮台琴拓片,他比旁人更加准确深入地理解舅舅的内心情感和精神寄托。在写于1944年的自传中,这个中山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回忆了邓尔雅与绿绮台琴的往事:
1920年(民国九年庚申)我23岁。我在广东高师三年级。这年,我与四舅母表妹兰微结婚。我翻译莫泊桑的《余妻之墓》投《小说月报》发表。邓尔雅四舅获得绿绮台,我得有绿绮台琴拓本,题词云:“风入桐秋,月窥帘寂,绿绮梧桐庭院。奏罢南风,抱残峤雅,飘零土花斑点。广陵散,宫声往,畸人剩幽怨。水山远,暗情移,爨桐无恙,弦未上,焦尾早经泪染。问古调谁弹,坐空斋银烛重剪。想牙琴邓牧,后世子云难见。
容肇祖教授眼中的绿绮台琴,已经不再风华正茂,暮岁之琴,像人一样风烛残年,琴面斑驳,空无一弦,面对沧桑世事,只能哑口噤声。但是,容肇祖知道一张残琴对于一个读书人的价值和寄托。
饱经磨难颠沛流离的绿绮台古琴,终于以一副哑琴的沧桑在邓尔雅那里得到了最温暖的安置。
1929年,是绿绮台古琴一生中最静好的岁月。这年5月,邓尔雅用鬻印卖字的收入,在香港九龙大埔买下了一块地,为绿绮台琴筑一个温暖的小巢。三个月之后,小屋建成,邓尔雅命名为“绿绮园”。
绿绮园与绿绮楼,一字之别,都是东莞人为千年古琴量身定制的,也是邓尔雅与张敬修对英雄邝露的敬慕。这个情节,记录在《邓尔雅年表》中:
在香港新界大埔购地筑“绿绮园”,贮藏绿绮台琴,以表敬慕邝湛若之高风亮节。八月绿绮园落成。崔师贯来访,作“寻邓尔雅新居,观邝海雪旧藏绿绮台琴,为赋此解,依梅溪元儿体”。
邓尔雅筑绿绮园,只是为了给绿绮台寻找一个安全稳固的住所。那个时候的绿绮台古琴,已经丧失了发声的功能,它无法恢复到叶龙文的那个时代,让文人雅士在山水之间吟咏抒情。
由于交流困难,聋哑之人一般深居简出,在不可避免的社交场合,只以手势表达一个人的内心和情感。绿绮园中的绿绮台琴,由于不能歌唱,也只能以沉默的方式深藏不露,它拒绝抛头露面,显露风头。
真正的知音,只有面对一张无弦的哑琴时才能检验。绿绮园里的邓尔雅,当他沐浴焚香,虔诚地触摸一张古琴时,总是能够听到《高山》《流水》的声音,千年之前的人物,从琴的深处一个个走出来,与绿绮园的主人相会、相交。
在古琴漫长的历史上,绿绮台绝不是第一张无弦的古琴。
清代张随的《无弦琴赋》,是我读到的关于无弦古琴的最早文字。《无弦琴赋》的主人公,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东晋伟大诗人陶渊明。
因为没有记载,陶渊明琴桌上的那张琴显然不是名琴,而且,淡于功名,只在乡村陇亩间躬耕的布衣,也无力成为名琴的拥有者。陶渊明的古琴没有丝弦,也没有用于音阶标记的徽。每有客人走进篱墙,叩开柴扉,诗人便用家酿招待。酒酣耳热之时,五柳先生每每取过琴来,醉眼朦胧地虚按一曲。
闭目陶醉的诗人,早已看出了朋友们的诧异与不解。后来的《晋书》,也认为陶渊明“性不解音”,所谓的无弦空弹,只是故弄玄虚。
我在五柳先生的《与子俨等疏》中,找到了驳斥《晋书》的证据:
少学琴书,偶爱闲静,正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然有喜。尝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
陶渊明诗中,提及琴处甚多,“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弱龄寄事外,委怀连琴书”,“清琴横床,浊酒半壶”,连《归去来兮辞》中,也有“乐琴书以清忧”的句子。所以,在陶渊明那里,无弦胜过有弦,无声胜过有声,《幽兰》虽然没有声响,却如庭园的花草一样芬芳,《流水》还没有弹奏,却似屋后的小溪潺潺流过。
绿绮台琴弦绝于可园,一张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名琴,见过了太多的岁月生死,弹尽了天下所有的琴曲,它的衰败,是器物的宿命。绿绮台弦断之日,便是它的哑声之时。此后的岁月里,名琴化为铁石,只有邓尔雅,在绿绮园的夜深中,能够听到《广陵散》的绝响。
自古至今的琴家名单上,找不到“邓尔雅”这个名字,窃以为,邓尔雅是一个真正懂琴的人,他是绿绮台的知音,他以一介隐士的姿态,深藏在七弦之后。所以,哲人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句出自《道德经》的千古名言是绿绮台琴最早的注脚,后来李白的“大音自世曲,但奏无弦琴”,“抱情时弄月,取意任无弦”,陆龟蒙“垆中有酒文园会,琴上无弦靖节家”,司空图“五柳先生自识徽,无言共笑手空挥”,苏东坡“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的诗和欧阳修“若有心自释,无弦可也”的主张,更是为绿绮台与邓尔雅的结缘做了最有力的辩护。
七
古琴,是世界上唯一设置了密码的神秘乐器。在一个发声物体众多,丝弦簧管均可速成的快餐时代,人类离高雅七弦的距离越来越远,那些由阿拉伯数字组成的密码,只能用在金钱财富的防线上。
我在东莞居住的二十多年里,无数次进入过可园,在没有认识绿绮楼和邓尔雅之前,我只是可园的一个过客,那些古旧的青砖黑瓦,遮蔽了我的眼睛,隔绝了一张古琴的天簌之音。
在所有能够用美来形容的发声体中,只有古琴,才是乐器的化石。由于时光的古老,我们无缘见到曾祖父、曾祖母以上的长辈。对于吉他、长号、口琴、手风琴、管风琴、排笙等现代乐器来说,古琴,是它们遥远的祖先。
我曾经被七根细若游丝的弦和桐木板隔绝在声音之外,我与古琴的缘分,直到老年才冲破那道坚固的篱墙。查阜西,是掩护我逃出禁锢耳朵的电网高墙进入音乐世界的引路人。两年前,我在海天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修水县志》上,见到了这个令人尊敬的义宁先贤,他以古琴大师的身份为我解惑。
查阜西的故里,离我知青时代的下放地不远。在那个鄙薄知识和文化的混乱年代,我们这些所谓的读书人,无一人知道漫江公社的来苏大队,竟然是大名鼎鼎的古琴大师查阜西的籍贯。
查阜西一生致力古琴研究,民国二十五年的时候,即在苏州创立今虞琴社,主编《今虞琴刊》。20世纪40年代,查先生赴美讲学,传授古老的中国琴艺,一时轰动国际琴坛。
两年前我返乡时,专门去漫江寻找一个古琴大师的足迹,空手而归,毫无所获。对一个为古琴而生的人的追寻,只能来自纸上。当我在黄脆的文献中看到查阜西先生的《现代古琴曲传谱解题汇编》《存见古琴曲谱辑》《古指法辑览》《历代琴人传》等琴学著作时,立刻产生了高山仰止的崇敬。尤其是那部被琴学界誉为中国古琴学百科全书的《琴典集成》,让一个琴外之人五体投地。
查阜西先生的贡献在于,将七根古老的琴弦推陈出新,将虞山派的传统风格发扬光大,形成了个人清越、雅朴、富有韵味的艺术特征,复苏了濒临灭绝的古琴音乐。
天下所有的名琴,尽在查阜西的掌握之中。邓尔雅的绿绮台古琴,虽然不再续弦,但远在北方的查阜西先生,依然还能听到抱邝露琴殉国时的悲壮声音。这个与吴景略、管平湖齐名的古琴大师,最早在西方的学术圣殿里找到了中国古琴的足迹,当他提着录音机走遍中国内地,收藏起古琴的所有声音之后,他眺望到了与内地一河之隔的香港大埔的绿绮园,虽然无法近距离地与邓尔雅交谈,和绿绮台握手,却深为理解一张名琴的归宿。在查阜西的心目中,绝弦之后的绿绮台琴,再也不可能重复国难当头时的抱琴殉国,也不会再现惠州西湖泛舟时名人悲欣流泪的雅集了。邓尔雅和查阜西,是两个不曾相识的文人,他们所居之地,相隔数千公里,只是一张古琴,将两人的精神连在了一起。
1929年的绿绮台琴,静静地安放在邓尔雅精心构筑的绿绮园中。绿绮台琴一生中最安详的姿态,就是弦绝之后的面孔。绿绮台琴告别了可园时期门庭若市的热闹,也失去了泛舟湖上的文人雅趣。于无声处听惊雷,是对现实生活一种夸张的描述,对于有生命的古琴来说,“弦外之音”则是一个更准确的成语。能够发生弦外之音的古琴是七弦的精灵,它已经超越弦上发音的规律,而能够听出弦外之音的人,则是月夜里的樵夫。人世间许多不可能的事情,却在古琴深处发生,古人用了许多后人熟悉的诗句,描述了古琴的神奇:
莊周高论伯牙琴,闲夜思量泪满襟。(罗隐《重过随州故兵部李侍郎恩知因长句》)
借问人间愁寂意,伯牙弦绝已无声。(薛涛《寄张元夫》)
闻说萧郎逐逝川,伯牙因此绝清弦。(温庭筠《哭王元祐》)
知音既已死,良匠亦未生。 (邵谒《赠郑殷处士》)
真正的古琴,只与知音结缘,所以,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流传千年不朽。只是不辨音乐的耳朵,永远无法揭晓古琴与其他乐器的区别。
邓尔雅的诗文,许多都与古琴有关。他在《绿绮台琴》一诗中,就有“崇祯甲申毅宗烈皇帝御便殿鼓琴忽七弦俱断”的说明,而在《听琴师杨子遂先生弹琴》中,更有“群聪难索解,聋者独知音”的独特见解。邓尔雅从未以琴师扬名,却对古琴的理解深入到了骨髓,七弦的本质,被他用中医般的敏感手指,轻轻地触探到了脉搏的跳动。
古琴与其他乐器的本质区别,在于面对对象的不同。古琴只向弹奏者敞开内心,古琴美妙的声音,弹奏者往往是唯一的听众,在虚静中,弹奏者听见的是自己的心灵之音,而其他乐器,用声音取悦他人,听众以及欢呼喝彩的掌声多寡,则是对乐器和演奏者的最高奖赏。
古琴的美妙之处,还在于与其他乐器弹奏的差异。当中国的民族乐器和外国的西洋乐器在教材上指引技法的时候,统一、规范必然是书上的教条,而传统的古琴谱上,只标明左手按弦和右手弹奏的指法,音名、节奏则隐匿无痕,不同的演奏者按照各自的理解处理琴曲,演奏者和创作者身份的交叉变换,使琴曲在古典的意境中复活,变化多端,生机无限。所以,有论者认为,古琴具有不可再现的当下性,或许正是“琴”字底下那个“今”想体现的妙义。
邓尔雅终生浸淫在书画篆刻艺术中,他用触类旁通的灵感觉悟打通了个人心灵通往古琴境界的秘密孔道。他在《绿绮台记》中回忆了自己于光绪壬寅年(1902年)在潘氏缉疋堂与马平杨子遂畅谈古琴艺术和绿绮台琴流离命运的往事,为绿绮台的未来和绿绮园埋下了伏笔。
崔岱远先生在《京范儿》一书中真实地表达了古琴的境界,这些描述,正是邓尔雅、查阜西追求的人生方式。在真正的琴家那里,琴只是修养和雅玩,不是职业,也不是谋生手段,更不是在歌舞场里出卖的艺术。“琴人只在感触极深时才会去弹琴,他们的琴艺也只是献给能理解他的人,而不能去变成钱。”
弹琴是一种境界,听琴同样是一种境界。弹琴和听琴都是极讲究的事情,而精于此道的人也都是内心高贵的人。他们或许现在很穷,但他们永远也摆脱不了精神贵族的派头和文人的影子。他们深信“一箪食,一瓢饮,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权贵们请他们弹琴也必得在相互尊重的氛围下大家一起玩儿。即使有些馈赠,也不能明码标价。若真是有了标价,那琴家也就真不乐意弹了。而所谓的雅集,也只限于三五知己。要是有陌生人在场,是不会轻易弹的。必得先坐下喝茶攀谈,若是投机,再摆琴,焚香,弹奏。若不对路子,也就找个托词婉言谢绝了。因为琴声是无处逃心的。琴者的情绪、心思,乃至气质、品性,会听的人全听得出来。谁又肯轻易对陌生人抛露心声呢?
八
邓尔雅和邝露,都是绿绮台琴的贵人。遇上一个贵人,是一张名琴的幸运。对于绿绮台琴来说,最好的贵人,并不能保它一生无忧,而是竭尽全力爱护它,在它遇难之时,奋不顾身。邓尔雅,作为绿绮台琴的贵人,更是在大难来临之时,两次让绿绮台琴化险为夷。那两次危难场面,均记录在《邓尔雅年表》中。
1920年,是绿绮台琴与邓尔雅结缘的第七个年头,没有任何征兆,预示绿绮台琴的第一场灾难。杨宝霖先生在《邓尔雅的〈绿绮园诗集〉》一文中有简略记叙:“是时粤中政变频繁,尔雅广州寓所遭兵火,书画焚烧殆尽,幸绿绮台琴无恙。1922年,尔雅携眷避地香港。”(《容庚容肇祖学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1920年的兵燹,对于邓尔雅来说,是一次重大损失,而对于绿绮台琴,则只是一次虚惊,或者一次灾难的预演。杨宝霖先生的记叙虽然简略,却透露了邓尔雅未来行动的某些信息。两年之后,邓尔雅带着家眷离开广州转往香港,躲避乱世,更多的是出于绿绮台琴的安全。
一个将古琴作为自己生命组成部分的人,选择香港避居,当是他视琴如命的必然逻辑。从邓尔雅用象牙缩刻一对绿绮台琴作为女儿嫁妆的行动中,所有人都可以看出绿绮台琴之于他的价值和意义。所以,“1929年,邓尔雅以治印、卖字所得,积资买地于九龙大埔,构小园,名为绿绮园,以中贮绿绮台琴”,就成了一个文人的选择。
邓尔雅用诗表达了他为绿绮台琴建筑暖巢的心情:
宋时庐墓锦为田,累叶犹容近祖先。
堂窄高吟暖岚气,岛荒长物富春天。
剩残山水非生客,勾股梅枝入梦圆。
床左囊琴虽弗御,不妨高举契无弦。
此诗之前还有八句。除了为绿绮台筑室告成纪念之外,邓尔雅还为能够近守位于元朗葵涌的祖墓而欣慰。
八十多年过去,绿绮园成了纸上描述的建筑,后人无法通过实物看到那座寄托了邓尔雅心血的房屋。1937年7月的颶风,是一切人工建筑的杀手,绿绮园不幸葬身在风暴中。从诞生到消失,绿绮园,只在香港大埔存活了六年。
1937年飓风的威力,没有视频资料记录那些恐怖的现场,在文献的记载中,邓尔雅的绿绮园屋顶被吹跑,只剩下四堵墙壁,藏书尽毁。在风灾面前,邓尔雅的心碎成了一堆瓦砾,但是,奇迹却也在废墟中出现,他视同性命的绿绮台琴,安然无恙。
“奇迹”,都是无法用语言解释的现象,在幸运面前,邓尔雅没有感恩上帝、佛祖、菩萨、鬼神等通灵的偶像,他认定的只是一张名琴的气节,那是一个抱琴殉国者英魂的护佑。
风灾之后,邓尔雅立即迁居九龙,他要为绿绮台寻找一个更安全的家。冥冥中,他得到了来自邝露的暗示。他用《丁丑七月飓风大步小园藏书被毁感赋》表达了绿绮台琴劫后幸存的庆幸。
绿绮台琴,在邓尔雅心中,已经成为抱琴殉国的抗清英雄邝露的化身。对一个英雄的崇敬,通过一张古琴折射,邓尔雅的高尚之举,同样得到了朋友的尊敬。
曾经在惠州西湖游船上参加过叶龙文召集的岭南名家雅集的丹霞别传寺和尚今释,在聆听过绿绮台的声音之后,精心创作并手书了长诗《绿绮台琴歌》。邓尔雅的好友潘至中,在广州的书肆中见到这幅墨宝,知道了绿绮琴藏于邓尔雅处,当即买下长卷。后来邓尔雅来潘至中家中探访,看到《绿绮台琴歌》欣喜不已,当他读到“南社风俊邓先生,求琴飞涕哀虫蚁。莫道无弦曷若弹,望海筑园惟景止”等诗句时,感慨唏嘘。
邝露当年,拥有两琴。在邝露的心爱之物中,绿绮台和南风,是一双同胞兄弟。邝露殉国之后,手足分离,血肉撕裂,邓尔雅能够感受到古琴的疼痛。如今的绿绮台,成了琴的孤儿,再也无人知道南风的生死下落。
绿绮台琴,还有另外一重意义上的琴缘。在所有的琴史文献中,绿绮台还和春雷、秋波、天蚃并列为岭南四大名琴。岭南四大名琴,在琴的家族中,就是一母所生的同胞手足。邓尔雅在绿绮园寂寞的长夜里与孤独的绿绮台琴沉默相对的时候,常常想起春雷、秋波、天蚃,却不知它们流落在何方。
邓尔雅从未想过,绿绮台和秋波、天蚃,会有团聚的一天。
1940年,广东的一些文化精英被日本侵略军的战火赶到了香港,许多珍贵文物也随着它们的主人,来到了这个暂时安全的地方。绿绮台和秋波、天蚃相会的因缘,就在这个时候产生。在中华文化协进会的倡导下,邓尔雅带着心爱的绿绮台琴,参加了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举办的广东文物展览会,绿绮台和秋波、天蚃,一同在这个艺术氛围浓郁的展览馆中相会,接受无数观众惊喜的目光。著名的岭南四大名琴,除了春雷缺席之外,其他三琴,在文化的圣殿里,享受了千载难逢的荣耀。而此时的唐代名琴春雷,被张大千带到了万里之外的异国巴西,它缺席了这场古琴的盛会。
古琴,不仅是一种乐器,更是一种由木头、丝弦和精神组成的生命体,爱琴之人,则是它们的天使和护法。只是由于人的寿命短暂,古琴终不免易主更弦,但是它们的故事,总是和人融为一体。
邓尔雅七十二岁高龄时病逝于香港。在最后的日子里,绿绮台琴静静地陪在病榻旁边,邓尔雅时时抚摸,依依不舍。他以一种异于常人的方式,与绿绮台琴告别。
五年之后,香港大公报举办了一次隆重的广东名家书画展,邓尔雅的儿子将父亲所藏绿绮台琴和今释和尚的书法长卷《绿绮台琴歌》展出,引起了文物界和艺术界的轰动。已经蚀于虫蚁而喑哑多年的绿绮台琴,又一次复活,让人看到了殉国的烈士和英雄的气节。
九
关于绿绮台琴的下落,有多种线索。陈莉女士认为“此琴由其后人捐赠广州博物馆”的说法似乎更让我信服。
我不是琴人,只是出于一个东莞市民的情感和写作者的需要想看一眼那张邝露殉国时在现场见证的古琴,想触摸一下邓尔雅先生留在琴上的余温。可是可园的绿绮楼上,只剩一个空阁,不见了绿绮台的影子。
惆怅,是可园,也是所有游客无法避免的遗憾。
我在灯下为邓尔雅和绿绮台琴绞尽脑汁的时候,一条信息和视频跨越千山万水到达身边,古琴的乡音将我带回到了义宁,在故乡的舞台上,游子终于见到了查阜西先生,听到了一个古琴大师遥远的声音。有史以来,这是义宁首次以古琴的名义,为一个被忽略了的先贤正名。在查阜西古琴艺术座谈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古琴艺术家和古琴研究学者,一致肯定了查阜西先生“传统琴学的总结者和现代琴学的奠基者”的地位。“查阜西在古琴造诣上是最为杰出的,没有查先生就没有我们这一代琴人对古琴的延续”的评价,让一张古琴穿透百年时光,在义宁的幕阜大山中水落石出。
这场迟到的古琴盛宴的高潮,是一台名为古琴经典的音乐会,在富丽堂皇的大剧院舞台上演奏的《梅花三弄》《离骚》《广陵散》《渔樵问答》《流水》《乌夜啼》《阳关三叠》,虽然古意盎然,但却没有了空灵的意蕴。在古琴时代,所有经典的琴曲都是在面对知音和个人内心的情境下完成,月夜、空山、幽篁、冷雨、古渡、断桥……这些自然界中的景致,在琴声里化作了永恒的意境,真正的琴人,不会在权贵和金钱面前低头,真正的古琴,不会在闹市和俗人面前发声。
我不相信华丽的现代化剧场是古琴开言的最好场所,我怀疑最懂音乐的耳朵,也未必能在五光十色的舞台上领悟到高山的巍峨,听见山泉飞流的声响,知音不在,琴弦再也不会突然崩断。在八百里幕阜大山中,在辽阔的义宁故土上,最适合古琴弹奏的场所,应该是偏僻幽静的漫江来苏,能够成为古琴知音的听众,应该是那些勤劳朴实的乡人。一个游子对权力宣传的不敬,本质是对艺术和大师的景仰。
古琴的身体上,找不到装饰的金属,但七弦的声音,却全是骨头。典故“雪夜访戴”中的戴逵,以琴为修身之道,而不作艺人之技,多次拒绝大宰武陵王司马晞弹奏古琴的邀请,在司马晞的纠缠之下,戴逵摔碎古琴,留下了“碎琴不为王门伶”“别鹤凄凉指法存,戴逵能耻近王门”的千古佳话。
从遥远的故乡义宁回到东莞,能够为我洗去一身疲惫的当是音乐。我踩着清朝的青砖登上可园的绿绮楼。为绿绮台而来的人,只会得到失望。可园的管理者们让绿绮台琴回归的设想一次次破灭之后,只好请一个王姓琴人仿制了一张绿绮台琴。那张后人斫制的古琴,以替身的姿态,虚拟在古旧的岁月中。
真正的绿绮台古琴,只能在岁月深处寂寞,没有人看得穿它的心思。幸好琴事频繁,爱琴之人,总能在新闻中得到慰藉。
2018年8月8日,号称古琴拍卖价格之最的古琴松石间意,将离开北京的保利艺术博物馆,不远千里来到南粤,在肇庆庆祝广东省第十五届运动会。这张898岁的古琴,由于宋徽宗的御制和乾隆的御铭,在古琴拍卖史上以1.3664亿元独占鳌头,创造了世界古琴和世界乐器的拍卖纪录。
在《羊城晚报》看到这则消息的同时,我立即联想起了邓尔雅的绿绮台琴,想起了查阜西尽一生心血搜集的一百多首古琴曲。每一张名琴,都有着不同的命运遭际,在特殊的器物后面,活着的都是人物。
焚琴煮鹤,是汉语中最令人恐惧的一个成语。这个在李商隐《杂纂》中与清泉濯足,花上晒裤、背山起楼、对花啜茶、松下喝道并列的煞风景之举,却令我想起残暴的秦始皇和十年浩劫。拿琴当柴烧,把鹤煮了吃,只是人类失去了理智之后的疯狂。绿绮台琴一生中,有过战火的历险,有过风灾的考验,所幸它都一一逃脱,没有成为焚琴的悲剧。
一千多年前,就有人用詩歌见了古琴的命运。唐朝赵博在《琴歌》中看见了世道光阴:
绿琴制自桐孙枝,十年窗下无人知。
清声不与众乐杂,所以屈受尘埃欺。
七弦脆断虫丝朽,辨别不曾逢好手。
琴声若似琵琶声,卖与时人应已久。
玉徽冷落无光彩,堪恨钟期不相待。
一张名琴,无论出身如何高贵,无论血缘如何正统,总免不了断弦、蒙尘、烂尾,直至腐朽。从物质层面来说,没有一个人的寿命是古琴的对手,但千年过后,琴不复存在,但琴背后的人物,却在岁月的尘埃中站立起来,栩栩如生。
责编:梁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