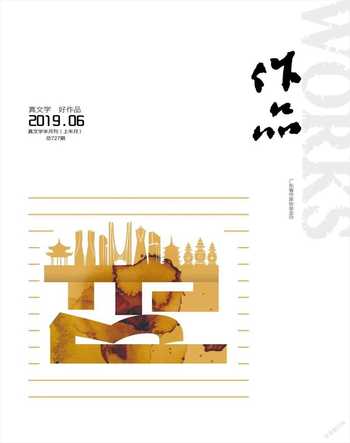读黄礼孩《抵押出去的激情》(评论)
周晓坤
黄礼孩的诗集《抵押出去的激情》,从内到外异常朴素简约。当你翻开书页,轻轻越过栅栏,蓦然发现,原来这片诗歌花园深处芳菲嫣然,根深千尺,根源于土壤中强大的诗歌张力与精神力量。诗集中不设置章节的划分,但风格、内容主题大概相似的诗歌放在一起,使阅读仿佛观山,起伏交叠,各有千秋,内心也随之微波频起,领略万般。我喜欢这种自由的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慢慢游吟,也认识了诗人的很多面:忧郁、热情、出尘,抑或清醒……真挚且多元。
“你从不制造盲目的差异”,是诗集中诗人送给友人库什涅尔的句子,我想用来形容黄礼孩也是贴切的,在种种对比观照之中,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完整的”诗歌世界,在其中,没有一种碰撞是多余的。罗吉·福勒说:“凡是存在着对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力量、冲突和意义的地方,都存在着张力。”黄礼孩的诗歌,便在种种延伸与聚合之中,蓄积着巨大的能量。
一
他总是于尘世的细微处,寻找着云层中的钥匙。
黄礼孩的诗歌理想是高而纯粹的。至于那些形而上的诗思究竟具体指向什么,在诗作中,他没有给出明晰的答案,只是运用隐喻,将它们悄悄地藏在云朵、光、火焰、大海、牧场、星空等原始性意象之中,尝试对“云中之境”进行想象性的描绘:“在虚无之上,花朵抬头,骑着白马”(《放荡的心应了天穹的蓝》)。诗歌之所以为诗,正是源于这层可爱的阻隔,但在随笔中,大概可以发现黄礼孩对诗歌终极追求的解释:“它所辐射的词面有良心、正义、大爱、勇气、坚持、真诚、独立、自由、热爱、明亮、宽阔、唤醒、丰盈、人性等。”那是哲学层面的追问,是闪光的道德,是对不设功利的美与自在完满的追求。
在黄礼孩的诗歌中,强烈的对比始终存在。有时候,这种对比体现在光与色的反差之中,例如光明与黑暗、黑色与白色:“光线剪出形态异样的影子/黑绿分明/一树树的梨花晃动/轻柔如微小的白色之虹”(《风吹草叶参差不同》),这只是从意象的表面含义来看。而有时候,看似对立的两种意象内涵互成指涉,造语奇特。例如《一匹马亲吻大海》:“火躲在深山泉水的身上”,乍一看,仿佛水火不容,却慢慢发现,泉水自大山深处喷涌不息的生命力与泠泠发亮的光潋,用火来形容最是妙不可言。在《灵魂》一诗中,“金钱、商品、噪音和废气”与“民谣、孤独、野鹤、春声鸟语”等词句交叉出现,反差强烈的场景不断替换,诗人对于现代性弊端的隐忧也不言自明。
诗人作为一个叙事、抒情的主体,不是单单跻身、悬挂于高高的光明之境进行俯视的,他也和我们每个人一样,置身在尘世之中,饱尝污浊、压抑、琐碎而依旧向往飞升。原始性自然,则是他所选择的飞升的依凭。在诗句中,这种向上飞升的向往之情是无法掩饰的:“向上,与未融化的天际交织(《摆渡向你的黎明》)”;“向日葵是这个黄昏唯一的野兽,是狂野之箭”(《野兽》),富有直射云霄的气概。用了很久去尝试理解,为什么在黄礼孩的诗歌中,深黑沉寂的海底之中,也会有火焰和光明的存在,直到读到《火焰之书》:“明天再柔弱的大海/也会升起太阳/海底的火焰之书/纵容了我的心/动身去朝圣”,方才明白,即便在黑夜,阳光也从未逝去,它只是沉入了大海,去照耀另一面的世界。必先有下沉的勇气,才会有飞翔的姿态。这种经过陌生化處理的联系,使读者驻足、流连于诗意,进行诗性思考,进而也将问题引向我们应该如何诗意地思索、面对眼前的生活。灵与肉双向在场,使诗人的意识与价值立场更加明晰,表意也有了更深刻的真诚与真实。
“自然”对于黄礼孩而言,不仅仅是生态层面的含义,更有自在自得的意蕴:自然是一个熟悉亲切的老友,诗中的“我”,亦是自然中自由浪漫的个体存在,人与自然平等而和谐。在《野火》中,有一句“他的忧伤,迷宫一般抵达花溪的腹部”。仅仅是水倒映出诗人忧伤的面容一事,经过黄礼孩诗艺的加工,仿佛迷宫般复杂的心意也得到了拥抱,便有了与自然推心置腹、心心相印之感。又如《光线》一诗:“仿佛把我点燃/被你呼吸/在甜美的光线里。”在寻常视界中,多以人为中心,少有草木呼吸人、感知人的先例。可见,在黄礼孩那里,人与自然是真正融为一体、和谐共生的。另有一些诗歌,只是一种随手的浪漫,是诗意的缓缓流淌,别无其他深刻的意义贴附。譬如《哥特兰岛》,只是看似慵懒随意地写到了海岛上一些寻常景色,而诗歌的美感,宛如倾泻的日光,也像袅袅氤氲的炊烟,慢慢倾吐着一种万物相宜的状态。“红烛迎人,俊得江山助”,自然之于黄礼孩来说,便是如此,教会我们如何换一种眼光来观看世间万物。
黄礼孩提倡“完整性写作”,旨在抛却事物表层的光魅,直达本质更高层的天空,又兼他所使用的意象多原始性的自然之物。或许有人会说,这样的诗歌追求过于理想化,未能与中国当下现实物象发生密切的联系。但其实,正如黄礼孩在随笔中说的:“诗歌的现代性依然是一个问题。现代性不在别处,而在思想力那里,在思想力的批判那里,在思想力的速度那里,在思想力的拓展上。”在另一个层面上,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对于现代思想的抵达呢?他选择了在自然的细微处中,寻找最接近本质的真理,寻找高蹈的理想。那不是一种简单的回避,在这一上一下之中,有着广阔的空间让诗心驰骋,理想看似高不可及,却实在地存在于每一天的生活经营里,蕴含着巨大力量,扭结了尘世与诗心,从现有的世界生发出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思想。
二
他总是努力攀登,涵养环顾万物的眼界与胸怀。
“少年爬上南坡/看见光源向四个方向延伸/他受到暗示/召集体内的云朵”,《牧云》中的牧羊少年,站在山坡,看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光明。作为诗人,黄礼孩始终努力拓宽自己知识的来源,将更多的美融汇在诗作中。在更高的视点上,他能够看到传统,也能够看到当下;他能够看到本土,也能放眼世界;他能畅饮缪斯赐予的甘泉,也能嗅到沟渠中的腐恶。如此,他必然见证了许多有意味的对比,这样的诗歌创作才有了张力。诗歌不能太轻,它需要这种力量。走在黄礼孩的工作室,四壁皆是接顶的书架,各种类别的书籍陈列其中,内容涉及古今中外,便不禁想起他曾说的:“谁在阅读中获取开启思想的钥匙,谁就拥有一个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世界。”想起他在《诗歌的风度》中,从里尔克的超验风度,谈到古老的《道德经》。源源不断的才情,也多多得益于广博的知识。
诗歌是世界性的,黄礼孩自己也在访谈中表示,西方诗歌、理论、文化的影响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在阅读诗作的过程中,却常常能感受到来自中西两方向的文化感染。譬如《黄昏,入光孝寺》,前半段诗中,梵音、灯火、菩提树、冥想,语言简净,书页中散发出香火的神秘气息,把人们带入禅境的安宁;后半段中,波兰教堂、波罗的海、唱诗班,又带领读者进入基督的神圣世界。然而,这两种文化,或说是宗教元素,最终都融在同一种和谐的宁谧之中。这种宁谧不同于“月出惊山鸟”那般绝对无声,诗歌中每一个字眼都是轻轻的:“波罗的海的声音正一层层落下来”,海浪轻推之间,诗人利用纯净之音,带领读者找到内心真正的安宁。同样还有《木兰花必是美的——致扎家耶夫斯基先生》一诗,开篇推杯换盏的盛宴极具现代感,笔锋一转,又引向窗外的枝丫:“木兰的身世/我了解/它原产于中国/曾作女郎来过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笔下/现在/木兰有另外的岁月”。借中、波两国皆有的木兰花,表现了诗美的超越性。
诗人表现出的本土诗韵,不只是在面对国际诗歌环境中才生发出来的,也不是运用几个诸如“白居易”“宣纸”这样带有中国古典元素的词就完成了的,碰撞与交流存在于形式与更深层的精神内核中。黄礼孩诗歌中与自然相交的自在生命状态,带有天人合一的温润;在鸟鸣声中得到关于虚空的体悟,又有一种出尘的玄妙。作为一个带有个体潜在经验的读者,哪怕在一些以西方世界为底色的诗句中,我的脑海中也总翻出不同的诗句。“隐匿起来的情人”,使我想到“爱而不见,搔首踟蹰”;“苔藓/它那么微小”“阳光偶尔对它露出笑容/很快又消失”,又让我想到“白日不到处”那如米小的苔花。可是,再翻几页,看到陌生化的奇妙造喻,设置得精致精准,看到阿尔卑斯山脉,眼前浮现的便又是鲜花果园、油画般美丽的长裙金发少女,十字架与教堂钟声,这其中总有一种奇妙的火花难以言喻,不同的美在此处堆叠、契合了。令人讶异的是,中西文化的气质,就这样自然而不着痕迹地融会在黄礼孩的诗歌创作中。本土与国际,也许从来不是截然冲突的,它们在黄礼孩诗作中形成了有趣的互动,造就了独特的美学风格。诗人能够带给我们多元的美学享受,也许正因为他始终努力站在更高的视界,在诗人自己都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四面八方的美尽收眼底,再经由他的笔二次绘出。
或许如黄礼孩所说,我们大多数的时间是处在中国的文化氛围之中,但也要具备世界性的眼界,走出自身的狭隘,注入现代意义的力量。我一直相信那行诗句,“美的事物从来都是共享/诗歌亦如斯”。语言、宗教信仰也许有界限,但诗意却常常相通,哲思的神圣性常常相通。不同文化韵味在黄礼孩诗歌中的碰撞、融合,使我再次相信诗歌的容量,相信短短几行文字,可能反而包含了无尽的所指。
三
他总是以温柔的力量,发掘无用中的大用,做一个笃定的筑路人。
黄礼孩的语言是温柔克制的,正像他待人接物的谦和亲切。他对于黑暗之境的书写是有限度的,从来没有过疾言厉色,也没有审丑式的细致刻画,他只是用哀伤而严肃的眼眸凝视着:“是我从未见过的/一个黑色的梦”(《苔藓》),“一张张病态的脸/像一座座飞翔的坟墓”(《沉下去是为了浮出海面》),“猫头鹰躲在口袋里/幽灵一般的视像/随时把幸运带入不祥的黑色的梦境”(《条纹衬衫》)。另外,他的诗作中有着坚定的对抗性——他一直在用文字对抗时间,对抗美好事物终会被消磨殆尽的命运,对抗黑暗之于光明、自由的打击。人生中,除了上帝赐予我们存在于世间的时光之外,我们什么都留不住,带不走,韶华宛如朝露般难以长久:种子会腐败,天鹅会死去,熟悉的亲人也抵不过时间的召唤。珍惜光阴的唯一途径,便是赋予时间以意义,抵挡丑恶、追求光明。“不敷衍自己的理想/才不死于时间的哀伤/去爱这阴沟里的黑暗/又穿过它们/把不安而闪烁的对称/带到尘埃之上/捍卫尊严的/一定是那个被叫做命运的词/纠集一群暴动的文字将岁月戳穿”(《风中谈话》)。柔软温和,饱含哀婉的语句之中,也不妨拥有暴动的力量,化为文字感动心灵的行动力。
黄礼孩曾说,诗歌是离商业化最远的文体。我想,这虽注定了诗歌的孤独,却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浸染污浊。一如“成全了你的一无所有,却被大地和天空予以怜悯”,诗歌是贫穷的,也是最富有的艺术。而黄礼孩却仍在努力,发掘这些“无用事物”中疗救的作用,做无私的船夫,希望将更多的人渡向彼岸的世界,哪怕,只是在船头遥望一次彼岸世界中不一样的花圃,看见凡俗之外的存在。于坚说:“所谓好的诗歌,是那种在人类的阅读历史中,能够以原创的言说方式、鲜明的个人风格感应心灵,激活感觉和普遍经验的诗歌,所谓‘具体的普遍性’。”为了诗歌理想,除了自费办杂志、诗歌节,策划创意性的诗歌活动等,黄礼孩的诗歌还做到了具体性经验与普遍性诗思之间的结合。黄礼孩在写作时也有一些偏爱的意象,譬如大海中的鱼,这或许与他生长海滨的家乡经验有关。在诗集中,“鱼”这一意象出现了11次,而借鱼儿抒发的诗意不尽相同。有时,他用鱼儿的逝去折射自然生态的破坏,“夜的刀刃是否伤害到梦的心脏/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把鱼放回大海/没有人活在一场好当的春天里”(《没有人把鱼放回大海》),晒在竹竿上的鱼,忍受着漫长的情非所愿的沉默。有时,诗人利用大海与鱼儿相生相依的关系,表达一种挣脱现世桎梏的渴望,“鱼渴望被海粗暴地抛弃”(《飞翔的鱼》)。总之,都在具体事物中表达了现代社会中带有普遍性的焦虑。还有一些与爱有关的诗,从题目与事件来看,是非常具体的:2月17日,等一个人的电话。长诗娓娓道来,爱得真切与等待的焦虑,在最后的泪水中激起了读者强烈的回响共鸣。他有着整合普遍与特殊的天赋,形成了一种可感而保有个人风格的诗歌。
如此,他用诗歌引起了读者对此岸的思考与跳脱,让诗歌最大程度地进入日常生活,成为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一本诗集,温和安静地摆在那里,它并不是简单的几行抒情性的文字,它意味着对被日常生活消磨而略显迟钝的感官的一次唤醒,意味着自我审美的革新,它的力量类似海德格尔用艺术对大地的看护,与诸神和万物本质共在的状态。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人生经验,并没有什么所谓“合格”的读者,也没有哪一种理解可以被说成是错误的。一首诗写了什么,缘什么而触动了诗人的心弦,也许只有诗人自己清晰地知道,但这也许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的诗歌怎样能如一滴水渗入我们心中园圃,能否开出一朵花来。当我们喟叹诗歌地位失落之时,黄礼孩仍在坚持,我们是有可能摆脱这个世界的束缚与异化的,因为我们是有主体性的人,因为我们还有诗歌。在这个意义上,黄礼孩是倔强的,他的坚持,使他在现世与云朵之间铺就的虹桥愈发宽阔、长久。
尘世与天空;古典与现代,本土与西方;柔软与力量,此岸与彼岸……看似对立的双方,对于黄礼孩的诗歌起到一种延伸、拓展的效果。它们彼此分离、告别,使诗歌有了表達的空间;又最终聚合统一,将各种表意凝集在一起。
皮埃尔·马舍雷曾在《文学创作理论》中提及,批评应勇于面对作品的“本来面目”,不为“应然”作解作注,的确,诗歌是最不需要营销的文体了。在此,我便是怀着这样的努力,作为一个最普通而没有天赋的读者,从自己的感悟与阅读出发,尝试按下黄礼孩诗歌世界的门铃。寻找和遗失,皆是人生常态,值得庆幸的是仍有人愿意热爱,那么,他是可敬的。
参考文献
[1]黄礼孩.抵押出去的激情.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2016年
[2]黄礼孩.午夜的孩子.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
[3]黄礼孩.我爱它的沉默无名.第五届中国赤子诗人奖专号,2017年6月1日
[4]黄礼孩.谁跑得比闪电还快.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年
责编:李京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