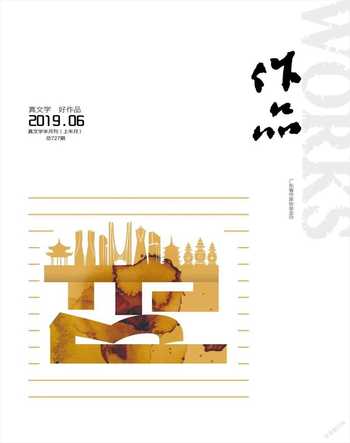黄礼孩:诗是感性的宗教(评论)
申霞艳
黄礼孩温和、谦虚、耐烦,他那标志性的微笑让人安心,那笑意中有一股定力,是从他的心里流出来的。他的沉默也别有意味,他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黄礼孩这个名字仿佛是个暗示,让他始终保持住可贵的童心,即使在他因名声大噪而得意忘形的时刻,也依然能从他清洁的大眼睛中感受到他心灵的澄澈光芒。
我在《花城》杂志工作的时候,黄礼孩的办公室也在水荫路上,经常会接到他的邀请电话,让我去陪远方的朋友一起午餐,或是夜里约几个好朋友同看一场电影。我们看电影的时候,礼孩泡茶、搞水果,赶专栏,样样不误。礼孩有特别的亲和力,他的身边总会有几个来自不同朋友圈的人,比如摄影师、导演、编剧、雕塑家、油画家、舞蹈家、各式生意人、老乡,最多的还是诗人、作家,必定会有美女。他能将不同职业、兴趣的人发展为诗歌的朋友,仿佛一位生活创意大师,黄礼孩的饭局就是跨界、共赢。他就像哪吒,有三头六臂,可以同时开展九项工作而不感烦躁,其中必有高于常人的人生智慧和意志。“定”在我看来,几乎是消费社会最为稀罕的品质,只有心有所属方能“定”,“定”让人专注,有耐心、闲心和诗心。
黄礼孩将左边的心给了宗教,右边的心给了诗歌,这是他立于风口而不移的根基。于他,诗歌乃感性的宗教,宗教是理念的诗歌,内部要求是同一的,就是虔诚!而教徒的虔诚正是黄礼孩与其他人、诗人区别开来的标志。虔诚让他的眼睛落在低处,紧贴大地,那些细小的生物、叶子和风吹草动都得以感知;他的心向着苍穹,与星星和阳光一起律动。世俗与崇高之间的张力构成了黄礼孩书写的对象。
大批评家布鲁姆在《读诗的艺术》中开宗明义道“诗比其他任何一种想象性的文学更能把它的过去鲜活地带进现在”。艾略特在著名的文论《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指出诗人最杰出、最个人的部分依然受到传统的有力昭示,我们不仅要关心传统的过去性,更要关心传统的现存性。实质上,作为一个古老的诗的国度的后裔,我们既感到传统资源的丰厚,也常常感到推陈出新的困难,因为农业文明的诸多意象都已经被祖辈书写陈旧,就像土地千百年来被反复耕耙一样。“年年岁岁花相似”,诗词大会上飞花令的游戏既让我们领略了诗歌的包罗万象,也让我们感慨传播的残酷无情。
诗人是在与千百年来的传统竞争,当然更是与自我竞争。留给当代诗人的抒情空间似乎十分狭窄,所以我们必须另辟蹊径,将意义生产方式陌生化、当下化、个人化。黄礼孩的《苔藓》就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苔藓,它那么微小
像一粒粒沙子
没有人知道它们的身世
苔蘚习惯用潮湿的眼睛看一切
呼吸腐败的空气
它坐在暗处
似乎在等待
阳光偶尔对它露出笑容
很快又消失
只留下森林巨大的阴影
是我从未见过的 一个黑色的梦
这让我们很容易想到清代诗人袁枚的励志诗《苔》: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牡丹,花之富贵者也”,“世人甚爱牡丹”,袁枚以此为背景,吟咏微小的苔花,肯定低级植物的本能,鼓励读者去爆发内在的生命力。当黄礼孩面对苔藓,语言的幽灵、传统的阴影折磨着他,诗人“轻轻地把世界从另一面转过来”(《音乐 瞬间的风》),于是,他找到了再度书写的缺口,在袁枚诗歌的基础上将意象掉转,进而咏叹苔藓的不求闻达,安然自若。黄礼孩将苔藓人格化、自我化,“没有人知道它们的身世”,看来随意之笔,却通向诗人广阔的无意识,歌唱无名者和卑微的事物。“苔藓习惯用潮湿的眼睛看一切”不仅写出了苔藓的体征,也写出了诗人眼中的泪水。“一切景语皆情语”,是诗人的泪眼赋予了苔藓“潮湿的眼睛”,黄礼孩对贴近土地的苔藓亦爱得深沉。苔藓固然也等待阳光的恩赐,同时甘居森林的阴翳之中,与泥土贴心贴肺,交换心情,做属于自己的黑色的梦。苔藓的背后是诗人之眼、诗人之心,颇像一幅自画像,默默地追求人世间的美德。“诗言志”,我将这首诗理解为诗人黄礼孩的明志诗,他以苔藓传达心声,以苔藓的生存处境自喻,将自己的人格融进浩大的隐逸传统之中。这首诗引导我们去关注事物的阴面,去关注广大的无名者和沉默的大多数。诗评家李悄梅就谈论过黄礼孩喜好使用细小的意象,比如苔藓、海棠、蚂蚁等。
在黄礼孩的诗歌世界,低处乃高频词,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上善若水”。诗人感触良多,愿意追随流水的梦想,去观察低处、书写低处、赞美低处。低处是黄礼孩重要的叙事空间,因为低处虚空,有容纳力,低处踏实,有承受力;就像大地、河谷承接万物,藏污纳垢然而孕育新生。荷马在《颂歌》中唱道:“我要歌颂大地,万物之母,坚固的根基,最最年长的生物。它养育一切在神圣的土地上行走,在海上活动和天上飞翔的创造物。……”向你致意,大地母亲,繁星密布的天空的配偶。请为我的歌而友善地赐以令人欢欣鼓舞的粮食吧。荷马的歌颂有力地启动了歌谣的方向。
黄礼孩承接了这个伟大的诗歌传统,开启面向低处的写作。长期关怀细小的事物使他有能力为低处的、日常的、不起眼的事物赋神。比如《窗下》:
这里刚下过一场雪
仿佛人间的爱都落到低处
你坐在窗下
窗子被阳光突然撞响
多么干脆的阳光呀
仿佛你一生不可多得的喜悦
光线在你思想中
越来越稀薄 越来越
安静 你像一个孩子
一无所知地被人深深爱着
在这首广为传诵的诗中,“仿佛人间的爱都落到低处”就是诗眼,赋予了整首诗以光,而“落到低处”乃发光体,引人遐想。如果改成“这里刚下过一场雪,仿佛爱洒落人间”也成立,但意象单一,缺乏层次,没有了立体感和延展性。记得里尔克曾经写道:“雪花上千次落向一切大街”,这就是上天怀有的伟大的齐物意识,是对古典诗歌执着的田原意识的更新。而黄礼孩的诗表达了人道情怀。大爱总是洒向人间的疾苦,洒向低处,洒向远方……爱在低处,眼在“低处”,谦卑之心亦在低处。在《飞鸟和昆虫》中,黄礼孩夫子自道:“我一直在生活的低处;”又如《劳动者》:
到处都是缺乏雨水的生活
恍惚的下午 一个从乡下来的劳动者
拿着石头 蹲下来
看一群蚂蚁在搬家
教堂的钟声
飞过了建筑群
上城、下乡,上下是社会地位的尊卑,乡下是低处。乡下来的劳动者会蹲下来,降低视角,与低处的生物平等。低处,只有低处才能看见蚂蚁搬家,只有低处才能聆听神的召唤,只有在低处,人才能领略上帝的意旨和慈悲。神性和尘世并不违和,它们亲密无间。比如《远行》:
母亲病后
她像坐一次慢船去天国
她的航行
越来越远离她的身体
她离去之后
我在海棠树下望着蓝天发呆
一夕之间
命运早晨给予的
傍晚又收回去了
疾病就像一艘慢船,让人颠簸不安,度日如年。“远离她的身体”让人感受分离,既是母亲灵魂与身体的分离,也是母亲与尘世、与亲人的分离。“一夕之间/命运早晨给予的/傍晚又收回去了”将整首诗提升了,个人丧母的哀痛被融入到广阔的历史时空之中。死亡作为生命的终点赋予了全部生命以意义,因为整个生命的道路在回忆中清晰可见。死亡乃宗教的出发点,也是诗歌和一切艺术的出发点。宗教和艺术拓展我们对人生的感受和勇气,尤其是面对命定的终有一死的事实。早在17世纪,约翰·多恩就在布道文中写道:“我们的整个人生只是一个插入句:我们接受自己的灵魂,而后再还回去……”终极意义上生命具有被动性。我们在面对终极的被动的生、死中展开想象,就像博尔赫斯写死亡“像水消失于水中”,像泰戈尔写飞鸟“天空没有留下鸟的翅膀/但我已飞过”。诗歌能够将转瞬即逝的瞬间纳入亘古不变的时间隧道之中,将个体的生命视为人类千年历史中的一环。在《飞鸟和昆虫》中黄礼孩写下具有智慧的人生感悟:“我知道飞得再高的鸟/也要回到低矮的树枝上……我知道再小的昆虫/也有高高在上的快乐……”
黄礼孩的诗歌中密布着许多让人难忘的比喻,这是对日常事物的偏离,语言从实用的逻辑偷偷位移,比如“向日葵是这个黄昏唯一的野兽,是狂野之箭”(《野兽》),这样的诗句并不仅仅诞生于浩大的想象力中,更深处是狂放的人类意志,是挑战和超越的雄心。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梵高的向日葵,想起凡·高绘画气质的超越性和疯狂性。罗曼·罗兰在自己的阅读笔记中写道:“人类心灵有一个很小的场地,由社会习俗的荆棘篱笆和偏见的壕沟紧靠着圈起来,精神驯顺地在固定的草场上吃草。只有几只稍微大胆的牲畜,才能越过障碍偷看一眼外面。至于越过障碍,那是胆大妄为!唯有像尼采和帕斯卡拉那样的疯子才敢放胆一试!”① 凡·高就是这些伟人的同类,他们理想高远,心意相通,以不同的艺术形式照亮人类思想的禁区,为追求自由而牺牲安稳的日常生活。黄礼孩以野兽和箭比喻向日葵,显然也是在向这种崇高的挑战世俗的精神致意。
理解这种隐蔽的抱负,才能理解沉浸在诗意中的黄礼孩有时也会像刺猬,写出《去年在朝鲜》这样有力的政治诗。这首诗探索了将政治诗个人化的可能,丰富了礼孩的诗歌面相。“统治者的时间需要战争的影子来填满”高度浓缩了历史的苦难与暴烈;告别、猫头鹰等意象呈现了极权制度下的恐慌。“这里没有通往教堂的路”既是写实又是写意,宗教意象像渔火一样在他的诗歌写作中闪烁。最后诗人通过大海和贝壳的歌唱传达了对自由的信心。大海也是黄礼孩的核心意象,是他全部写作的出发地。他从大陆最南端的徐闻来,大海的气息是故乡送给他远行的礼物。大海的宽阔、深沉、汹涌也是黄礼孩取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黄礼孩持续多年编辑的《诗歌与人》,被誉为“第一民刊”;他帮很多朋友编书,有时候,他一年编辑出版的图书数量等同于一个小型的出版社的产量。黄礼孩具有开放的国际视野,他举办了一个人的诗歌奖,没有邀请任何名人组成评委会,他相信自己的眼力,也相信自己的公正。2011年托马斯·特朗姆先获得他颁发的诗歌奖,半年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曾引发媒体高度关注。这个奖一直颁给世界一流诗人。与巅峰诗人的互动也扩张了黄礼孩的寫作范围和表达技艺。黄礼孩还非常有意识地培养诗歌读者和诗歌气氛。他极力促成图书馆举办新年诗会并亲力亲为,将诗歌与音乐、现代舞、雕塑等多个艺术门类联合起来。还记得2014年的新年诗会命名为“光芒涌入”。的确如此,随着他坚持不懈的努力,诗歌的光芒涌入了我们这座以商业闻名的城市,新年诗会也成为图书馆标志性的活动,吸引大家从四面八方过来感受诗意的光芒。
黄礼孩从未间断诗歌和艺术评论工作,近年来对电影、美术、话剧、音乐、纪录片等不同门类艺术的评论写作也拓展了他的关注范围,不同艺术门类的表达方法也启迪着他的诗歌写作。随着生活经验的拓展,黄礼孩的诗歌写作面貌也日渐丰富。
黄礼孩将青春献给了诗歌事业,曾被林贤治老师赞为“诗歌王子”。不管世界如何变化,诗人的初心未变,他安于低处。在诗歌路上跋涉,他路过险滩、戈壁、荒野、暗礁,也翻越高山,白日放歌,遍览沿途风景。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可以毫无愧色地说自己领略了生命内部的奥妙,并接受了神交付他的使命。
注释:
① 罗曼·罗兰:《罗曼·罗兰读书随笔》,金城出版社,2018年,第15页。
责编:李京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