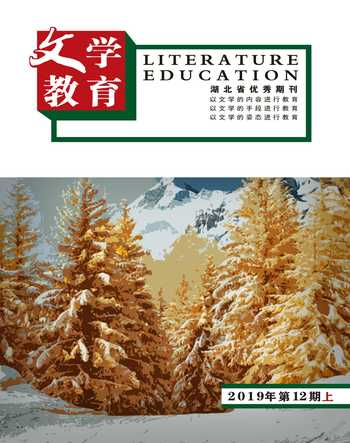从英美新批评的视角分析陈彦《装台》的现实意义
内容摘要:《装台》是陈彦继《西京故事》后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得益于作者本人二十年深入剧团的人生经验,陈彦将一群装台“下苦人”的底层生活搬上了自己小说的舞台。台上、台下;尊严、卑下;诚实、虚伪,在小说中借由虚幻梦境与沉重现实的反讽与隐喻构成一种生命的张力,引发关于普通人如何生活的深刻思考。
关键词:陈彦 《装台》 英美新批评 隐喻 反讽 张力
继《西京故事》后,陈彦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装台》同样将背景放在了他所熟悉的西安,从社会底层小民众的喜乐疾苦处下笔,在大热闹的浮生百态中聚焦中国传统的生存哲学与生命力量。《装台》的故事主角是祖祖辈辈生活在西京城的刁顺子,靠着肯出力吃苦,性格厚道又兼具一点处世必要的圆滑,顺子逐渐组建起了自己的装台班子。陈彦的笔墨围绕着他的家事与这一方使装台的老少爷们能够养家糊口的舞台展开,却远没有止步于此。作者通过将刁顺子生活五次发生重大变革的关键点同“蚂蚁意象”巧妙结合,使得《装台》细读自有一番滋味在其中。
《装台》里两条主线并行,如同两路针脚般将刁顺子的生活紧紧缝纫在一处:一条是刁顺子在舞台上所要进行的装台工作,一条则是他不得不面对的家长里短。刁顺子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晨昏不分地忙于舞台的布置,以及剧务的负责人周旋,低声下气服软好话地为自己和兄弟们争取更多的酬劳,舞台上的演出再怎样热闹精彩,大多数情况下也与刁顺子无关,而与他息息相关的小家之中上演的每日风波,较之舞台上的爱恨情仇也毫不逊色。难嫁的女儿菊花是顺子的一大心结,新娶入门的第三任妻子蔡素芬本来可以让他在疲惫的生活中得到一点慰藉,但女儿同继母之间不断升级的真实战争令顺子只想选择工作受累,好从家中的紧张氛围中逃离喘息。事与愿违,时间不仅没能缓解菊花对蔡素芬的敌意,第二任妻子带来的女儿韩梅因假期归家又使家中的战火愈演愈烈。在《装台》的文本中,反讽、隐喻以及情节节奏起到的修辞效果构成的张力使刁顺子的生活被放置在了更大的舞台之上,从与观众无缘,无足轻重的装台人变成了被作者请到聚光灯下的主角,这个名为人生的舞台所呈现出的正是平凡普通人的生活哲学。
一.反讽:顺子的生活并不“顺”
刁顺子是西京城内普通的装台人,可他也有不普通之处,西安城内说到装台第一个想起的就总是他,这全凭他的肯“下苦”。然而他的一生似乎没有顺遂安稳过,顺子勤快肯干,但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坎儿似乎无法都用“下苦”解决,在家中,他虽为自己大女儿菊花操碎了心,菊花却丝毫没有替他省心一二,这唯一的亲骨血反倒成为了他人生中的桎梏;在工作中,他对自己的兄弟们关照有加,但这群下苦人也給他惹了不少麻烦;甚至除去这些人,连刁顺子家的一条瘸腿狗,都能引发一场大战。小说围绕刁顺子展开,顺子身边的人和所经历的事都带着一些对应的意味,仿佛镜子的两面,一面是美好的愿景,一面是不如意的现实。从小说的发展中,可以提取的对应例子很多,比较典型的可以举出三个:美貌的韩梅——容貌不佳的菊花、佛像的圣洁——世俗的玷污、名叫好了的狗——人面桃花中的“狗”。
顺子有过三场婚姻,第一场婚姻的对象貌美轻浮,留下菊花后在腊月初八和人私奔,而菊花的相貌没有随她娘那般姣好,反而随了平平无奇的刁顺子,有些过分“扁平”。第二任妻子赵兰香善于操持,带来的女儿韩梅也同母亲相像,容貌出众。菊花和韩梅的关系在童年时期相处融洽,失去母亲的菊花很高兴继母的到来带给了她朴拙的父亲所不能提供的母爱,也因有了韩梅作为姐妹和玩伴,消解了一些父亲忙于装台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孤单。但随着赵兰香的去世,韩梅的逐渐长大,菊花的心性逐渐扭曲,二人间从融洽逐步走到针锋相对的局面。同为顺子的两个女儿,韩梅和菊花似乎从表到里都截然相反,菊花是刁顺子的亲生女儿,她的母亲留给顺子的是不如人意的回忆甚至来自乡邻眼光的耻辱,而韩梅虽然不是顺子的骨肉,但她的母亲赵兰香在的那几年可以说是顺子人生中难得的踏实日子,邻里夸赞有加。这一对姐妹俩相貌美丑,在读书上的才能甚至在爱情上的际遇都似乎是镜子的两面,菊花因容貌不佳一直没有对象,使得她对于自己的相貌越发在意,高考落榜后自己开的美容店也没有起色,于是将一切归结到父亲的无能上;韩梅容貌姣好,在商洛读大学的期间还结识了作为同学的男友,她对刁顺子这个继父感恩的情绪更多。但这二人却并非毫无相似之处,刁菊花与韩梅的共同点在于她们都让刁顺子劳心劳力,苦不堪言。韩梅为了留在西安城内拼命守卫自己在二楼的一间房间,而菊花倾尽全力要将“自己以外的所有女人”从他无能的父亲的房子里赶出去,两人都在宣誓自己的主权,甚至发生了两次争打和血淋淋的杀狗事件。菊、梅、兰、芬刁顺子生命中最亲密的女人名字中都充满花香,但无论美丑,性格缓急,出于本心还是天意,都没能把他的生活点缀得更加精彩,相反带来了无数的痛苦折磨。刁菊花的所作所为固然并不讨喜,作为菊花反面的韩梅,也无法使人感到美好和安慰,作者通过完全相反的姐妹二人道出了某种无奈的真理,丑恶的对立面总是被冠以美好的希冀,但往往美好并不等在那里。
寺庙,神佛,这些本该在香客们虔诚地香火中烟雾缭绕的意象有时也并不慈悲。顺子在经历了为《金色田野的颂歌》节目装台,却遇上了诈骗捞钱的草台班子,一无所获后,经剧团的剧务寇铁介绍,为寺庙活动进行一次装台,以期能稍加得到资金补偿,尽快为兄弟们发下工钱,然而在寺庙这种“圣洁所”,装台兄弟中的墩子却做出了不洁事,被僧人们发现,墩子早已先行逃走,顺子代为受过,在佛堂中苦跪一晚。被玷污的菩萨像看起来和顺子的第二任妻子赵兰香长得很是相像,这是顺子悄悄在心里想却不敢告诉任何人的秘密。菩萨在寻常人眼中,常常是一种寄托,去庙中进香的香客,也通常是对着“救苦救难”的菩萨祷祝祈求,以期让自己的生活产生一些良好的改变。赵兰香的到来,对顺子而言,似乎也具有这种意味,她的加入了顺子的家庭,那几年中是顺子少有的衣服头脸整洁,赵兰香持家有数,手巧人勤,也给予了菊花母亲般的温暖和关怀,可以说,她对于这个家所做的一切,称得上是救其于水火。讽刺的是,这种仿佛美梦般的“神迹”并不持久,很快赵兰香的病逝使刁顺子的家更加风雨飘摇,就如同寺庙中给人以美梦安慰的菩萨,眉目下垂,看似大慈大悲,却给顺子带来了皮肉之苦,就要到手的工钱也就此泡汤,甚至是寺庙中本该六根洁净的出家人,行事也势利而跋扈,这种反差和对比下,顺子依旧从“菩萨”中得到了对生活的信心和安慰也就变得更加使人感到唏嘘悲痛。
顺子家分崩离析的导火索来自菊花的“杀狗事件”,这条名叫“好了”的狗是赵兰香留下的,对她的女儿韩梅来说意义非凡,对刚进入家门,备受菊花针对排挤,顺子无奈忍让而内心颇感委屈的蔡素芬而言,好了也曾给过她一丝安慰。好了是一条狗,虽然名叫好了,却一直拖着一条断腿,小心翼翼地察言观色,只敢对韩梅撒欢扑撞,虽然蔡素芬将它抱在怀里连声念着它的名字时,或许也期待一切都会像好了的名字一样,慢慢变好,但直到她离开这个家,一切也没有真正好转,所有人的关系依旧紧张,好了也最终被菊花杀死,彻底断了它这个讨口彩的名字所能带来的幸福期望。好了生就一条狗,犬生凄苦,顺子生为人身,却在扮演一条狗中达到了人生巅峰。《人面桃花》汇演中,因演员临时无法到位,顺子客串出演了在女主人公身边的一条狗,在扮演一条狗的过程中,顺子尝到了从未体会过的掌声和鲜花,甚至轻松顺利地拿到了工钱,在剧情中这条由人扮演的狗同样死亡,但不同于好了的死,顺子在扮演这条狗死亡的过程中,感到快乐无比。名叫好了的狗,由人扮演的狗,两起死亡,台上的是美好的愿景,台下的是血淋淋的现实。
二.隐喻:从物到人
从素芬来到家中起,顺子见过五次蚂蚁搬家,第一次是素芬刚来的夜晚,顺子发出了自己与蚂蚁同样疲于奔命,信命安命的感慨;第二次则是带素芬同去城郊为《金色田野的颂歌》进行装台,二人坐在田埂上,只觉得乡郊的蚂蚁比城里的更大,托的物体更重,更要硬抗着生活;第三次是菊花与韩梅发生冲突,用开水烫死正在搬家的列队蚂蚁;第四次与前几次有所不同的是,顺子先做了一个梦,梦中他也变成了蚂蚁,同蚂蚁一起奔波生活,醒来再次看见蚂蚁搬家;最后一次见到蚂蚁,是在尾声部分,顺子心态平衡,觉得托着重物的蚂蚁们走得很有尊严。
蚂蚁作为一个典型意象,在整部小说中反复地出现。第一次代表的是素芬来到家中,生活虽苦,但顺子秉持一直以来的“下苦”信条,安于此道,决心两人一起在忍耐中,将日子过得有些声色。第二次在乡郊则是二人关系的蜜月期,顺子在西安城内土生土长,甚至对乡郊的更为辛苦的“蚂蚁”抱有同情,这也是最后一次二人一起观看蚂蚁,自此之后,菊花杀狗逼走韩梅,烫死蚂蚁,素芬不堪忍受菊花的折磨,再也无法像蚂蚁一般忍耐,就此离开顺子,也迎来了全书中最为关键的一次蚂蚁描写——顺子的蚁梦。
这个故事其实并不令人感到陌生,人变成了蚂蚁饱尝悲欢荣辱大起大落,唐代李公佐在《南柯太守传》中就已经写过。蚂蚁的意象,在此时与南柯一梦的典故自然地关联在了一起,有趣的是顺子的蚁梦同南柯太守的正好形成了一组对比。淳于棼梦中蚂蚁变作了人,他在其中享尽人生跌宕起伏,好事多过坏事,而顺子的梦中,人变作蚂蚁,除却劳作,便是风险,坏事多过好事,南柯国王一年之约,淳于棼魂归蚁国,而顺子在大梦方醒后,却是回归到依旧波折不已的现实生活中去,回归到他的位置上,去做那一班同是下苦人兄弟的支柱,领头人,继续硬扛着生活。
梦境与现实,台上与台下,如果说舞台是一场美好的大梦,上面上演着美化过的悲欢离合,那么台下的现实,最深有体验的莫过于顺子等与舞台無缘的装台人。大幕一旦拉开,意味着表演就要开始,也意味着顺子等人的装台工作已经完成,就要退出不属于他们的舞台。顺子梦醒回归现实,便是从梦境的聚光灯下,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台下,他是西安城内的小人物,同他一样的小人物数不胜数,就像他在蚁群中所见的成群结队的蚂蚁,他们经受苦难,但互相扶持拉扯,他们的舞台在于台下,在生活之中,顺子对此有所领悟,故而感到一种庄严自持的骄傲与满足,才会在小说的结尾处,觉得如果导演看见了缓慢行进的蚁群,会要求为它们打上聚光灯束。关于蚂蚁含混的隐喻落到现实之中,现实的重量将看来虚幻缥缈的含混拉扯进泥土,得以生长出小人物的生活哲学。
三.张力:从琐事到巧合
俄国形式主义将情节视为修辞功能的一种,在《装台》中,情节的节奏传达出这样的情绪:《装台》的故事中,主人公的生活并不顺利,称不上遭受大风大浪,但也是坎坷无比,就这样苦熬度日,内心麻木而疲惫,又带着一种未开化般的野蛮生命力量。与这样的表达主题相契合的是整部小说的叙事节奏,在情节的安排上,从头到尾充满小波折。
顺子的生活从来不顺,小说开头第一页的短短篇幅中,就已经是焦头烂额,剧团的工作忙得人焦头烂额,已经是“两头不见天儿”,仓促娶了新妻,还没进门,女儿已经在指桑骂槐地宣示主权。顺子感到对女儿愧疚,选择隐忍,新来的女主人也感到委屈,小小的院落中人跳狗叫,碗盆摔做叮当乱响。故事从一开篇就将读者带入进一种焦虑的情绪之中,但作者笔锋一转,又给这根拧紧的弦松上了一松。蔡素芬的到来并不全给顺子和整个家庭带来了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对顺子来说,这个女人使自己又重新感受到了年轻和活力,燃起了他对生活新的向往。读者刚刚从压迫感中找到了喘息的空间,菊花在窗外对正与新婚妻子温存的父亲的谩骂又再一次将顺子和读者一起拉扯回了紧张的空气中。
全书在这样反反复复的拉锯中行进,波折之间的联系强度却不过大,如同顺子的隐疾一直拖延就医般拖拽着推进,给读者带来一种强烈的疲惫感,在这种感觉中放大了顺子对于生活的逆来顺受,又在读者已然形成了期待视野,认为顺子的人生难以发生太大改变时,通过顺子不堪忍受寇铁的欺压,一改往日的唯唯诺诺服软递话,前去强硬讨要工钱,在此之前他已经去寇铁家中拜访了三次,每次的态度都几近软弱,按顺子的观点,“这么多年来,他就是用自己的低下,可怜,甚至装孙子,化解了很多矛盾,解决了一个又一个不好解决的问题”。但到了最后,真正使他拿到被拖欠已久的工钱的,却是他难得的强硬。
顺子是西京这个古老的大城市中最底层的普通人,与他的小学同学相比,他也算混得不上不下,但在他小学老师眼中,这个平凡的学生是几十年来唯一还记得每年登门拜望的孩子,他虽然平凡,甚至被生活逼迫的有些懦弱,却绝不卑微,靠本事吃饭,堂堂正正。同小学老师的两次拜访对话,暗中使顺子这个人物在读者眼中的形象发生了改变,在生活苦难的稻草一根根落下时,骆驼不仅没有被压垮,反而从在苦难中的坚守过程中,找到了自己人生的尊严。在这个叙述过程中,情节变成了构成张力的手段,而对情节节奏的出色控制则是张力得以实现的重要原因。
四.结语
我们给予平凡者目光的时候并不多,能够将视线落在普通人身上投入笔墨的作者也不多,舞台上的戏固然好看,但实际上演悲欢离合的舞台总是生活。反讽,隐喻,这些手段构成的张力实际上来自于普通人对于生活的各自感悟,读来才能知其味,解其意。普通人在苦难生活中的“下苦”,往往正是其人格光辉的体现,庄严自持的坚守,值得任何一盏聚光灯的照射和凝视,以及为之自豪。南柯太守可以一梦了之,作为普通人的一份子,总难成梦,梦醒后如何有尊严地活着,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彦.装台[M].作家出版社.2015.
[2]徐翔.戏台边上的悲喜人生———论陈彦《装台》的底层书写[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0).
[3]曹顺庆,卢康.中国话语”重建的文脉——以当代西方文论在中国的研究情况为视角[J].中外文化与文论.专栏一.
[4]李曦朦.韦勒克文学架构的理论来源和对英美新批评的超越性发展[J].文教资料.2018(36).
(作者介绍:王梦楚,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理论及文艺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