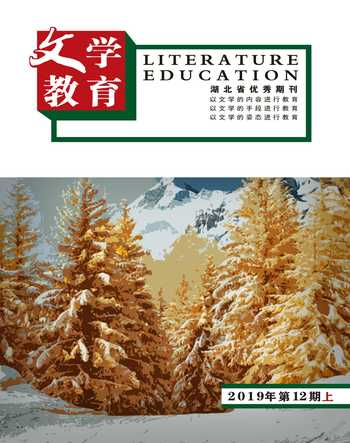以独特的方式叙述
鄂西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群山层峦叠嶂,一座山和另一座山,模样相似,天山相接处,朦朦胧胧。作家温新阶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过,所以他对这片土地的感受与众不同。他笔下的文字,带着山野的气味,大地泥土的味道,干净利落,没有世俗的杂味。这來源于生长的文化背景,更重要的是作家对于土地的热爱和精神尺度。这种分寸的把握,不是口头喊的口号,是思想和精神铸造的一道防线。
大多数人热衷于热闹,写作为娱乐的形式,大家聚在一起,相互吹捧,贴到微信平台上炫耀,安慰一颗庸俗的心。散文不是生活的记录,把一些琐碎的生活,用文字写出来。它有自己的标准和规矩,不是随意乱来的。在当下散文写作,制服式的统一,丧失个性的凸现。林贤治说道:“近世文明有—种泛化倾向,风气所及,散文写作亦不可免。泛化的危险就在于:消灭个性。”这种个性决定作品的成功与失败,丧失“个性”,作品归于同质化的行列,大家彼此彼此,相互吹捧,共同混在一起。个是指自己单独的存在,与别人不相干。性是说从心,具备生命力、创造力和提升能力。当它们组合起来,心理专家郝滨先生认为:“个性可界定为个体思想、情绪、价值观、信念、感知、行为与态度之总称,它确定了我们如何审视自己以及周围的环境。它是不断进化和改变的,是人从降生开始,生活中所经历的一切总和。”总体是说,是个体独立并与其他个体区分开来的特性。
当下的散文写作,泛化已经泛滥成灾,而且贴上妖美的标签,摇身一变,成为一种所谓的“先锋”。它们缺少精神的浓度,病菌侵入肌体的每一处,更多的是在起哄。作家温新阶独往独来,在鄂西的山野中寻找
生命的原生态和自然状态。“鄂西的男人们一辈子在山峦间行走,一直想看看天边的阳光或是晚霞,却一直没有能走到那片阳光或是晚霞中去。”一个男人走在山野中,这不是旅游观光,而是为了生存,负重前行。背在身上的金竹脚背篓,不是演出的道具,它是生活中装载物品的工具。这只大地生长竹子编织的背篓,结实耐用,和人的肌肤相贴,吮吸身体的温暖、渗出的汗水和情感。他们如影随形,既是劳作工具,又是寂寞中形影不离的伙伴。
作家温新阶对竹背篓的感情,从文字中表现出来,“韩琪回到家把那张照片递给漆叔,漆叔看着照片,眼泪花花地,已经远去的岁月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在眼前闪过,他赶了十年骡马,十年,三千多个日日夜夜,有许多难忘的记忆,有许多感人的片段,构成他人生中色彩斑斓的一页。现在,自己也老了,他赶过那些骡马肯定早已不在世上,过去的骡马道已经荒草及腰,只有水泥公路上,汽车来往如梭,几乎家家户户都买了小车,儿子的一辆车据说大几十万,买个酱油都要开车去的。”速度改变时间,也改变人与记忆的关系。一张图片,引起的不仅是回忆,也是安慰和寻找。不同的车,由不同的人操作,人与汽车是机器的接触,人与骡马的交往,是生命与生命,体温与体温的贴近。这种过程刻骨铭心,一生的惦念。老眼中淌出的泪结满沧桑,核中积存的情感,不带一点矫情。
时间是情感的流动,这是痛苦的。作家温新阶写出的每个字,,饱吸大地丰富的营养。简白中,写出的每一个字,看似随意的描写,却是道出人生的痛苦和发问。如果套用在文学创作上,可以说什么样的作家,就讲什么样的话,写什么样的作品。作家的心胸越广大,眼界就辽远,奔向远方,有着自己独立的精神体系,他写出的不论任何作品,都会远离虚假,越来越真实。“自然者,道之真也。”道家说出真,它是万物的自然而然的本性。真是事物的组成部分,是存在于之中的情,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的义。作品的好坏,流传多久,决定它的价值,是否有存在的意义。
散文不是简单的生活记忆,它是从胸襟中汹涌而出的激流,带着原性生命状态,未经过尘浸染的激情。它具有真实、个性和素朴,一路高歌,留下的是生命的大歌。如果情感虚假了,布满水分,脱离散文的本质,丧失野性植物精神的写作。
马克·吐温指出:“有时候真实比小说更加荒诞,因为虚构是在一定逻辑下进行的,而现实往往毫无逻辑可言。”作家温新阶是独立的个体,他对生活的认识,有着自己的看法和表现。这使他的文体鲜明,不加过多的修饰,丢失真实的原貌。笔力的丰富,让文体多维如同一棵大树,承载更多内容。
作家温新阶的鄂西,不仅是记忆中的事情,那是他文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构筑文本中组织的元素。
作家温新阶高扬自己的风格。他的每一个文字,饱含灵魂的纤维,保持一颗火热的心,忠诚于家乡大地。
高维生,著名散文家,出版散文集、诗集三十余种,主编“大散文”“独立文丛”等书系,现居山东滨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