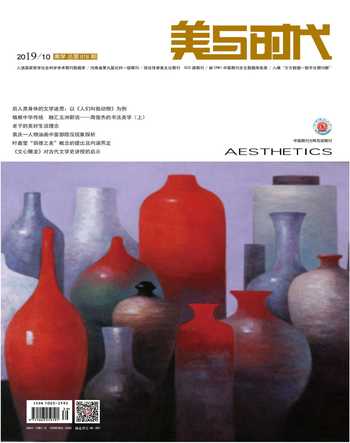《文心雕龙》对古代文学史讲授的启示
摘 要:《文心雕龙》一书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对我们讲授古代文学史亦多有启发。该书自《明诗》至《书记》二十篇文体论部分,论述三十余种文体的发展史,为我们分体讲述文学史提供了范式;《文心雕龙》亦重视基本的文学理论,将文学史与文学理论有机结合,进行论述,启发我们在文学史的教学中应巧妙结合文学理论,使文学史更易为学生接受;刘勰充分借鉴吸收了前人的文学批评成果,成就了《文心雕龙》的体大思精,这启发我们解决文学史问题应注意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以使文学史的讲授更为系统深入。
关键词:文心雕龙;文学史;文体论;文学理论;借鉴前人
古代文学史是高校中文专业的基础和主干课程,同时因为文学具有慰藉人的情感、为人们提供诗意栖息空间的特性,面对当前传统文化日益受重视的现实,这个课程对其他专业学生及众多社会人士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如何更好地完成古代文学史课程的讲授,也就成为高校相关教师不断思考与探索的重要课题。传统“作家生平思想——作品内容——艺术特点”的三段式教学模式受到诸多挑战,为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不断有一些新的教学方法与思路被高校教师们不断尝试和运用。《文心雕龙》作为我国古代一部伟大的著作,体大思精,价值表现在多个方面。刘勰在论述文学发展及各种理论问题时所采用的一些方法,可为高校古代文学史课程的教学所借鉴,使文学史的讲授更为系统、全面和深入。
一、为分体讲述文学史提供了范式
《文心雕龙》共五十篇,其中自《明诗》至《书记》共二十篇,属于该書的文体论部分,详细论述了当时流行的三十余种文体。如何在并不长的篇幅中,将一种文体的各个方面包括源起、发展、代表作家作品、风格、写作要领等在内都呈现在读者面前,并非易事。刘勰论文体有一套明确的原则和方法,即《序志》篇所言:“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1]456“原始以表末”是论述每一体文章的起源和流变;“释名以章义”是解释各种文体名称的涵义,就是通过每一体文章的命名来表明这类文章的性质;“选文以定篇”是选出各种文体的代表性作家和作品来加以评定;“敷理以举统”是敷陈事理来举出文章的体统,主要说明每一体文章的规格要求,或标准风格。这样一来,一种文体的发展史就被系统地呈现出来了。以《诠赋》篇为例,《诠赋》篇论赋体的发展史,进行了最重要的“原始以表末”的工作,作者先追溯赋这一文体的起源云:
《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瞍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途,实相枝干。故刘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也”。[1]76
刘勰认为赋起源于《诗经》六义之一。这段文字中“释名以章义”,释“赋”为“铺”,突出了赋体“铺采摛文”的特征。继之,刘勰论述了赋体的早期形成过程:“至如郑庄之赋‘大隧,士蔿之赋‘狐裘,结言短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1]77如春秋时期郑庄公诵“大隧”,士蔿诵“狐裘”,都由少数韵语组成,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赋;到了屈原的《离骚》,赋体境界进一步扩大;至荀况作《礼赋》《智赋》,宋玉作《风赋》《钓赋》,不仅真正以“赋”名篇,还用了“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的赋体特有的表现手法,赋体至此与诗划境,真正形成了。接着,作者论述赋在秦汉以至魏晋的发展,指出汉宣帝、成帝之时是赋发展的繁盛时期,以至“进御之赋千有余首”。而且,作者指出,自汉至晋,赋的创作有“鸿裁”与“小制”两种,即后人“大赋”与“小赋”之谓。大赋“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小赋“触兴致情,因变取会”[1]79,它们在赋学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体现了赋的发展流变。
作家、作品是文学史的基础。刘勰重视每种文体的代表作家和作品,《诠赋》篇“选文以定篇”部分列举了先秦至汉代的代表赋作家和作品:“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宋发夸谈,实始淫丽;枚乘《菟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鵩鸟》,致辨于情理;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1]80继之又列举了“魏晋之赋首”八家:王粲、徐干、左思、潘岳、陆机、成公绥、郭璞、袁宏。可以看出,刘勰于赋最重汉代和魏晋时期,这正是赋创作最为兴盛、发展演变最为集中的时期。所列汉代辞赋之英杰八人,及代表性作品八篇,皆是文学史上公认的卓越赋作。所列魏晋赋首八人,虽未具体列出代表性作品,但亦皆是被公认的赋体代表性作家。
“选文以定篇”之后,刘勰概括了赋体的理想风格,即“敷理以举统”部分:“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1]81认为既要有“丽词”,又要有“雅义”,只有二者有机结合,才是优秀的赋作。
值得注意的是,刘勰论各种文体的发展,往往最重视“原始以表末”,因此《文心雕龙》文体论部分各篇,都颇有分体文学史的意义。同时,他又能对某一文体的代表作家、作品予以具体指出、详细评述,在促进这些作家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而对理想文风的宣扬,则使指导写作的意义凸显。罗宗强先生有言,《文心雕龙》“首论文之起源,辨源流,谓文渊源于六经。继论各体文章之产生、流变,描述出各体文章的发展风貌,做出评价。既可以看出史的脉络,又可以看出他对待历史的价值判断准则。在他对各体文章作历史的考察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有着完整的文学史方法论”[2]。这就为我们用另一种方式进行古代文学史教学提供了思路和范式:分体讲述文学史。我国古人进行文学创作,勿论文学文体,连实用文体也颇追求文学性,因而文学文体和实用文体都应是古代文学史的关注对象。传统文学史的讲述一般以时代为经、以作家为纬,其优势在于“史”的意识强烈。但其缺点在于:一,往往会忽略一些在我国古代占有重要地位的实用文体,由于文学史限于体制和篇幅,一般只讲述诗、赋、骚等文学文体,略及一些重要的他体文章;二,不能很好展示各种文体的发展轨迹,传统的文学史往往只关注一些文体在兴盛期的存在状态,而对其如何产生、衰落以至消亡,则很少提及。而如《文心雕龙》这样分篇讲述各种文体的发展史,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文学史讲述思路。我们的古代文学史课程亦可以采取分体讲述的方式,只不过需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每一时代最重要的文体的代表作家、作品上,同时兼顾那些组成这一时期文学的其他文体。如何讲述每一种文体,《文心雕龙》的文体论部分也已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式。在这一范式下,我们既要关注每种文体的含义,产生、发展及衰落的过程,代表性作家作品;又要重视这种文体的风格、特色、写作要求等,给予该文体较全面的展示。
二、文学史与文学理论的有機结合
古代文学史和古代文学理论皆是高校中文专业的重要课程。在一般的高校课程设置中,文学理论课程因理论化程度较高,往往会开设在古代文学史课程之后。但实际上,二者之间非泾渭分明,古代文学史的接受是需要有一些基础的理论知识,古代文学理论则总是以具体作家作品为基础。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勒内·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在《文学理论》中就曾言:“文学理论不包括文学批评或文学史,文学批评中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或者文学史里欠缺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显然,文学理论如果不植根于具体文学作品,这样的研究是不可能的。文学的准则、范畴和技巧都不能‘凭空产生。可是,反过来说,没有一套问题、一系列概念、一些可资参考的论点和一些抽象的概括,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编写也是无法进行的。”[3]在将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结合论述上,《文心雕龙》再一次为我们提供了范例。《文心雕龙》的二十篇文体论,比较纯粹地论述了各种文体的发展史和体制风格等。但对于一些相关理论,如作家才性和文学作品的关系、社会风气等是如何影响文学的发展、文学的发展与前代文学遗产的关系等问题都未作表述。但事实上,作为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自然少不了这些内容。刘勰在二十篇文体论之后,列《体性》《通变》《时序》《物色》《才略》等诸多篇目,论述了一系列文学理论问题,作为各体文学史的补充,将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有机结合,呈现出有血有肉的完整的文学发展过程。
如前所述,《诠赋》篇讲述了赋体自先秦至魏晋的发展史。在其他篇章中,结合赋的发展,刘勰谈及了一些基本理论。如认为文学的发展总是和继承前代文学遗产分不开的,赋自然亦是如此。《通变》篇言:“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篇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1]272自周至晋,文学在后代不断学习前代的过程中前行,包括汉代的赋,也是在学习楚骚的基础上发展兴盛。同一篇中,刘勰又以赋的具体描写为例,从细节上说明后代文学对前代文学的借鉴:“夫夸张声貌,则汉初已极,自兹厥后,循环相因,虽轩翥出辙,而终入笼内。枚乘《七发》云:‘通望兮东海,虹洞兮苍天。相如《上林》云:‘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入乎西陂。马融《广成》云:‘天地虹洞,固无端涯,大明出东,入乎西陂。扬雄‘校猎云:‘出入日月,天与地沓。张衡《西京》云:‘日月于是乎出入,象扶桑于濛汜。此并广寓极状,而五家如一。诸如此类,莫不相循,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1]274自枚乘《七发》,至张衡《西京赋》,皆有对于事物广大的形容,后作总是在不断沿袭前作,又试图通过变换句式、加强夸饰等方法而超越前人,文学也就在这样的学习与试图创新中向前发展。
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1]408,文学的发展总是受到时代风气,如社会背景、学术风气、政治举措等的影响。《文心雕龙》对这些问题都有明确的认识,所论及于赋之处,亦往往能和《诠赋》篇相印证。《诠赋》篇论述魏晋之赋首的八位作家,包括两位建安作家:“仲宣靡密,发篇必遒;伟长博通,时逢壮采。”[1]80他们的赋作风格都偏向于遒劲有力,这种赋风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关系密切,即《时序》篇所谓:“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1]404一代学术风气也会对文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诠赋》篇论赋的发展,于东晋赋不甚重视,所论及东晋作家只有袁宏,其赋作以《东征赋》最显,属于以游历的方式写历史人物和历史典故的纪行赋,并未表现突出的时代特征。《时序》篇对东晋一代赋作进行了更明确的概括:“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1]408因玄学流行,东晋一代文学受学风浸染,时势虽极艰难,文辞表现上却都平静舒缓。具体的赋作也像是在给《老子》《庄子》之类的书作注解,宣扬道家思想而已。文学的发展更与统治者的爱好及政治上的举措密切相关,尤其是赋体,在发展最兴盛的时期与统治者的关系最为紧密,因为统治者崇儒尚文的政策,大批赋作家汇积于中央王朝:“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柏梁展朝宴之诗,金堤制恤民之咏,征枚乘以蒲轮,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孙之对策,叹倪宽之拟奏,买臣负薪而衣锦,相如涤器而被绣;于是史迁寿王之徒,严终枚皋之属,应对固无方,篇章亦不匮,遗风余采,莫与比盛。”[1]399虽然王朝所笼络的作家亦多作他文,但如枚乘、司马相如、枚皋等作家皆最善作赋。统治者的举措是促进彼时赋创作繁荣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作家的才性经历自然也是影响作品风格的重要因素,赋作风格的形成往往与作家自身的诸多因素相关。左思和潘岳都在大赋的创作上取得了重要成就。《诠赋》篇称“太冲、安仁,策勋于鸿规”[1]80,而何以如此,《才略》篇言:“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无遗力矣。潘岳敏给,辞自和畅,钟美于《西征》,贾余于哀诔,非自外也。”[1]429左思用思极深沉,潘岳才思敏捷,是成就他们优秀大赋的才华因素。而冯衍之所以能写出《显志赋》,则是因他“坎壈盛世,显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1]425。冯衍幼有奇才,一生追求功名,然命途淹蹇,白首无成,意欲回归家庭,又遇悍忌之妻,这样的遭遇才成就了《显志赋》。
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篇集中论述了赋体的源起、发展演变、代表作家作品及体制等较纯粹的赋学史问题。同时又在其他篇目中论述了赋的发展与社会变迁、学术风气、政治举措及作家个人才性经历的关系等理论问题,将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相结合,极好地呈现了赋体自产生之后,在历朝历代的发展事实。这种将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相结合的论述方法,给古代文学史的教学提供了极生动、切实的参考范例。我们进行古代文学史的讲述、勾勒,不能抛弃基本的文学理论,否则文学史就陷入了“真空”中,而非有血有肉的历史。《文心雕龙》的做法值得文学史讲述者学习借鉴。
三、解决文学史问题,应在充分借鉴前人的基础上进行
古代文学史的讲述是要勾勒出文学的历史发展,其实就是要解决一个个文学史问题。如讲述一种文体的发展史,其实就是要回答这种文体是如何产生的、如何发展的,它的代表作家作品是什么、它的体制风格如何、它的发展受到哪些因素影响等问题。又如讲述一位作家,要回答的是这个作家的文学史地位如何,他和同时代人有什么相同或不同,其不同是什么造就的,他在推动某种文体、某类文学的发展中做出了什么贡献等问题。如何更好地回答文学史问题,《文心雕龙》再次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方法参考,那就是一定要重视前人的意见和认识,在充分吸收前人看法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来。
《文心雕龙》是一部具有集大成性质的文学批评巨著。在它之前,已产生多种文学批评著述。刘勰在《序志》篇中对这些著述进行了综合评价:“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玚文论,陆机《文赋》,仲治《流别》,宏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1]454在刘勰的叙述中,既往的类似著述虽然很丰富,但都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其批评不可谓不严苛。但实则,继之刘勰又言:“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按辔文雅之场,环络藻绘之府,亦几乎备矣。”[1]457他承认,在《文心雕龙》一书中,不免有同乎旧谈之处,他就是要在“折衷”旧谈的基础上,提出新见。在实际的行文中,刘勰也是这么做的,他對很多问题的论述,都参考了前人,将前人的意见巧妙地吸收渗入,终又超越前人。如《时序》篇论述建安文学言:“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1]403-404这段文字叙及建安文学的时代背景、作家群体、时代风格及成因,字数不多,但很好地呈现了建安文学的概貌,颇富真知灼见,每为后世论建安文学者所引用,奉为至言。但实则其中颇多参考前人之处,如关于建安作家汇聚于邺下的表达,应来自曹植《与杨德祖书》:“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4]593关于应玚的评价,应来自曹丕《与吴质书》:“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4]591关于阮瑀的评价亦来自曹丕《与吴质书》:“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4]591 关于建安文学时代风格的概括则应是借用了曹植《前录自序》:“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虽触类而作,然芜秽者众。”[5]刘勰多借建安时期作家的评论来完成对建安文学的叙述。在将诸多成果揉合一起之后,带来了至其时为止关于建安文学最全面、客观又最深入的评价。
我们在文学史的讲述中,如也能像《文心雕龙》这样,充分吸收前人的成果,亦将会有更多的收获。如讲述西晋太康文学的代表作家潘岳时,要确定潘岳的文学史成就和地位,即可先参考时人的评价。潘岳身后,人们对他的评价从几个不同的方面展开,一言其才华高妙,如《晋书·潘岳传》言:“岳少以才颖见称,乡邑号为奇童,谓终、贾之俦。”[6]1500《诗品·上品·潘岳》将潘岳置于上品,言:“陆才如海,潘才如江。”[7]二言其为西晋文学的代表人物,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言:“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遗风余烈,事极江右。”[8]三则言其优于辞采,李充《翰林论》有评云:“潘安仁之为文也,犹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绡縠。”[9]《世说新语·文学》引孙绰言云:“潘文烂若披锦。”[10]四言其最善哀诔文,如王隐《晋书》言:“潘岳善属文,哀诔之妙,古今莫比,一时所推。”[11]房玄龄等《晋书·潘岳传》言:“辞藻绝丽,尤善为哀诔之文。”[6]1507
相对两晋南北朝其他评论家,《文心雕龙》对于潘岳的评价更为全面。刘勰在《诠赋》《祝盟》《诔碑》《哀吊》《谐隐》《比兴》《指瑕》《时序》《才略》等多篇中论及潘岳。总体而言,对其所评多同于时人,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刘勰在数篇中论及潘岳善于大赋的写作,称其为魏晋赋首之一,认为《西征赋》《藉田赋》等大赋是他赋作成绩的主要体现,这就提示我们关注潘岳哀诔文以外的作品。但当我们把目光转向《文选》时,会发现《文选》对潘岳的认识与《文心雕龙》不甚相同,主要在于对潘岳赋的评价。《文选》共选潘赋8首,这8首分布于“耕藉”“畋猎”“纪行”“物色”“志”“哀伤”“音乐”七类赋中。潘岳成为《文选》中入选赋作最多、赋作分布类别最广的作家。《文选》所选既有其逞才大赋,又多咏物、抒情小赋。可知,萧统认为潘岳乃赋之大才,各种赋作皆很擅长,不仅是西晋,亦是先秦至萧梁最重要的赋作家。这种认识既不同于刘勰,更不同于同时期的其他批评家。这也启示我们在讲述潘岳时,必须重视其赋的创作,探讨他在赋学史上的地位,或许才能对这个作家有更完整、全面的认识,而不是只读一下他的《悼亡诗》,读一两篇哀诔文了事。有效吸收前人成果,灵活运用于文学史的讲授中,会使我们的文学史教学内容更为丰富深刻,对很多文学史问题的解决也大有裨益,帮助我们有效防止囿于文学史教材的知识体系而忽略诸多古今人的研究成果。
四、结语
怎么讲授文学史,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也是每一位高校相关教师时常思考的问题。有效学习与借鉴古人的做法未尝不是一条有效的途径。如《文心雕龙》这样优秀的文化遗产,价值是多方面的。其论文体方法、讲述文学史与文学理论有机结合、积极充分吸收前人成果的做法等,都是我们讲授文学史时可以借鉴学习的。将之运用到教学的实际中,可使文学史的讲授更系统、更生动、更深入。
参考文献:
[1]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2:293-294.
[3]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 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33.
[4]萧统.文选[M].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
[5]曹植.曹植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434.
[6]房玄龄,等撰.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钟嵘.诗品集注[M].曹旭,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141.
[8]沈约撰.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778.
[9]严可均.全晋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1767.
[10]刘义庆.世说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3:143.
[11]虞世南.北堂书钞[M].北京:中国书店,1989:391.
作者简介:赵俊玲,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