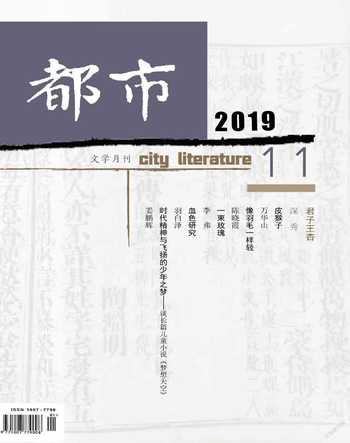血色研究
羽白泽
一
我费力地想睁开眼睛,却发现这个简单的开闭动作都难以实现。接着,一束光照进我的眼球,眼睛刺痛,白茫茫一片,后来我看到了一些模糊的影子。
那些影子在我面前走来走去,一会儿聚集,一会儿分散,分不清是男是女,也看不清发型,衣服,鞋子,听不清他们的语言,甚至,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人类这种生物。
我觉得头疼,我开始伸手去摸自己的头,但是怎么都使不上力,我尽力往下看,却发现我的头难以低下,因为我的头似乎在被什么东西拉扯着,我闻到了一些血腥味,接着,我的眼睛余光开始看到一些红色的类似血渍的东西。
脖子突然感到刺痛,似乎被蚊子咬了一下,我又开始沉沉睡去。
耳边似乎响起了一些声音,“快跑”,“不要被抓到”,还听到撕心裂肺的呼唤,隐约意识到那是温菲菲的声音。
温菲菲?
我的思绪突然停顿,我的思维和意识都集中在这个风花雪月的名字上面,我开始回想有关她的一切。
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站在大学图书馆的杂志阅览区,穿着白色的连衣裙,扎着长长的马尾,手上拿着《脑科学报》向我招手。当时我的心为之一颤,感觉空气都是甜甜的。没想到导师李教授给我派来的搭档这么漂亮,这么富有青春气息。
“大脑负责记忆的区域十分活跃,这说明他回忆到了重要线索。”一个电子声音传来。
脖子又一下刺痛,我的眼睛睁开了。慢慢地,我从眼睛不适到开始看清楚一些影子,意识也从对温菲菲的回忆中醒了过来。
“现在看清了吗?她长什么样子?”一个声音冲着我喊道,我可以确认这是个愤怒的中年男人。
“白色裙子,黑色马尾……”我还没说完,针管再次扎向了我的脖子,我意识到之前的脖子刺痛都是拜这些蓝色的针管所赐。
一股电流冲向了我的大脑,让我的脑海出现了混乱的画面,有童年时的,也有长大后的,我开始觉得疼,头很疼,我拼命摇头,拼命挣脱,却发现牵引我的线越来越紧,直到我动弹不得。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又开始做梦。
白色的墙壁上挂着巴普洛夫的画像,画像正下方的桌子上摆放着一只透明的玻璃器皿,一个完整的大脑组织被泡在福尔马林液里。那些大脑的神经元组织在溶液里自然地舒展着,有点像艺术品,在向世人展示着它们的价值。
我正欣赏着这个作品的时候,有人拍了我的肩膀。回头一看,是温菲菲,她温暖而甜甜的笑容让我觉得心情更加舒展。
“第一次看是挺有意思的”,她把双手插进白大褂的口袋里,仿佛这样就能够对眼前的一切置身事外,“有了新进展,进来看看吧。”
我跟在她身后走进了一道铁门,前面是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里放着两篮苹果和香蕉,除了一个猴子骷髅标本,我没有看到其他生物。接着我跟着她走近了其中的一扇门,隐约听到了一些嘶鸣。我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
她回头笑着说没事儿,继续走,我便佯装没事的样子继续走。门里面,是一只活猴子。同时一股刺鼻的味道冲进我的鼻腔,一直钻到了我的胃里,让我想吐出今天晚上喝的咖啡。
猴子的脑袋上环绕着层层纱布,身体则被禁锢在一个跟它一样高的盒子里。它瞪着大大的眼睛看我,嘴巴也张得很大。
温菲菲说,“这只猴子刚做手术不久,正在恢复。”
我有些震惊,原来猴子竟然是这样被拿来做实验的。
“什么手术?”我的声音有些颤抖,我开始怀疑做数学算法的导师为什么让我这个数学研究生来温菲菲的实验室看猴子,而且是这么可怜的猴子。
“简单来说,就是在它的脑袋上开一个洞。”她的声音十分平静。
我在打量猴子的表情的同时,也在怀疑我眼前的温菲菲还是不是我在第一次见面时为之心动的温柔女孩。
“你来看,棍子上有钩,猴子的脑袋上装了一个环”她驾轻就熟地拿起一根长长的不锈钢棍,用棍一端的钩子挑起猴子脑袋上的一个环,只轻轻一挑,猴子就乖乖跟着她往房间里面走,然后自觉地走进了墙角一只敞开了门的笼子,温菲菲随即将笼子的门关上。
“不好意思,刚才做完实验忘记把猴子关进去了。”温菲菲笑着说,“研究成果在这里,她指着房间另一头的大屏幕”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到一个彩色的大脑切面图案,图案的中心区域是红色的,其他区域是黄色或者蓝色,但是面积最大的是红色区域。
“这个红色区域就是控制猴子的思维区域”,温菲菲指着红色区域继续说,“我们做了几十个样本,虽然有所不同,但是每当给猴子的大脑电流刺激,这个区域就会十分活跃。”
“我……”我不想在一个美丽的女孩面前承认我并没有听懂她说什么,我在绞尽脑汁地想,我究竟来这里干什么,这些研究跟我的论文有关系吗?
“我想去下洗手间。”
可能也只有這个下三烂的理由才能让我有时间缓一缓。
我在洗手间里开着水龙头,任凭水顺着水龙头流向水池,看着镜子中的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觉得自己就像那个被纱布包裹的猴子一样可怜。我掏出手机,看导师发来的微信,只有一个“加油”的表情包。接着,我听到了一阵嘶鸣。我的耳朵竖起来了。
二
我跑出洗手间,看到温菲菲正急匆匆地跑进另一个房间,我跟了上去。
温菲菲正拿着不锈钢棍将一个个猴子都往笼子里送。
我探着头朝着房间看,一排排的笼子,住满了猴子,猴子们嘶鸣着。
“进来看看,”温菲菲说,“不用怕的。”
“它们都是实验猴子吗?”我装作沉稳地说道,“上次你手上的伤就是它们咬的?”
“是豆子咬的。”温菲菲指着角落里一只笼子里的猴子说道,“平时它最乖,但是那天它做了手术以后不知道怎么发了疯,对着我的手就是一口,害我打了好几针疫苗。”
“哈哈,你还给猴子取名字。”我被她逗笑了,觉得自己也并不是那么惧怕那些猴子了。
我跟着温菲菲走出了房间,突然觉得实验室里的味道没那么刺鼻了。
“刚才李教授发微信过来,让我把实验数据给你。”温菲菲关上猴子房间的门说道。
“其实……”我有些羞涩,“我不太懂你们的理论,不知道需要我们从哪个方向来处理这些数据。”
“与其他生物相比,人类和猴子是近亲。”她一边将U盘插进电脑一边说道,“我们的目标是知道人类和猴子相比,其心理及大脑工作过程有多少相似度,在哪些方面相似。”
“你这么说我就懂了。”我的心扉敞开了,我终于成功地把一个未知问题转化为了一个我熟悉的数学问题,这样我就可以用数学的套路来解决这个未知问题了。“就是采集到的猴子数据,然后和人类的数据进行对比,得到结论。”
这个问题很简单,就像是比对蓝山咖啡和雀巢咖啡的区别一样,小菜一碟。
“大脑区域开始休眠。”一个电子声音传来。
我被蓝色针管弄痛了脖子,再次醒来后,我又听到了那个熟悉的愤怒的男中音,“快说,她究竟长什么样子?”
我一直看不清我眼前的男人,我只能听到他的声音,从他的声音里我判断出他很愤怒。
“白大褂,长马尾……”我的声音有些微弱,“她的脸,我想不起来了。”
“你说不说!”他在嘶吼,这种声音比那些猴子的嘶鸣还要洪亮,还要让我惧怕。
我不知道他对我干了什么,我只知道我的头被拉扯得很疼,感觉自己就像是温菲菲实验室里那些被开颅然后接上电线的猴子,在电流的作用下,大脑的区域在大屏幕显示出来供人研究。
“你知不知道,”他的声音里带着眼泪,“我三岁的女儿就是被那个女人害死的!”
这一刻,我异常清醒。
三岁的女儿……我的脑子开始混乱起来,怎么会牵扯到一个三岁的孩子呢,我实在想不出这些事情究竟有什么联系。
我的脖子又开始刺痛,我知道,我又要开始被动地回忆了。
回到数学研究所,我跟导师汇报完情况后,就开始着手研究怎么处理这些数据。一开始我打算用常见的因子分析法来处理,但是处理结果噪声很大,且有冗余。在查阅了国内的领先研究技术后,并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我转而开始搜索国外的方法,国外在数据处理方面最热门的就是“非凸”技术,因子分析法只要用数据处理软件就可以搞定,换句话说,就是用现成的软件进行处理,只要把数据输入,就可以得到结果,但是“非凸”却需要建立三个数学模型,才能开始导入数据。
一个阳光正好的下午,我坐在导师办公室,在他办公室的黑板上写下了我建立数学模型的过程,以及自创的数学公式。
导师放下手中的咖啡,一边郑重其事地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500”这个数字,“五百年才出一个定理,数学已经被前人研究得差不多了,我们现在能做的一切只是改进。你现在的公式是彻底推翻了前人的公式和定理,从某种角度来说,它肯定是不可能成立的。”
我不知道怎么跑出的办公室,只知道自己身上有一股咖啡残留的味道。
温菲菲再次联系我的时候,我正在用超级计算机计算我自创的数学公式的精确度。
计算完成后,我回了她电话,告诉她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对她的数据得出一个非常精确的结果,希望她能再给我们一些时间。
她把我约了出来,就在研究所附近的咖啡馆里,那儿时常有很多同学在交流学习心得以及最近的研究成果,他们手捧咖啡,谈笑风生,或者双肩依偎,儿女情长。
“我刚做完公式精确度的计算,再给我一点时间,数据就会处理好了。”我猛喝了一口咖啡。
“李教授说你们停止了数据处理,正好,我这边有了最新的数据,我们的实验就要成功了。”她端起咖啡闻了一下,又放下杯子,眼睛红红的,“这段时间谢谢你了。”
“可是……”我放下杯子,“数据真的快处理完了,而且我能从现有的计算中预测到数据的结论,就是人类和猴子之间……”
她用手做了一个暂停动作,制止我再继续说下去。“我女儿病了,我要停止工作去照顾她。”
“她多大了?”
“三岁。”她快哭了。
三
从咖啡馆回来后,导师给我安排了其他的学习和工作任务,我的时间满满当当,根本没有时间去回想上次的实验数据。
我几乎都把温菲菲忘了。
我曾经对她产生过幻想,以为她跟我年龄相当,我们的学习和工作又有交集,也许会有不错的结果,但是我并不知道她有女儿,这倒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这就意味着她有丈夫,她是人妻。而我,只是一个其貌不扬的单身汉,仅此而已。
再次跟她扯上关系,是一次科幻会议。
导师派我去成都参加科幻大会,我跟同学讨论了很久,为什么一个科幻大會会想到邀请我们这种搞数学研究的人去参加,后来才知道,有个科幻作家写了一本关于数学的小说,叫作《算殇》,还得了科幻大会一等奖,内容是一个疯子数学家研究了一套算法,算法应用以后世界大乱。大会觉得这个小说跟数学关系很大,所以就邀请我们搞数学的来探讨探讨。
晚上跟一群科幻作家在成都的街头撸串的时候,我喝了点啤酒,便开始说起了自己之前自创的那个数学公式,以及它还没有被应用就被迫停止的事。那群科幻作家对这事儿挺感兴趣,便开始往下引申,比如他们猜想,这个数据处理完以后将改变人类和猴子之间的生殖隔离,或者那个温菲菲的女儿其实不是人类,而是只猴子。
我喝醉了,我梦中情人的女儿不是人类,是只猴子?难道他们没有看过达尔文的《进化论》吗?猴子虽然和人类是近亲,但是人类想要生出猴子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有生殖隔离。
哈哈,这群科幻作家的脑洞真大,真敢想啊!
第二天酒醒以后,我就忘了这茬事儿了。谁知道在酒店去会场的接送大巴上有人把这个猜想当笑话讲出来了,还有昨晚的朋友圈视频为证。
为此,我专门加了这个人的微信,又仔细看了几遍那个视频,的确,确实有人说温菲菲的女儿是只猴子,叫豆子。
豆子,豆子,豆子……
我的脑袋轰的一声,脑海里立马浮现出了那天在她实验室的画面,她指着墙角笼子里的猴子说,“就是这个豆子咬了我。”
“大脑区域出现异常。”电子声音传来。
但是我的眼睛睁不开。
“我女儿叫豆子。”男人的愤怒减了不少,“我想你见过她。”
“豆子……”我的声音颤颤的,“见过,在笼子里。”
“都是她!”男人站起来,“温菲菲,看上去温柔善良,但是骨子里却是个疯子,连自己的女儿都害!”
“豆子,”我顿了一下,“是你的基因吗?”
“废话!”男人说,“她是我的一切,我看着她出生,长大,她是人类,活生生的人类!”
一束强光照进眼球,我慢慢睁开眼睛,我穷尽全身力气,想看清这个男人的样子,但是始终只能看见一个模糊的影子。
他的浑身长满了毛,活像一只猴子。
对,像猴子。就像是一个人穿着猴子的毛皮扮演的猴子。
“你看,你的眼睛舒服多了吧?”男人说道,“温菲菲的研究成功了。”
“太好了,我一直都想帮她完成数据处理,但是始终没有完成,直到参加完科幻大会以后,我回到研究所做完了数据处理。”我很自豪,我成了一个近五百年前所未有自创公式的数学研究生,今年刚刚24岁,会成为所有得过菲尔茨数学奖的数学家中年龄最小的。“我想,今年我就可以拿到菲尔茨了。”
我感到眼睛有些不舒服,我尽力看清眼前的男人,他是一个英俊潇洒的男人,身上并没有披着猴子的毛皮。
我想,我可能是出现幻觉了。我告诉自己。
“你不用猜了,”男人说道,“我女儿是被吓死的,温菲菲的研究成果证明了人类和猴子的心理相似度,她將猴子的大脑组织注入了女儿的大脑组织,女儿看到人类时眼前出现的影像是猴子,看到猴子时出现的影像是人类,她后来很喜欢去实验室玩,就是因为把那些猴子当成了人类,后来她被猴子咬伤,不治而死。”
我闭上了眼睛。
原来我的眼睛出现了问题,也是被注入了这种大脑组织。
我被圈养了。
责任编辑高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