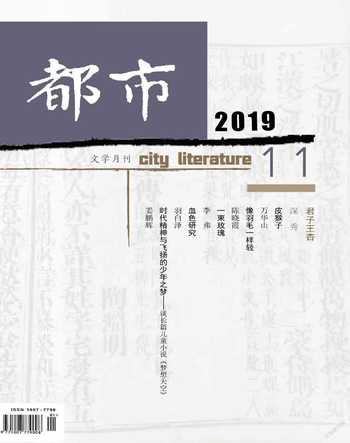像羽毛一样轻
陈晓霞
我刚睡下许宝花就来了。她一定是听见了刚才杜红霞和我的谈话,脸上燃烧着熊熊火焰。她说李金堂你跟我走吧,这种窝囊日子不过也罢!她过来拉我一把,我一下就从床上飘到了半空。看来死亡不是一件坏事,它会使人变得强大。许宝花活着的时候可没这么大本事。那时她虚弱得像一片掉落的树叶,一阵风就能被吹到天上去。她是死了以后才重新开始生长的,不仅长出了力气,还长出了脾气。她说你跟我走,去看看真正的太平日子!许宝花这么冲动,我反倒冷静了。我说宝花你别急,我早晚会躺到你的墓穴里去。现在我还有事要做,等我把想做的事情做完就去找你。
我這么说,表明我还要在杜红霞的监管下生活下去。虽然我早就受够了,而且我知道杜红霞也受够了,但我打定主意绝不妥协。杜红霞是我儿媳妇,公道地说,这是一个能干的女人,许宝花去世后,她把家事料理得井井有条。她天生是个干大事的材料。可惜社会上所有干大事的位置都让别人占去了,她只能把天大的本事用到家里。杜红霞有一张锋利的嘴巴,她最爱做的事情就是用尖牙利齿修整够得着的每一个人。她嫁到李家二十三年,我儿子李小军和我孙子李妥妥都被她修整得溜光水滑。现在她的任务是修整我。
因为她认为我被“狐狸精”迷住了,并由此认定我是个不忠实的老男人。自从她无意间碰到我和一个年轻女人在公园长椅上说话,就把我和“为老不尊”“拈花惹草”“老流氓”等词语联系在了一起。她看我的眼神充满了鄙夷和不屑,她还把埋没半生的才华用在对这件事情的调查上,很快就掌握了那个女人的姓名、单位、电话号码以及我们之间的通话次数。尽管她还没有搞清我和女人的谈话内容,但她确定我们的关系已经大大超出了正常范围。她和李小军反复商量,为避免我犯更大的错误,最终决定把我接到他们家去住。那时许宝花才去世不久,老房子里还有她平时擦的友谊雪花膏的香味。我每天在这些熟悉的香味里吃饭、喝茶、晒太阳,心肝肠胃全都妥妥地待在肚子里。我说我不走,我在这所房子里住了半辈子,我的命早和它长在一块了,我要和它共存亡。杜红霞笑了,她说您看您一开口全是我、我、我,您心里从来就不考虑其他人。我说其他人是谁?我住我的房子,和其他人有什么关系?杜红霞说,这我可不能告诉您,人得自己悟,靠别人教就没意思了。
后来她又提了两次,我又拒绝了两次。可是到第四次我拒绝不了了,因为我病了。有一天我屁股以下忽然变得青黑乌紫而且疼得要命,医生说这是我稀里糊涂把治心脏病的药物吃多了,导致的大面积皮下出血。说到这里我得表扬一下我的儿子李小军,我不得不说有个好儿子真是人生最大的幸福。虽然杜红霞对我的每次敲打,背后都有李小军的意思,但我一说我病了,我儿子连夜就把我送到了医院里。医生对李小军表示了不满,责怪他对我平日的用药监管不力,这次出血幸亏是在下半身,如果发生在脑袋上人就完了。我偷偷打量一下李小军,他脸上闪过一丝慌乱的表情,那是庆幸和后怕的综合反应。我心里呼啦一下舒坦了。这就够了,这说明儿子担心我了,后面天大的事情我也不怕了,我就在医院里踏踏实实睡着了。
出院后,我搬到了儿子家。我不是冲杜红霞搬的,也不是冲没人照顾搬的,我是冲李小军无意间流露的那丝慌乱搬的。一想到儿子为我担心的样子,我就又心疼又幸福。半夜里我对许宝花说,你看,血脉连着呢,错不了。许宝花每次过来样貌都不一样。这次她变成了四十岁的样子,正是她人生最精明能干的时候。她麻利地翻看杜红霞给我准备的被褥,又瞥了眼我带过来的黑色皮包,说你别高兴得太早了,就怕你们三个李家爷们儿也斗不过一个杜红霞!
那时我还心存侥幸。我想杜红霞不理解我不要紧,李小军懂我就行了。他知道他爸是个热心肠,特别是碰到有人轻生这样的大事,说什么都会过去拉一把。所以那天我不仅喊住了那个要投湖的女人,还把我的手机号码也给了她。我让她有事找李叔,我说她遇到的都是人世间最正常不过的事,为这点事就不活了太不值得。为了让她回心转意,我甚至悄悄把了结自己的打算都放弃了。我的话很管用。她一声不吭盯着我,有点像饿极了的人,把我说的每一个字都当救命的粮食吃进肚子里。从那以后我们就经常通电话。刚开始我给她打得多,后来她就越来越多地打给我。这说明我的思想工作是有效的,至少她又有了继续生活的热情和勇气。这是我退休以来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虽然我常常被杜红霞围追得无路可逃,但我这个狼狈肉体的精神还是健壮的,至少我还能用精神带领这个六神无主的女人,小心穿过荆棘,走向光明大道。
对于杜红霞的猜疑我从不解释。夏虫不可语以冰,对杜红霞,我同样难以让她理解君子的含义。
没多久,杜红霞就找我谈话了。她先说老房子租出去了,租金用作我的生活费。我想了一遍老房子里的角角落落,那里面全是我和许宝花的生活记忆。我有些舍不得,不知道新住户会不会像我们一样爱惜它,但我没把担心说出来,我知道有些事情不能求全。我说行,你看着办。接着杜红霞又提出,我以后最好不要老往外面跑,如果实在闲得难受,就在小区里转转,或者找看门的老头儿聊聊天。我说这不行,我才七十六岁,身体好得很,搬来之前我天天出去找人说话,为什么来到你家就限制行动了?杜红霞说,主要是为您的安全考虑,大街上车来车往,我们不放心。我说次要原因呢?次要原因才是主要原因吧!杜红霞倒也痛快,她说,您的朋友里面有女的吧?女的里面有单身吧?你们孤男寡女在一块,容易让人说闲话。我说接下来你是不是还要限制我跟女人说话?杜红霞说,也不是绝对限制,以后和三十岁以上的女人说话,您最好注意点分寸。我说岂有此理!小军妈妈都没限制过我的自由,你倒来对我指手画脚,办不到!
第二天我照常跑了出去。我想着杜红霞给我立的种种规矩,干脆中午也不回家。我在街上转来转去,直到肚子叫起来,才到一个街角小饭店里要了份饺子。刚咬一口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我好久没吃到白菜馅饺子了,这说明许宝花离开我已经很久了。过去她总是给我包白菜馅饺子吃,把我的肠胃伺候得舒舒服服。以前我没觉出什么,许宝花离开了,我才发现她的存在意义重大。没有了许宝花,我活得越来越像一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我一边吃饺子一边哭,因为许宝花再也不能复活了,这意味着我再也不会有自己的家了。
我挨到太阳偏西才往回走。正是下班高峰,满大街的车都在匆匆忙忙往家赶,我却永远没有这样的时刻了。再没有那样一个家,情深意长等在那儿,让我心急火燎地赶回去。在小区外面,我远远看见了三楼胖子的妈。老太太躲在绿化带背后,正像我中午那样在抽抽搭搭地哭。我心里更难受了,我知道一个人如果不是伤心透顶绝不会偷着出来掉眼泪。本想过去问问情况,但一想到杜红霞也许正在十一楼上监视我,我就蔫头耷脑地从她身边过去了。杜红霞倒没审问我,只是脸色不好看,搁盆放碗摔摔打打的。我很想跟小军说说街角饭店的饺子,如果他有時间,我们爷俩可以过去吃一次,顺便回味一下他妈包的饺子的味道。可是我起了几次头,小军都岔到别的事情上去了。他现在是个分公司经理,下班和上班一样忙。整个晚上他一会一个电话,根本顾不上和我好好说上几句话。我闷闷不乐,不知道这样的日子究竟还有什么奔头。好在快睡觉的时候妥妥给我来了个电话,我的心才像呼啦敞开了一扇窗户,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妥妥问我能不能给他帮个忙。我说我孙子找我,那还有什么话说。妥妥说他大四的学费被舍友借去给女朋友打胎了,现在学校催得紧,舍友又还不上,他也不敢跟杜红霞说,所以只好向我求救。我问交多少,妥妥说,7000吧,应该是7500,那500我自己出。我的心脏紧跳了几下,这是我两个多月的退休金。我想了想我的存款数,经过许宝花生病和我住院折腾,上面已经所剩不多。但我还是决定帮我孙子一把。我说没问题,明天爷爷就把钱足额给你打过去,你自己的500块用来买点好吃的。妥妥问,您和我妈处得怎么样?您别跟她一般见识。我的喉头紧了紧,说放心吧孙子,都好着呢。妥妥说,钱的事千万别让我妈知道,不然我就活不成了。
我当然知道杜红霞的厉害,现在她是家里的女王,谁也不敢轻易招惹她。所以第二天我什么也没说。我若无其事吃了早饭,若无其事穿好外套,然后像往常一样准备出门。我没想到杜红霞会把身子挡在门口。李小军上班去了,她的气势又大了一些。她说你到哪儿去?她没用“您”字,而且她有本事,让自己吐出的每一个字都闪着寒光。很明显,她知道我势单力薄,明目张胆来欺负我了。
我按住突突的心跳说,我出去转一转。
她说,昨天你在外面跑了一天,今天哪儿也不能去!
我说,谁给你的这个权力?哪条规定说我不能出门?
她说,别说权力,也别说规定,只要我不让你走,你就出不去这个门!
我说好,我这就问问李小军我还能不能出这个门!
我掏出手机,觑着两眼找小军的号码。心脏疯狂地在我胸膛里冲来撞去,撞得我两脚怎么也站不稳。我有点着急,因为越是不稳我越找不到小军的号码。这时杜红霞从地板上捡起一张单子。她说你拿存单干什么?我吓了一跳,原来我掏手机的时候顺便把准备提钱的存单也带了出来。
我说,你管不着。
她说,你是不是下定决心和那个女的好了?我先把话说头里,我和小军不反对你找老伴儿,但如果你想和她一起生活,你的存款必须交给我们来保管。
我说,钱是我自己的,找不找老伴儿是我的自由,凭什么把钱交到你们手上?
杜红霞说,你放心,钱我们一分不会动,名字还是你的,密码也是你的,我们只是防止别人骗走你的钱。三楼胖子他妈你认识吧?她被新找的老伴儿一下骗走了六万块钱,今天早晨上吊死了!
这话把我吓得不轻。后来杜红霞告诉李小军,说你爸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当时我倒没在意我的头发,我只是感到漫天悲哀。我想起了昨天胖子的妈在外面偷偷哭的样子。一个人热热闹闹一辈子,活到最后,竟然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谁还是你的贴心人?谁还在关心你的喜怒哀乐?胖子妈没有这么个人,我也没有。就算我有李小军和李妥妥,在他们的世界里,我也不过是鸿毛一羽,再难搅起一丝波澜。这个想法让我难过极了。我一屁股坐到凳子上,情不自禁又掉下泪来。我这时的样子一定可怜极了,我不用杜红霞欺负就自己败下阵来了。我觉得许宝花说得有道理,这样的日子不过也罢。但我孙子还在学校里眼巴巴等我打钱呢,我不能做个没有信誉的爷爷。所以我又强打精神站起来。反正日子已经够烂了,再烂一些又能怎么样呢。我的脸上大概出现了一些悲壮的神色,杜红霞吃了一惊,她看着须发花白的老头儿阴沉着脸色向她走来,慌乱中露出了女人的胆怯。她没再拦我,她眼睁睁看着我走出家门,没有再说一个字。
给妥妥打了钱,我不想回家,就在银行前的台阶上坐了下来。暖洋洋的太阳让我安心。我现在明白了,以前村里的老头儿为什么总爱靠在墙边晒太阳,那是他们心里的热量太少了,所以才特别稀罕暖和的东西。我不知道在太阳底下坐了多久,快要睡着的时候,我接到了那个女人的电话,她的声音听上去和太阳一样叫人舒坦。
她说,李叔,今天复查结果出来了,指标真的比以前好了很多!
我说,这下你信我了吧?放心吧,以后还会越来越好的。
那边笑起来,说,您说能好我就一定能好,您说了算!
我说,那当然,你李叔从来不骗人。
那边说,李叔,您要是我爸就好了,可以给我撑撑腰。可惜我爸走得太早了。
我说,我虽然不是你爸,也一样给你撑腰!
我被自己的大话吓了一跳。一个灰心丧气的孤老头儿,竟然自不量力地要给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打气撑腰。我还说得跟真的一样,声音洪亮,底气十足,而且不知什么时候站了起来。我在太阳地里边走边说,好像身体里真的有了庇护别人的力量。其实五个月前,这个女人试探着往湖水里走的时候,我差不多和她怀着一样的绝望。刚开始我没注意到她,我净想自己的心事了。直到我把两脚伸进水里,才发现前面的湖水已经把她吞了一半。阳光反射在湖面上,映得两个孤独的身影像两具闪着寒光的冰雕。我不知怎么就喊住了她。我的呼喊是给同类的,在她听来,却更像父亲呼唤女儿。她看着一脸凄切对她喊叫的白胡子老头儿,忽然大哭着向他跑来。
那天我向她开了最大的空头支票。我保证她身体会好起来,会有一个可靠的男人来爱她,还说只要把眼前的坏运气熬过去,前面就全是好运气在等着她。
从此我们隔三岔五通个电话,我的手机因此终于派上了用场。她可比小军细心多了,遇到天气不好或者我头疼脑热总会打来电话叮嘱几句,我有什么事情也会跟她聊一聊。我愿意跟她聊。这个世界上除了她没有谁还愿意跟我说这么多话。我生病那几天,她竟然跑到医院看我来了,一只手拎一罐鸡汤,一只手拎一袋苹果,着实把我吓得够呛,我怕万一被杜红霞碰上,又免不了一场战火硝烟。小军也吃了一惊,我注意到他的脸色明显暗了一下,好在这姑娘直爽,她大大方方告诉小军,我是李叔的朋友。她一来就忙活开了,帮我盛鸡汤,给我削苹果,中间还不忘淘好毛巾让我擦手。我一边吃一边偷偷瞟小军一眼,随时准备向他解释。但是小军什么也没问,他很快就出去接电话了,半天也没回来。我暗地里拿她和小軍比较了一下,觉得有个女儿真是不错。
我回到家已经12点多了,房间里静悄悄的,餐桌上扣着一小盆冬瓜炖排骨,应该是专门给我留的,因为李小军中午不回家吃饭,而杜红霞从来不吃肉。我把这视作杜红霞给我的示好信号。她为早晨的无礼后悔了,所以专门给我做了排骨表示悔过。我先进了卧室,想把剩下的2500块钱放起来,可是我怎么也找不到我的黑皮包了。今天早晨它还好好搁在柜子里,一上午工夫它就不知去向了。我一下急出了满头大汗。我也不管杜红霞是不是已经午睡了,站在她卧室门口大喊起来。
杜红霞!杜红霞!你看见我的黑皮包了吗?
杜红霞睡眼惺忪走出来,说我给您锁起来了,您那样放在柜子里太不安全了,随便什么人进来都可以拿走。
我说锁在哪里了?把钥匙给我。
杜红霞说,您又要取钱啊?今天早晨不是刚拿走一万块的存单吗?
我说这是我的事情,我的东西我自己掌管。
杜红霞当啷一声把钥匙扔在桌子上,说,看把您给吓得,没人想要您的钱!我就不明白了,您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攥着钱做什么?您还真想把钱留给那个女人啊?
杜红霞的话刀子一样扎在我心上。原来在她眼里,我已然老成一根朽木了,老到钱已经对我失去意义,老到我很快就没有时间享用,老到只能坐吃等死的年纪了。可我一点也没感觉到死亡的临近。我像每一个正常活着的人一样,相信自己生命还长。除了多年的房颤,我还算是一个健康的男人,我还在等着李妥妥结婚那一天,向我孙子郑重送上我的祝福。如果不是杜红霞嫌吵,我甚至还想把年轻时拉过的二胡也重新操练起来。活着就是活着,呼吸,走动,做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只要我不妨碍别人,别人也没权利妨碍我。我愿意把我的钱用在未来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上。可杜红霞不由分说就把我放进了等死的队列里。她收走我的房子,拿走我的皮包,限制我的行动,管控我的支出,就因为我七十六岁了,就因为她比我年轻,她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她具有这种权利。
我没吃那盆炖排骨。我拒绝领受杜红霞的好意。我带着辘辘饥肠去了街角的小饭店。我觉得自己不是去吃饭,而是回家。我和许宝花的家已经属于别人了,我只有在小饭店的油腻饭桌上,通过咀嚼一个又一个白菜馅饺子,才能捕捉到一点点家的感觉。我想起三十年前的那个除夕。那时宝花的健康还在,小军才是个准备高考的十七岁少年。我们坐在饭桌前,一边吃饺子,一边猜想小军的未来。在说到将来的儿媳和孙子时,我们开怀大笑,好像那是一件遥远的事情,遥远到永远不会到来。我一幕一幕回想那些往事,不由热泪横流。泪眼蒙眬中,许宝花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身边,她看着我,什么也没说,只把我的头轻轻揽在她的怀里。
晚上我对小军说,等租户到期,我就搬回去住。小军很吃惊,我爱看他这副样子,他瞪大眼睛的时候简直和许宝花一模一样。他说您是对我们不满意吗?我说,我在老房子里住习惯了,在这里有点不适应。小军盯着墙角不说话,过了好一阵才说,我还以为您和我一样,只要咱们住一块,做什么都是踏实的。我说,我住这里你踏实吗?小军说,当然啊,睡觉的时候我经常想,我正在和您呼吸着同一间房子的空气,这样就和小时候我挨在您身边睡觉差不多。
我的眼睛湿漉漉的。我说,儿子,有家饭店的饺子不错,抽时间咱们去吃一次。
小军说,让红霞包吧。饭店里的饺子哪有咱自己包的好吃。
我说,不是去吃饺子,是去吃味道。
我很满意和小军的这次谈话。那几天我心里热乎乎的。为了维持和平局面,我甚至没有再出门。我在屋里整理老照片,我把父母的照片、我和许宝花的照片、小军一家的照片按顺序放在影集里。这样,家里的所有人就聚到了一起。我看着他们,他们也看着我。我觉得我有孤独感是不对的。至少我还能和我的家人一起聚在影集里。即使我已经七十六岁,头发白了大半,我父母从照片里看我的眼光,仍然充满了欣赏和喜爱。
至少,比起那个女人我是幸福的吧。杜红霞的话提醒了我,我为什么不能给她点钱呢?三十多岁的女人,患上乳腺癌,丈夫又跑了,靠那么一点病休工资养活自己,她暗地里的悲伤一定数也数不清。我估摸了一下存单上的数字,从未来用途中给她匀出一份来。这一份虽然不能救她于水火,但总归能给她添点取暖的柴火。对一个待在冰天雪地里的人来说,每一根柴火都是有用的。
我七十七岁生日那一天,小军专门买了一条鱼,他说下班后要和我喝两盅。我很高兴。我没觉出大一岁的自己有什么变化,只不过像太阳西下,铺在地上的影子又长了一截。杜红霞不会收拾鱼,我说我来吧。这段时间我和她基本和平共处,想到不久就要回到老房子去住,我的心里又有了盼头,对她也就没有那么多计较了。
鱼很滑,不断从我手里脱出去,我的手上沾满了鱼的鲜血和黏液。这时我的手机在桌子上响起来。杜红霞过去瞟了一眼,咕哝一声替我挂了。她正在擦地板,拖把在桌子底下过来过去,撞得几只椅子咣当直响。没多久手机再次响起来。我说谁的电话?杜红霞说,不认识。我说手机没显示吗?杜红霞突然扔掉拖把,涨红着脸对我说,除了那个女人谁还会给你打电话?年纪轻轻找什么人不好,非要摽个老头子,心里打什么鬼主意以为别人不知道?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说着她就接通手机,把刚才的话对着里面重复了一遍。
我像手中的鱼一样张大了嘴巴,心脏怦怦狂跳起来。我眼睁睁看着杜红霞的话像利箭一样穿过我,射进那个女人单薄的身体里。那个女人像风中的树叶一样颤抖起来,我的嘴唇也跟着颤抖起来。风呼呼地从我耳边刮过,把我的声音扯得支离破碎。我听见自己对杜红霞说,把手机给我,把手机给我!
杜红霞把手机丢在桌子上,因为激动,她的双颊变得通红。你对着镜子看看自己,都什么年纪了,还搞老少恋,你就这么离不开女人?你为你儿子想过吗?为李妥妥想过吗?你弄个女人回来对全家有什么好处!
我用抓鱼的手抓起那只滑溜溜的手机,粘液和血迹把我的半张脸蹭得一塌糊涂,我的眼前也模糊得一塌糊涂。我说,孩子对不起!叔给你赔不是,刚才的话,你……你就权当没听见。那边叫了一声叔就哭起来,那哭声把我的心都要搅碎了。好在她很快就把哭声咬住了,她抽抽嗒嗒地对我说,叔,我打电话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给您祝个寿,祝您生日快乐。
我努力笑出声来,我说谢谢你孩子,叔很快乐,非常快乐。
狂跳的心就在这时安静下来,天地也安静下来。手机忽然没声音了,外面开着的电视也没声音了,盛鱼的不锈钢盆子被我碰了一下,翻了个跟斗掉在地上,也没发出任何声响。我像一片羽毛飘落下去。我看见整个房子掉了个个儿,地板一下跑到了天花板上。一切都不在原来的位置了,只有收拾了一半的鱼躺在厨房中央,正透过餐椅林立的细腿瞪着我。杜红霞满脸惊慌地从天花板上跑过来,她俯下身子,嘴唇大幅度地对我喊叫。我听不见她在喊什么,这样真好,我再也不想听到她嘴里发出的任何声音。
我还想对电话那边再说几句话,我怕那个女人刚刚搭建起来的世界又塌掉了。但我一句话也吐不出来。这时许宝花笑盈盈地走过来。全世界都静音了,只有她的声音清晰无比。她拉起我的手,无限温柔地对我说,走吧金堂,跟我走,咱们去过太平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