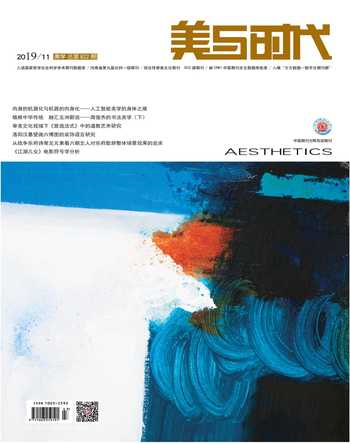论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者家国情怀的“悲剧性”
摘 要: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者家国情怀的悲剧性,这个问题能够在现实和历史两大维度进行讨论。其中现实一维包括启蒙和救亡两大方面。而启蒙方面又分为对民众和革命者的启蒙。在救亡方面,主要表现革命者们在斗争中忍辱负重的艰辛状态,并借此彰显他们家国情怀的悲剧性。历史维度则结合儒家的相关论述,把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者的家国情怀阐释为一种普遍仁爱,具有形而上的意义。从家国情怀悲剧性这一角度讨论鲁迅在当时文人中的独特性。
关键词:鲁迅;启蒙;革命者;家国情怀;悲剧性
鲁迅在民国众多知识分子中很独特。是“左翼”作家的领军人物。而“左翼”作家中却鲜有人具备鲁迅那样深厚的哲学造诣及古典文化修为。在精神气质上,亦罕有人能像他那样能在强烈的现代意识驱使下秉持“永远革命”的态度。而独特性为鲁迅本人带来的最大感受是孤独。鲁迅本人似乎也喜欢谈论孤独。他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1]他推崇“个人的自大”:“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于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嫉俗,渐渐变成厌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2]在社会治理方面,鲁迅也谈孤独:“猛兽是单独的,牛羊则结队。”[3]他还写过颇像自我对话的《孤独者》,小说主人公魏连殳从国外游学归来,被身边的人视为异类,被学界排挤,把孩子“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宝贵”[4]。在界定鲁迅的身份时,汪晖竟认为学者、小说家之类的身份并不能很好地概括鲁迅的写作生涯:
鲁迅是杰出的学者、卓越的小说家。但他的写作生涯却既不能用学者、也不能用小说家或作家来概括……他不愿把自己及其研究编织进现代社会日益严密的牢笼……他宁愿成为一个葛兰西称之为“有机知识分子”的战士。战士,这是鲁迅喜欢的词,一个更简捷的概念[5]。
汪晖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角度:可以不把鲁迅归于当时的文人群体之中,把他称为“战士”可能会更恰当。“战士”的身份较好地体现了鲁迅的特质。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鲁迅自身的现代性特质,可能还有比“战士”更贴切的词:革命者。革命者是特殊的战士,民国时的革命者是具有家国情怀的战士,是承担启蒙和救亡双重重任的战士。
本文试图讨论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者家国情怀的悲剧性,并借此角度进一步讨论鲁迅的独特性。关于革命者家国情怀的悲剧性,笔者从现实和历史两大维度出发进行了讨论。现实一维包括启蒙和救亡两大方面。而在历史维度,笔者把这种家国情怀的悲剧性追溯到儒家思想,并试着做出形而上的讨论。这可能与鲁迅对儒家礼教激烈批判态度不符,笔者在后文将做出解释。
一、以启蒙与救亡为主题的
现实环境下的“悲剧性”
(一)现实维度的启蒙方面,包括对民众的启蒙和对革命者的启蒙
首先是对民众的启蒙。李欧梵在《铁屋中的呐喊》中谈到鲁迅的小说《药》:
烈士被庸众所疏远和虐待,成为孤独者;但这孤独者却只能从拯救庸众、甚至为他们牺牲中,才能获得自己生存的意义,而他得到的回报,又只能是被他想拯救的那些人们关进监狱、剥夺权利、殴打甚至杀戮。他们看着他死去,然后卖他的血和买他的血去“治病”。[6]83
李欧梵指出了鲁迅笔下烈士们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孤独。他们为了民众的福祉流血斗争,而得到的回报却是:“只能是被他想拯救的那些人们关进监狱、剥夺权利、殴打甚至杀戮” “他们看着他死去”“卖他的血和买他的血去‘治病”。他们的悲剧性,由于民众的不理解而愈加凸显。如若民众理解,烈士们便不会孤独,他们的付出乃至于牺牲就不会被漠然地对待。其实,民众吃革命者的血这个例子本身具有很强的象征意味。现在,抛开象征单纯看这个例子本身:受到封建迷信蛊惑的普通民众坚信必须吃人血才能治病,而血是不是革命者的其实并不重要。不妨作一个假设:当地发生了革命武装流血冲突,斗争双方皆有伤亡。而如若民众恰巧蘸了反革命者的血吃呢?这在一定程度可能会稀释鲁迅作品的悲剧性和冲击力,但有助于我们更加冷静地去看待问题:也许民众会做出一些令革命者心寒不已的事,与其说他们是出于恶意,倒不如说是出于无知。反过来看这个问题:既然庸众蒙昧不理解革命,那么革命者的任务便不仅仅是要斗争,还应该教育庸众,使他们摆脱蒙昧并理解革命。换一种表述方式:革命者在致力于救亡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对民众的启蒙。
启蒙是改造旧社会的一项重大任务,革命者立志破旧立新,显然也不能忽视民众思想蒙昧落后的状况。如若一直不关注对民众的启蒙,反过来还要责怪民众对革命麻木不仁,那这种责怪就有些不近情理。鲁迅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把启蒙作为自己作品的一大主题。当然,毋庸置疑,是民众的不理解造成了种种革命者悲剧性的场面,所以笔者依然认为:未被启蒙的庸众对革命者的伤害一定程度上凸显了革命者家国情怀的悲剧性。
其次是对革命者的启蒙。也许读者认为革命者相较于民众是被启蒙过了的,为何文章还要讨论对革命者的启蒙呢?原因在于启蒙是一个不断深入推进的过程。鲁迅显然也注意到了从时间的维度去讨论启蒙。在著名的“铁屋子”隐喻被提出几年之后,他又举出了“吃醉虾”的隐喻。后一个隐喻一定程度上比较消极地回应了前一个隐喻,同时也为前一个隐喻就启蒙的讨论增加了时间的维度。他在“吃醉虾”的隐喻中讲到:
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鮮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玩赏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7]
读者不要被“醉”字误导,鲁迅在做启蒙的工作,他并不是想让民众迷醉,而是想让人更加清醒。然而人越是“清醒”,就越会“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所谓“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其中“越”这个字暗含了启蒙的时间维度:革命者心境的痛苦是伴随着启蒙的深入而不断加重的。在“铁屋子”的隐喻中,鲁迅还持有些许希望,他认为如果有几个人醒来,就不能说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可能。而“吃醉虾”的隐喻显然要更加悲观。革命者在这个隐喻语境中的处境极其被动,丝毫没有可以抵抗的可能,毕竟“醉虾”是任人摆弄而无力反抗的。而更令人痛心的是,对于仇视革命的人们来说,革命者不断加深的痛苦是可玩赏的。这种痛苦的加深凸显了革命者家国情怀的悲剧性。
下面作一个概括,“吃醉虾”的隐喻在如下方面体现了革命者家国情怀的悲剧性:革命者在启蒙深入后不断加重的苦痛,仇视革命的人对革命者痛苦的玩赏。对于鲁迅来说,可能还要加一条,即亲眼目睹革命者因自己唤醒而承受苦痛的心痛懊恼的情感。
(二)现实维度的“救亡”方面
鲁迅有一个“肩闸门”的隐喻:“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8]这段话出自《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跑到光明地方的人是指孩子们。可以就这个例子作一个拓展说明,如果这个“肩闸门”的人是鲁迅,那么到宽阔光明地方的人除了他的孩子,还应该有青年人。鲁迅很喜欢青年人,在很多文本中都表达了对青年极高的期望。如果抛开语境,也许还可以进一步延展这个隐喻:可以把“肩闸门”的人类比为同旧势力作斗争的革命者,而把到宽阔光明地方去的人们类比为革命者所要拯救的国民。“肩闸门”行为本身具有一定悲剧意味,这个隐喻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革命者“负重”的状态。当然,革命者们不仅仅要“负重”,他们还要“忍辱”。鲁迅在《自嘲》中有句很有名的话“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9],其中勤勤恳恳甘为“孺子牛”的表述是“肩闸门”的另一种具体写照。而为千夫所指,即被敌人和蒙昧大众侮辱则是革命者“忍辱”的一种体现。除了承受这些侮辱,他们还要承受来自阵营内部品行低劣者的羞辱诋毁。
鲁迅曾这样说自己:“是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舐掉血迹,至多也不过呻吟几声的。”[10]188他话中所指伤害他的人不是反革命者,也不是普通民众,而是他曾给予厚望的青年。“救亡”的命题太大,其背后涉及到了太多的纠葛,很多是出现在革命者阵营内部。一些革命者并不赤诚,革命阵营内部也存在很多由他们挑起来的纷争。当革命者们在顽强抵抗旧势力的同时还要承担着来自阵营内部那些猝不及防的打击的时候,其家国情怀的悲剧性便愈发凸显出来。鲁迅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对青年关怀备至,但是后来恰恰是这些他曾经深深信赖的青年给予他巨大的伤害。他曾指出“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历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10]188。“肩闸门”的人本已不堪重负,这个时候他所放“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的人却还要在他身后对他“反噬构陷”,玩阴谋耍手腕。“反噬构陷”的行为颇有恩将仇报的意味。对此鲁迅补充说:“世故也愈深,所以也渐在回避了。”[10]188看上去他似乎有所放弃,但是就他的生平以及他后期所迸发出的强大斗争能量来看,鲁迅在他的革命者立场上并没有丝毫动摇。甚至在他去世的1936年还提到:“但我,老实说,也没有去想过敌人什么时候会失败的事情。就只觉得这样和他(敌人)扭打下去就是了,没有去想过扭打到那一天为止的问题。”[11]革命者们长期负重而不言放弃,备受各方诋毁侮辱而没有丝毫妥协,他们家国情怀的悲剧性由此而得到彰显。
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者家国情怀的悲剧性可以总结为:在“启蒙”方面包括蒙昧的民众对革命者的伤害以及革命者启蒙深入后痛苦的加剧;“救亡”方面包括革命者对重负的承受以及对各方打击的容忍。
二、中华历史传统对“悲剧性”的启示
家国情怀驱动下的人生十分艰难,很多人会质疑:这对人到底有没有意义?显然我们不能混淆一件事即对民族的意义和其对个体自身的意义。鲁迅曾长期在思考人生的意义,并对此作出过很多讨论。他在《野草》中探讨得尤其深入,也表现了很强的虚无主义倾向。下面摘取《野草》中的《过客》一段内容试作讨论。当被问到要到哪里去时,鲁迅笔下的客人道:“但是,我不知道。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是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个地方就在前面。”[12]李欧梵曾对此作出解读:“不管多么荒诞无意义,即使走向的仍是死亡,生命总得走去。即使走向的未来也仍是黑暗,也决不返回过去的黑暗中。”[6]117鲁迅虽然有虚无主义倾向,但并非那么彻底。他也曾写过“创作总根于爱。杨朱无书。创作虽说抒写自己的心,但总愿意有人看。创作是社会性的。但有时只要有一个人看便满足:好友,爱人”[13]。可以发现,鲁迅在一定程度上洞识了人生的荒诞虚无性,但他也将自己的创作根植于爱。可以尝试作个不恰当的解读:既然所有人最终都将走向的是死亡,那么走的方式尤为重要,走的方式本身一定程度上能够凸显生命的价值。鲁迅把他的写作事业根植于“爱”,这也可以理解为他走的一种方式。鲁迅用文章攻击了无数人,而他写作的目的却是和“爱”相关的。那么他爱的对象只是他的好友或者爱人吗?可能不仅仅是。正如他写文章一样,好友或爱人去读是最低的程度,看的人越多自然越好,毕竟“创作是社会性的”。那么鲁迅这一生所写的文章所根植的“爱”是什么呢?虽然鲁迅对传统儒家文化有很大的批判,但是作为深受传统文化熏染的中国人,作为对中华古典文化颇有造诣的知识分子,就精神气质上来看,鲁迅颇有儒家那种“爱人”的“仁者”气质,颇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士大夫风范。当然这可能与很多人印象中那个极力抨击儒家传統文化的鲁迅形象不是很符合。但正如学者曾指出的:
就传统本身而言,它是一个内蕴复杂的结构……被指责为全盘反传统主义者的鲁迅、胡适等五四知识分子……在生活实践层面,却是传统家族伦理的身体力行者……由此也足见传统并非那么容易断裂[14]。
林毓生也曾指出鲁迅在“隐示的、未明言的层次”发现 “中国文化传统中某些遗留成分具有知识或道德的价值”[15]。当然儒家的“仁”与鲁迅所说的“爱”并非完全相同,儒家提倡的是由血缘亲情推广开来有差等的“仁爱”,但是也正是儒家“仁爱”的差等的特质使得我们看到连接二者的可能。士大夫对一般大众的爱是一种普遍的仁爱,不同于血缘亲情之爱。而鲁迅对民众之爱恰恰也是一种普遍仁爱的体现。他们的这种普遍的仁爱散发着一种崇高而冷漠的气质。康德对普遍仁爱的表述十分有助于我们认识上述二者的普遍仁爱的相通之处:
普遍的仁爱是同情其不幸的根据,但同时也是正义的根据……一旦这种情感上升到其应有的普遍性,它就是崇高的,但也是冷漠的……若不然,有德性的人就会像赫拉克利特那样痛苦得不停淌着同情的泪水,尽管有一切这样的善心,却无非是成为一个软心肠的闲人。[16]
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鲁迅在深深关爱同情民众的同时却又在狠狠地嘲讽挖苦他们;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生活状态总是莫名的郁郁不快;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儒家士大夫会以天下为己任,穷极其一生致力于推行仁义、仁政。鲁迅如同儒家那些士大夫一样,他们的普遍仁爱并不是软心肠,而是一种散发着崇高光辉的道德品格。
鲁迅和儒家士大夫们所选择的当然不是舒适的生活方式,而是严格遵守道德律令的生活方式。他们有更高的追求,宽以待人、严于律己,以身边儿人的快乐为快乐。日本学者竹内好认为鲁迅是个殉教者:“鲁迅并不认为自己是殉教者,而且很讨厌自己被看作殉教者。但是在我看来,他的表达方式确实殉教者式的。”[17]竹内好讲到了赎罪与鲁迅写作的关系,还猜测“鬼”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但正如竹内好自己所指出的那样,可能鲁迅本人也不会承认他的这种说法。但是竹内好的确发现了鲁迅那种张扬道义的苦行僧般的写作态度。这种态度显然也是很多“殉教徒”所持有的。但是显然鲁迅不信宗教,儒家的士大夫们也不是很在意鬼神。虽然方式可能类似,但是他们所坚守的东西是不同的。如果说殉教徒是为了彼岸世界的某种东西,并抱有赎罪的心态去实现其目的的话,那么鲁迅和士大夫们所坚守的更有可能还是停留在此岸的世界上。那么是此岸世界的什么呢?具体内容应该各不相同,但大体方向都应该不会脱离普遍的仁爱。所以相较于“殉教者”,笔者更倾向于称他们为“殉道者”。但他们为什么会坚持去做这种殉道者呢?对鲁迅有很大影响的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曾说过:
我们不妨这样来看自己:对于艺术世界的真正创造者来说,我们已是图画和艺术投影,我们最高的尊严就在作为艺术作品的价值之中——因为只有作为审美现象,生存和世界才是永远有充分理由的。[18]
正如尼采所言:“只有作为审美现象,生存和世界才是永远有充分理由的。”很难说有着深厚美学造诣的鲁迅和孔子等儒家士大夫在实践的时候没有在潜意识中察觉到这一点。反观他们的行为,确实可以感觉到他们像是在打磨艺术作品那样打磨他们自己的生活,也能感觉到他们借此去追求在美学维度上更丰富、更有品味、更有价值的生活。而这种生活方式是对生命有限性的超越以及对生命意义的极大张扬。而且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也可能会理解为何孔子这位儒家的代表人物会有“吾与点也”这种看似与儒家入世进取主张相矛盾的态度。
但是毋庸置疑,无论是鲁迅还是儒家,他们所主张的生活方式并非完全符合尼采意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与尼采的主张相悖。尼采曾指出:
在这个义务和权利的领域里开始出现了一批道德概念,如“负罪”“良心”“义务”“义务的神圣”等,它们的萌芽就像地球上所有伟大事物的萌芽一样,基本上是长期用血浇灌的。难道我们不能补充说,那个世界从来就没有失去血腥和残忍的气味?就连老康德也不例外,他那“绝对命令”就散发着残酷的气味。[19]
而鲁迅和儒家士大夫们恰恰是按照散发着残酷气味的“绝对命令”而生活的。鲁迅虽然欣赏尼采并受其影响,但他对尼采的思想并非全盘接受。正如有学界认为鲁迅是中国“温和”的尼采的说法。下面摘取一例:
鲁迅虽然主张文化批评,提倡主观意力,鼓吹“超人”,但他却没有接受高山樗牛他们提出的本能满足论,也没有接受他们非道德主义的解释……鲁迅所选择接受的是他们的“温和”的尼采观点,而每碰到“强横”的地方,鲁迅就略过去。[20]
在尼采高扬权力意志的主张可能会使人们具有非道德主义的倾向的时候,鲁迅选择了“略过”。毕竟人的感性与道德两大维度并不是完全不可调和。而且如殉道者般那样严格服从道德律令的生活也并非不可以被审美化。鲁迅和儒家士大夫们把对“绝对命令”的坚守融入生活,并且把自身的生活打造为艺术作品。当然也正是这种对残酷“绝对命令”的坚守使得他们的生活表现出强烈的“悲剧性”。那这样的生活方式对人自身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说尼采是在高扬人的权力意志来抵抗生命自身的荒诞虚无性,并凸显人的意义的话,那么鲁迅和儒家士大夫们则在道德维度为尼采的说法做出了一些调整,使人的价值散发出些许柔缓温和的道德光辉。
三、结语
《论语》中的一段故事:“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21]子路在石门过夜。守城门的人问:“从哪里来?”子路说:“从孔氏那里来。”守门人说:“就是那个明知做不到却还是要做的人吗?”其实孔子身份的悲剧性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这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守门人体现了当时普通百姓对孔子的大致看法:他是在和他自己过不去。而孔子的这种,近乎是有目共睹的“悲剧性”的生活,也由于他的“仁以为己任”而表现出悲壮的意味。反观革命者鲁迅,他的“悲剧性”何尝不是这个“知其不可而为之”呢?显然他们在普遍仁爱驱动下过着殉道者般的苦行生活是很難为推崇幸福的世俗所能理解的。
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者的家国情怀背后有着现代性与儒家仁爱传统的交织。这可能是当时“五四运动”时期革命者们潜意识中的一个特征。而这为我们认识鲁迅在文人集团中的独特之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无论是相较于非“左翼”的还是“左翼”的文人,鲁迅可能在现代性和传统这两个方面都走得更远。在现代性方面他走得更激进极端;而在中华传统仁爱的精神气质的传承方面,可能也要比当时的知识分子做得更加内化,乃至于不仅仅是一种文本的研究阐释,而是内化为了他自己写作的一种方法论。当然在这两个方面走得更远的鲁迅本人陷入了对当时现状的深深不满当中,其所彰显出来的革命者家国情怀的悲剧性也愈加鲜明。这也就使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感觉,问到民国文人谁的作品有悲剧气质,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常常会是鲁迅,正是他自身的特质使得他作品的“悲剧性”十分鲜明,让人印象深刻。
参考文献:
[1]魯迅.这个与那个[M]//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52-153.
[2]鲁迅.随感录三十八[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27.
[3]鲁迅.春末闲谈[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16.
[4]鲁迅.孤独者[M]//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93.
[5]汪晖.《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序言:序四[J].鲁迅研究月刊,1996(11):57-62.
[6]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M].尹慧珉,译.长沙:岳麓书社,1999.
[7]鲁迅.答有恒先生[M]//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74.
[8]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35.
[9]鲁迅.自嘲[M]//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51.
[10]鲁迅.致曹聚仁[M].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1]冯雪峰.冯雪峰忆鲁迅[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97.
[12]鲁迅.过客[M]//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95.
[13]鲁迅.小杂感[M]//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56.
[14]陈汉萍.全盘反传统抑或改造传统:重审鲁迅与传统文化[J].社会科学战线,2010(12):108-121.
[15]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M].穆善培,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6:252.
[16]康德.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M]//康德美学文集.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92.
[17]竹内好.鲁迅[M]//近代的超客.李东木,赵京华,孙歌,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8-9.
[18]尼采.悲剧的诞生[M].周国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21.
[19]尼采.论道德的谱系[M].周红,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45.
[20]张钊贻.早期鲁迅的尼采考——兼论鲁迅有没有读过勃兰兑斯的《尼采导论》[J].鲁迅研究月刊,1997(6):4-18.
[2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159.
作者简介:王继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硕士研究生。
——从“悲剧性”和“心流”的角度解读书法史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