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丧文化”表情包的图像传播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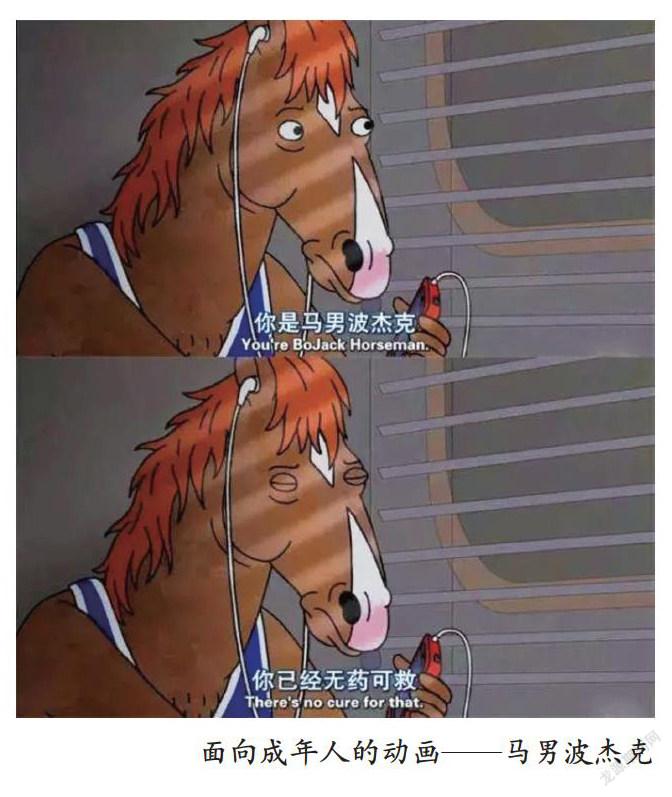
摘 要:“丧文化”表情包作为青年亚文化现象,体现了一种新的时代特征。从图像传播的视角看,“丧文化”表情包的画面元素不拒绝审丑和非真实,是一种“主动污名化”的情感表达,其网络传播特点具有娱乐化和视觉化倾向。
关键词:丧文化;图像;表情包;网络亚文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网络‘丧文化’的视觉传播与价值导向研究”(201810363066)研究成果。
“丧”字是近几年的网络热词。从词源上看,“丧”字本身就带有图像意味,甲骨文为“ ”,中间的主体部分为养蚕的桑树,而围绕桑树周围的四个“口”字实为从四周吃食桑叶的蚕虫,象征着“满树的蚕虫将桑树的叶子吃光,在后续的金文变形中甚至在象形文字底部直接加上了‘亡’字,‘丧,亡也’,意为‘消失’”[1]。“丧”作为甲骨文的意象生动而残忍,观者不由得会想象自己的人生竟如桑树一般,由四面八方的威胁蚕食殆尽,不断地失去,从而充满了无力感与劣等感。
在互联网时代,随着网民“表情包大战”的火热进行,一波以“悲伤蛙”“马男波杰克”“懒懒蛋”和“葛优瘫”为代表的“丧文化”表情包开始登上“斗图”大舞台。表情包作为网络亚文化,是图文结合的典型代表。“丧文化”表情包的火热,意味着“丧文化”在当代青年的内心占据着一席之地,表情包为其表象之一。从图像的角度关注流行文化,即以直观的符号修辞贴近青年人的内心世界,把握时代的脉搏,体味互联网时代下亚文化话语权的多样性。
一、“丧文化”表情包的画面元素使用
当下,人们通过数字媒体生产大量的图片。这种大规模的图片生产可以解释为一种保护性和逃避性的反应。现今的图片生产表现出一种美图狂热,大多体现为真人实拍图片的修补与美化。网络中众多美图软件应运而生,更出现了以“柔光自拍”为卖点的智能手机,以此篡改人们所感知到的“并不满意的现实生活”。与此同时,与“美图照片”相对应,网络上却很少出现制作精美、美轮美奂的表情包。虽然同样追求对现实的暂时性逃避,但表情包制作简单甚至粗糙、不讲究艺术美或是文字美,更有不少用户二次制作的表情包像素不高、图像模糊,仅能勉强达意,奇特、怪异、缺陷、任性。表情包在形式上最大的特点是不和谐。
丑感,在广义上是美感的一种。“‘丑’使人感受到历史和人生的复杂性和深度,这给人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感,从而使人得到一种带有苦味的愉快”[2]。丧文化表情包更是如此,它的元素内容不会拒绝表现丑。相比起过多修饰的美图照片,揭露丑或是进一步的塑造丑成为网络时代的潮流。如雨果所言,“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3]。这种刻意扮丑元素的选取与青年人“反鸡汤”的亚文化潮流相呼应,即被大众宣传的美不一定是真实的,呼唤一种反乌托邦的思考方式。例如,在网络上传播最广的四大丧文化表情包中,“悲伤蛙”“马男波杰克”的形象都是拟人动物的卡通形象,但颠覆了以往人们对“可爱的动物卡通”的认知。“悲伤蛙”和“马男”的画面线条较为成人化,在一般动物卡通形象会避免的皱纹、牙齿、体毛等方面却毫不忌讳。同时在一般动物卡通形象着重表现的梦幻闪亮的眼睛和纯真快乐的表情却刻画寥寥。在巨大的认知反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两位动物主角的成人化表情,一位负责悲伤和痛苦,另一位负责冷漠和绝望。人的第一视觉目标往往是眼睛,所以受角色下垂的眼角与巨大的眼袋影响,即使“悲伤蛙”偶尔出现上扬的嘴角,也会使观者觉得这并非是真心的笑容,而是不情愿的“悲伤式”假笑。
“丧文化”表情包元素的形式构成与一般表情包并无太大区别,以图文双构模式为主,即图片与文字配合,图片占视觉主体,文字是对图片的语境解释。一般表情包的图片来源,主要分两种类型:真实人物式表情包和虚拟人物式表情包。其中前者包括影视故事的截图和明星事件的照片,后者包括动画或漫画的截图和再造式涂鸦。可以发现大多“丧文化”表情包倾向于选取虚拟人物进行再加工。“丧文化”表情包的图片多数来自漫画、动画,相比起现实人物,虚拟人物可以通过更直观夸张的手法表现出动漫原作者和表情包二次制作者的强调重点。如“悲伤蛙”将悲伤直接表现在它下垂的五官上、“马男波杰克”则用马的身体穿着人类的衣服参与人类社会,充分体现人的异化与疏离。这两种虚拟形象的创造,就是赋予其命运的一种形式。“对所有这些角色来说,它们的作品规定了它们,至少是以作品被这些角色所确定的样子,显像和存在并无界限,人们不再讲述‘故事’,而是创造自己的天地”[4]。举例来说,“马男波杰克”的表情包,绝大多数为动画截图,保留其原始的画面与字幕,二次创作较少,最大限度的展示原作。而原作的意义也足够丰满,单张的台词和画面足够传达“丧”的意义。作品主角是一匹中年过气的明星马。年轻时他主演的电视剧风靡一时,而今却只能与废柴一同生活。他自私不负责,自卑又毒舌,他知道自己是个混蛋,但他也想做个好人。其中有代表性的动画台词截图有:“你是马男波杰克,你已经无可救药”“活着的感觉就是自己的尿道被不断地猛踢”等。这样的台词从一匹马的口中说出来,已由恶搞性质的形象审丑过渡到荒诞感。艾斯林认为荒诞感展现了“人在荒诞处境中所感到的抽象的心理苦闷”[5]。“马男”焦虑、恐惧、绝望的形象与丧文化表情包的需求不谋而合。“马男”元素的使用使动画截图的传播能最大程度地传达感情。“丧无需言”,这种主角元素的选择也体现在其他丧文化表情包上。它要求主角带有消极的故事与经历,吸引观者快速融合画面,进入语境。被麦克卢汉认为的冷媒介的卡通参与度更高,我们“看漫画、动画时需要补充所缺失的信息”[6],这也为虚拟式人物表情包带来了充分的参与性。
作为视觉次重点的表情包文字部分往往是用户二次创作的重点。除去以“马男波杰克”為代表不改变原作画面字幕的一类,其余的表情包为“原图+原创字幕”或是“加以改动的原图+原创字幕”。字体以鲜艳的颜色显示,对字体位置排版等并无艺术性的考虑,活泼易读即可。虽然用户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原创个性化字幕,但文字内容主要是各种亚文化的网络流行语,以情绪化、口语化为特点。“丧文化”表情包的文字内容,主要是“丧”主题的流行语,如“差不多是一个废人了”“不想努力,只想颓废”“颓废是糖,甜到忧伤”等。观察多个表情包可发现特定的字词往往会重复出现,如“颓废”“不想”“放弃”“失望”“悲伤”等。“图文双构模式具有互文性优势,文字和图像不再孤立地产生意义,它们通过彼此来产生信息。”[7]针对如何进一步将文字表达得更充满情绪、更口语的问题,现实中交流由语言、语气、表情、肢体动作联合传达含义,但在网络社交中无法做到面对面的交流,这种情况阉割了语气、表情和肢体,变得只有语言,让一些微小的、意义含混的主观含义无法传达。表情包图片和文字加以巧妙配合,使被输入的文字有了人的主观参与,这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使用者此时的心理活动和想表达的真正含义。
二、“丧文化”表情包的画面情感表达
“丧文化”表情包画面的情感,“如钟摆一般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来回摇摆”。网络上流行的四大“丧文化”表情包都逃脱不了这两种情感的控制:痛苦和无聊。如“悲伤蛙”表情包的画面以其流泪大哭或是强颜欢笑的表情特写来体现痛苦;“葛优瘫”表情包的画面以其懒散瘫卧在沙发上的整体动作来体现无聊。如叔本华所言,“究其根源,痛苦和无聊是一种双重对立的存在,一是外部的或客观的,一是内在的或主观的。匮乏的环境和贫穷会导致痛苦,一个人没有真正的需求则会导致无聊”[8]。不论是痛苦还是无聊,都使人的力量停滞郁积,所以“丧文化”表情包的画面常给人以负能量的印象。
“丧文化”表情包作为青年亚文化的一种,它“负能量”情感的表现可以说是刻意的、强调的,是一种“主动污名化”。出于青少年的反抗心理和自我保护机制,很容易产生“与其被主流文化定义和批判,倒不如提前定义自己、批判自己”的想法。所以“丧文化”表情包的生产者们会将他们痛苦和无聊的消极情感进一步放大,在释放情绪的同时先主流文化一步来“主动污名化”。“一切新文化都是青年亚文化”[9]。
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图像的情感表达方面,一种亚文化,“尽管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其‘焦点关切’(focal concerns)、其独特的形态和行为——不同于产生它的‘父辈’文化,但也会与‘父辈’文化分享某些共通的东西”[10]。以“葛优瘫”表情包为例,它是指演员葛优在1993年情景喜剧《我爱我家》里的剧照姿势。中国九零后、零零后的年轻人其实对这部喜剧没有太深刻的印象,《我爱我家》严格来说是他们父母一辈的记忆。但这样一部喜剧的剧照却在二十多年后在网络大火,加入亚文化表情包之中,这是大家都难以预料的。原作葛优饰演的二混子季春生,在表情包图像中穿着宽大滑稽的花衬衫、留有漫画式的胡子和“地中海”的发型,嘴巴微张、双眼无神、仰头向天。图像中人物的“坐姿”介于“坐”与“躺”之间,用不到腰部肌肉,同时脖子也能靠在沙发上,脖子部位的肌肉被“架空”,人自然就感觉放松了。而且人物有台词“(我)过得很好。也就是三天没吃东西,八个月没洗澡,不记得上回在屋里睡觉是哪年的事了。”——借上述人物图像以表达无聊颓废情感,存在于上世纪的人物设定与青年人的“丧文化”巧妙配合,青年人更是先父辈一步对此进行再定义,在广泛传播中达到自己叛逆的胜利。“葛优瘫”表情包在两代人之间新产生的图像情感既存共通、也显新异。
三、“丧文化”表情包的网络传播特点
“丧文化”表情包的制作与使用,是自嘲先他嘲一步的策略,是一种与外界建立对话的方式。“丧文化”表情包的网络传播特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从丧文化表情包本身而言,它的弱关系促进其传播,如曼纽尔·卡斯特所言:“当今支配性功能的空间结合的确发生在由信息技术所导致的互动网络里。在这种网络里,没有任何地方是自在自存的,因为位置是由网络中的流动交换界定的。”[11]中国的网络社会与费孝通所定义的差序格局有所不同,丧文化表情包虽然属于小众的亚文化,但它能做到在传播中开放、积极和兼容。丧文化表情包并不是为青年人所独享,它所表达的情感强烈且易懂,传播门槛较低,并且与父辈文化在图像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共通(如上文提到的“葛优瘫”表情包),进而“丧文化”表情包在网络上使用人群较多、范围进一步扩大,对话范围更广。
(二)从“丧文化”表情包的传播媒介而言,“一种媒介的表现形式难以和这种媒介本身的倾向性对抗”[12],“丧文化”表情包的网络传播平台具有娱乐化倾向,这也使“丧文化”表情包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戏谑性自嘲、一种大家都默认的黑色幽默。在这种认知语境下,传播者与观者都默认了这种情感隐喻,即这是一种自嘲或是一种娱乐,抒发个人“丧”的情绪,点到为止,不会过于泛滥。适度地制作或使用“丧文化”表情包是一种与外界积极交流、释放情绪的方式。相比起让个人内心的“丧”感在封闭孤独的环境下不断地升温加重,网络环境下的一笑而过,使“丧感”的排解与疏通有了存在的可能,从而产生了正面作用。
(三)从“丧文化”表情包的视觉构成而言,图像为主、文字为辅的设计迎合了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适应了娱乐业的发展,舍弃了对“丧”的深度沉溺。图像的过多使用使表情包倾向于一种表演艺术,与大段的文字相比,它需要被“看”而不是被“思考”。“丧文化”表情包所呈现的滑稽式审丑人物形象或是“丧萌”的漫画形象都可理解为一种潜在的减压方式。若这种“丧感”在网络上流露出大段严肃性文字并得以大范围传播,这才是过度的负面情绪释放、一种会传染他人的消极方式。
四、结语
“丧文化”表情包作为一种图像化的解压方式,它的适当传播更像是网络亚文化群体的一种心照不宣。人民日报谈“丧文化”的流行:“年轻人总体上并不丧,不需要过度忧虑”。在“丧文化”表情包无聊懈怠、漫无目的、欲望低迷的画面表现下,其传播内核是幽默无害的。青年人在网络上通过滑稽和自嘲式的图像将今天的不顺利一笑而过,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明天的希望。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1:84.
[2]叶朗.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73.
[3]雨果.克伦威尔序[M].缪灵珠,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373.
[4]加缪.西西弗神话[M].杜小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123.
[5]伍蠡甫,編.现代西方论文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357.
[6]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7]迪克,主编.话语研究:多学科导论[M].周翔,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96-97.
[8]叔本华.人生的智慧[M].韦启昌,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30.
[9]蒋原伦.一切新文化都是青年亚文化[J].读书,2012:107-112.
[10]霍尔,杰斐逊,编.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M].孟登迎,胡疆锋,王蕙,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77.
[11]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506.
[12]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111.
作者简介:沈馨雅,安徽工程大学艺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