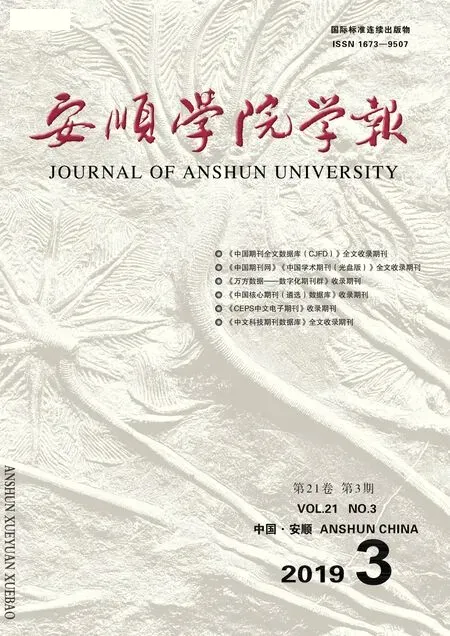明清时期桂北三江侗族地区法制儒家化研究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广西 南宁530006)
一、明朝——国家礼法体系外的三江侗族
(一)法律实施上的“华夷有别”
中原法律体系的体躯是法家所创,但是其生命是儒家所赋,法家重刑治,儒家重礼治,礼法之争,最后以儒家胜利而奠定了“礼刑一体”的中原礼法体系[1]。与儒家礼法一起被统治者用于封建王朝统治的是儒家的“华夷之辨”。明朝在对待非汉民族时具有强烈的敏感与偏见,朱元璋将“华夷之辨”作为“国策”贯彻到非汉族地区的礼教推行与刑法实施当中。
在三江地区(明清时行政区划名为怀远县),“夷夏之防”从汉与侗、苗、瑶、壮等分别聚居的情况就可看出。在推行教化时,知县苏朝阳将儒学署设于汉人聚居的老堡县的县衙内,对三江侗族地区的辐射有限。而对于儒家文化普及率较低的民族的法律适用问题,明王朝在《大明律》中规定:“凡化外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2]然而,实际的法律援引情况却并非如此,民国《三江县志·行政组织之沿革》记载:
县境傜(瑶)僮(壮)伶侗,盘踞山谷,耐杀喜斗。向示羁縻,不习官法,为以彝治彝计,乃设六刀酋长缘大傜峝(峒)二峝(峒),置六刀,付与各酋,每傜(瑶)犯法,请刀行诛。[3]
六刀酋长由各民族内部选出,实际上是明王朝安插在少数民族内部的镇压人员。由此可见,《大明律》关于“化外人”的法律规定,仅显示明王朝有将少数民族纳入国家法律体系的宏愿,事实上,少数民族享有很大程度上法律的自治以及军事的自卫权。
(二)三江侗族于国家组织外自觉形成的社会规范
三江侗族地区处于国家法律和基层组织之外,但这并不意味着三江侗族地区常年处于混乱的状态。除了关乎家族荣誉的“血族仇恨”不得不报的情况外,三江侗族地区大多处于有序的状态。在家族组织上,三江侗族地区形成了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组织,宗族内有相应的习俗和规约。除此之外,多个或者几个毗邻的侗族村寨组成或大或小的“款组织”,款组织集法律自治与武装防卫于一体。款组织的领导者为“款首”,款首在每隔三五年举办的“款民大会”上由民主选举产生,鼓楼是侗族款民大会的集会地点,成年男性侗民均需参加。款首是义务性质,不拿酬劳,身份同时还是巫师与款军首领,办事的信服度是其能否获得群众支持而继续担任的标准。而为了让处理各类事务有一定的标准,款首们商定适用于款组织下各村寨的法律规范,名“款约”[4]。此外,村寨作为小款或小款的一部分,是联结家庭组织与款组织的枢纽,由寨老管理,其内部也会制定村寨内部的规约,是款约的一部分。
(三)清朝之前三江侗族处理各项事务的规定
要研究清朝之前三江侗族的社会规范需要参考清朝时期以汉字翻译的《六面阳规》《六面阴规》与《六面威规》[5](简称“三江本款约”),其内容在清朝及之前就以口头的形式在三江侗族社会中起着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主要如表1所示。

表1 “三江本款约”中对于各类事务的规定
二、清朝——三江侗族法制儒家化时期
(一)儒家礼法文化的渗透
1.科举学校体系的建立
清政府作为满族入主中原,对于民众和儒家知识分子基于“华夷之辩”所产生的抵触情绪,一直采取规避和消除的态度。为塑造正统的身份,清朝颁布的《大清律例》沿袭了《大明律》的做法,以象征中原礼法传统的《唐律疏议》为蓝本,并对“化外之民”沿用明朝“凡化外人有犯者,并依律拟断”,这也表现出清政府把自己看成是“化内之人”的心理。对于广西这一“渐染之地”的治理,顺治帝时定下了“以文德绥远,不欲穷兵黩武”的基调[6],显然清政府很清楚文教对于边疆地区民族文化上趋同于中原的重要性。
三江侗族地区文教萌生之际始于“三藩之乱”被平定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广东龙门举人廖蔚文被派到怀远县任知县,一上任就于古宜梓潼阁开办书院,并在古宜城东门内办义学一所。义学专为贫寒子弟和少数民族群体设置,免费教学,书院和义学都延请名师讲学,廖蔚文还出示文件,招揽各村各民族子弟进到古宜城中读书[7],在廖蔚文担任知县的这段时间,怀远县已经达到“书声夜分不辍,即远方亦闻风兴起,诵读相闻,且课稿络绎送至,文风蒸丕变矣”[8]的情形。随着三江地区学风渐浓,三江侗族地区在乾隆年间开始出现第一批读书应试者,《三江县志·列传》载:
龙从云,龙仁潭,龙在沼,龙继光,吴成章,吴盛文,吴成学,吴老田,杨萃肚,杨老五,十人特倡译集资兴学,延聘通道县栗团宿儒肚正先生来村(马胖)主讲,于时而村中之耕者、读者,机声、书声,相闻作矣。[9]
官方和民间教育机构的落成,给了三江侗民进入学校,接受教育的机会。作为科举考试官方文字的汉字,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三江侗族民众识知,三江侗族开始用汉字记录款约。
2.乡约宣讲
知县廖蔚文深知对三江地区侗、苗、傜、僮进行普及教化的重要性,在将各族招揽进义学的同时,其十分重视接受教育的各族人士对乡村的反哺作用。廖蔚文让各族子弟在县城接受教育的同时,还倡导其回到所在乡村宣讲《上谕十六条》,目的不仅仅是要各族子弟读书识字,更要识礼。
《上谕十六条》是对顺治帝《六谕》的扩充,《六谕》是沿袭了明朝时期的《圣训六谕》,而《圣训六谕》是对宋朝时期开始出现的民间乡约的官方化[10]。
对于《上谕十六条》具体执行的情况,《三江县志·学风》提到“朔望宣讲,前清盛行……宣讲所,前有定时订地”[11]。“朔”“望”分别指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在这两个固定时间,不管是官还是民,都要到固定地方参加“乡约宣讲”。另外,知县廖蔚文为了将儒家礼法灌输给文教尚未昌明的三江侗族民众,还创造了朗朗上口的《宣谕》,比如《宣谕林溪》:
江源直到武陵津,风俗依然见旧秦,汉代至今几易主,夜郎此日有移民,文身椎发银为饰,鴃舌侏离鸟共鸣,给紴宣扬知向化,不教鹿豕结成僯。[12]
3.三江地区侗族与汉族的联合
除了科举学校体系与乡约宣讲体系的推行,浸润儒家文化的汉人的行为举止也影响着三江侗族。民国《三江县志·民间规约》载:
当太平天国革命军兴,清咸丰六年(1856年),贵州开泰永从苗首戴老寅、龙老盘趁机倡乱,窜入县境,浔溶丹阳三区,惨遭蹂躏,独平江全区侗人团结一致,与之抗,大小数十百战,虽有伤亡,全境卒赖以安,嗣则黔之清流苗乱,历咸丰六、七、八、十一年,同治元、二、八年间,不时扰犯,皆能予以堵击……当是时浔江河里一带之团亦崛起,迨黄金亮等之侵扰,而有三峒六甲联组九合局之扩大款。[13]
“六甲”地区为汉族聚居区,此区的汉人是在宋朝时从福建逃难而来,民国《三江县志·民族》载:
汉人,先后来居境内,散处各地,日益滋蕃,衣冠文物,亦渐渍于各族,其先入内地斩棘披荆,开辟浔江者,首当推六甲人……六甲人,宋大观元年,金兀术侵扰中国时,福建汉氏曹、荣、龙、李、潘、杨、欧、马、蓝、侯、龙、谢十二姓,联合由福建省汀州府逃难,经广东,达柳州,而至古宜……立县治老堡。[14]
可见,三江地区的三江侗民与汉族为抵抗太平天国引发的战乱而开始联合,这让三江地区侗与汉成为利益共同体,这加速了儒家文化的传播。《三江县志·列传》载:
赖步瀛,由广东梅县松源堡迁居县属富禄,岁贡生,好学力行,仁民爱物。咸丰间,邑西有苗匪之乱,桂黔当局,合兵会剿,以步瀛服众望,聘为指导官,随营参赞,佥议殄灭,步瀛力主安抚,一时仁生声播,纵横百里。[15]
从赖步瀛的影响可以看出,以“仁义礼智信”为行为规范,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想的汉族儒家知识分子,在各族民众抵御战乱中起到了榜样的作用,这无疑会引起各族民众以其行为方式为楷模。
(二) 三江侗族地区法制儒家化
三江侗族在自身的宗法组织下本身就十分重视伦理道德的建构,加上与汉人接触增多从而对其言行举止的耳濡目染以及儒家礼法秩序在教化过程中潜移默化的熏染作用,三江侗族逐渐以儒家礼法来维系宗法组织和款组织中的伦理道德。
1.儒家“天理”观念的产生
汉字翻译款约的过程是三江侗族社会规范儒家化的开端,“阴规”“阳规”二词在儒家中的本身就象征了天地间的秩序,董仲舒于《春秋繁露》称:“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16]到了同治十一年(1872年),三江地区独峒乡款民集议《独峒乡条规碑》时在最后强调:“立规之后实执款条,各安本分,诚守天理,愚无同受害而风俗醇矣,不亦懿乎。”[17]
宋代理学家提倡将“三纲五常”视为“天理”,《独峒乡条规碑》中“各安本分,诚守天理”,就是要每个侗民遵循“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把“仁义礼智信”当成是做人的道德标准,这是款约第一次表达对儒家伦理秩序的遵奉,正符合康熙帝《上谕十六条》对民间“敦孝弟以重人伦”的期望。
2.款约的文明化与正规化
在儒家文化的传播中,款约首先经历了文明化与正规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在与象征国家礼法权威的官府的互动中达成的。三江侗族在抵御外来侵扰时,当地的官员利益与其开始达成一致,到了光绪元年(1875年),三江侗族与官府开始在处理刑事案件时发生联系。这年十月,怀远县令接到马胖乡侗族团练武生吴昌义奏报:
常有外来游棍,成群结党,向各村民倚事生端,恣行吓索,又或暗肆偷窃,窍门挖孔,盗取牛马,奸弊丛生,实属不堪其扰。[18]
知县得知此事,向直隶州请示严行查禁此事,派差前往捉拿。还张贴告示晓谕马胖群众:
嗣后如有前项匪棍,纠伙入境,向尔等恣其故态,扰害地方,准即约众拘拿,解送到案,定即按律从重惩办,决不姑容,至宵小盗窃牛马,应即一并严拿治究。[19]

表3 《马胖乡苗侗族条规》对各类犯罪的处罚规定
除此之外,知县还留下“示勒碑”,让侗民“刻石纪法”,马胖乡侗民将这一游棍侵扰事件和政府处理规定刻在石碑上,以作为“判例”援引。这表明知县进行政府公权的法治表达的同时,承认三江侗族武装上的自卫权,显示了政府试图与三江侗族合作,一同将三江侗族地区的匪盗绳之以国家法的意愿。
马胖乡民众“示勒碑”上刻“判例”的同时还在增刻了《马胖乡苗侗族条规》[20],主要内容如表3所示。
由此可见,虽然政府承诺“按律从重惩办,决不姑容”,但是马胖乡仍然希望自己处理偷盗一事。但为了在政府权威与民间习惯之间找到平衡点,三江侗族首先是取消了《款禁碑》和《六面威规》对偷盗牛马的死刑。其次,根据事件严重程度,《马胖乡苗侗族条规》将各类事件划分不同层次,最后将每个事件依据侗族的经济基础,统一制定了量化标准。“半路强截公罚64000文”,“挖墙破公罚32000文”,“偷牛盗马公罚32000文”,符合政府“严拿治究”的规定。而“私代官讼公罚12000文”可以看出三江侗族民众对于沟通民间与官府的“讼师”,还是不能接受。“头人受贿,偏袒不公公罚64000文”更是款首提升自己在三江侗族民间的信任度的重要举措。
综合看来,《马胖乡苗侗族条规》比《款禁碑》和《六面威规》更为正规,这也使中原流官认识到三江侗族合理有序的社会秩序,从而默许其继续进行法律上的自治。
3.三江侗族融入国家“礼法”体系
20世纪初期,三江地区伦常废弛,鸦片泛滥,赌博成风,匪盗猖獗。由此,光绪三十年(1903年),浔溶两河暨三峒六甲联合为前所未有的大型款组织,在浔溶二江举行集议,制定了《浔溶两江集议条例》[21],主要内容如表4所示:

表4 《浔溶两江集议条例》对各类事务的规定
以上各条,俱就乡党中所宜禁也,倘有明知故犯,无论大小事合众款同科,不许私自罚,方合公款,或归款罚,或呈官究治。
民国《三江县志》称:“其条款更较前完备,而遵守者殆普遍于全县矣”[22]。这说明《浔溶两江集议条例》已经相当于是三江地区的“自治规约”,其之所以能在汉族中运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浸润二百多年儒家文化的三江侗族与三江地区汉族具有共通的礼法观念。“不孝,不弟(悌),不仁,不义,败风,乱俗”,在中原礼法中,这都属于违反《大清律例·刑律》的严重刑事犯罪,三江侗族将“孝”“弟”“仁”“义”作为侗族社会的行为规范加以维护,体现了其礼法化的特征,而从“如有忤逆不孝之辈,理该族长言诫,倘若不遵,即传大款送官究治” 这一规定中可以发现三江侗族社会中的族长和款首与政府官员已经结成了维护伦理道德的“战线”。
通过对比“不孝罪”与其他犯罪的处理规定,可以看出“不孝”在三江侗族社会已经是最大的犯罪。款首对于其他犯罪可以处以罚款,也可以上呈官府处理,但唯独只有“不孝”是“即传大款送官究治”。对于不孝案件的不同类型,官府处理时会参照《大清律例·刑律》从严处罚忤逆者。如此一来,三江侗族地区的社会规范,以及民间与官府的配合关系,都呈现与中原地区趋同的态势。
结 语
各民族的法律文化都是中华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江侗族与三江地区汉族“齐于一法”更是体现了儒家法文化强大的凝聚作用。在如今法治中国的建设中,以“孝”“仁”“义”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仍是中华民族进行道德建设中的重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