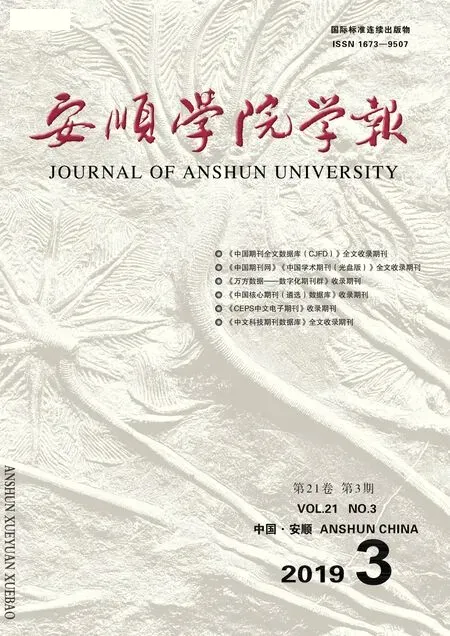安顺屯堡工匠特征分析
(安顺学院旅游学院,贵州 安顺561000)
“一人之身,百工之所为备。”[1]传统工匠的手工制品,伴随着人们的日常起居,推动着国家的基础建设,促进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屯堡工匠,于明清时期从江南、中原各地移民至安顺。他们从最初的军需用品制造,到后期屯堡区域以及周边社区生产生活用品的制作,在满足民众生产生活需要的同时,通过副业经商的方式集聚了较为丰厚的资本。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多元化,传统手工制作所带来的经济收入已经不能满足大多数工匠对于生活质量提升的要求,越来越多的工匠转入其他行业。与此同时,现代机械化生产以及人们物质生活的丰富,手工制品逐渐地从大众的视野中消逝。工匠群体面临着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以及适应社会发展的两难抉择。目前在屯堡文化的相关研究中,鲜少有对屯堡工匠的专题研究,仅散见于相关的屯堡研究论文、论著中。在当前社会对“工匠精神”“工匠文化”高度关注的背景下,加强对安顺屯堡工匠这一群体的关注与研究,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工匠”“屯堡工匠”释义
在古代汉语中,对工匠有“工”“百工”“匠”等称谓。
据“工,象曲尺之形,盖工即曲尺也”[2]、“兴事造业之谓工”[3],“工”的词义从曲尺发展到工人、工业。春秋时期,管子即提出了“四民”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4]作为国之根本,四民之一的“工”,指的就是从事手工劳动的人。
“百工”指从事手工业劳动的人,如“百工居肆, 以成其事”[5];有时指掌管各种从事手工业劳动者的官吏,如“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审曲面执,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郑玄注云:“百工,司空事官之属。于天地四时之职,亦处其一也。司空,掌营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庙,造宫室车服器械,监百工者。”[6]
“匠,木工也。从匚从斤。斤,所以作器也”,段玉裁注:“工者,巧饰也。百工皆称工、称匠。独举木工者,其字从斤也。以木工之称引申为凡工之称也。匚者,矩也。”[7]因此,在《说文解字》中,匠是对工的总称,指的是遵循行业规则,以各式手工器具为工具从事手工业劳作的人。
从以上释义可以看出,从事手工业劳动的人都可以称为“工”“百工”“匠”。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强调“工在籍谓之匠”[8],那些有专门户籍(匠籍)的专业人员才能称为匠。
综合上述引文,本文所指的工匠,是具有某一项专业技术的从事手工业制造的劳动者,他们的劳动范畴包括设计、生产、销售相关的手工艺制品。文中所指的工匠,专指传统社会中从事手工制造的工匠,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机械工匠,以及信息化时代的数字工匠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
“屯堡即明洪武时之屯军。妇女青衣红袖,戴假角。女子未婚者,以红带绕头上。已婚者改用白带……男子善贸易,女不缠脚。一切耕耘,多以妇女为之。家祀坛神,多力善战,间入行伍,衣冠与汉人无异。”[9]屯堡,据《安平县志》记载,为明代朱元璋“调北征南”及其后期相应政治举措迁徙到安顺的军民,在与安顺特有的地理历史、民族文化相互作用下产生的汉族移民文化区。屯堡工匠,就是生活在安顺屯堡文化区域内,具有专业技术能力、从事手工业制造的屯堡人。他们是屯堡族群中具有一技之长、从事手工劳作的人群,通过技能创造了财富价值。他们所体现出来的屯堡工匠精神及匠作文化,成为屯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屯堡工匠在内的中国传统工匠群体,是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出现的:做釜甑的皇帝、造宫室的伏羲以及制车的轩辕,他们即为《考工记》中“圣人之作”,创造的不仅是物质层面的器具,还有文字、图画等精神产品。在整个人类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传统农业时代,工匠用他们的智慧和手作,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进行创造,为社会大众带来了生活的便利。可以说,工匠的创作,是人工与自然的有机结合,是“天人合一”的产物。
二、安顺屯堡工匠的“由来”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的传统工匠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从现有文献来看,在西周至春秋时期,工匠是一个被统治者重视的群体,如《尚书·酒诰》云: “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毋庸杀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10]《管子·乘马》云: “工治容貌功能,日至于市,而不为官工者,与功而不与分焉。”[11]因为有了“工”的身份,工匠可以免于刑罚、徭役,甚至有接受教化的机会。秦汉以后,统治者加强了对工匠群体的管理,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隋唐时期“工商不得仕进”;元明两朝制定了专门的匠籍世袭制度。清顺治二年(1645年),匠籍制度废除,工匠获得人身自由,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社会群体。
中国传统工匠,世袭者居多。殷商时期的工匠即为世袭,从殷墟出土的墓葬来看,出土工具的墓从早期到晚期都有,“即工之职业,世代不变, 特别是那些有熟练技术,专门为王室制造各种器具的百工更是如此。”[12]在古籍中亦有相关的言论:“今夫工,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协材,旦暮从事,施于四方,以饬其子弟,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为工。”[13]从技艺传承的角度来说,长期一起生活、协作,耳濡目染,有利于经验的积累和技术的提升,故而出现工匠传承的世袭现象。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为了生计转学技术的工匠。如宋代有文描述:“即早辰(晨)桥、市、街、巷口,皆有木竹匠人,谓之杂货工匠,以至杂作人夫,道士僧人,罗立会聚,候人请唤,谓之罗斋。”[14]雇工制度的发展,从侧面说明了农民转化为工匠的人数逐渐增多,这是社会发展和个人生存需要所带来的职业转变。“在此处所经营的手工业中,有十二种高于其他行业,因为它们的用途比较广泛和普遍。每种工艺都有成千个工场,而每个工场雇用十个、十五个或二十工人。在少数工场中,甚至有四十个人工作。因为这些工人受工场老板的支配。”[15]这是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描述的元代杭州手工业繁华的场景,说明当时杭州已经有了专业化的手工作坊,并有了雇工。
洪武十四年(1381年)攻克普定后,明政府于次年二月设置普定卫。朱元璋认为“屯田之政可以纾民力, 足兵食。边防之计, 莫善于此。”[16]于是在安顺一带实行卫所屯田制度。洪武年间,在今贵州境内设置24卫,卫所官军约20万。今安顺境内设有普定、安庄、平坝3卫,其中普定卫设78屯、7堡,安庄卫96堡、1屯,平坝43卫堡、1屯[17]。除军屯外,还有民屯、商屯。“岁计军粮七万余石,本州及普宁(疑普定)、播州等处发征粮一万二千石,军食不敷,宜募商人于本州纳米中盐,以给军食。”[18]“移民就宽乡,或召(招)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而军屯则领之卫所。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19]出于军队供养,以及游民、罪民安置的目的,明清政府后期向黔中地区迁移大量的商、民,不断丰富了卫所的群体。
安顺屯堡工匠,产生于明代匠籍制度下。明代的工匠制度承袭元朝而来,在元朝官人匠、军匠、民匠的基础上,把工匠分为军匠、民匠和灶户。军匠服务于中央和某些地方的兵工机械机构。据史料记载,从洪武二十年起,全国的都司卫所都设置了军器局,从事军事器物的生产。民匠是中央及地方各手工业场里面的工人,其工作内容从设计、制作到供应,主要为皇室、官府和贵族生产各种手工业产品。灶户,则分布于各个盐场中从事相关劳作的匠人。从来源及工作内容来说,安顺屯堡工匠应属于明代军匠和民匠两种类型,他们衍生于明代的军屯、商屯和民屯中,从事着兵器打造、房屋建造,乃至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的制作等劳动,为屯堡区域内的生产和生活需要提供了物质保障。
三、安顺屯堡工匠的分布
由于地理位置以及卫所功能划分,安顺屯堡可以分为交通线和田坝区,其中贯穿平坝、安顺、镇宁,东起清镇,西至镇宁,沿滇黔古驿道和今天的交通要道分布的七眼桥、大西桥、头铺、 三铺、马官等地称为交通线;今天普定县的马官、余官,西秀区么铺镇的大屯、小屯,旧州及刘官、黄腊、双堡、东屯、杨武等屯堡区域为田坝区[20]。
交通线上的屯堡以戍守为本,主要是为了保障驿道的通畅。同时,这一带的可耕种地少,故而在农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屯堡人“善贸易”的特长,发展出许多副业和手工业。在屯堡区域有名的商贩,如“吉昌的鸡贩子,中所的猪贩子,九溪的米贩子,章家庄的布尺子,鲍家屯的腰带子”[21],基本分布在交通线一带的屯堡村寨中。田坝区是安顺一带少有的成片适宜耕种、水土肥沃的地区。这一带的屯堡人以务农为主,以保障粮食供应,极少从事其他商业副业活动。
屯堡区域内,有许多专业化的手工作坊和工匠,民间就有“四坊五匠”(一般“四坊”指烧酒坊、油榨坊、豆腐坊、染坊。“五匠”指木匠、石匠、铁匠、银匠、泥瓦匠。在不同村寨中,内容会有稍许不同)的说法,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目前屯堡村寨中流传下来的传统手工技艺不多。据调查了解,当前屯堡地区的传统工匠集中在以下村寨中:

表1 屯堡村寨代表性工匠分布统计表
上述表格中,呈现出的是当前屯堡村寨中主要流传、具有典型意义的工匠。从其流传情况来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当下仍被社会发展或是屯堡人日常起居所需要的工匠,仍在从事相关物品的制作,并不断发展,例如木雕、银匠,包括丝头系腰在内的屯堡服饰制作等;二是因为文化旅游发展,逐渐被人们重视的工匠,例如从事传统屯堡建筑的石匠及铁匠等;三是已被现代化生产技术所取代,停留于人们口传和记忆中的工匠,例如泥瓦、织布、烧砂锅(砖瓦)的工匠。无论是存在着的,还是已经消失的,这些工匠都是屯堡文化建构的重要因子,共同支撑着整个屯堡社区的发展。
四、安顺屯堡工匠的特征
屯堡工匠在屯堡文化不断形塑的社会历史和制度背景下,在与当地社会和环境的不断适应、融合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当地其他工匠群体的特征。
(一) 互构性
从工匠在各村寨的分布情况来看,有些工匠很多村寨都有,如石匠、木匠等,而有些工匠则是仅存在于某些村寨,如丝头系腰仅有鲍家屯生产、织布主要在本寨等。但是,屯堡工匠并未因此隔离,而是形成了有机的体系,具有明显的互构性。
1.物质上的互相补充
屯堡工匠的互构性,首先体现在物质上的互相补充。在屯堡区域内,生活在交通线上的屯堡人,以戍守为主要任务,通过务农和副业作为生活保障;与此同时,兼顾驿路所需的军事及生活用品的中转和交换、沟通田坝区屯堡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田坝区为屯堡区域内集中成片的产粮区,是各卫所粮食补给的重要保障。因此,存在于不同区域的屯堡工匠,他们生产的产品通过集市贸易,互相流通,互为补充。以面具雕刻工匠为例,刘官乡周官村的地戏面具雕刻,主要面向东部屯堡片区的地戏队,蔡官镇下苑村的地戏面具则面向西部屯堡片区,但是周官与下苑村的地戏面具雕刻工匠之间有一定的交流,也有各自的特点,他们共同满足了屯堡区域内对地戏面具的需求。即使在进入市场之后,彼此之间有各自的销售偏向和渠道,良性共存。屯堡妇女穿着的大袖子,制作工匠分别为田坝区的旧州、东屯,交通线的九溪、二铺等。他们生产的大袖子,通过赶转转场的方式,销售给整个屯堡区域的女性。其他工匠亦是如此,他们在不同的屯堡村寨间存续,但是用各自的手艺,共同促进了整个屯堡区域对生产、生活制品需求的满足。
2.精神上的互相认同
认同,是个人与他者在心理、情感上不断趋近同一的过程。安顺屯堡文化能够以活态形式存续六百多年,学界一致认为屯堡族群之间的相互认同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不管是明朝“调北征南”而来的屯军,还是后期“调北填南”,以及出于政治目的的移民、个体游民,生活在屯堡区域内的民众,同是移民的身份以及同样的生存环境,让他们对屯堡这个群体从心理到情感上都有一个不断趋同的过程。个人、家庭与屯堡社区之间,除了物质上的依赖,情感和心理上的认同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屯堡工匠所呈现出来的精神上的认同,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屯堡群众对于工匠的认同。屯堡工匠拥有精湛的手工技艺,深谙村落的传统习俗,一般来说在村寨中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设计、生产的器物,从物质到精神,能够满足屯堡人的需求。因此,屯堡群众对工匠群体有较高的认同度。例如,20世纪80年代走村串寨进行地戏面具雕刻的工匠,在给村集体雕刻地戏面具的过程中,由村中各户人家轮流安排伙食,这其中并没有出现不愿意安排的人家,而是以能请工匠到家中就餐为荣。
第二,屯堡工匠对屯堡族群的认同。屯堡工匠首先对自己祖先在明清时期“调北征南”而来的历史引以为豪,认为手艺是从那时就传下来的。在与西秀区傅家寨铁匠传人孙先生的交谈中,他对祖上打制兵器、后造马掌的历史讲述生动,其中深含自豪之情。其次,以屯堡人忠孝仁义、诚实守信的品质来规范自身的行为。地戏面具雕刻艺人,在雕刻文臣武将的面具时,以精湛的技艺,通过面部的线条设计以及着色,把历史人物的忠肝义胆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傅家寨孙氏铁匠,家族有不打制刀具的组训,因为刀具能害人命。因此孙家只在自用时才会打制菜刀、镰刀等刀具用品,但从不拿到市场上售卖。
(二) 自足性
屯堡工匠衍生于在相对封闭屯堡文化系统中,具有自足性的特征。在屯堡区域内,工匠种类涉及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能够满足屯堡区域内民众的生产和生活需求。自足的范围,一是家庭,二是屯堡社区。除了世袭下来的工匠外,许多屯堡工匠,最初是为了家庭的生活需要而进行生产的,例如编竹制生活器具、建造房屋的工匠。随着工艺的提高和产量的增加,才拿到市场上去交易。从这个角度来说,对家庭的自足,首先表现为物质上的满足:吃穿用度基本上由自家生产;其次,是手工技艺所带来的经济上的充裕。他们能够用自己的手艺,创造出比务农更高的经济收入,更好地满足家庭的日常开销。
在屯堡工匠中,许多手工艺制品是专销屯堡区域的,例如屯堡女性服饰,除了少数爱好者的收藏,其余的都是屯堡区域内的女性在购买。地戏面具在20世纪80年代走向市场之前,也是为了屯堡社区跳地戏需要而进行雕刻。此外,屯堡工匠作为屯堡人,在传统社会中,存在不与当地少数民族往来的心理。因此,其生产的商品,也只是在屯堡社区内流通。
在屯堡区域内,有许多从事手工业及相关副业的专业户和商人,但是整体上来说,规模不大,以家庭为主,主要是为了满足一个家庭、一个区域的需求,不是纯商业性,亦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例如九溪村的祭灶糖生产,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几十上百家到现存的十余家,他们参与制作的都是家庭成员,自家生产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售卖,属于家庭小作坊的商业形式。鲍家屯的丝头系腰也是同样的情形。就算是当前比较具有市场的地戏面具雕刻,虽然有多家公司化的经营,但是经营主体仍是以家庭(家族)为核心。
屯堡工匠自足性特点的产生,有其历史根源,也有社会因素。从历史上看,屯堡工匠来源于明清时期。在明代,自给自足是其自然经济的特点。由于商品货币经济不发达,从平民百姓到王公贵族,从农业生产到军事战争,所必需的手工业品和建筑工程,以及战争中使用的剑戟戈矛,不能仰赖于市场,必须通过官营手工业的工厂和作坊的造作。官营手工业的制成品,是供给封建统治者自身使用的,一般不许私自进行买卖,也不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在明代自给自足官营手工业制度的影响下,屯堡工匠从产生的源头就是为了满足屯军的军事、生产、生活等方面的需要,自足便是其主要的目的和特征。
从社会环境来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制度的变迁,屯堡人的地位逐渐边缘化,曾一度被误认为是少数民族。“所谓‘凤头鸡’者,身份则介在一般汉人和苗民之间,虽则比下有余,而实比上不足。莫说‘征股者’的风韵已经烟消云散,反而多少有些寄居在一般汉人檐下的气概,至少文化方面是比较的落后。然而,其祖宗都是首先的征服者。”[22]失去制度保障的屯堡人遭受异族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打击,又受到后续移民的生存挤压和文化蔑视,生存环境艰难。为了生存,屯堡人延续着其独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以特定的生活习俗、装束、语言、仪式等标识族群的边界,在与周边少数民族和后续的汉族移民的生存博弈中形成族群内部高度认同。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只能依靠屯堡工匠的手艺,制造出生产、生活的相关必须器具,以保证族群的正常生活,以及种族的延续。
(三)兼业性
在工匠发展的历史上,除了部分官匠、军匠等专门为官家服务的工匠外,许多民匠具有身兼商、农的特征。“士农工商虽各有业,然锻铁工匠夫必不耕种水田。纵使不耕种水田,春月必务蚕桑,必种园圃。”[23]屯堡工匠亦然,基本上兼有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经营的身份。从现有的屯堡工匠来看,基本上都生活在屯堡村寨中,家中都有农田。除了极少部分已经专业化且具有一定商业规模的工匠外,许多工匠都是忙时做农活,闲时做手工。在调查中,九溪制作祭灶糖的黄家,基本上是在冬月、腊月两个月做得最多,一是这个时节市场需求量大,气温低易于保存。二是冬季没有农活,家庭成员都可以参与制作和销售。孙兆霞教授在吉昌屯做契约文书的调查时发现,许多人购买土地的资金都是从做木工、石匠等副业中获得,“从事副业人口的增加对土地产权流转的促进现象,还映射出屯堡人由亦农亦戎的军士,到亦农亦商亦副农民的职业变迁信息。”[24]
屯堡工匠兼业性的群体特征,除了行业发展的历史原因外,还因为屯堡人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仅靠农业生产不足以支撑其基本生活的需求。
一是过于沉重的赋税。要实现自养,除了生产出能够保证自己最低消费的粮食外,还要提供相当部分的粮食供给其他军士食用,这决定了屯军必须按照较高的科则上缴粮食。因此,屯军缴纳的屯粮比非屯堡区的农户所纳的“科粮”高数倍。此外,明代中后期的逃军问题更是加重了屯军的负担,屯田起征的田赋远高于“劝民开垦”的科田。据咸丰年元年(1851年)《安顺府志》记载,平坝卫辖区内屯田和科田每亩的税率(斗)分别为2.64、0.54,普定卫为2.18、0.53[25]。直到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改卫设县时,屯军沉重的赋税并未取消。仅靠农业,难以维系一家人的生活,压力极大,往往只能通过手工业及相关副业来进行补充,缓解沉重的经济负担。
二是人地矛盾凸显。如上文所述,安顺屯堡一般是占据了地理位置好、土地肥沃的地区,并以屯、堡作为据点,逐渐发展成独立的村落,最后发展为连片的屯堡区域。但是固定区域的生产力有限,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生存空间固定的屯堡村寨的人地矛盾日益凸显。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本身就具有技术并善于贸易的屯堡人就逐渐发展手工业以及其他的副业,来增加经济收入,满足家庭的正常开支。因此,源于屯堡形成的历史原因,以及现实沉重的生活压力,让屯堡工匠具有了手工业制造和农业生产的兼业性的特点。
结 语
屯堡工匠,作为传统工匠中的一部分,其身上体现了精益求精的中华工匠精神,以及诚实守信的行业操守。同时,作为屯堡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因为其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文化和地理环境,不断形成了异于其他工匠群体的互构性、自足性、兼业性的特征。美国学者桑内特认为:“匠艺活动给获取技能带来的情感回报有两个层面:人们能够在可感知的现实中找到归宿;他们能够为自己的工作而骄傲。”[26]屯堡工匠用他们的手艺技术,在不断建造着屯堡文化的物质元素和精神归属的同时,也给工匠自身带来了情感的函化和自我认同。屯堡工匠在劳作的过程中,将铸于生命中的族群文化和家国情感物化到各种手工制品中,成为屯堡族群文化的创造人和传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