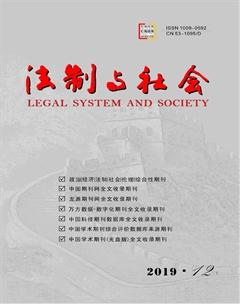网络远程ADR的实现路径探析
钱小语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12.273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成果,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框架体系,而依法治国更是治国理政的一大重要方针政策,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热情日益高涨,从未停歇。人们的权利意识也越来越强,以诉讼方式解决矛盾纠纷早已成为了人们捍卫自身权利的强有力手段。但是解决纠纷的手段和机制是多方面的,既有诉讼方式、仲裁方式,又有新兴的司法ADR调解手段。
自上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兴起了ADR制度以来,这一制度便得到了欧洲一些国家的普遍认同和效仿。随着时间的发展,ADR模式也渐渐出现在了中国大众的视野里。随着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加快,人民群众的价值诉求也呈现了多元化的特点,许多新兴的问题也渐渐浮出水面。社会司法现状和司法资源的紧缺,也使得法庭在审判前对于ADR程序的重视程度远胜从前。与此同时,网络上的ADR也得到了初步的发展。
一、网络远程ADR的内涵和特征
(一)网络远程ADR的内涵理解
ADR是“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英文简称,中文上可以理解为“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通俗的理解就是在法律诉讼程序以外、以非诉讼方式解决争议纠纷的方法。而“网络远程ADR”,即在网络部分特定软件程序中引入ADR模式,以网络软件的发展带动ADR模式运行,对矛盾纠纷的解决实现远程调解控制。
(二)网络远程ADR的特征
1.ADR模式的出现,体现了在纠纷解决中利益的导向作用,将问题的焦点集中在了为实现当事人双方根本利益的最大化上。通过管理层的直接参与,不仅能够对矛盾的争端进行解决,还更有可能达成具有前瞻性的协议。
2.ADR的出现并不仅仅意味着调解机制在民间的运作发展,基层法院的诉讼步骤中也早已添加了ADR程序。法院案件审理与调解内容的无缝衔接,为民间的和解协议增添了法律效力,也为当事人之间对于协议的践行增加了保障。
3.“以和为贵”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奉行已久的,司法ADR模式的出现是对“中庸之道”的司法把控,而网络远程ADR更是以互联网为载体,在私密环境中通过第三方协助,从而达到双方利益至高的平衡点,也更容易被人民群众心中普遍的厌诉情绪所包容。
这些方面既意味着调解在法治纠纷解决领域中重中之重的作用,又体现了ADR模式在我国依法治国实践中的进一步发展。
二、网络远程ADR引入的法理依据
(一)中国传统思想与司法ADR
传统对人们的影响在于通过其传承的思想来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等。对于法律的传承,也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和价值取向的改变而一步一步衍生。
从《易经》中的“讼,惕,中吉,终凶。”到明朝王世晋的:“太平百姓,完赋役,无争讼,便是天堂世界。”普通的中国人日常生活很少讲法,说话做事,解决矛盾纷争一般讲“理”,若有人言必称“法”,大家就会觉得他矫情卖弄。但“理”与“法”同时存在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同时也是中国社会有别于西方社会的特殊现象。“理”普遍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没有文字形式,却是世俗生活中人们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以及行为准则。
同样,因为“法理不外乎人情”,普遍精神服从于特殊私情,法治精神让位于人伦情理。在中国,人际互动和民众的日常生活逐渐融合,形成了一种人情法则的文化规则。这些,就是ADR与中国传统法律理念相契合的具体表现,也是传统儒家文化中追求自然秩序和谐的理想要求。
(二)人本主义与司法ADR
如果说中国古代人本思想就是“以人为本”,那么最早提出“以人为本”应该是法家先祖管仲:“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人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重视人的价值,而其含义中与本论题最贴切的莫过于当中法与民的关系。
孟子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观点,荀子也曾说过,“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无一不体现了人本主义的根植。相对于传统诉讼模式的顽固性和抵抗性,司法ADR的出现更符合传统模式中对于人本主义的需求,也更能体现民众所需的“人本主义”的精髓。在纠纷解决中融入“人本”,减少双方当事人的关系僵化,充分考虑当事人在社会团体中的个体地位。以司法ADR为基点,有利于建设以当事人为中心的纠纷解决机制。
三、网络远程ADR引入的瓶頸
(一)传统诉讼模式由来已久,短时间难以改变
现如今,传统的诉讼模式已经不能很好的适应大部分人的生活现状。主要体现在:第一,人们生活的忙碌性,导致了并没有足够的时间耗费在诉讼程序中。法院诉讼程序的繁杂也使得诉讼当事人常常因为法院的需要而往来奔波。这也在无形中增加了人们的诉讼压力。第二,律师费用的价格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普通的工薪阶级,甚至是更低的生活家庭。且法院的法律援助律师也并不是所有的诉讼均有时间提供援助。且但大部分人的保守观念在于,相信司法的权威性,从而对于初期ADR的发展采取观望和不信任的态度。
(二)网络远程ADR引入初期,各方面成本较大
远程ADR模式的引入,不但需要最初的人力成本,而且对于我国法治环境的要求也有明显的提高。司法裁决因其终局性的法律地位而被人民群众广泛接受和信服,又因为司法的公正性和全局性导致了人们对于诉讼制度的普遍崇敬,这既是对我国法治建设成果的一种宣扬,也是对审判活动在纠纷解决中的重中之重作用的具体表现。
在现行法院系统中,仍然存在审判人员不足而案件数量繁多的矛盾情况。虽然在远程ADR模式引入后,会一定程度上减少需要审判的案件量,但纠纷化解系统中“头重脚轻”的现状不是短期之内可以解决的。网络远程ADR的引入初期,不仅仅是单方面的对于ADR人才的需求,更是对于主导法院的矛盾化解机制的改变的需求。远程ADR机制从萌芽、形成、发展和完善,需要的不仅是司法机关的单方面投入,更是需要行政机关、社会民间团体组织和人民群众的通力合作。ADR的网络引入,对于网络运营和程序的发展具有较高的要求限制,既要保证网络程序的合法化,又要确保案件内容更新与法院系统之间的流畅运行。
(三)立法层面发展尚不完善
由于法律的滞后性特征,在我国法治发展如此繁荣的现代社会,法治的发展仍未停歇,法治化建设的进程仍在推进。但纵观我国的全部法律法规,关于矛盾纠纷多元化调解机制的规定也只是零散的分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等法律、法规中。
其中,对于司法ADR的发展、甚至是对于网络远程ADR的引入都在处于初期的萌芽探索阶段。并且,网络远程ADR的引入还需要在考虑到他的相关制度和程序的设立,以及与法院、检察院和社会民间组织的相互衔接中,减少基层组织的功能弱化和投入懈怠的情况。
四、网络远程ADR的具体实现路径
(一)以社交软件为着力点,与传统诉讼模式相结合
纵观网络发展,和移动互联的迅速崛起。生活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社交软件来促进人们的沟通。技术的进步带来社交方式的创新,而互联网社交软件的发展自然也是日新月异的。
从1997年开始,猫扑和西祠胡同这种综合性网络社区的诞生,到1999年的QQ上线;再到2011年微信、知乎的兴起,和2016年火山、抖音短视频社交的横空出世。无一不透露着互联网社交软件发展的漫长和精彩。
人们对于社交软件的依赖程度是不可估量的,如若在社交软件中引入ADR模式,那么人们对于ADR模式的了解和认同也会与日俱增,这样既有利于ADR模式的发展,也有利于网络社交软件全面性和法治化的进程步伐加快。
(二)初步探索阶段,成本转化
网络远程ADR的引入与运行在我国尚且处于萌芽时期,在借鉴国外先进发展经验的同时,也应该正视我国法治建设背景下的发展现状,因地制宜的发展司法ADR。
微信社交平台未来的软件应用涉及面非常广泛,网络远程ADR的具体实现就可以以微信作为最初的着力点。在对法院立案时间和立案地点的解放下,增加相关司法ADR人才培养计划。让法院案件审理与ADR无缝衔接,为民间和解协议的践行增添了法律效力。
现在全国中实施微信立案的试点法院——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当事人只需要微信关注公众号“海淀法院自主立案服务号”,就可以通过指定步骤,自行完成立案工作流程。其中為保证案件真实性的“OCR文字识别”“身份验证与人脸识别相结合”等技术,都在公众号的服务系统中得到了很好的运用。既有效的减少了可调解的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又增加了双方调解程序的合法性和法律的积极示范作用,在纠纷解决中融入生活习惯和人情世故,达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网络ADR运用的最本质体现。
(三)立法引领:推进法治对于ADR模式的多元化建设
我们应当全方位、多角度整合国家现有法律法规和暂行条例中对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规定,对于分布在各个法律规范中的零散纠纷化解规定化零为整,统筹推进ADR法治程序建设。并且结合我国当前国情和网络发展现状,设立相关部门法规,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ADR程序适用法》《网络远程ADR模式试用条例》等。实际对司法审判中的相关审查程序进行调整,在现存的民、刑事案件认定标准中,增设部分可调解案件中当事人对于纠纷解决机制的程序选择。
在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后,统筹兼顾,在增设网络远程ADR程序的大背景下,加强相联系的网络安全条例进行制约,以减少ADR程序运行中的网络安全弊端,挖掘网络司法程序潜力。
五、结语
从总体上来讲,网络远程ADR的实现是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其不仅仅需要的是法院司法程序的改变,更是对网络司法制度的变革和创新。只有通过全方位的统筹分析,结合我国当前的发展趋势和基本国情,增设网络远程ADR的相关法律法规,形成以法院为核心,行政机关和民间基层组织为辅助,人民群众为基础的新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才可以将各个与司法审判相联系的部门联系起来,系紧他们之间的ADR纽带,以形成对网络远程ADR的规范化、法治化和多元化发展为最终目的追求。
参考文献:
[1]李融.ADR的法律价值及展望[J].甘肃农业,2006(4):202.
[2]陈立峰.论构建我国司法ADR制度的法律依据:法律文化与法律传统[J].未来与发展,2012:70-73.
[3]刘亚玲.司法ADR与我国法院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J].诉讼法论丛,2005(00):378-389.
[4]杨玉龙.微信立案让法院更智慧[N].人民法院报,2017:1.
[5]杨兴培.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与实践[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3):80.
[6]左红霞.浅析我国司法ADR的构建[J].学理论,2011(17):149-150.
[7]刘刚.从司法ADR视角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重构[D].华东政法学院,2006.
[8]迈克尔·利斯,龙飞.ADR:2020年的全球发展趋势[N].人民法院报,2013 (6).
[9]徐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实践困境与路径探析[J].中国应用法学,2017(3):6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