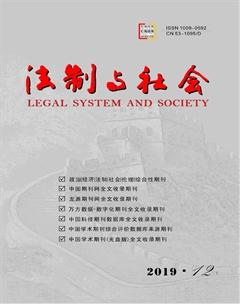减刑、假释中认定服刑人员是否有财产刑履行能力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
黄松青
中图分类号:D92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12.262
2012年7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实施《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第2条第3款规定:“罪犯积极执行财产刑和履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的,可视为有认罪悔罪表现,在减刑、假释时可以从宽掌握;确有执行、履行能力而不执行、不履行的,在减刑、假释时应当从严掌握。”该规定明确,服刑人员财产刑执行情况将直接影响对其减刑、假释。特别是类似故意伤害案等有被害人的案件,财产刑的履行至关重要。“因罪犯的犯罪行为造成物质损失的,罪犯应当给予被害人赔偿”。 但是在影响罪犯的减刑、假释之前,首先需要判断罪犯是否有执行、履行财产刑的能力?在实践当中,认定罪犯是否有财产刑履行能力的做法有限,且存在着诸多不足。笔者结合实践当中主要做法及其缺陷谈谈如何认定罪犯的财产刑履行能力。
一、当前认定罪犯是否有财产刑履行能力的主要做法
对认定罪犯是否有财产刑履行能力的规定,主要集中在省一级部门的规定,比如我省公检法司四家共同出台的闽高法[2013]186号《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规定》第47条规定:“对原判的财产刑和附带民事赔偿尚未执行完毕的罪犯,提请减刑时,应提供起始或间隔期内的个人消费账目。对家庭困难,确无执行能力的罪犯,由公安派出所、乡镇(街道)或司法所出具家庭经济情况证明。无法出具证明的或服刑期间无接见、无汇款、无信件的罪犯,由服刑监狱、看守所出具罪犯在服刑期间消费情况证明。”上述规定,罗列了认定罪犯是否有履行能力的三种方式:一是罪犯在间隔期内的消费情况;二是乡镇街道、司法所、派出所出具的罪犯家庭经济情况证明(以下简称困难证明);三是由监狱出具的罪犯在服刑期间无接见、无汇款、无信件的证明(以下简称“三无人员”证明)
二、主要做法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间隔期内消费情况及其存在的问题
在监狱报送的减刑材料当中,对于财产刑未履行完毕的罪犯,会附罪犯在间隔期内的消费情况证明。如果罪犯在间隔期内每个月消费超过300元的必要生活开支,可以认定罪犯具有相应的财产刑履行能力。如果罪犯每个月消费超过300,且财产刑未履行完毕,法院则可能裁定不予减刑或者扣减减刑幅度。但是该做法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罪犯控制消费,规避履行财产刑
罪犯在间隔期内的消费情况可以作为其没有财产刑履行能力的证明,但并不可靠,比如罪犯控制消费。在狱内服刑,罪犯的穿着和日常伙食等均有国家承担,生活保障不成问题。所以对于以财产刑数额较大的罪犯来讲,其完全可以通过控制消费来规避履行财产刑,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该罪犯有财产刑履行能力的情况下,法院一般都会予以减刑。
2.借卡消費
笔者所派驻的监狱规定,罪犯在财产刑履行完毕之后,每个月最高允许消费500元。在实践当中,对财产刑未履行完毕的罪犯,会通过借用财产刑已履行完毕的罪犯的卡进行消费。这样自己的消费记录上则会显得较少,但实际上,其他罪犯的卡消费已经超过规定的300元,甚至更多。所以根据消费情况来认定罪犯的财产刑履行能力,证明力不足。
(二)困难证明及其存在的问题
困难证明是由公安派出所、乡镇(街道)或司法所出具的服刑人员家庭经济情况证明。用来证实服刑人员家庭的经济状况,从而从侧面反映其没有财产刑履行能力。实践当中,困难证明一般是由监狱要求服刑人员家属提供,并告知其出具困难证明的的主体(即公安派出所、司法所、乡镇街道),服刑人员家属找上述部门开好证明后,寄往监狱入档,作为减刑材料提供,以证明服刑人员没有履行能力。但在实践当中,困难证明几乎沦为了一种“形式书证”,其作为证据关联性、客观性和合法性均存在缺陷,难以反映服刑人员的财产刑履行能力。
1.关联性缺陷
除未成年服刑人员以外,家庭困难与否与服刑人员是否有财产刑履行能力并无必然的关联。
根据我省公检法司四家共同出台的闽高法[2013]186号《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规定》第49条的规定:“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未成年被告人有个人财产的,应当由本人承担民事赔偿义务,不足部分由监护人予以赔偿,但单位担任监护人的除外。对被判处罚金刑的未成年罪犯,其监护人或者其他人自愿代垫付罚金的,人民法院应当允许。”所以对未成年服刑人员来讲,如果其本身没有可共执行的个人财产,由家庭成员和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允许家庭成员和监护人代缴罚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困难证明具备一定的关联性。家庭困难可以证明未成年服刑人员没有财产刑履行能力。
但对于成年服刑人员来讲,困难证明就失去了作为证据使用所要求的关联性。根据我国《刑法》第59条的规定:“没收财产是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没收全部财产的,应当对犯罪分子个人及其扶养的家属保留必需的生活费用。在判处没收财产的时候,不得没收属于犯罪分子家属所有或者应有的财产。”根据该规定,对于财产刑的执行,应当只针对被执行人本人,家属所有或者应有的财产并不属于被执行的范围。所以家庭是否困难与被执行人是否有财产刑履行能力并无必然关联。实践当中,大部分家属为了服刑人员能够减刑,不惜举债缴纳财产刑,但笔者认为,根据目前的法律规定,家庭成员并无义务代服刑人员履行财产刑。
2.合法性缺陷
证据的合法性至关重要,由于困难证明由家属提供,上面所盖印章的真假存疑,且真假难辨,不管是监狱的管教民警还是检察官、法官都不是专业的鉴定人员,且也没有可供对比的公章,无法辨别真假,所以困难证明的合法性大打折扣。笔者所在的检察室,每个月人均将近50个的减刑案件,每份困难证明都到开具该困难证明的机关核实显然不可能。所以,仅凭一份印章都真假难辨的困难证明,显然不能够有效的反映服刑人员的财产刑履行能力。
3.真实性缺陷
实践当中,开具服刑人员家庭经济情况证明的主体为基层单位村委会或者街道办事处,司法所和派出所是在前者盖印之后加盖上去以示确认,并没有重新调查核实,也就是说,一份困难证明的真实性与否是由基层单位村委会或者街道办事处决定。而且不管是司法所或者派出所并不可能全面了解服刑人员及其家属的经济情况。理由如下:一是作为基层组织的村委会、街道办事处等没有能力掌控服刑人员的财产状况,不可否认,基层组织作为最接进民众的政府基层管理组织,对基层群众的状况了解情况有其天然的优势,但也仅仅是限于本地区是否有居住的房子等基本情况。对于固定资产如房产,登记的是在不动产产权中心,存款在银行,基层组织如何获知服刑人员及其家庭成员的财产?二是开具困难证明的单位并没有权力查询和了解服刑人员及其家庭成员的财产状况。对于公权力机关来讲,法无规定即禁止。法律并没有赋予基层组织查询公民财产的权限,其开具的困难证明显然不能真实反映服刑人员及其家庭成员的真实财产情况。而且“监狱对犯属开来的困难证明只是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如开具的部门是否符合规定等,但无法保证困难证明的真实性” 。
困难证明除了存在上述3个问题之外,还存在一个问题是部分服刑人员无法开具困难证明,有些是服刑人员家属不愿意开具;少数是港澳台、外国籍服刑人员的无法开具。如果仅凭一困难证明断定服刑人员是否有财产刑履行能力,对上述人员显然有失公平。
(三)“三无人员”证明及其存在的问题
“三无人员”证明是由监狱出具的,针对在服刑期间无接见、无汇款、无信件的服刑人员,出具证明,间接证明其没有财产刑履行能力。在实践当中,“三无人员”证明被广泛采用,“服刑期间与外界无通信联系、无外来邮件、无亲属朋友会见的,一般来说也无财产刑履行能力”。
笔者认为,监狱出具的“三无人员”在合法性上毋庸置疑,关联性也无疑问,但真实性却存在缺陷,“三无人员”是否一定就不具备财产刑履行能力。特别是对于一些诈骗数额巨大的服刑人员来讲,如果诉讼阶段司法机关没有及时对其财产进行查封和扣押,无法认定其是否有财产刑履行能力,在不影响对其减刑的情况下,由于犯罪成本的降低,服刑人员完全有可能隐瞒赃款,控制消费,有能力履行也拒不履行。“财产刑执行涉及行为人及其家属的切身利益,往往未等到执行阶段,行为人及其家属便已经转移、隐匿、变卖可供执行的财产,造成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假象。” 所以,仅仅依靠监狱出具的“三无人员”证明同样无法达到认定服刑人员是否有财产刑履行能力的效果。
综上所述,对于服刑人员是否有财产刑履行能力的认定,靠消费情况证明、困难证明、“三无人员”证明,并不能有效体现服刑人员的真实情况,也与制度设计的初衷相违背。
三、认定服刑人员财产刑履行能力的解决途径建议
目前的法律规定中,没有如何认定服刑人员财产刑履行能力的相关规定。最高法关于减刑中考量罪犯财产刑履行情况的规定,使得实践当中,服刑人员是否有履行能力的认定全部归结到执行阶段。而执行机关在缺乏對服刑人员财产了解的基础上,不得已采用了困难证明等漏洞百出的做法,不仅不能准确客观的认定服刑人员的财产刑履行能力,也违背了法律的严肃性,制度设计并不科学。笔者认为,对于服刑人员的财产刑履行能力的认定,应从诉讼阶段、交付执行阶段、执行阶段共同查清和认定。具体建议如下:
(一)诉讼阶段应启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财产调查程序,核实其可供执行的财产,以明确其是否具有财产刑履行能力
1.侦查机关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调查犯罪嫌疑人可供执行的财产,并根据需要采取查封、扣押和冻结等措施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22条的规定:在侦查活动中发现的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各种财物、文件,应当查封、扣押;第231条规定: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查询、冻结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并可以要求有关单位和个人配合。上述规定,赋予了公安机关在侦查时,对犯罪嫌疑人的财产进行查封、扣押和冻结的权力。但该规定的仅限于“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财物”“侦查犯罪的需要”的情况出现时,才能行使上述权力。而且在实践当中,公安机关往往只是扣押犯罪嫌疑人随身携带的财物,而对其房产、存款等财产却没有积极查询和扣押。
笔者建议,扩大上述措施的使用条件,即对可能被判处财产刑的犯罪嫌疑人,即可采取查封、扣押和冻结其财产的措施。具体做法是侦查机关在侦查时,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判断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财产刑以及数额。对于可能被判处财产刑的犯罪嫌疑人,对其财产刑先行查封财产和冻结存款,以保证对其财产刑的执行。当然查封、扣押和冻结的财产数额,应以其可能被判处财产刑的数额为限。移送审查起诉时,侦查机关应将调查的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情况作为证据移送检察机关。
2.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应核实侦查机关是否对犯罪嫌疑人的财产进行调查,是否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查封、扣押和冻结的措施
检察机关承当审查起诉职责,不仅应对案件的事实和证据进行核实确认,对于可能被判处财产刑的案件,也应核实侦查机关是否对犯罪嫌疑人的财产进行核实,监督侦查机关是否有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采取查封、扣押和冻结的措施。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告知其若主动退赃退赔,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可以从轻处罚,并核实其是否有隐匿、转移财产,向其表明财产刑履行将对判决量刑产生影响。督促犯罪嫌疑人积极退赃和退赔。在起诉时,应将犯罪嫌疑人的财产调查状况以及查封、扣押和冻结情况作为证据移交人民法院。
3.法院在开庭时,应调查核实被告人的财产状况;判处财产刑时,应参考被告人的财产刑履行能力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4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中可能判处被告人财产刑、责令退赔的,刑事审判部门应当依法对被告人的财产状况进行调查;发现可能隐匿、转移财产的,应当及时查封、扣押、冻结其相应财产。”但在实践当中,法院往往忽视了对财产状况进行调查这一职责。
所以笔者建议,法院在开庭时,应将公诉机关提交的被告人财产状况调查情况予以质证,向被告人核实,查清所查封、扣押和冻结的财产是否属于被告人所有,并且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犯罪分子的财产状况判处被告人合适的财产刑。
(二)交付执行时,法院应将对被告人的财产状况调查结果列入执行通知书,送达执行机关
虽然法律规定了法院应当对被告人的财产状况调查,但在实践当中,法院并没有告知执行机关财产状况调查的结论,导致执行机关对服刑人员的财产刑履行能力无从查起。故笔者建议,在法律层面上规定,作出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在交付执行时,应将罪犯财产状况、财产刑履行能力等内容列入《结案登记表》中交付执行机关。为执行机关判断罪犯是否有财产刑履行能力提供依据。
(三)执行刑罚时,执行机关应综合判断服刑人员的财产刑履行能力
1.成年服刑人员
对成年的服刑人员呈报减刑时,执行机关应主要参考人民法院对服刑人员的财产状况调查结果,并结合服刑人员在间隔期间的消费情况,以及汇款情况综合判断服刑人员是否有财产刑履行能力,取消困难证明的做法,“对于尚未被追缴、返还或没收的赃款赃物的去向,必须要求罪犯予以说明,并综合其他证明材料进行审查。” 之后根据其财产刑履行情况,综合判断服刑人员是否积极履行财产刑,以决定是否对其呈报减刑。
2.未成年服刑人员
对于未成年服刑人员的财产刑履行能力的认定,除了做到以上成年服刑人员的做法以外,笔者建议,可以通过以下做法来认定:如果未成年服刑人员自身财产不足以履行财产刑,需要家属代为履行的,监狱可以直接发函到服刑人员户籍所在地的司法行政机关,由当地司法行政机关对服刑人员的家庭财产情况进行调查,当然这前提是应立法赋予当地司法行政机关对这一类服刑人员家庭的财产状况调查的权力。参考司法行政机关在出具审前调查评估意见的做法,由司法行政部门出具关于该类服刑人员家庭是否困难的证明,并由司法行政部门对调查结果负责。
注释:
郭宗才,鲍善昌.减刑可与财产类判决关联执行[N].检察日报,2008年3月18日,第003版.
陈辉.对刑罚执行中财产刑执行存在问题之分析与思考[C].福建省院监所检察专栏——监所检察业务研究.
贺要生.建立减刑假释与执行联动机制 破解刑事案件财产刑执行难[N].湖南日报,2010年11月21日,第003版.
王会义,黄筱帆.减刑、假釋与财产刑、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执行关联机制研究[J].监所检察工作指导,2014(2).
赵新强.财产刑执行与减刑、假释联动机制探索[J].人民检察,2014(15) .
参考文献:
[1]尚婷婷.我国减刑适用之实证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5.
[2]张洁.减刑、假释制度的现实困境与完善[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论文,2015.
[3]付小容.质疑与回应:“赔钱减刑”的正当性论辩[J].西南大学学报,2016,42(2).
[4]刘呈志.检察机关减刑、假释同步监督的路径化构建[J].法制博览,2015,11(中).
[5]刘钰.减刑、假释同步监督机制之完善[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5,28(3).
[6]宋高初.我国赔偿减刑关联制度评析[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5,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