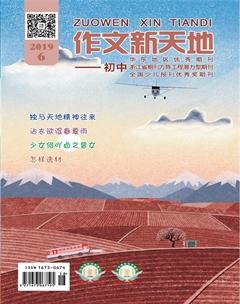我的读写简史
信世杰
在我很小的时候,还没开始认字,就喜欢捡一根小木棍,蹲在地上“画字”。地是沙土地,我先用手掌推出一块平地,再拿小木棍在平整的沙地上一笔一画地“写”,笔画有时复杂,有时简单,写成什么样完全随心随性。那是一种现在回忆起来都很奇妙的体验,就像农民插好一地秧苗,画家勾勒好一张线稿,我每次“写”完,也会心满意足地欣赏自己的作品,虽然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写”或“画”的是什么。我想,先民在造字之初也是这样的行为和感受吧,虽然先民所造之字是形与义的统一,而我留在沙土地上的“字”只是幼童依靠想象随意赋形。这是我人生读写的最初体验。
年幼时,父母在外工作,一两周回来一次,我也算半留守儿童,跟着爷爷奶奶生活。我爷爷是个木匠,不但木工活做得好,还会讲神仙鬼怪各种故事。北方大炕冬天烧得很暖,冬日白昼短,黑白电视也收不了几个台,吃完饭我们就早早上床进被窝。无数个冬天的夜晚,我躺在暖烘烘的土炕上,躺在爷爷奶奶中间,伴着爷爷讲的故事和窗外的风雪声入睡。爷爷会讲孙悟空大闹天宫,讲哪吒闹海,讲黑猫警长,每次听到主人公的新武器,我都缠着爷爷第二天给我做一个。孙悟空的金箍棒、哪吒的红缨枪以及黑猫警长的小手枪,我都有,晚上听爷爷一遍遍讲故事,白天拿著武器带领小伙伴大战虚拟的妖魔鬼怪,这是上小学之前真正无忧无虑的童年记忆。是爷爷讲的故事和做的玩具创造了我的童年。
我上的小学是附近几个村子一块办的联合小学,我姑父就是这所联小的校长。姑父家就住在教学楼后面的小平房里,旁边是平常不怎么开放的阅览室。小学时,我每天中午在姑姑家吃饭,午饭前,姐姐就带我到阅览室看书。姐姐比我大三岁,爱读《女生日记》之类在我看来很无趣的书,而我喜欢看“世界未解之谜”这类在她看来有些可怕的书。倚着我姑父是校长这点“特权”,我喜欢的书可以借回家看,什么时候看完了再还回来。因为比其他同学多看了些“未解之谜”,我的知识面自然广些。三年级第一次写作文,我写了一篇《海陆空三军用车》,大概是一篇科技说明文,被老师当作范文读给大家听,有同学背后议论说我是抄来的,我听了之后很高兴,觉得自己写作水平实在不赖,老师同学都说好,虽然表达的方式不太一样。凭着老师同学的鼓励,我开始自我膨胀,学了“离离原上草”后便尝试写古诗,有模有样地在方格本上创作了好几首,每写完一首都会自我陶醉一下,沉浸在自我诗化的世界里,仍像多年前那个在沙土地上“画”字的幼童。可惜的是,我幼年的 “诗集”早已在几次搬家过程中遗失。
整个小学六年期间,我把姑父家隔壁的小阅览室里感兴趣的书都读了一遍,比读课本要认真而有兴致得多。升到初中之后,读的书反而变少了,那时候网吧在村镇兴起,叛逆的乡村少年都被吸引到了电脑游戏世界。升初二时,父母终于下决心把我送到了市区一所寄宿制学校。城市对我来说是个新奇的地方,即便是城市里的寄宿制学校,也跟原来村镇学校不同。转学到新学校后,我见城里的孩子都有英语词典,私以为这就是他们英语成绩比我好的原因,便回家把这事告诉了我妈。我妈心一横,卖了家里的十三袋玉米,带我去商场买了一台最新款的诺亚舟学习机。我心满意足地拿到了学习机,却发现英语学习过程中它的用处并不大,而学习机里内置的名篇诗词散文则成了我每个晚自习的抄写素材。抄写诗词散文不是老师布置的作业,纯粹是无聊课业之余的个人爱好,但正是延续于整个中学时代的抄写习惯,将这些内置在学习机中的文学经典也内置到了我的身体里,成了我正式的文学启蒙。
进入到城市念书后,接触到的文学作品也多了起来,校园周边的小书店里,十元一本的盗版书是我那时最经济实惠的精神食粮。不管是马尔克斯、川端康成、鲁迅、莫言、余华、苏童还是王小波、余秋雨、韩寒、郭敬明、安妮宝贝、七堇年,看到什么就读什么,真正的饥不择食,雅俗共赏。整个初、高中时代,读这些闲书是我课业之余最大的乐趣。也正是因此,在高考报志愿时毫不听取他人建议,极其坚定地报考了中文系。
读大学之后,读书更多,面也更广,便开始写些散文、小说往外投稿。投稿时满怀信心,可结果总是杳无音讯。一气之下,我与舍友合办了一份中文系系刊,自编自印,每月一期,忙得不亦乐乎。自己编杂志,同时也是创作主力,看着自己写的文章被印出,被阅读,被师友赞赏,又找回了三年级第一次写作文时的那份得意感、满足感。
本科读完后,凭着对写作的执念,也得益于创意写作专业的开设,我便考研到上海大学创意写作专业继续我的读写生涯,硕士、博士一路读到现在。攻读硕博士期间的读写生活,跟中学和本科不太一样,以前读书写作全凭兴趣,而现在有更重的任务在肩,需要有目的地读理论著作,写学术文章。虽然理论和学术的读写也有其自身趣味,但总不及随心随性地读写来得自在。于是,如今学业之余的读写成了我最珍视的乐趣。
现在,我依旧常常想起多年前那个用木棍在沙土地上“写字”的幼童,我愿让那种由读写而来的自我满足感延续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