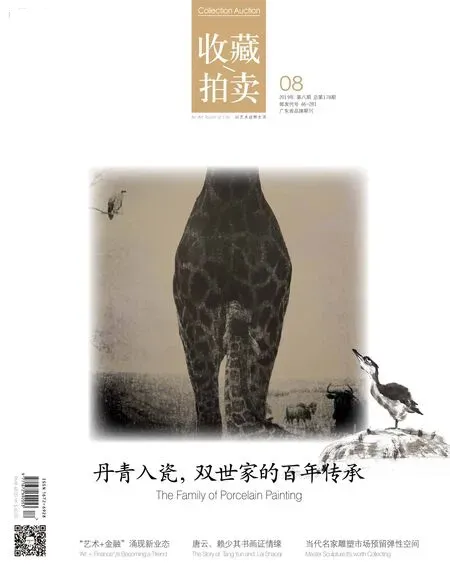铭绘造就文房之“雅”
文/图:谷卿
在儒家语境中,人们似乎一贯对于“器”和“物”充满成见:孔子强调“君子不器”,《尚书》则告诫统治者不要“玩物丧志”。不过,作为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且萌蘖于斯的概念,“物”实际上承载着许多超越于物质的精神内涵,“礼藏于器”在商周时期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礼乐制度得以具象化,人们在威严和庄重之中切实感知到秩序和力量的存在,而那些箴铭碑诔等刻镂于物质材料之上的语词,最终也定型为一种尤为“体制弘深”的文体。
《大学》中记述的“汤之盘铭”,应当是早期器物铭刻中最著名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词约而意深,既点出汤盘洗沐以自新的物质功能,又据此寄以道德日新、学问日进的希冀和祝祷,极备戒警、劝谏之用。若从文学的视角加以审视,器物刻铭往往是有韵之文,多与诗合,能行而远之,或本即上古诵歌谣谚的孑遗,像殷墟所出一些甲骨所刻卜辞,其文学意味宛然可感:“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简约质朴,恰同汉代乐府《江南可采莲》诗中句式契合。
正是古代铭刻中存在和体现出的这些精神理想与文学趣味,让“物”超离“玩好”的层面,成为一种充满雅意的事物,中古以来的文士也渐渐在经世治学之余,开启了对这类“物”的审美,他们发现到蕴藏其中的那种历史性维度。
文人参与文房雅物创作
唐宋文化精英参与文房器物的艺术制作或许具有偶然性,但过程中那种对永恒性的追逐无疑是明确的,白居易歌咏作为赏玩之用的太湖石“在世为尤物,如人负逸才”,他期待的是将来与自己有同好的人能够“睹斯石”而“览斯文”。从徽宗为东南花石亲题“卿云万态奇峰”,到米芾为所收珊瑚作图与诗,则正可一窥“文心”如何将“雅趣”与“物恋”相融;他们这类充满灵韵的艺术创作和文化实践,被后世的解读者和转述者抽象为人文与自然深刻互渗,而长久地流传在古典语境的审美话语里。

饶宗颐自书敦煌诗紫砂壶

饶宗颐无弦琴铭易水砚

饶宗颐临中秋帖玉笔筒
明清时期,更多文人主动参与到雅玩的生产和消费中,这些物中的“文”雅,已非仅是文学的呈现,它们甚至影响观者的思想、塑造玩赏和使用者的文化品味,人文、自然和社会越发复杂和多元的互动,得以凝聚和显现在一件件雅玩器物上。
一个可见的事实是,民国以降直至于今的文玩刻绘,逐渐失掉了趣味的传统和传统的趣味,工、艺、学亦相乖离而不能融通,虽然技艺愈加纯熟,设计尤多精审,但大多只为单纯追求装饰性甚至奢侈感,制器者和书画者、铭刻者的心绪与情感已不能见,相互之间仅有“合作”而缺乏沟通和理解,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
文人铭绘的复兴
作为通儒式的艺术和学术大师,选堂饶宗颐先生曾以余力参与创作了大量文房雅物,在金玉、甲骨、竹木、绢帛等材质及砂壶、毛笔、折扇、砚台、笔筒、琴、墨等器具之上,题诗作画、补图刻铭,驰骋神思、独运文心,于斯道有振起之功,足称近百年文人铭绘文玩之集大成者。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于2006年出版12册《饶宗颐艺术创作汇集》,其中第11册《文房清供》即收录部分此类文玩器物,观之可见选翁创作多样性之一斑,册中一些作品的刻制者为唐积圣,他对选翁的文心墨趣和笔意都有不俗的理解,故而能成其“雅”。
此外,镂竹名手汪伟亦常取选翁书画摹绘于扇骨、臂搁、茶则之上,以留青法刻成,神采飞扬,若真笔留迹,既似百年以上的古物,又丝毫不失生气。以往艺林朋侣之中,也有很多心意相通的合制文玩、铭绘雅物者,如吴昌硕和沈石友、唐云和徐孝穆、谢稚柳与沈觉初以及王世襄和范遥青等,他们之间推敲商略,铭绘诸器已非泛泛传摹复刻而已,其间透露的性情、交谊、机锋、密意,常引人在玩赏之间品味赞叹,选翁之于唐氏、汪氏,也正如此,是故雅物种种皆能形神毕备、清婉动人,自不待言。
在类似“游戏”的过程当中,文人雅士的铭绘“点化”了物品和器具,赋予它们特别的精神价值和人文意涵,而制作者和赏玩者都由此获得愉悦感——这样的愉悦感始终富有深度以及互动性和传播性,完全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物质消费所带来的“快感”。由是,那看似现实的艺术生活和实践,也自然而然具有了沛然可期的纪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