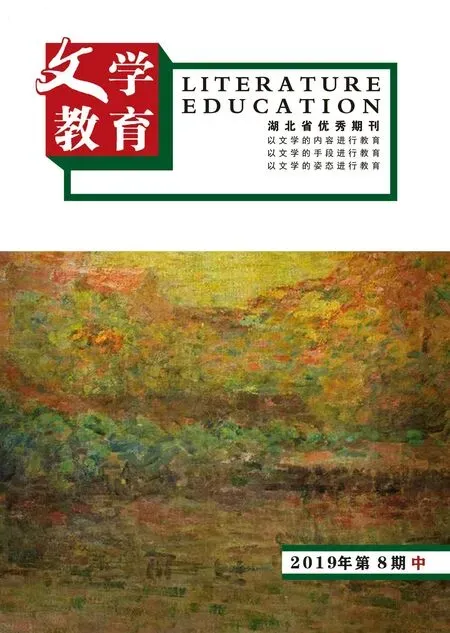《中国翻译家辞典》中的德语译家群体
吴昊龙
一.引言
德语翻译家群体在中德两国交往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为促进双方交流、增进双方理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长期以来,中国德语界对于翻译家的研究局限于文学领域,散落于文学研究的专著中,很少涉及其他领域的译家译事的研究。近年来,国内译界开始重视译家和译事的社会历史考察,探索他们成功的内在动因、心路历程、外部环境、社会需求和素质准备,[1]相继出版专著《中国翻译家研究》、译著《历史上的译者》。但以译者群体为对象的研究为数不多,学者周领顺和刘泽权先后以地域和性别为划分标准研究译家群体,然而直到今天学界尚未就翻译家所从事的工作语言范围进行划分并深入研究。此外,前期研究如由刘泽权撰写的《大陆现当代女翻译家群像》虽然全面梳理了特定领域的女性译家的翻译活动,但缺乏对翻译家的思想共性的考察。有鉴于这一学术空白,本文以《中国翻译家辞典》中的德语翻译家条目为研究对象,借助中国知网、超星移动电子图书馆等资源渠道全面梳理德语翻译家的生平、译介领域、翻译成果,旨在研究并回答如下三个问题:
(1)中国德语翻译家们呈现怎样的时间、地域分布特点?他们有什么样的教育背景?这三点因素对译家们的成长有哪些影响?
(2)中国的德语翻译家在哪些领域从事翻译实践?他们对这些领域的翻译做出了哪些贡献?
(3)翻译家们在翻译实践中形成了哪些认识?有无共性之处?可否为后世译家所借鉴?
二.词条的考证与甄别
《中国翻译家辞典》的词条中一般包括翻译家生平、教育背景、翻译工作语言、译事以及译介成果等信息。本文研究范围是《中国翻译家辞典》所收录的、精通德语、有德语译著的译家,借助英、俄、日等其他语种译介德语作品的翻译家不纳入考察范围。通篇阅读《中国翻译家辞典》后,笔者发现该辞典中某些词条的信息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如对于翻译工作语言介绍不充分。有些词条虽然交代了译著成果的国别,却无法确定该译著是直接从德语译介还是由其他语言间接译介,因而有待进一步考证和甄别。
本研究借助“超星移动”数字图书馆、“孔夫子旧书网”等平台在线对《辞典》中出现的国别为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等的译著逐条查询,并结合百度搜索引擎进一步考察翻译家的工作语言并最终甄别出71名德语翻译家。
三.《中国翻译家辞典》中德语翻译家们的成长环境探究
翻译家的成长同大的时代背景、地域分布以及教育背景密不可分。德语翻译家的成长环境也受到时代变迁、地域差别以及不同的语言学习条件的影响。为全面考察德语翻译家们的成长环境,本文以出生年份、地域分布和教育背景为三个考察因素进行如下分析。(表一附后)
从出生年代来看,《辞典》所收录的翻译家大多出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即从晚清到民国初年的历史时期。1900年前,我国同德语国家的交往形式主要为官方往来,民间交流有限,出生于这一时代的翻译家直接接受德语教育的寥寥无几。郭沫若、成仿吾等翻译家就出生于这一时期,他们是在留学日本等国家期间逐渐接触并了解德语语言和德国文化的。少数翻译家如生于1899年的商承祖则因随父旅居德国,就读于汉堡中学而奠定了较好的德语语言基础。20世纪初,我国高等教育逐步建立,蔡元培等一代教育家以教育兴邦,北大、清华以及复旦等高校相继建立外文系,促进了我国翻译事业的进步和一大批翻译家的成长,毕业生中不乏如冯至、田德望等翻译大家。冯至生于1905年,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1928年留校任助教,后又留学德国,成为我国现代德语翻译和德语教育的奠基人之一。[2]《辞典》中收录译家数量最多的时段就是1911-1930年的二十年间,这代译家们经历了战火纷飞的时代,他们之中亦很少有人直接学习德语,多数人是留学德国或学习外国文学后才逐步认识并热爱德国文化的。留学生群体中汇集了季羡林、贺麟等知名学者。1931年后出生的翻译家成年时正值新中国建立,因而有更多机遇接受德语专业科班教育,高年生、张玉书、杨武能、高中甫等一大学者通过学习德语语言文学专业成为翻译家。
地域因素对译家成长亦至关重要。《辞典》中所收录译家中籍贯为沿海开放省份的所占比例最高,尤以江浙沪等地区数量最多。上海是我国最早通商口岸之一,译家宗白华和庄瑞源都曾在中学时代在上海同济大学附属语言学校学过德语,进而产生了对德国文学和哲学的浓厚兴趣。[3]华北地区的京津冀鲁也是也是较早对外开放的地区之一,著名翻译家王以铸就生于九国租界天津市,城中布满各国书店,因而他日后能成为通晓古希腊,拉丁,俄,德,英,法,日,西班牙等多种文字的翻译家。
教育背景无疑是考察翻译家成长的核心要素。《辞典》所收录的71位翻译家中以德语语言文学为专业的仅为14名,另有13名为非德语专业的德国留学生,这两类译家占总人数的37.5%,不到一半的比例。以国内其他外语专业为背景的翻译家却构成了最大的群体,共17人,他们大多都能驾驭多种工作语言,具有扎实的中文功底,著名译家钱鸿嘉和傅惟慈位列其中。钱鸿嘉毕业与浙江大学外国文学系,谙熟英、法、德、俄、日、意大利、捷克、西班牙、拉丁等语种,为上海译文出版社专任编辑。此外,这一群体中还包括中央编译局的俄语译家们,他们大多因为翻译马恩原著的需要在工作后开始学习德语。留学生群体中也诞生了很多知名译家,这其中不仅有季羡林、田德望等留德人士,还包括朱光潜、郭沫若等留学其他国家的学者。朱光潜就在留学英国期间利用准备撰写博士论文的期间到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德语,郭沫若则是在留日期间阅读了海涅、歌德等人的德语原著。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德国文化的吸引力。
四.各领域翻译家的翻译活动历史考察
如表一所示,哲学和马、恩著作以及文学构成《辞典》中译家的主体部分。下文着重以这两个领域为重点探究翻译家的翻译活动。
1.哲学和马、恩著作领域的译家翻译活动考察
德国在世界哲学历史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集大成者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思想就是通过翻译家的努力译介到中国的,黑格尔研究专家贺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20世纪50年代后,贺麟主要翻译了黑格尔、斯宾诺莎和马克思的德文原著,其中黑格尔的著作包括《小逻辑》、《哲学史演讲录》、《精神现象学》等等。[4]在这之后,中央编译局的翻译家张奇方、易克信等在贺麟的帮助下继续着对黑格尔哲学作品的译介工作。根据贺麟的指导,一些德语的哲学术语进行了统一,如将“Idee”译作“理念”,将“Dasein”译成“定在”等等。张奇方和易克信两位译家还根据俄文的译本的某些出入同贺麟进行探讨,最终翻译了黑格尔的哲学经典《法哲学原理》。[5]
1919年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不断地被译介到我国。民国时代,就有进步翻译家从事马恩著作的翻译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根据史料记载,翻译家郭大力于1928年开始试译《资本论》。为了做好全文翻译工作的准备,郭大力利用几年的时间钻研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自修德文并于1934年起再次开始工作。[6]1937年,生活出版社决定出版《资本论》全译本。此时,王亚南也参与了翻译工作。经过二人的通力合作,1938年,《资本论》1-3卷终于问世。这部资本论是1974年前我国最完善的译本,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著作,最早于1920年由陈望道从日语版本译介到我国。后来,成仿吾多次参与翻译并修正《宣言》的各个译本。1976年,译家李逵六被调中央党校,协助成仿吾校译马恩著作,重新翻译了《宣言》。(表二附后)
2.文学领域译家翻译活动考察
德语文学翻译家群体的特征在于他们多数为高校学者,其中的13位翻译家都是德语专业科班出身,他们既是德语国家文学翻译的开拓者,又是我国德语学科的奠基人,如冯至、张威廉、商承祖、杨武能等等。他们都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稳定的工作环境,长期从事着德语翻译实践。当然,他们之中也不乏有像钱春绮先生等高水平自由译者。
从译作的作家归属来看,被译介最多的当属歌德和海涅的作品。歌德的《浮士德》在我国有多个译本,郭沫若、钱春绮、钱鸿嘉、董问樵、梁宗岱、绿原都曾翻译过该著作。这些译者都力图最大程度地再现歌德这篇鸿篇巨制的文学价值。郭沫若早在留学日本期间便开始接触并翻译浮士德第一部,1947年出版了整部浮士德译本,前后共耗时二十八年左右。绿原先生在其《浮士德》译序中提及自己在翻译全文前曾阅读了前几代译家的中译本以及冯至先生的研究结果,而这对他的翻译工作而言大有裨益。总体来说,新的译作继承前人并有个人的发展。[7]此外,德国的现当代大文豪,如托马斯·曼和海因里希·伯尔等多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也是重要的译介对象,但其中译本数量远不及歌德的作品。托马斯·曼是德国现代文学大家,192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60年代曾出版傅惟慈的中译本。海因里希·伯尔则是德国当代作家的代表,其作品多反映小人物生活的不易,197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代表作《女士与众生相》(也译作《莱尼与他们》)于80年代被译介到中国。
从翻译方向来看,多数译家从事外译中翻译,少数文学翻译家也从事中译外,这其中包括张连根、李逵六等。张连根翻译了《1977-1979年中国优秀短篇小说选》并于1981年由联邦德国森德勒出版社出版。李逵六翻译了季羡林的《留德十年》。刘梦莲翻译了德语版《熊猫画册》等。但同德国的汉学家相比,中国译家的文学外译作品为数不多。(表三附后)
五.德语翻译家翻译思想阐释
德语翻译家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翻译思想。他们也针对翻译学中长期讨论的问题如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翻译标准等问题提出了观点。
哲学翻译家贺麟从哲学的角度明确肯定了可译性的存在。他认为不同的语言之间存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部分。[8]而翻译的任务就在于寻找不同语言之间“心同此理”的部分,从而建立起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的有效沟通。译家马君武在广西大学的纪念周讲话中提到了我国古代的佛经翻译并表示当代中国人也可以照样达到这一目标,暗含对可译性观点的认同。[9]
翻译标准的问题时至今日仍是译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在这一方面贺麟认同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认为“能信能达且有艺术功力为归。”[10]贺麟对于“雅”的理解是“声调铿锵,对仗工整,有抑扬顿挫的笔气,……”,一种形神兼备的理想的译文状态。马君武也主张遵循“信”和“达”的标准,注重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和译文语言的流畅。但马君武对“雅”嗤之以鼻,认为“雅”是刻意追求,矫揉造作,不能经世致用,不应成为翻译所追寻的目标。文学翻译巨匠冯至的翻译标准更贴近于他的诗歌翻译实践。他在翻译《漫游者的夜歌》这首短诗后有如下表述:“我翻译这首诗,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注意每行诗的节奏,用韵脚来补偿实在难以表达的音调。”冯至认为诗歌翻译要做到形意兼备,既要“信”又要“雅”。科技领域翻译家郑太朴提倡译著行文应浅白晓畅、通俗易懂,对白话文有着特殊的偏好,注重“达”。文学翻译家杨寿国也谈到了“信”、“达”、“雅”,但他补充了“信”与“达”实现的条件,即“语境”,认为某一个词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之中才能被赋予意义,译者也只能在具体语境中才能准确把握原文语句所指,才能做到“信”。[11]绿原也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对于翻译标准抑或是翻译批评的见解,他认为翻译批评不仅要重视“信”,不能单纯盯着原文,同时也要客观地审视译文,挖掘好译文的精妙之处。
六.结语
本文对《中国翻译家辞典》的71名德语译家进行了描述,全面考察了影响译家成长的因素、各个领域翻译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译家思想的共性,得出如下结论:1.时代变迁、地域环境和教育背景都是塑造翻译家的关键要素。时代和地域制约着教育的发展水平。因此时代和地域是间接影响因素,教育是直接影响因素。总的来说,中国德语翻译家的成长和发展得益于近代以来我国外语教育和翻译教育的发展。2.译介绝不是一项孤立的行为,既有同代译家之间的交流互动,也有先后几代译家之间的衣钵传承。中国德语翻译家们是在互动与传承的关系中共同推进翻译事业发展的。3.中国德语翻译家们尽管表述不一,但几乎都认可翻译的可译性,认同严复“信”、“达”、“雅”。当代译家提出了翻译的语境问题和以译文为中心的翻译批评观,这无疑是对前人翻译认识的深化和发展。



注 释
[1]赵亚军.论翻译家研究的理论模式.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6(4):40
[2]林辉.中国翻译家辞典.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216
[3]林辉.中国翻译家辞典.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762-763
[4]范先明.近代哲学家贺麟:理论、实践及影响.上海翻译,2016(3):9-14
[5]中央编译局网页:往事点滴网址:〈http://www.cctb.net/topic/jd90/jshg/201108/t20110830_29381.htm〉(accessed 2018-05-15)
[6]林辉.中国翻译家辞典.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250-251
[7]孙瑜.浮士德——汉译者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研究.上海:复旦大学,2013:27
[8]方梦之,庄智象.中国翻译家研究(当代卷).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9
[9]杨丽华.中国近代翻译家研究.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84
[10]方梦之,庄智象.中国翻译家研究(当代卷).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11
[11]杨寿国.具体语言环境——正确传达的依据.外国语,1989(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