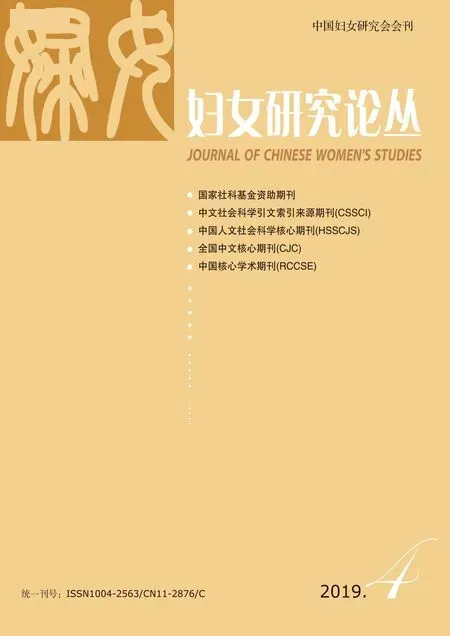韩国“慰安妇”议题的形成、发展过程与社会意识问题*
[韩]李贞玉
(1.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2.天津外国语大学 亚非语学院,天津 300204)
韩国“慰安妇”问题因韩日外交、社会观念和个人心理伤痛等原因被尘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40年间鲜少被提及。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韩国女权运动发展和女性权利意识崛起的前提下,经过社会团体的不懈努力、受害者的公开证言、媒体的报道、民众的讨论和声援等活动,“慰安妇”问题由一个静态的历史问题发展为由一系列事件推动的具有现实影响力的社会议题。本文试图梳理韩国日军“慰安妇”议题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并从口述文本化、受害者权益和民众心理等多个角度分析“慰安妇”议题的建构与传播及其背后所隐含的基础共识与多重分歧。
一、韩国“慰安妇”问题的历史背景
1931-1945年,为防止大规模强奸行为、性病传染以及军事机密泄露,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等地强制征召年轻女性,将她们集体收容在前线和占领区的慰安所,成为日军的性奴隶。由日本民间主导的随军慰安所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就存在,而日本军队主导建立的随军慰安所则始于20世纪30年代。1931年,日本海军在上海以“贷座敷”(日本公娼制度中对取得官方经营许可妓院的称呼)为基础建造了海军慰安所,成为慰安所的范本,随后,日本陆军开始在占领区各地建造慰安所。1937年,日本军队开始系统设立随军慰安所。
收容在慰安所中的女性年龄一般为11-30岁不等,规模较小的慰安所有七八人,规模较大的慰安所有四五十人。此外,战争期间日本在库页岛和日本九州等地区为了推动军工厂及战争建设相关公司的发展,以强制劳动的工人为慰安对象,政府和企业联手运营了企业慰安所,亦有大量女性被征召。



严格来讲,女性“挺身队”不能等同于日军慰安妇,但从殖民时代到现在,韩国社会常常用“挺身队”指代“慰安妇”,原因是当时“被日本拉走就意味着失去贞洁”的认识比较普遍,而且“挺身队”的女性也有一部分被送进了慰安所。因此,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等民间组织的活动均围绕“慰安妇”问题展开,韩国语境下谈及“挺身队”问题也普遍默认成“慰安妇”问题。
韩国“日军性奴役受害者”问题的社会议题化建构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逐渐开始的,当时伴随着韩国民主化运动中女性运动和劳工运动的开展,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等民间社会团体提出“慰安妇”的历史问题。在此之前,“慰安妇”问题仅少量存在于文学作品中对相关历史的描写,并没有形成社会议题。
二、韩国“慰安妇”社会议题的形成过程
1945年8月15日,朝鲜半岛取得独立。1948年8月,大韩民国成立。战争结束后,相当一部分日军性奴役受害女性被当场枪决,或被逼迫自杀,也有一部分幸存者回到了韩国。日军性奴役受害者是战争期间日本军队性暴力行为的牺牲品,遭受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创伤,在当时的韩国父权社会中备受歧视和排斥,由于贞操观念等原因,她们自身也感到羞耻,不愿提及慰安所的经历。战争结束后“慰安妇”并没有被明确为日军强制征召的受害者,甚至社会舆论中还存在“卖春”的说法。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的将近40年间,由于韩日间外交关系、韩国社会伦理意识、个人对于伤痕记忆的压抑等诸多原因,韩国的日军性奴役受害者不得不保持沉默,集体处于失声状态,韩国社会对“慰安妇”问题也反应冷淡。
“慰安妇”问题在韩国社会开始引起反响的一个重要事件是1991年7月18日,有过从军“慰安妇”经历的金学顺打破沉默,发表有关“慰安妇”问题的证言。这也是韩国女性以“慰安妇”身份出现的首次公开证言。“慰安妇”问题被揭开,一方面是受到韩国女权运动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民间组织的不断努力,金学顺也是在民间组织的协助下得以公开发表证言的。在金学顺公开发表证言的当天,多个民间组织联合组成的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召开会议,向韩日各界发送公开书函,并向国会发出请愿书,要求韩国政府关心和解决有关“从军慰安妇”问题的6个要求事项[1](PP 320-331)。金学顺的证言鼓舞了更多受害者发声,一些受害者陆续公开发表证言,展开对日本侵害行为的控诉。1991年12月,“从军慰安妇”受害者文玉珠、金富善先后发表证言。日军性奴役受害者站出来揭露日军罪行,揭发被遮蔽的历史事实,成为韩国“慰安妇”社会议题发展的基本前提。1991年12月6日,日本官房长官加藤纩一发表“日本政府困难对付从军慰安妇问题”的言论,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向日本大使馆发表公开书函提出抗议,表示决意定期游行,直到“从军慰安妇”问题解决[1](PP 320-331)。

有关“慰安妇”问题的研究随之在韩国学术界和民间机构展开。1992年1月,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发现了战时资料《陆支密大日记》并公开发表,其中披露了关于“从军慰安妇”的重要记录。此后,吉见义明联合日本其他学者成立了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围绕“慰安妇”议题展开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公开日本防卫厅防卫资料室收集的日军回忆录等材料,以施害国的身份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成果,出版了《从军慰安妇资料集》,这对相关史料不足的韩国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慰安妇”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一系列证据以及韩国政府和民间社会的压力下,1993年8月4日,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就“从军慰安妇”问题发表了“河野谈话”,这是日本政府首次承认强制征召“慰安妇”的事实。
韩国研究界在“慰安妇”问题历史资料收集上遇到了较大困难。一方面,较多重要资料被日本政府和军队销毁;另一方面,大多数有价值的史料在日本和中国两地,很多重要的资料未被公开。因此,韩国研究界初期研究主要以已经公开的资料和证言为基础,集中于以口述证言揭露日本罪行,对“慰安妇”事实进行确认。与此同时,并行展开对受害者的生平研究。“慰安妇”的证言和口述资料对复原历史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在朝鲜居住的朴永心曾通过口述证言叙述了在中国充当“慰安妇”的经历以及在昆明美国管辖的俘虏收容所的生活,美国情报部门和军队的报告书和照片印证了朴永心的证言,后来参加云南地区作战的一名日军士兵证言被发掘,多重史料交叉印证了史实。

经过韩国各界十多年的努力,“慰安妇”问题从尘封的历史变成韩国社会和民众最关心的社会议题之一,并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日本政府对“慰安妇”问题的态度在韩国不断受到强烈批判。
三、围绕口述文本化展开的“慰安妇”议题传播以及其后受害者权益的保障

慰安妇受害者口述文本化活动,一方面收集证言和史料,以证言的形式揭露罪行,这有助于确认“慰安妇”事实,核实日本帝国主义对日军性奴役受害者实行征召的强制性;另一方面采用受害者口述生平史的方法,重视她们的语言内容和主观感受,以日军性奴役受害者的个体经验和记忆创造公共历史。无论战争期间还是战后,“慰安妇”群体基本都是韩国社会结构中的底层,往往受到他人、社会环境和制度的多重排斥。慰安妇受害者的口述生平史关注作为女性的“慰安妇”的个人经验,重视主观感受叙述。日军性奴役受害者在强制征召时期遭受性侵犯和性暴力,造成了身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后遗症。口述文本化重视受害者的生平史,将受害和创伤的历史一直延续到当下,通过深入访谈,关注她们的经历和创伤,以及性奴役造成的肉体和精神的后遗症对当下生活的影响。其后韩国国内外政策对“慰安妇”的支持和资助,也是以证言为基础展开的。
除了通过口述研究确认受害者的事实之外,韩国学界还进行了历史学、女性学、心理学等多个层面系统性的研究,如“慰安妇”制度的成立和运营状态、作为施害者的日本兵心理分析、受害者的精神后遗症、日本的法律责任等。
战争结束后,慰安妇受害者回到韩国,往往和家人断绝联系,不愿回老家,且难以维持生计。有人放弃了婚姻,年老后无人赡养。也有人滞留在中国,缺乏返回韩国的途径,直到中韩建交之后,才恢复国籍。一些慰安妇受害者当初由朝鲜到中国,已经无法再回到朝鲜,与家族离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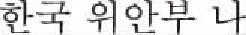
四、“慰安妇”议题的社会意识:基础共识与多重分歧
目前韩国社会整体形成了关于“慰安妇”问题的基础共识,对于日本提出的诸如“慰安妇”是否自愿参与随军慰安、“慰安妇”是否是战时公娼等议题的讨论,持坚决否定的态度,形成全社会愤慨之势。历史教科书中“慰安妇”部分的编纂、术语的使用也逐渐形成统一的历史表述。对慰安妇受害者身份的质疑成为韩国社会无法容忍的言论,韩国大学中甚至出现了对“慰安妇”问题持不同看法的学者因被视为发表不当言论而遭解职的情况。

对于整个韩国社会而言,“慰安妇”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战争罪恶的受害者,而且作为日据时期韩国民族遭受屈辱的缩影,成为历史伤痛的象征,因此“慰安妇”问题又联结着靖国神社参拜问题、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日本右倾化等多个议题。而关于“慰安妇”问题,在韩日政府之间、韩国政府与民间社会之间、韩日民间社会之间多个场域,也存在着多重分歧。

韩国民间团体也认为日本方面的反应不够充分,继续要求日本政府和加害者公开谢罪并进行法律赔偿。日本政府应当被追究国家责任,日本军人、公务员及部分个人招募性奴隶,设置、运营慰安所,应追究个人刑事责任。1992年1月8日,日本首相宫泽喜一访韩之前,慰安妇受害者向日本驻韩大使馆转达了要解决“慰安妇”问题的诉求,大使馆没有回应。民间组织自此开始定期抗议集会,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前开展“星期三示威活动”,提出日军要承认对“慰安妇”的犯罪行为、道歉并进行法律赔偿、处罚相关人员等一系列要求。“星期三示威活动”一直持续到今天,并作为持续时间最长的和平示威活动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随着韩国慰安妇受害者不断离世,人数不断减少,少女像成为韩国慰安妇受害者的象征,而少女像问题逐渐成为慰安妇问题最重要的指向之一。少女像具有受害者、伤痛记忆和“星期三示威活动”的多重象征意义。首个少女像诞生于2011年12月,当时为了纪念“星期三示威活动”20周年,在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组织下,经过公众募捐,由知名雕塑家完成名为“和平碑”的少女像,立在日本驻韩大使馆门前。日本政府就驻韩大使馆门前的少女像撤出和搬迁问题与韩国政府不断交涉,这个过程反而强化了少女像作为抗议运动象征的形象。之后,韩国各处的少女像数量不断增多。

虽然《韩日慰安妇协议》并没有出现“强制拆除”等词汇,但该协议签署的第二天,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等团体就开始发起全民反对协议的运动,韩国年轻人自觉加入保护少女像的队伍,首尔大学生24小时守在少女像跟前,以防少女像被拆除。2016年12月,位于釜山日本领事馆后面道路的少女像一度被拆除,但是通过釜山民众和大学生的力量,又重新竖立起来。2016年10月底开始在首尔举行的烛光示威(要求朴槿惠下野的抗议游行)中,一度出现过巨大的少女像,朴槿惠政府被认为在“慰安妇”问题上失误颇多,受到各界强烈的批评。按照《韩日慰安妇协议》,韩国政府需要协助拆除少女像,但之后少女像剧增,到2017年8月15日,韩国至少有80余座少女像,韩国中学还发起了百所中学建像运动,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等处也建成并竖立了少女像。2017年5月,韩国新任总统文在寅在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电话中表示,出于尊重国民心理的考虑,日本政府要求韩国政府尽快拆除少女像是不现实的。
韩国文在寅政府搁置《韩日慰安妇协议》之后,重申了“慰安妇”问题的国家立场:在“慰安妇”问题上,日本政府从国家立场上有责任,但韩国政府不愿意因慰安妇个人的补偿问题而影响韩日之间的外交关系,也不会围绕《韩日慰安妇协议》展开法律论争,但“慰安妇”问题终究还是人权问题,韩国政府会争取在联合国等国际舞台上获得支持并展开活动。换言之,韩国政府支持为赢得国际舆论的各种活动和慰安妇个人对日本提出补偿的请求,但不会将“慰安妇”问题提升为韩日间正式的外交问题。韩国政府这一立场显然是考虑韩日外交关系、民间力量等多个因素所提出的符合政府政治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五、结语
多种力量的协作与对抗共同推动了“慰安妇”议题的扩散,多重分歧的存在也将使“慰安妇”议题得到更充分的讨论和更持久的传播。有关“慰安妇”的讨论不是单纯的日本方面是非对错问题,围绕议题采取的措施也不只是解决具体问题的手段,国家地位、民族尊严、公众情感和政要形象等因素都夹杂其中,难以剥离。“慰安妇”议题隐含了韩国遭受的历史伤痛,在韩国国内形成了相对统一的基础共识,但在此之上又存在着多重分歧,包括民众与部分学者对“慰安妇”问题所持态度的分歧,民众对政府采取的救助措施、政府对日本所做妥协的不满等。虽然各方一直提出追求基于“历史和解”共识,但就韩国方面而言,对于“慰安妇”问题,国内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持续高涨,尤其对于日本殖民地时代所遗留的历史问题更加敏感,这点从国内对于“慰安妇”问题历史叙事中“受害者”意识不断加强也可以看出来,甚至各方对于“慰安妇”问题的分歧并没有趋向解决,而是不断加剧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