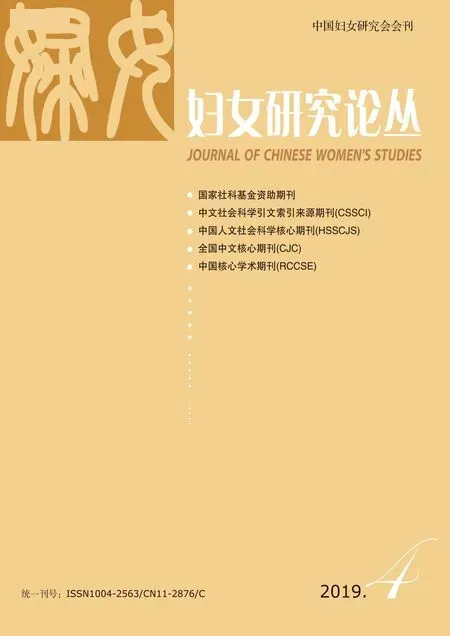陪读妈妈:性别视角下农村妇女照料劳动的新特点*
——基于陕西省Y县和河南省G县的调查
吴惠芳 吴云蕊 陈 健
(1.3.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 社会学系,北京 100193;2.英国谢菲尔德大学 社会学系,谢菲尔德 S10 2TN)
一、研究背景
照料劳动包括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家务劳动以及对儿童、病人和老年人的直接照料[1]。目前关于照料劳动的研究主要和女性就业机会、女性地位与性别关系等问题相联系,且这类研究集中讨论其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呈现[2](P 8)。关于有酬照料劳动的研究,尤其是“全球照料链”(global care chains)的讨论,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女性流动到发达国家与地区从事有酬照料劳动并引起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照料赤字及福利不平等的相关问题[3](PP 369-391) [4](PP 1-21)。关于中国的照料劳动问题,已有研究多聚焦家庭照料劳动负担对城市女性就业或从事其他有酬劳动机会造成的影响[5](PP 43-54)[6](PP 61-68)[7](PP 9-10)以及家政女工问题[8](PP 51-57)[9](PP 16-21),但后一类研究更注重流动女性务工人员的权益问题,并没有特别强调有酬照料劳动的分析视角。关于中国农村照料劳动的研究包括了农村儿童照料服务的质量及其政策意义[10](PP 55-71),也涵盖了照料老人对农村女性劳动时间的影响[11](PP 1-15)。总体来说,照料劳动作为一种分析视角,在农村妇女的研究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采纳。
与农村妇女照料劳动问题相对应的是两大社会现实问题:一是劳动力乡城流动背景下的农村妇女照料劳动与责任问题;二是近十多年内发生的农村教育快速转型。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流动规模的持续扩大,无论是“离土不离乡”的本地非农产业就业,还是“离土又离乡”的外出务工,以务工收入为主的非农收入对农村家庭的贡献率越来越高,农村家庭的生产功能不断弱化,情感功能与照料功能变得越来越重要[12](PP 64-66)。同时,由于传统“社会性别规范”[注]查菲茨的“性别公正理论”中的一个概念,见乔纳森·H.特纳著,邱泽奇等译:《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176-180页。(gender norm)的影响,农村妇女依然承担着照顾和教育子女的责任。因此,在劳动力流动的背景下,留守在农村的女性不仅承担了对子女物质生活的照顾,而且成为家庭教育的主角和学校教育的配角。200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83.2%的留守妇女正在照顾至少1个未成年子女,其中35.5%的妇女照顾两个未成年子女[13](P60)。即使有流动的机会,她们在流动与留守状态之间徘徊的人生轨迹亦随着照料责任的变化而不断变化[14](PP 178-190)。在这一时期,农村妇女从事的照料活动主要在乡村完成,本文将其称为“在乡照料”。但是,在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实施逐步深入并导致县域内城乡教育资源重构之后,农村妇女照料劳动的空间、内容和形式也发生了变化。
进入21世纪后,农村教育政策对农村家庭照料劳动的安排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中小学布局调整政策使农村学校数量锐减,大量农村儿童进城读书。有研究指出,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使得农村小学数量由2001年的416198所减少至2015年的118381所,下降幅度之大、时间之短,为历史所罕见。在城乡发展程度差异和城乡优劣观念的影响下,办学城镇化,村落教育衰弱,造成了“文字上移”现象[15](PP 110-140)。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包括城乡经济发展不均衡、城乡学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农村家庭经济收入提高、家长对子女的教育预期提升等[16](PP 66-74)。现有研究的主要关注点是学生的成长与学校教育管理问题,如教育的城市导向、寄宿制问题、教育资源浪费、村庄的离散凋敝[17](PP 2-12,P 188)等。与之相伴的农村家庭照料安排则是愈演愈烈的陪读现象。有研究显示,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陪读现象,西部地区或经济欠发达地区尤其明显。已有研究不仅文献数量较少,而且主要关注陪读家庭的经济负担和学生的教育质量问题[18](PP 97-112)[19](PP 249-251)[20](PP 121-124)[21](PP 53-54),鲜有研究专门关注进城陪读的农村女性群体。本文所讨论的“陪读妈妈”,是指为了给进城读书的子女提供日常照料而陪读的农村妇女群体。借助关于劳动力“离土”与“离乡”的讨论,与前文所讲的“在乡照料”相对照,本文将陪读妈妈的照料劳动定义为“离乡照料”。对于农村妇女来说,“离乡照料”既是其承担照料劳动的一种形式,也是其流动的一种形式,但它又与农村女性劳动力为寻求有酬劳动机会的流动相区别——妇女通常在县域内流动,从事的劳动以家庭照料为主,处于无业或不充分就业状态。
本文期望借助照料劳动的分析框架和性别分析视角,关注“陪读妈妈”这一个独特的照料者群体,试图揭示农村妇女照料劳动的新特点及其社会意义。通过对陕西省Y县8位陪读妈妈、河南省G县12位陪读妈妈[注]为了保护被调查者隐私,本文所用案例均做了化名处理。的深度访谈,本研究形成了20个陪读妈妈的典型案例资料。同时结合对这2个县4所学校的4位教师、3位村干部、妇联工作人员、教育局工作人员的访谈,以及针对家长的小组访谈,尝试探讨以下4个问题:第一,陪读妈妈群体形成的社会条件和家庭照料分工策略;第二,陪读生活对妇女个体的影响;第三,陪读妈妈在陪读地(通常是县城)的社会融入与社会排斥问题;第四,陪读这样一种“离乡照料”劳动对于妇女发展与乡村社会文化的意义或影响。
二、陪读妈妈:农村家庭教育期望攀高与教育资源走低的结果
前文提到,西部地区或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陪读现象更为明显,其主要原因在于,越是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地区,教育资源越有限,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和教育质量差距越显著。本研究以笔者2016年和2017年分别在陕西省Y县及河南省G县开展的实地调查为基础。Y县和G县均有数量庞大的陪读妈妈群体,但在形成原因、群体特征、社会融入以及县城社会对其的态度等方面,有共性也有差异,因此既能表现陪读妈妈的群体性特征,又能展示其在不同社会情境下的多样化特征。
陕西省Y县陪读妈妈群体的出现与农村家庭收入提高、农村家庭教育期待提升以及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校数量的锐减是同步的。Y县地处山区,地理位置较为偏僻,20世纪90年代初Y县农村劳动力开始外出务工,外出规模迅速增长,至20世纪末达到高峰。但是,外出的劳动力以男性为主,女性多在家务农、照料家庭。21世纪初,随着Y县不断出台相关支持政策,当地的林果业得到快速发展。一方面,林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另一方面,林果业的收入较传统粮食作物收入高得多,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放缓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速度。随着当地农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农民对子女的教育期待也不断提升。然而,同一时期,Y县农村义务教育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2002年,Y县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工作。据县教育局统计,2003年,全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为200所。2015年,经过十余年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之后,全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仅有27所,甚至还有数所农村学校的在校生数量不足50人。通常情况下,一个乡镇有1-2所中心小学和1所初中,且往往会获得高额的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有新建的教学楼,图书及教学设备等配备齐整,但由于乡村整体的落后状况、教师待遇低等问题,乡村教师不断流失,教学质量难以保证,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学生流动到县城就读。2016年,在农村义务教育学龄段儿童中,94.4%在县城学校就读。无论是初中还是小学,农村学生的比例都在逐年增加。进城读书儿童日益低龄化,甚至延伸到幼儿园时期。县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超班额现象十分突出。例如,Y县A小学43%的学生来自农村,有陪读家长,且80%以上的陪读者为母亲;B中学7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有陪读家长,其中78.8%的陪读者为母亲。陪读妈妈和孩子大多在县城租房居住,聚居在特定区域。通过观察陪读家庭聚居的居住区,笔者发现,这些家庭大多租赁面积20-30平方米的房屋,既有平房也有楼房,居住空间较为拥挤,但通常离孩子就读的学校较近,以方便上学。总的来说,Y县农村家庭的教育期望日益攀高,农村学校的方便程度和教育质量却逐渐走低,导致农村儿童大量进入城市就读,陪读妈妈群体随即出现。
G县是河南省人口大县,也有数量庞大的农村学生带着“陪读妈妈”进入县城读书。20世纪80年代初,G县已有人外出务工,是河南省农村劳动力最早外出务工的县之一,目前该县有超过一半的农村劳动力在外地务工,形成典型的“打工经济”。与陕西省Y县相似的是,G县农村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期待也较高,但经历过波动。20世纪90年代,是当地打工经济最盛行的时期,大部分农村家长并不追求孩子上大学,多希望孩子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挣钱。进入21世纪,G县人员的务工类型开始转变,工厂就业、自主创业者增多,务工者逐渐意识到受教育程度对其职业发展的制约,教育期待开始攀升。与陕西省Y县不同的是,尽管G县也执行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布局调整政策,但因其人口总量大、地势平坦、居住集中,被撤并的农村学校并不多,对农村学校格局的影响不大。对G县农村学校影响较大的是教师问题。早期,G县每个村都有一所小学,教师多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聘用的民办教师。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民办教师辞退工作的逐步推进,民办教师数量锐减,村级学校开始合并。经过10年左右的调整,G县重新形成了学校格局并延续至今——基本每2-3个村有一所小学,每个乡镇至少有一所初中。但是,尽管县教育局不断出台政策鼓励为乡村学校聘任新教师,但年轻、高水平教师流失现象越来越严重,对乡村学校的教育质量产生了不良影响,也促使农村家庭开始寻觅更好的教育资源。
与乡村学校下坡式发展不同,G县县城教育快速发展,尤其是私立学校教育的发展引人注目。2008年,G县教育局发布了一系列鼓励和支持私立学校发展的政策,包括同意公办学校教师到私立学校任职等。总的来说,私立学校对农村学生及家长更有吸引力主要在于:第一,教师工资几乎是公立学校的两倍,吸引了大批高水平教师入校任职;第二,学校管理严格,实行教学业绩考核制度,以学生考试成绩衡量教师业绩;第三,开放招生,只要付得起学费即可入校。因此,一方面是乡村学校优秀教师流失、教育质量下降,另一方面是县城私立学校师资水平高、教学质量高、管理严格。近10年时间,越来越多的农村学生进城就学,县城学校尤其是私立学校的学生规模迅速扩大。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乡村学校的在校生数量迅速缩减。例如,全县学生规模最大的4所私立中学,在校生数量均超过5000人。由于私立学校没有住宿条件,农村进城读书的学生只能住在校外,需要家长陪同照料,因而催生了规模几乎同等庞大的陪读妈妈群体。大部分陪读家庭在县城租房陪读。由于G县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起步较早,部分务工人员收入较高、有一定积蓄,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陪读家庭在县城购房。可以说,G县农村儿童被日益走高的家庭教育期望推出了教育质量下降的农村学校,县城快速扩张、教育质量高、完全开放的私立学校则吸纳了这些学生,同时伴生了大规模进城的陪读妈妈群体。
三、离乡照料:农村女性的劳动固化与人身依附
儿童教育流动与陪读妈妈群体的形成,与城乡学校布局和教育发展密切相关,陪读妈妈的生活状态却与县域经济发展状况有更大的关系。根据陪读期间是否务工或务农的情况,本研究把陪读妈妈分为全职陪读和就业陪读两类。陕西省Y县地处黄土高原,全县人口约12万,其中县城常住人口约6万。该县农业经济以林果业为主,大量的农村劳动力留在本地务农,林果收入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Y县县域工业较为落后,工业产值不及工农总产值的1/5。然而,Y县却是一个教育大县——县城常住人口中,学生人口占1/3左右,其中包括周边县来Y县知名高中就读的学生。大量的流动学生造就了规模庞大的陪读妈妈群体。据县妇联调查,全县有2617名陪读妈妈在学校周边地点租房居住。河南省G县位于平原地区,全县人口约180万,县城常住人口约27万,市区初具规模、人口密度较大。该县粮食产业发达,机械化操作程度高、农业劳动力需求较低,农业收入在农民收入来源中占比较低。该县目前约有70万人在全国各地务工,务工收入是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了县城就业机会的种类和数量,也影响了陪读妈妈的就业机会。
(一)全职陪读妈妈的被动与能动
案例1:白凤,35岁,在陕西省Y县县城租房陪读照料两个孩子,儿子读初三,女儿读小学三年级。她曾经和丈夫一起在北京务工,生两个孩子时都曾在村里留守一段时间,一般把孩子带到一岁大后就再次外出务工。2011年,他们发现儿子在乡里的中心小学学习成绩不好,也看到周围很多人家把孩子送到县城读书。于是,他们也托关系让孩子转学进了县城的小学,由奶奶陪读。2014年,儿子升入县城的一所中学,女儿也于同年进入小学读书。为了更好地管理子女的学习,白凤和丈夫商量,决定由她回来代替奶奶陪读,丈夫继续在北京务工。白凤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30平方米的房子,每月租金300元,开始了陪读生活。儿子每天早上7点出门,女儿8点出门;两个孩子都要在家吃午饭;下午,女儿4点回来,儿子五点半回来。白凤有打工经历,非常希望能在县城找到一份工作,哪怕赚得少一点。但是,她的空闲时间严重碎片化,连超市都不愿意聘用她。她说:“我感觉我干的活儿都是废活儿,天天干也看不见活,钱又没赚着。”孩子成绩一出现波动,她就开始担心:“我已经啥活都不干,全力扑在孩子身上,如果照顾不好、孩子学习不好,对不起丈夫在外打工的辛苦,过年回来我也没脸面对他。”
全职陪读妈妈把全部精力用于陪伴和照料孩子,既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也没有机会从事非农生产劳动,她们没有个人收入,丈夫的收入是其全部生活来源。既然陪读妈妈劳动的全部内容是照料,那么照料的结果或效益便成为衡量其劳动价值的标准。白凤感叹的“我已经啥活都不干,全力扑在孩子身上,如果照顾不好、孩子学习不好,对不起丈夫在外打工的辛苦”,也“没脸面对他”,可以解释为陪读妈妈把自己的价值系于孩子的学业成绩上。有的陪读妈妈不堪压力也会对孩子直接表达“我受了天大的委屈给你做饭,你不好好读书就把我亏了”这样的话。就陪读妈妈而言,如果需要照料的子女超过2个,照料的劳动需求与时间分布很难给陪读妈妈留出务工的机会,“一天做三顿饭,中间2个小时空,哪个老板招工人会要我们这样的工人”?有的陪读妈妈在农忙时会回乡务农,将孩子寄养在亲戚家,或由老人陪读,甚至让孩子自己买饭吃。但是,她们认为这只是临时性的、辅助性的劳动,家里的林果收入是丈夫创造的,她们将自己的回家劳动比作“省了一个工人的工资”。同时,男性将“带好娃娃”“顾好孩子”作为妻子的第一责任,认为她们放下孩子出去挣的钱,“还不够给孩子买吃的”,所以“不如在家做饭带孩子”。“女的苦一天看不见钱,男的苦一天,总有收入。给你一毛钱都是人家挣的钱”——一个陪读妈妈这样评价自己的陪读劳动;同时,一个在外务工的爸爸这样评价自己的劳动:“家里的贡献当然是我贡献大了,我一个人赚钱。”即使妇女有工作,她们的收入依然被男性认为是“辅助性”的,是“入不敷出的”。笔者在Y县访谈的8位陪读妈妈中,仅有1人在超市打工,且只能打半日工,日薪30元;有2人在周末或农忙时返回村里帮助丈夫劳动;其余5人均为全职陪读。因此,全职陪读、照料孩子虽然表面上看是妈妈们的主动选择,但其本质是母亲对家庭照料需求的被动回应,是家庭内部照料劳动的性别分工。
案例2:卢云,42岁,在Y县县城陪读两个女儿。她的儿子已经20岁,在南京做学徒工;丈夫43岁,在福建一家模具厂务工,每月工资4000元左右。18岁时,卢云外出去西安务工,经老乡介绍认识现在的丈夫,婚后两人一起在外务工。22岁时,她怀孕返乡,生下了儿子,儿子满周岁后又继续外出务工。儿子7岁时,卢云生下了女儿,因婆婆无力照料两个孩子,她开始留守家乡,一边种地一边照顾孩子。3年后她又生下了小女儿。2010年,她把家里的耕地流转出去,计划到县城务工。卢云把两个女儿都转到县城学校,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由车库改造的房子,每年租金2000元。幸运的是,卢云在一家节能灯厂找到了工作,每月收入1000元左右。每天早上,她送大女儿上学,然后把小女儿送到姨妈家照料。中午大女儿在学校吃饭,卢云通常带着馒头、烙饼和咸菜作为午餐。下午4点,她收工接大女儿放学,再去接小女儿,然后回家做饭。因为娘家所在村庄离县城很近,她从娘家“借”了一小片地种菜,以节约生活支出。两年后,小女儿也开始上学。因学生数量暴涨,学校担心孩子安全问题,要求学生在学校吃完午餐后必须回家休息,下午上课时间再回学校。如此一来,卢云因为中午要回家照料两个女儿,工作时间被打断,因此很快就被工厂辞退了。她只好继续寻找新的就业机会。截至2016年夏天接受访谈时,卢云仍未找到合适的工作。卢云和三个孩子每月花费在1000元以上,但是她的丈夫每年只在过年回乡时主动给她三四千元,“他说不能多给我,怕我乱花钱”,平时都是等她要钱才给。卢云说:“他(丈夫)还嫌我在家不赚钱,家里开支全靠他一个,没有他这个家就塌了。”
在劳动力外出流动较多的地区,卢云这样的案例并不鲜见。农村妇女随着照料责任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人生轨迹,与她们的生命历程紧密联系在一起[14](PP 178-190)。“在乡照料”模式中,因为老人或子女的照料需求,妇女在家乡村落与务工地之间不断地往返流动;转入“离乡照料”模式之后,陪读妈妈则不断在有酬的就业劳动与无酬的照料劳动之间变换轨迹。为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而流动,是女性作为母亲的能动性体现,但照料责任是父权制社会结构赋予的女性责任和女性劳动,农村妇女很难逃离这一结构性力量。关于陪读照料劳动和务工/务农赚钱的劳动价值之间的比较,陪读妈妈大多认为“人家(丈夫)比我贡献大”,“他比我辛苦,我一天照顾娃娃,吃了还有个休息时间,他白天黑夜都要忙,整天忙,忙完还要自己做饭”,“我和孩子有什么需要的东西,都得跟人家(丈夫)伸手要钱,人家赚钱,我俩是纯粹的消费者”。陪读使妇女陷入完全的、显性的失业状态而失去对家庭经济的决策权。
(二)就业陪读妈妈的挣扎与骄傲
案例3:李云彩,40岁,在G县县城陪读两个孩子。她婚前曾在外务工5年,婚后留守在家8年后随丈夫外出务工。但是,务工两年以后,女儿在村里学校的学习成绩令她非常担心。她虽然没有期望孩子一定要考上大学,但务工经历让她充分领会了教育的重要性。她认为,县城的学校比乡村学校管理更严格、要求更高,一定可以改善孩子的学习状况。于是,李云彩和丈夫商量后,决定自己回乡照顾两个孩子。她在县城租了一间房子,把女儿和儿子分别送到县城的小学和幼儿园,并开始寻找打工机会。但是,照顾孩子让她的工作时间受到很大限制,从2009年到2013年一直没有工作。2014年,李云彩因偶然机会参加驾校学习并拿到了驾照。她跟别的司机合作承包了一辆出租车。如果她跑白班,接孩子、做饭,都不耽误;如果跑夜班,更不会耽误白天照顾孩子。2015年底,在面临翻建家乡老房子还是在县城买房的选择时,考虑到孩子读书和他们夫妻的长远职业打算,他们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因此,李云彩成为G县少数“住在自己家里”的陪读妈妈。在此期间,李云彩和丈夫一直种着自家和娘家的土地共15亩,除了供应自家粮食和蔬菜外,每年农业纯收入万元以上。家里大部分农活靠公婆雇机器或雇人完成,李云彩的丈夫在农忙时返乡干活。过几年公公婆婆年龄就更大了,李云彩希望丈夫可以回县城跟她一起跑出租车,以方便照顾孩子和老人。
由于陪读流动,农村妇女不仅改变了居住地点,她们的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中国传统社会性别观念里,女性首要的社会位置是嵌入于家庭之中的,因此对于女性来说,作为生产性劳动的务工和作为再生产劳动的生育和家庭照料需求一旦发生冲突时,她们将不得不放弃前者。但是,生计压力又迫使她们和其他家庭成员一起,以多种方式谋求生计改善。李云彩一家人的生计方式多样,农业生产、本地务工和外地务工三种方式的结合,为家庭生计的稳定提供了有效的保障。由于孩子进城读书及自己长期在外务工,他们已经逐渐改变了之前打工、赚钱、翻盖新房的想法,而将家庭发展的中心转移至城镇,成为县域城镇化的主要人口群体。
案例4:张英,44岁,河南省G县陪读妈妈。她曾在广东、郑州等地务工10年,育有一儿一女。她的两个孩子曾经在郑州上学,后因户籍问题回老家上学,由爷爷奶奶照顾。一年以后,孩子学习成绩下降很多,她认为一则爷爷奶奶对孩子的监管不够严格,二则本村学校的教学质量也不够好,随即把两个孩子转入县城学校,同时自己返乡陪读。陪读期间,她尝试在县城找过多种工作。她试过半日工作制的超市工作,但这项工作容易影响接孩子和做饭;在毛织厂干过计件工,虽然工作时间灵活,但是工作时间长且收入低;最后她做了保险销售员,工作时间自由、收入也相对较高。2016年,女儿考入大学,张英的照料任务大大减轻,她在孩子学校附近开了一个美容院,雇了一位陪读妈妈。尽管丈夫认为张英的首要任务是“带好孩子,赚不赚钱不重要,赚那一点钱耽误孩子学习不值得”,两个人因此不断吵架,“他看不上我挣的那一点钱”。但她觉得,一方面赚钱让自己说话“硬气”了一点,另一方面,假如她像有些陪读妈妈那样,“除了洗衣做饭就是打牌玩手机,会给孩子树立一个坏榜样、懒惰不上进的榜样,不可能陪好孩子的学习”;而她努力工作,会让孩子觉得妈妈很辛苦,很努力,他们自己也会懂事,会努力学习。因此,尽管丈夫强烈反对,她一直没有放弃工作的机会。
张英的故事是陪读妈妈独立谋求务工或就业行动的成功案例。务工经历与个人能力、个性都增强了她的个体能动性,再加上G县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创造的有利环境,使其可以突破社会文化的结构性力量,为子女塑造一个独立、自强的母亲榜样。然而,她的言语中却充满着对全职陪读妈妈的不屑,用“坏榜样、懒惰不上进”形容她们。她开店的区域也是一个陪读妈妈聚居的地方。有的人家庭经济条件好,租住在楼房里;家庭经济条件差一些的,租住车库改建房或与人合租。在她眼里,尽管都是因为子女读书流动到县城,她是在靠自己的能力养活自己,而其他没有工作的陪读妈妈则是不值得学习的对象。陪读是因为照料责任而产生的妇女流动,它成为农村妇女群体内部分化或分层的一个新机制,有工作的陪读妈妈和没有工作的陪读妈妈形成了两个阶层。
(三)在家“就业”的陪读妈妈:无酬的陪读与商品化的照料
案例5:张玉,38岁,在G县县城陪读两个孩子。她曾和丈夫一起在河南省漯河市、郑州市等地务工多年,中间因孕育两个孩子,间断性留守4年。儿子曾随他们在漯河市上学,但因他们工作忙碌而无暇照顾,又回乡上学。然而,成为“留守儿童”(张玉自己用语)两年期间,儿子的学习成绩不断下降。张玉夫妇俩认为,儿子学习成绩下降与乡村学校教学质量和管理质量有很大关系。因此,2014年,张玉停止务工,返回家乡,把两个孩子带到县城读书,成为G县陪读妈妈的一员。然而,十几年的务工经历让张玉并不甘心只做一个洗衣煮饭的陪读妈妈,她想方设法找工作,但一直没有找到。两个孩子的照料工作让她的空间时间零散成上下午各两个小时左右,没有任何一个雇主愿意雇用她。同村一家人得知张玉陪读,委托她照顾他们在县城读书、独自住在校外的儿子,每月付给她伙食费600元、洗衣费300元。这个孩子和张玉租住在同一栋楼,张玉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通过这个高中生,她了解到有些高中生为了夜晚学习时间更长,自己租住在校外,无人照料。张玉表示,在女儿高中毕业之前,她恐怕很难找到正式的工作,因此她计划长期做这样的“编外保姆”。
当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商品经济越来越发达,其日常生活的商品化程度也会不断提高,原来满足家庭需要的自给物品和劳动就会被市场购买所替代。由于G县劳动力务工历史较长,经济较为发达,商品意识已经深深地嵌入每一个人的价值体系中。在G县,保姆等家政业态并未兴起,但是农村商业化的幼托机构和养老照料机构正在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家庭照料需求正通过市场来实现。由于G县的人口基数大,农村儿童大规模进入城市就读,陪读照料成为家庭照料的新需求,也出现了商品化或市场化的趋势。专门针对农村进城读书学生的纯商业化的照料机构在逐渐出现,但依然停留在非正规水平,被当地人描述为“一套单元房、几张上下床、两个做饭娘”,没有一般照料机构的营业执照、健康证等。笔者在G县访谈的12位陪读妈妈中,有2个妈妈同时承担了其他孩子的照料工作,并收取一定的费用。在学校无法为流动进城的学生提供合适的食宿条件、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无法陪读、私人照料机构可信度和照料质量低的情况下,农村家庭通过私领域的社会关系,找到像张玉这样的陪读妈妈提供照料服务,建立起公领域非正式的劳资关系。尽管没有正式的劳动合同制约,但双方凭借熟人信任,实现了非正规的商品化照料服务以满足流动学生的照料需求。
家庭不仅是生产单位,也是人口与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场所,因而承担着再生产性劳动与生产性劳动的双重任务。如果从社会再生产[22](PP 1341-1359)的框架来看,妇女进城陪读本质上是家庭照料劳动性别分工与地域转移的表现。第一,全职陪读妈妈不再从事生产性劳动,因此被视为家庭纯粹的消费者,其所从事的再生产性劳动由于不能为家庭创造“可见的”现金收入,其价值评判就完全取决于子女的学习表现。第二,陪读照料责任使妇女被劳动力市场排斥或边缘化,同时由于照料的“离乡”特点,她们又游离于家庭农业生产劳动之外,失去了参与劳动收益的机会。第三,无论是居家就业的陪读妈妈还是在外就业的陪读妈妈,都承受着来自父权制和就业市场的多重压迫,其生产性劳动的价值被认为是辅助的、次要的,陪读照料的再生产性劳动是其首要劳动任务。这种家庭内部的性别劳动分工,是男性承担生产性劳动、女性承担再生产性劳动的分工,也是男性承担有酬劳动、女性承担无酬劳动的分工,更是男性承担可见劳动、女性承担不可见劳动的分工。这样的性别劳动分工,是对传统性别观念中关于再生产性劳动是女性劳动的进一步固化,也是对父权制下农村妇女依附性地位的强化。
四、闲散妇女:陪读妈妈的社会排斥与群像污名化
陪读妈妈在城镇的居住区域与活动区域与当地人口有着明晰的“边界”[23](PP 201-204)——尽管来自同一县域,但她们的生活世界与城镇人口存在很大的不同。在Y县,由于农村进城读书的学生数量的比例较高,在县城小学中自然分化出不同的层次。C小学被认为是县城户籍儿童入学的主要学校,该校家长通常在县城有稳定的工作,包括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等。其余小学被认为是农村学生较多的学校,尤其是D小学和N小学,农村学生几乎占学生总数的90%。而在这些学校的周边区域,集中居住着大量的陪读家庭。陪读妈妈通常母子2-4人租住面积30平方米左右的一间房子,有的是平房,有的是楼房。当笔者在Y县开展调查时,当地人可以很明确地指出哪些区域是陪读妈妈居住较为集中的区域。这些区域通常是在学校周边,环境拥挤,一个平房院子可能住四五个陪读家庭,一套单元房则可能住两三个陪读家庭。在这些区域的住宅墙上,贴满了各式各样出租房屋的小广告。
陪读妈妈的娱乐休闲时间十分有限,同时因为远离熟悉的家乡社区和人群,她们很难在城市发展出自己的朋友圈或休闲伙伴,其社会交往圈狭窄,与当地妇女的日常生活存在明显的界限和疏离。在G县,由于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历史较长,不仅县城人口规模较大,流动人口所占比例也比一般县城高。陪读妈妈的社会交往并没有融入县城本地人的圈子,她们聊天、打麻将的对象依然是陪读妈妈或者陪读老人。和流动到城市务工的农村妇女相比,陪读妈妈的照料劳动价值几乎被完全忽视,反而是其无业、无收入状态以及休闲时间与城市节奏的不协调被无限放大,被当地人称为“闲人”。
城市社区对陪读妈妈群体的休闲生活、社会交往也形成了污名化的评判——进城陪读让农村妇女变成“不负责任的母亲”和“不安分的妻子”,在子女照料方面失责,导致农村离婚率攀升。照料孩子被认为是陪读妈妈的首要责任和全部任务,其他影响其照料的活动都可能被放大为该群体的污点。然而,对于陪读妈妈来说,由于脱离了乡村的熟人和亲友圈,她们的社会生活圈狭小,跳广场舞、打麻将、看电视、聊天包括微信聊天便成为其主要的休闲方式。但是,除了在家看电视,其他活动都被认为是“不管孩子”的表现。学校老师在谈到农村孩子进城、妈妈陪读有什么问题时,就举例说陪读妈妈打麻将、跳广场舞和聊微信,影响其监督孩子做作业,是“不负责任的陪读妈妈”。但是,细究起来,陪读妈妈由于时间零散而导致的就业困难,因文化程度较低难以对孩子进行学业指导,其陪读大多仅为对孩子的生活的照料,这些并没有被考虑到。
2015年平安夜,一位陪读妈妈因赴网聊情人的约会,导致无人照料的孩子半夜从窗户摔下致死。这一极端事件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在当地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当地农村离婚率持续上升这一社会问题也被归因于妇女进城陪读后受“花花世界”诱惑而嫌弃农村家庭和丈夫,社会舆论和媒体开始将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缺陷导致的农村离婚问题转嫁到陪读妈妈群体之上。
Y县电视台制作了微电影《进城以后》,讲述了一个陪读妈妈“误入歧途” 与商人发生婚外情、只顾花钱享乐而不顾孩子,后因孩子生病、学习退步,母亲又“幡然醒悟、回归家庭”(妇联干部语)的故事。除此以外,Y县还有多首流传甚广的打油诗,描述陪读妈妈的出轨现象:
为了娃娃受教育/娘俩搬迁进城去/丈夫辛苦把工打/妻子不久便心花/可怜孩子染重病 /多亏园丁把爱洒……
农村家户有了钱/都把娃娃城里转……各个巷巷都住满/都是为娃把书念/进了城,开了眼/花花世界才看见/描眉画眼巧打扮/没事就到广场转……拿手机,聊微信/你有情来我有意……麻将场里玩几圈/弄到半夜两三点/娃放学,不见妈/肚子饿的吱哇哇/家里人,和老汉/辛辛苦苦抚果园/提起婆姨心不安/金戒指,银项链/看见老汉不顺眼……
大众媒体选择性的报道将个别陪读妈妈的局部特征放大为其群体形象,在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的同时,也在不断强化着陪读妈妈的负面形象,使之在更大程度上被暴露于社会公众面前,更加凸显了其污名记号,进而勾勒出其被社会排斥的群像。某位在县城居住的被访谈人在谈到陪读妈妈的情况时说:“现在进城的农村妇女把城里的风气污染得不成样子了,很多妇女扔点钱让孩子去吃饭,自己就去逍遥找乐,和别的男人约会,打麻将……”但是,当问及具体案例情况及判断的具体依据时,她也说不出所以然,只是举了上述陪读妈妈出轨导致孩子无人照料致死的故事。由于陪读妈妈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殊群体,关于这个群体的负面形象信息传播速度和广度、受关注度均远大于其正面形象信息的传播,而普通大众则易于接受这样的信息,从而塑造和强化了关于陪读妈妈的负面形象。
基于当地离婚率不断升高、陪读妈妈群体不断扩大以及上述极端案例引发的社会影响,Y县政府部门也开始实施一些针对陪读妈妈的干预措施,以预防相关问题严重化。县政府办公室曾经制定文件,指出“随着农村学生向县城聚集,许多农村妇女涌入县城”,要求相关部门加强“进城闲散妇女管理和教育工作”;县妇联出台了《六个方面加强农村进城妇女教育管理工作》的文件,提出要通过举办“道德讲堂”等活动,对进城的农村妇女“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家庭美德教育”,以“提升农村妇女的精神品味”。一方面,陪读妈妈在照料子女之外的闲暇时间与城市职业妇女的工作时间重叠,因此从时间上讲,其休闲活动与城市生活节奏不协调,显得其“闲散”;另一方面,她们打麻将、跳广场舞这样的休闲活动,被认为与城市的“精神品味”不协调,因而其“精神品味”需要提升。换句话说,这些文件赋予陪读妈妈的名称“进城闲散妇女”,充斥着对于这个群体的排斥和歧视。“进城”是对其农村来源和农民身份的歧视;“闲散”是对妇女的职业歧视,或者是对其照料劳动的无视;“妇女”则是性别歧视。在这些文件的指导下,县教育管理部门和妇联、政府联合开展了多种对陪读妈妈进行“管理和教育”的工作。农村学生较多的学校在组织家校互动会时,专门针对陪读家长开设讲座。学校老师在讨论有学习问题的农村学生时,常常将原因归结在陪读妈妈身上。妇联还开设了“社会闲散妇女讲座”,三八妇女节文艺汇演表演了关于陪读妈妈问题的小品,希望“利用多种形式对她们进行教育”,影响她们的行为。县委党校在几所中小学校开展了关于“母德母爱”的讲座,讲座部分文本内容的媒介话语分析更清楚地呈现了其教育、“呼唤母教回归”的目的(见表1),陪读照料被认为是母亲的天职,社会问题被认为是由于妇女违背母亲天职的结果。

表1 关于Y县“母德母爱”讲座的媒介话语分析
据我们调查,Y县农村离婚率近年的确出现快速上升的趋势,2012年、2013年和2014年的农村户籍人口离婚对数分别是结婚对数的19%、26%和23%。笔者在综合了县妇联、律师事务所、教师及村干部、农民访谈中所列举的离婚案例后,总结出农村离婚率上升的核心影响因素是人口流动。其中包括:农村夫妻二人在外务工导致离婚;一个在外务工、另一个留守在家导致离婚;男性外出务工带回外地媳妇儿,贫困、婆媳不和等因素使跨地区婚姻难以维系,最终离婚;农村妇女进城陪读导致离婚。笔者访谈的Y县3个村近5年内仅有4个离婚案例中的妻子是陪读妈妈。对于妻子进城陪读,留守在村的丈夫们认为,“陪读造成的两地分居对婚姻没什么影响,毕竟为了供孩子读书的共同目标是不变的”,“两个人分开或在一起都是为了家”。
陪读妈妈对于媒体的污名化消费和社会组织的“教育管理”持妥协态度。对于媒体塑造的负面形象、社会传播的污名故事,被访的陪读妈妈或者表示自己“没看过、不知道”,或者表示“听说过,但是应该只是极少数”,同时极力展示自己经常在家、“微信聊天的人也都是认识的人”等良好形象。有些陪读妈妈表示,听完妇联的讲座之后会反思自己照顾孩子的行为是否符合要求。陪读妈妈被迫以社会要求的“母德母爱”“妇德纲常”等要求来评判和约束自己的行为,社会对陪读妈妈的形象书写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她们对自身的角色期待。由于在城市社会处于话语劣势,尽管其“污名”形象愈来愈彰显,但陪读妈妈们并没有反抗,反而是以沉默、妥协应对。
五、结论与思考
陪读现象体现的是中国城乡关系中,作为照料劳动承担者的妇女、作为劳动力再生产方式的教育和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陪读妈妈群体的出现,是继劳动力外出务工与留守人口共同支撑的“拆分型”[24](PP 13-36)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之后,中国农村家庭再生产系统为了适应宏观社会变迁而出现的又一次调整,而且是跨地区的调整。在照料体制中,国家的行动和进退对于照料责任担当方影响很大[5](PP 43-54)。在国家教育政策调整、农村家庭教育期望提升和传统父权制、家庭主义价值观共同作用下,大量农村学生进入城镇学校就读,产生了新的照料需求并由此出现陪读妈妈群体。与以往备受关注的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问题不同,农村儿童的教育流动催生出农村家庭照料的新特点:离乡照料。在很多区域,“留守”已经不再是农村妇女的重要特征,她们成为流动的留守妇女。离乡照料也使农村家庭的离散化程度进一步加剧,由于妇女的日常生活脱离了乡村的地域,对农村老年人照料供给可能带来影响。因此,陪读妈妈群体的出现,也是农村家庭承担社会公共政策和国家以教育推动城镇化发展[25](PP 163-179)代价的表征之一。
陪读是传统性别规范对妇女再生产角色的强化,也是对父权制的强化。20世纪60-80年代,女性主义研究者强调了妇女的无酬照料劳动和家务劳动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关键作用,并指出其中蕴含的维护父权、性别与阶级不平等的意义[26](P 2)。照料劳动和性别关系、父权制问题也经常被放在一起讨论。陪读妈妈既脱离了乡村的生产性劳动,又被城镇的劳动力市场排斥或边缘化,成为纯粹的依附者,孩子的学业表现成为她们再生产劳动价值的评判标准或依据。由于父权制把价值赋予了孩子,因此陪读妈妈获得尊严或蒙受耻辱的根源,都是和孩子密切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约束女性行动的社会规范。
陪读妈妈因不创造有形及可见的劳动价值,其被城市社区排斥的程度甚于一般城市社区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成为被 “区隔”的群体和政府规训的对象。一方面,城市及媒体利用强势的话语权力创造偏颇的社会舆论,将妇女“制造”为农村家庭离散化背景下婚姻不稳定的罪魁祸首。如果陪读流动被看作一种城市嵌入的尝试,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居民利用他们的优势,以媒体、政府、社会组织为代表,给作为外来者的陪读妈妈贴上了种种社会标签,如嫌弃农村家庭和农村丈夫、不负责任、背弃母德等,并对她们进行管理和教育工作;另一方面,流动的陪读妈妈则妥协于父权制思想下的这些约束,将污名化的群像作为自我管制及自我约束的参照。
当前,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中国妇女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明确提出加强农村妇女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推动广大妇女以主人翁姿态参与乡村建设与乡村发展行动。然而,在中国教育发展、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农村妇女并未成为“发展”的受益者。从在乡照料到离乡照料,性别化的照料责任分工依然是农村妇女发展的障碍。推动全社会对妇女再生产劳动的正确认识,培育妇女的主体意识进而促进性别平等,应是新时代农村妇女发展与乡村振兴有机融合的关键。
——基于CFPS 2016年数据的实证分析